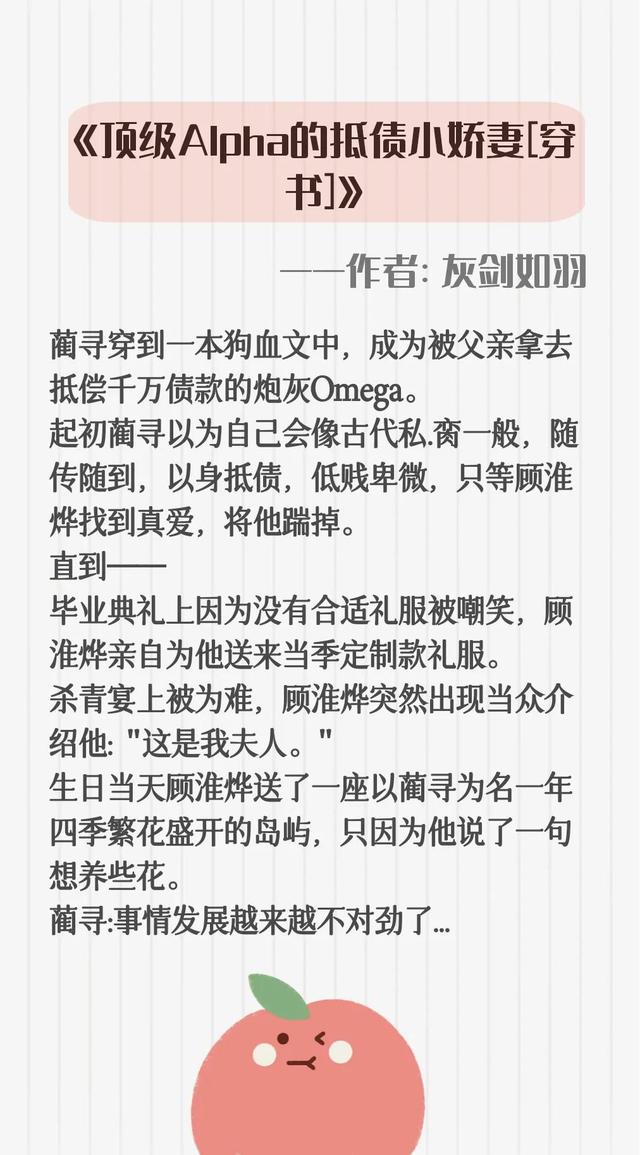工作的迷思是一部什么书(书评耳语者一个全面控制时代里的精神气质)
文/王栩(作品:《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毛俊杰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现在小编就来说说关于工作的迷思是一部什么书?下面内容希望能帮助到你,我们来一起看看吧!

工作的迷思是一部什么书
文/王栩
(作品:《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毛俊杰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
在历史学家看来,反抗苏维埃暴政的内在力量无疑被证明为源自于坚定的个人精神。对矢志于追求自由和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而言,生发自个人精神的道德视野在助力其坚持内心价值,对抗粗糙现实的岁月里有着悲壮的意义。这种意义在知识分子和斯大林镇压的幸存者所做出的对历史的书写下,定型为诚实和勇气凝聚的大写的“人”。它在公众层面成为记住历史的指向,却很难广泛代表普通人沉默着的“真实的声音”。
奥兰多·费吉斯的《耳语者》一书,选择将斯大林时代的千百万普通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此揭示了一个全面控制时代里极为普遍又吞噬人心的精神气质。如果说,个人精神在反抗极权主义时被拔高和放大,那也是已变成公众人士的向当局提出申诉的人对历史的集体经验,它得到历史学家欣悦的认同和接受,而忽视了广大的普通老百姓在历史上以“埋葬过去”应对恐惧的生存策略。
这种生存策略在极权主义的主导下是个人意义消失的基础。它对普通人的主导施加于潜移默化之中,毫无选择的摧毁了构成个人意义的一切来源,诸如家庭传统、独立思考、对未来的想象等。其具体而有效的形式在于压制,“让内心的道德、不安的声音彻底沉睡”。压制了每个人身上原本无法复制的“个人性”,千百万个独具特色的“我”,终于汇聚成具有集体人格的“我们”。这样的对自我的压制,或者生存策略,以埋葬过去为其核心主旨,最终对极权主义制度的融入来寻获自身的出路。
出路是普通人不同于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知识分子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后者是人类共通精神的象征,用对历史的回忆与书写选择记住,因此,其个人在历史上呈现出直面恐惧和对抗残酷的价值。普通人则不然,对普通人说来,极权带来的恐惧等同于生存的恐惧。这就是《耳语者》一书里,如何活着以及如何活得更好的历史真相。它是普通人对极权主义的现实触摸,用自己的生存努力同恐惧共存的历史经验。
经验是普通人在恐惧面前的分化。要么作为沉默的旁观者,漠视极权主义制度给他人带来的伤害和创痛;要么成为制度的合作参与者,在对他人的举报和加害中获取自己与家人的安全。这种遵循经验的日常生活准则不可避免的让双重生活成为极权主义制度下每个人的行为范式。公众生活中,依顺制度的要求,戴上虚伪的面具,以示自己忠诚公民的形象和规范,回到家中再冒着被他人窥探的风险稍许喘息的重拾自己既往的生活本貌。
风险在《耳语者》列举的那些事例里概括出传统被制度摧毁之际遍布人心的担惊受怕和极度畏惮。这类发自心底的恐惧即使在自己家里也不一定能得到丝毫宽慰。毕竟,家里留给每个人的喘息时间无奈地短暂,更多时候人们所面对的依然是他人对自己含义丰富的审视。这是布尔什维克对家庭的改造,用加速家庭解体的方式创建一个行之有效的集体生活。它所起到的作用在于,在意识形态上辅助于对反特权斗争的宣传,用集体生活增进人们对苏维埃制度的忠诚。对家庭的改造让共用公寓成为城市住房的标准样板,消除了私人空间和财产的同时,也使得住在共用公寓里的每个人几乎在众目睽睽下生活着。
这种生活掩饰在关于友爱和组织的宣传辞令下,无视隐私和个人意义的价值。它让偷窥盛行,举报成风,沉默成了人们无师自通的保护色。这样的保护色让每个人都不再信任除了直系亲属之外的任何人,不再对他人袒露内心真实的自我。人们活得谨慎,活得战栗,却并没有就此消极的沉沦。尽管新政权取得了胜利,并且寓辉煌于对传统价值的改造,可传统价值仍然在不遗余力地继续传承着。
《耳语者》用深情的笔触描绘了传承传统价值不容忽视的一类人群——祖父母们。其中,祖母的影响最为显著。她们不仅仅以自己从前的生活方式帮助孩子传承了19世纪的文化价值,还为孩子提供了道义上的平衡力,“以抵消来自父母的苏维埃影响”。祖母们让孩子知道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它相对于苏维埃世界而言,成为年轻一代对双重生活的践行下保持真实自我的原动力。
年轻一代从父母那里接受的教导总结成一条颠扑不破的生存哲学(经验),“孩子长大后如果想取得成功,必须适应苏维埃文化”。适应的同时,孩子在成长中也练就了掩饰这一必要的生存技能。适应和掩饰,共同构成了双重生活的核心主旨。适应苏维埃文化正确的行为观念,同时,掩饰自己内心对它生发出的质疑和不屑。过着这样的双重生活,人们普遍学会了用埋葬过去的方式来伪饰自己的忠诚,以期获得极权制度的接纳。而这样的接纳让普通人付出了不可预知的代价。
因为出于生存的考虑而朝向对制度的趋同,人们以对他人的窥探和举报助力了警察国家的强大。这种强大的反证在于全民的悄声窃议,它产生了“耳语者”这一独特的称谓。它代表了一类怕人偷听窃窃低语的人,也代表了一类暗地里向当局汇报的举报人。这两类人绘就了一幅苏维埃社会的恐怖画卷,使极权制度下的人们陷入全民噤声的时代氛围里。
这种时代氛围是引导全民接受的过程。接受这个制度的基本价值,顺从它的公共规则,在此意义上,成为制度的帮手而非它的对立者。所以,带着对制度的妥协,人们用自发行为的举报证明自己来换取制度的庇护。
举报是斯大林时代特殊的社会风气,对它的应对之法是用迂回的语言暗示出想法和意见。这让人际交往的社会领域日益缩小,“耳语者社会”不可避免的渐趋形成。在这一现实面前,人们面对的高压态势除了对制度的恐惧,还来自许多身为积极分子的年轻人对制度和规则的接受下亟盼有所作为的躁进行动。这些哀叹自己出生太晚的青年积极分子,对革命抱有浪漫憧憬,却没经历血腥的内战洗礼,他们用对父兄辈革命家的刻意模仿来为自己建造一条施展个人抱负的渠道。奥兰多·费吉斯对这些年轻人的揭示可以用单纯的动机概括出苏维埃理想对他们的主导作用,他们不是因为信奉共产主义而投身制度的怀抱,只是制度的活力对渴望完成重大事业的年轻人具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带着这一扭曲的心灵活在遍布“斗争崇拜”的斯大林时代,每个人都在悄声低语和举报他人的现实处境里挣扎着做出求生的努力。实在难以苛责极权主义制度下个人选择的对错、好坏。再者,单一的善恶判断也不是《耳语者》的定论。《耳语者》一书维系了一个警惕的论调,它揭示出极权主义的全面控制不是作用于一个时代,而是全民。有着全民之称谓的人们在极权主义的压制下,普遍失去了感受自己时代的能力。这让真正的记忆永远尘封,伴同犬儒盛行而来的则是对一切价值和道德观的漠视。所有人都在学着做一个冷酷的人,以此来掩饰自己大声发言的热望。哪怕这热望是自己真实的本性,也不敢将它流露而不会感到丝毫羞耻和愧疚。
(全文完。2022年5月7日)
——文中观点仅供参考,本人文责自负,与发文平台(含各类网站、论坛、自媒体、公众号)、转载纸媒、以及他人无涉——
作者简介:王栩。所用笔名有王沐雨、许沐雨、许沐雨的藏书柜、王栩326,定居重庆。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