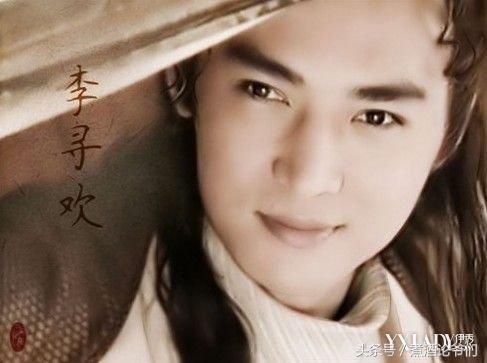黄裕生启蒙思想(黄裕生哲学是什么)
提要:就哲学是在有无之间的摆渡而言,哲学是一门科学,因为它涉及“有”,同时哲学又不仅仅是科学,因为它还关乎“无”;就哲学是追寻本原的一种努力而言,哲学既是一种返回自身的返乡之旅,也是一种成就自身的未来之旅,因此,哲学在根本上乃是一种为己之学与成己之学;就我们只有回到本原处才能回到自由身而言,哲学是还给我们自由的一种解放事业;而就真正的自身乃是自由身来说,作为成己之学,哲学的使命就在于成就自由与守护自由。
一
什么是哲学?哲学是什么?这两个问法一样吗?如果我们想对哲学的本质有所把握,我们应对哲学采取哪一种问法?笼统地说,这两种问法好像是一样的。在日常语境里,人们也通常把这两个问法当作是同一个问法。而在西语句式中,中文的这两种问法直接就被抹平(“统一”)为一种问法。但是,如果深究起来,这两个问法实际上并不一样。
在前一个问法中,真正问的是,哪些东西可以归到哲学之下?但归属于哲学的东西并不就等同于哲学本身。反过来说也一样,哲学并不等同于归属于它的东西。知识论是哲学,存在论是哲学,伦理学是哲学,美学是哲学,但是,哲学并就是知识论或其他,甚至也不等同于所有这些分支的组合;同时,一种没有知识论或美学的思想系统却也可以被称为哲学。这意味着,在“什么是哲学”这种问法中,并不真正涉及哲学的本质。
在“哲学是什么?”这种追问中,真正探问的才是哲学的同一性问题,即与哲学本身同一的东西。“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要寻求的是哲学的同一性规定。同一性规定才是对事物的本质的规定,而不是关于事物的关系属性。同一性规定是使一物区别于他物的自身性关系的规定。在这个意义上,追问哲学是什么,首先也才是追问哲学的本质的规定。
同一性规定或本质的规定,实际上就是最初的规定:既是逻辑上最初的规定,也是时间-历史上最初的规定。就像对树的本质的规定就是对最初被称为树的那个东西的规定,或者说,就是对最初作为树本身被给予的那个东西的规定。尽管树在后来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规定或属性,但是,它的所有这些规定与属性都以它的本质及其规定为基础。
由于同一性规定是最初的规定,因而是离我们日常生活最遥远、也最容易被遗忘的规定,以致人们常常迷执于事物的关系属性,倒忽略了事物的本质规定;也由于同一性规定是最初的规定,所以它是最直接却也是最模糊的规定,以致人们在展开对事物的认识过程中往往只抓住同一性中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的规定,而遮蔽了其他方面的规定。所以,追寻同一性规定不仅要突破事物的关系属性方面的规定,而且要“综合”本质性的规定。
这里要指出的是,同一性规定,也就是本质的规定,不同于本质本身。本质本身,也就是事物本身,是在直观中被给予的,或者说是在直接意识中被给予的,而对同一性规定也即关于本质的规定,则是在反思活动中完成的。因为只是在一本质物被给予我们之后,我们才反过来追问,这一本质物是什么,以求对这个本质物作出某种规定,以便可以对它进行演算与推理。
实际上,一切定义式的发问都隐含着对同一性规定的反思。在“哲学是什么?”这种追问中,就是对哲学之同一性规定的反思,或者说,是要在反思中把握哲学的同一性规定。
要在反思中把握哲学的同一性规定,也即其本质性的规定,首先要对哲学在其活动中所追问的问题进行反思。因为哲学正是在追问自己的问题的活动中作为哲学本身给予我们。所以,只有通过对哲学问题本身的思考与反思,才能对哲学的本质进行反思,从而达到对哲学本质的把握。如果我们对哲学问题进行足够的反思,那么,我们至少可以从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来理解与把握哲学。
一个是本原问题;一个是有无问题。
二
哲学最初是作为追问本原-始基问题的一种努力出现。本原问题并非简单只是一个世界的本质问题。本原问题的提出意味着人类的起源意识的觉醒:人们觉察到,我们生活的世界是有来源的,而我们自己是有来历的。这种起源意识使我们不停滞在眼下(也即现在)的事物,不满足于眼下事物;动物只能滞留于眼下的功能事物,也满足于眼下的功能事物。而人因起源意识对一切眼下事物与自己的身份持有怀疑与不信任,所以,人们不安于眼下事物而要越过眼下的事物,去追寻构成眼下事物存在之理由与根据的存在,这也就是在前或在先的存在。起源意识让我们获得一种超越性的眼光,让我们能够越超眼下事物,透过眼下事物,而瞥见源头事物。也可以说,因起源意识,我们能够开眼看“过去”,能够张开一只看“过去”的眼睛。动物是张不开这样的眼睛的,既使它有千里眼,它看到的永远也只是当下的东西。动物只有眼力,而没有眼光。眼力只能看到眼睛能看到的东西,而眼光则能看到眼睛看不到的地方。
对于起源意识来说,不仅眼前的一切事物都是不可靠的,而且连我们自身的身份都是可疑的:我们并不仅仅是当下的关系存在者,不仅仅是眼下的关系角色。
所以,起源意识也是一种怀疑意识,但又不仅仅是一种怀疑意识,因为它只是怀疑眼前的事物与当下的角色,却并不否定眼前的一切,相反,它因怀疑而要进一步去追问当下事物与当下角色的非当下性的根据,也即在先的根据。只有找到在先的、非当下的根据物,直至追寻到不出场的源头存在者,起源意识才不会因为当下事物的变动不居而惶惶不可终日,并且也才会发现并确认自己的本相身份而安于自己的真身与天位。简单说,追问本原问题,在根本上也是追问人自身的天位与真实身份的问题;而抵达本原,则意味着人回到了自己的天位而回到了自身。
在这个意义上,哲学追问本原的努力,既是追寻世界源头的努力,也是寻找与发现人自身的努力,也就是使自己成为自己的努力,使自己“成人”的努力。这实际上是同一个事情。因为返回世界源头的过程,一方面是突破一切派生的关联物而回到与本原共在的过程,同时也是我们不断摆脱经验自我、摆脱关系身份而返回自身的过程。世界的源头处,既是万物归一的场所,也是我们真正回到自身所在的位置。真正的自己,真正的“人”,并不是天下无敌、封闭独尊的原子独夫,也不是被网结在某种关系网络中的关系角色(比如父-子、君-臣、阶级分子等等),而是一个有天有地而顶天立地的中间者,一个超越了一切关系角色而与绝对源头共在的自在者,同时也是一个突破了一切因果性关系却可以开辟整个因果关系系列的自由者。
实际上,只有作为自由-自在的存在者,人才能真正洞见到本原,觉悟到绝对的源头。
这里,就人的自在与自由而言,自在与自由实是同一个意思。它们标明的都是人的一种超越性存在,也就是超越于一切关系物与一切派生物的存在。人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总是要比一切关系物与派生物“多”出一些,他既能开展出各种关系而置身于这些关系之中,也能突破这一切关系而超出这一切关系。就他能够置身于一切派生性关系之外而守于自身来说,他是一个自在者;而就他能够从自身开展出一切关系又能够突破这一切关系而返回自身来说,他是一个自由者。前者标明的是人的超越性存在的消极维度,也就是不可被穿透、不可被穷尽的维度,后者标明的则是这种超越性存在的积极维度:既能肯定出一个关系世界,也能从这个关系世界退身出来。退往何处呢?退回到关系之外却能开辟一切关系的自身。没有这个超越而开放的自身,我们不可能开辟出一个人的关系世界,也不可能从这个关系世界突破出来而对这个关系世界进行反思与改善。在这个意义上,超越性存在的消极维度更具有根本性意义。这意味着,真正的自由存在必定是包含着自在于自身的自由,或者说,人的真正自由必定是自在的,而人的自在也必定是自由的。
那么,为什么说,只有作为自由自在的存在者,人才能洞见到本原而返回本原呢?
我们知道,人向来就存在于关系世界之中而作为关系角色存在,比如一出生就作为母-子、父-子、兄-弟等等关系中的一个角色出现,同时还与周围事物处于各种功能性关系之中。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这个关系世界里,仅仅在这个关系世界里理解我们的存在与生活,那么,永远找不到这个世界的源头,永远远离这个绝对的本原。因为在这个关系世界里,我们能遇到的都是相对事物:一切功能性事物都会失去功能,正如父母都是会死的一样。难道这个关系世界的本原不在这个关系世界中?它既在这个关系世界中,又不仅仅在这个世界中。说它在这个关系世界中,是因为它从来就不曾离开过这个世界,它不在远处,既不在时间上的远处,也不在空间上的远处,因为我们循着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有限存在者,都能够遇见这个世界的源头;说它不仅仅在这个世界里,是因为它越出了这个世界,超出了这个世界,否则,它无法成为这个世界的本原。因此,如果我们只是作为关系角色而只看到关系事物,那么,我们永远也不能遇见它。
但是,实际上,我们这种特殊存在者从来就不只是作为关系角色存在,我们向来也作为自在-自由的个体存在,甚至首先是作为这种自在的个体而存在,因而这种自在自由的个体存在甚至是我们展开、确立一切关系角色与关系事物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我们突破、改变与完善一切关系世界的基础。
一方面,只是基于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个体存在,我们才能展开与确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器具与器具的关系,不是单纯的强者与弱者的关系。虽然我们的确一出生就进入了关系之中,但是,因为我们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关系项进入关系的,所以我们进入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而是自由体之间的关系(尽管人们通常并不觉悟到这一点)。正因为人们实际上都是作为自由者来确立和展开与他人的关系,才会确立起一系列仁爱的、充满道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是由于每个人都能够有自由的理性而是自由的存在,每个人才能够设身处地地把他人当作如自己一样的存在者来理解、对待,从而才能不仅仅把他人当工具,而是也把他人当作目的本身来对待,因而也才能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确立为人与人之间的基本法则,或者说,也才能把“你要别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确立为人间法则。凡是违背这一法则的人间关系之所以需要加以改变和修正,就在于这一法则既是基于个体的自由存在,又是维护个体自由的底线。因此,凡是违背这一法则的人间关系都必定是对关系项的自由的损害。从另一个角度说,那些建立在这一法则之上的伦理规范之所以正当而需要加以维护,不是因为别的原因,而只是因为它们间接地基于所要规范的对象的自由存在,同时也是对这种自由存在的维护。比如,在一些后儒思想中被看作是基于血缘亲情的“孝”,实际上与血缘毫无关系,否则,孝道无法外推。换言之,孝道之所以正当而值得加以维护,并不是因为它是出于血缘关系,而是因为它出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法则,而在根本上则是出于关系项的自由存在。不管是孝道中的“养”还是“敬”,都是基于孔子与耶稣所觉悟到的法则才成为正当的。否则,养的要求与敬的要求都不具有正当性。以为孝悌这些伦理要求与实践是基于血缘亲情的想法,实际上是对血缘关系的一种古老迷信,它与图腾崇拜以及其他偶像崇拜一样,是人类精神尚未达到绝对意识而停留于有限性事物的一种体现。① 孔子的伟大就在于他以仁学的绝对精神突破了血缘关系,确立起了超越一切(被夏商周奉行了几千年的)宗法制度的普遍仁爱原则。在孔子这里,孝之所以成为行仁之“本”,不是因为孝是基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伦理规范及其实践,而仅仅因为母-子与父-子关系是每个人(不管是以亲子身份还是以养子身份出现)遇到的第一个关系场所,因而成了每个人实践、确立、贯彻仁爱原则于人生的出发点。也就是说,在母子或父子关系中行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我们行仁的起点。这里,普遍仁爱原则是孝道的标准与尺度。换言之,仁爱原则是父-子关系的尺度,也是一切亲情的法则。
简单说,一切正当的人间关系都是基于孔子与耶稣所觉悟到的基本法则,而根本上则是基于人间关系项的自由存在。因为只有从这种自由存在出发,才能理解、确立、开展出一切正当的人间关系。但是,人们不仅生活在正当的关系中,往往也生活在不正当、不健康的关系中,而人们之所以会展开出各种不合理的关系,同样也是基于人们的自由存在。正因为人是自由的,人们才会越性而为,背叛自己的自由本性而背离出于这种本性的法则;倘若人的存在不是自由的,而完全是必然的,那么,人们在生活中展开的各种关系也就无所谓正当不正当、合理不合理。在这个意义,不管是正当还是不正当、合理还是不合理,一切关系都是基于关系项的自由存在才展开出来。
另一方面,也只是因为关系项的这种自由存在,我们才能够从各种关系中突破出来,以便修正一切不合理的关系,改善一切有待于改善的关系;同时,也只是因为人是自由的,我们才能从各种关系中解放出来,放下一切关系身份,既不再把自己与他人当作关系中的角色,也不再把相遇中的任何他物看作关系中的功能物,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退回自身而把他人当作自由者来对待,也就是当作他人自身来对待,同时也意味着把相遇的他物当作非功能性的自在物来看待。人成了自由人,物成了自在物,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管是自己,还是他人他物,都是未完成而是敞开的、活生生的,都置身于一个整体的可能性之中,或者说都被抛入一个永远不可被我们完全捕捉与把握的可能性整体之中。这个整体可能性或可能性整体,不是别的,正是一切事物的源头。一个置身于可能性整体之中的事物,也就是处身于它的源头之中。在这里,源头或本原以不出场的方式被置身其中的事物指示着。在场物总是指引地显示着一个不在场物。而放下了一切功能性关系角色的自由-自在的在场者,则既显示自身,又指引着不在场的源头。源头或本原不在远处,就在在场者之旁,不过,不是在角色在场者之旁,而是在自在或自由的在场者之旁。因此,只有真正能突破关系角色而回到自身的自由者才能洞见本原。

三
这意味着,要寻回本原,必须首先回到自身。在这个意义上,作为追寻世界本原的一种努力,哲学就是我们返回自身的返乡之旅。本原意识或起源意识,实乃一种乡愁,一种忧烦(sorgen),是对与源头共在的那个天位之所的怀念与向往。哲学就是一种带着乡愁的返乡之旅,它通过让我们脱离-摆脱当下-现在纷繁多彩的现象世界而把我们带回“过去”,在在场的当下世界的背后打开了一个以不在场方式在场的“过去世界”。
作为一种返乡之旅,我们也可以说,哲学在打开一个“过去”的世界的同时,也就让我们能够以过去的眼光看当下,能够以过去的立场看现在,把“过去”当作理解我们当前的生活与世界的维度,使当下世界不只是具有实用的意义,还呈现出“历史的意义”。儒家强调述古追远,并不是为了真相与故事,而是为了获得一种超越当下、超越“眼前”的一种立场,一种拥有本原力量的超越性立场。
但是,作为追寻世界本原的努力,哲学不只是一种返乡之旅,同时也是一种“未来之旅”。因为只有从当下的关系世界摆脱出来,才能真正返回本原。彻底的返回,就是彻底的解放。而彻底的解放,彻底的摆脱,就是自由。所以,彻底的返回本原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意味着回到与绝对的源头共在,与一个永远以不出场的方式出场的绝对他者共在,或者说,与一个永远以无的方式有着、以不在的方式在着的他者共在;另一方面意味着我们回到自身而回到自由。所以,对我们来说,回到源头,就是回到与绝对他者共在的自由存在中。相对于各种关系性存在总是封闭于关系之中而言,超越性的自由存在在根本上则是一种开放性的存在:它不仅让自己退回到可能性当中,而且让一切存在者都置身于可能性之中,甚至当下的现实世界,也不过只是一种可能性的展开。简单地说,自由就是守于可能性而打开可能性的存在。而这也就是未来的存在。未来是什么?未来就是希望,而希望就是被打开的可能性,就是靠眼光才看到-看出来的事物。在“希望的田野上”,就是在打开了可能性的地平线里。
所以,在源头处,在自由中,我不仅能够以“过去”的眼光看世界,而且同时也能以未来的立场看生活。哲学既是一种返乡之旅,也是未来之旅,自我解放之旅,自我成就之旅。哲学让我们能够站在未来的立场上理解与思考,而不是迷执于当前。哲学让我们能退出当前而返回自身,也让我抬眼望向未来,打开未来。哲学不仅让我们张开回望过去的眼睛,也让我们开了遥望未来的眼睛。哲学让我们拥有三只眼睛。
就本原意识带领着我们返回过去,又打开未来来说,本原意识或起源意识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时间意识,至少它包含着时间意识,或者要以时间意识为前提。这意味着,哲学作为追寻本原的努力,它实际上一直运行在时间意识中,甚至我们可以说,只是因为我们有时间意识,我们才会有哲学。虽然哲学曾经是以追求永恒的、非时间性的事物的方式运行在时间意识当中。在这个意义上,时间意识将随着哲学的成熟与反思的深入而成为哲学最核心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胡塞尔特别是海德格尔要专门讨论时间问题的原因。
但是,时间意识,实际上,也就是从有到无与从无到有的意识。没有对“无”的意识,没有对终结的觉悟,也就不会有真正的“开始”与“过去”,而只有从“有”到“有”的循环。而循环实质上是一种位移式的空间运动,而不是时间的绵延与扩展。但是,我们之所以有“开始”的意识,之所以会去寻找与发现“开始”,首先就因为我们有“无”的意识。有对“无”的意识,我们才会意识到有一个从无到有的事件,从而才有真正的开始。哲学通过概念的自由演绎从现实世界,也即从作为“有”的当下世界摆脱-解放出来,所能达到的真正本原实际上就是一个“无”,一个永远不出场的绝对他者就是一个无,就是一个整体的可能性存在。哲学退回到无而打开的可能性,也即打开的希望与未来,是一种有待于实现的“尚未”。未来是创造的,就在于它是从无中开显与实现出来的。
因此,真正的哲学并不只是与“有”相关,更与“无”相关。哲学在有无之间。作为一门科学,哲学是一门关于“有”的学问,但是,哲学不同于其他一切科学就在于,它不仅是科学,因为它不只是关于“有”的学问,它同时是一门与“无”相关的学问;或者更确切说,它不仅涉及有,而且涉及无,而其他一切科学只涉及有。不过,哲学与无相关并不是也不可能提供关于无的知识,而只是提供向无敞开的桥梁。有无之间永远存在着断裂,哲学就在有无之间进行摆渡。
如果说从当下世界摆脱出来而返回到源头处是一个从有到无的解放过程,那么,从源头处打开可能性而打开未来,则是从无到有的创造事件。但是,不管是从有到无的解放,还是从无到有的创造,都是一种自由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哲学就在有无之间进行摆渡,那么,也可以说,哲学既是以自由为前提,又是对自由的实践与维护。就哲学从追寻本原开始而言,哲学一开始就基于自由;而就哲学以追问世界本原为使命而言,哲学就是以守护自由与维护自由为使命。
如果说作为一门科学的哲学是一个概念体系,那么,它一定是一个自由体系,即向无敞开的体系,向绝对他者敞开的体系,因而一定是一个永远有可能性尚待展开的开放性体系。
四
就哲学实际上是运行于时间意识之中而言,哲学首先是一门通学。它不仅能够回望过去,而且能够打开未来,而这也就意味着既能够以过去的立场,也能够以未来的立场去面对和理解当下的现实。对于哲学来说,只有在过去与未来的视野下才能真正面对现实。换言之,哲学首先要能进入过去与未来,才能进入当下的现实,并进而理解现实和开辟现实。
同时,就哲学是追寻本原的一种努力而言,哲学更是一门经天纬地、安身立命的“大学”,它的使命首先不在于探究一国一族之兴衰(如果说有一种哲学只为一国一族服务,甚至只为某一集团某一党派服务,那么,这样的哲学一定不会是真正的哲学,而只是利益与权力的仆从),真正的哲学的使命在于立定世界之根本而昭明天下普遍之理于普天之下。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是一门以普遍主义情怀与普遍主义视野去追寻天下普遍之理的“世界之学”。因此,哲学不仅要穷通古今,贯通未来,而且要会通世界普遍之学,达乎天下普遍之理,以安天下人人之心。唯有安心,才能安身。
作为安身立命之学,哲学同时也是一门亲证的科学,一门为己而成己的科学。哲学所追问的本原、有-无问题既是这个“世界”的问题,同时也是每个人自己的问题。因为正如前面所说,唯在本原处,唯在作为整体可能性存在的“无”处,我们每个人才真正回到自由身而成为自身。因此,追寻本原的努力同时也就是返回自身的历程,而在有无之间的摆渡,同时也是每个人的自我解放与自我开显。这意味着,经历追寻本原,就是亲历自我返回,自我成就。实际上,任何哲学体系,首先都必须是对哲学家自己心灵生命中升起的问题的回答,否则它就无法安己之心而安天下人之心。唯有能安己之心,才可能安人人之心。这意味着,哲学学者必须首先以自己的生命、以自己的心灵担当起问题,换言之,必须首先在自己的生命中唤起那些大根大本的问题,使自己不解决、不面对这些问题就惶惶不可终日,只有通过亲自尝试解决这些问题来求得安宁。因此,真正从事哲学研究的人面对哲学史,其兴趣首先不在于哲学家说了些什么,而是理解他的问题,并努力与他一起面对问题,也就是说,首先是努力使哲学家的问题成为自己心中的问题,以便验证哲学家的解答的有效性——是否足以安心。
因此,哲学既是一门天下之学,也是一门为己之学。这里的“己”不是君臣父子关系里的自己,因为在这种关系里没有真正的自己,只有可被替代的各种角色;也不是什么利益主体或欲望主体,因为一切这样的主体都是临时的、不统一的,将随着利益相关项或欲求相关项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因此,这样的主体无法真正成为一个具有自身同一性的统一体。不管是关系角色还是利益主体,都只不过是每个人的一种临时身份,而不是他的真正自己。倒是只有退出这一切临时身份,摆脱各种功能性的关系世界,每个人才真正回到了他自身。这样的自身实际上就是自由身。哲学作为为己之学与成己之学,其所“为”的乃是这样一种自由之己,所“成”的乃是这样一种自由之身。
所以,当我们说,哲学是一门为己之学时,我们实际上也就是说,哲学是一门成就自由与维护自由的学问。哲学通常是以保持独立思想的方式承担起成就自由这一使命。从事哲学研究的人,既要能承担起哲学的这一使命,又要能受这一使命的塑造。成就自由与维护自由的普世情怀,以及穷通古今未来之变的超越精神,被哲学带进了从事哲学的人身上,又被哲学家发扬为一种传统,延续为一部历史。虽然我们今天就哲学学科的分类来说,有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的划分,但是,不管是从事哪个学科分支的研究,只要是真正在做哲学研究,那么,穷通古今未来之变,追寻天下普遍之理,永远都应是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们的一个基本追求。
就哲学的使命与精神来说,在今天,从事中国哲学研究,不仅需要坚守传统经学那种明明德于天下的普遍主义精神,而且更要以一个本源文化民族的开放胸襟去面对西学的深度与广度,使今天的中国哲学研究不是简单地重温国故,而是力图以现代性视野构建今日之“大学”。而从事西方哲学研究,虽以西方哲学为具体研究对象,却同样是以探求普世之理为要务。对于真正的哲学来说,“学不分东西,唯理是学”。因此,如果是在哲学层面研究西方哲学,那么,这种研究既不会认同欧洲文化中心论,也会警惕中国文化民族主义,而惟以探求天下真理为目标,惟以会通中西普世之学为归宿。
作为一门自由的科学,哲学同时也是一门纯粹科学,即不以任何派生性事物与经验性关系为考量的学问。因为只有排除一切派生性事物与经验因素,哲学才能找到构成一切派生事物与经验性关系的基础,也才能发现贯穿古今未来之变的最高原则。换言之,哲学是一门寻求从派生性事物与经验性关系中摆脱出来的学问。这意味着哲学要从各种日常世界与功用关系中解放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是一种解放事业。
作为这种纯粹的科学,哲学同时也是一门奉献虔诚、呼唤虔诚的学问。哲学不仅要求一切科学所要求的严谨与严肃,而且更要求思想的虔诚。唯有虔诚,能为真理与正义而抗拒诱惑,唯有虔诚能因真理与责任而抗拒浮躁,也唯有虔诚能为真理与信仰而忍耐苦难和不幸。简单说,唯有思想的虔诚,才能突破对功名利禄与派生事物的迷执而进入本原,回到自由。
《大学》说,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诚其意。如何才能诚其意?《大学》说格物致知。问题是,如何才能格物?首先是要问:要格何物?显然,要格的不是派生物,不是日常功能物,也就是说,不是要格角色物,而是要格纯粹物,也就是自身物。与角色物打交道,是日常生活与具体科学和技术学的工作。一切角色物都是关系物,也就是可被概念所规定与把握,并被带进各种关系中的事物。在不同的概念与关系中,事物将显现为不同角色。在化学概念系统里,水显现为H2O,而在物理概念系统里,它则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液体,而在日常话语系统里,水则是解渴的饮料。事物要摆脱角色物的地位,就必须摆脱概念,从概念中突破出来。哲学的使命就是通过概念的演绎摆脱概念,走向非概念的事物,也就是在纯粹意识中又不仅仅在纯粹意识中的自在物。自在物,就是在自己位置上的事物。这样的自在物,实际上就是整体物,是不可被概念-名相所划分的整体存在。
显然,致知格物,要格的就是这种作为整体的自在物。而要格这样的物,也就是要与自在物打交道,就必须从概念-名相中解放出来。唯有这种解放,才能真正面对自在物,与自在物打交道。而从概念-名相中解放出来意味什么呢?意味着空出我们的心灵,意味着把一切概念物、从而把一切经验物从我们的心灵中、从我们的思想中、从我们意识中排除出去,剩下什么呢?剩下纯粹的意识本身,剩下一个自主的自由域。纯粹意识本身就是一个自由的存在,因为一切关系,包括因果关系都是以这个纯粹意识为基础。自由的存在,就是自己的存在,就是作为自身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才是真正的“诚”。
因此,大学之格物,分开来说,一方面是我们从概念世界即角色事物中返回自身,返回自由,另一方面,是让事物在自己位置上存在,也就是让事物以自在物来与我们相遇。格物而知者,乃自已之自由与物之自在。知自己之自由,则明自己之为真实自己而能诚,知物之自在,则明他者之尊大而存敬畏之心。
所以,哲学呼唤虔诚,也成就虔诚。通过唤呼虔诚而唤回人的自身,成就人的自身。就哲学是一门维护自由而明明德于天下的“大学”而言,哲学不是一门日用之学,而是一门根本之学。它担当的是全人类的普遍正义与最高原则;唯当哲学真正承担起全人类的使命,它才能真正服务于一国一族之需要。哲学开辟的历史不是民族史,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史。
中国曾经以自己的哲学开辟了具有世界意义的东亚史,而今天,中国将再次面临着这样的使命,那就是:以会通了中西普世之理的哲学参与开辟新的世界史。这也是我们作为中国人在今天的哲学研究中能够打开和应当打开的一个希望。
(本文原载《江苏行政学学报》2012第一期)
① 实际上,从血缘关系无论如何都推不出“父当慈,子应孝”这个伦理要求(规范命令),把“父慈子孝”看作是出自血缘关系的一种“自然要求”,这是腐儒陷入的一个千年迷误。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