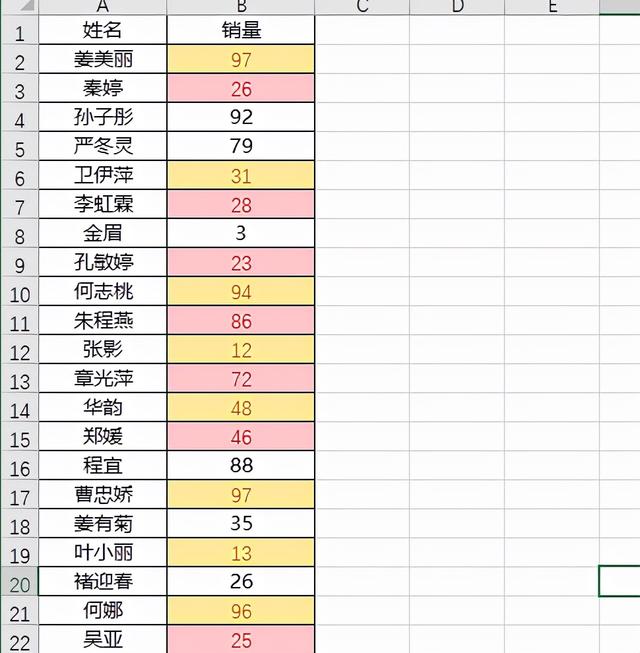slack未来发展趋势(企业级沟通工具Slack到底牛在哪)

这是9月一个星期四将近中午时分,在Slack Technologies不显山露水的旧金山总部,首席执行官斯图尔特·巴特菲尔德跟公司的设计和产品主管正开着一场会议。
会议讨论的一个问题在最近始终徘徊于巴特菲尔德的脑海里:这家开发团队协作软件的公司如今估值已高达 280亿美元,当它的人员规模扩大到200人、500人乃至上千人时,如何才能让它像当初只有8个人时那样出色?
巴特菲尔德为今天的会议准备了一份“可教原则”清单,希望与会成员能提前消化一下,其中包括:“事情别留给我来想”;“多点两下不碍事”;还有“数据解决不了任何有趣的问题”。
为了详细说明自己的观点,曾经做过电子游戏设计师的巴特菲尔德提到了一个涉及扫雷游戏的比喻——通关与否取决于玩家选择的第一步。“软件的设计工作并不比扫雷更容易,”他说,“我不觉得我们重头开始的次数足够多,第一天就出现了一个‘地雷’,它从未被质疑过,从未被重新考虑过。”
巴特菲尔德发飙了,因为某个声音打断了他:Slack设计总监布兰登·维莱斯塔克正从温哥华通过视频参加会议,而他的椅子正在吱吱叫。“你知道那些该死的椅子正在发出那种该死的声音吗?”巴特菲尔德说,“你能不能把那些吱吱作响的椅子扔出去?”
对于别的企业掌门人来说,这一刻可能只算是跑题了。但对巴特菲尔德来说,这是一堂方便的实例教学课:如果你愿意忍受吱吱作响的椅子,那还有什么是不可以得过且过的呢?
巴特菲尔德关注的东西事无巨细:Slack三处办公室的所有卫生间都播放着法国电台节目,因为他认为员工不应该被同事在卫生间里发出的动静干扰;公司Twitter账号上刚开始的那几千条推文都是他亲自操刀;在椅子事件的几分钟前,他正提议为Slack设计师安排新的座位表,免得大家相互比着磨洋工。
“你来啦!这一天变得更加美好了。”
—Slackbot
巴特菲尔德仿佛同时患上了ADD(注意力缺失过动症)和OCD(强迫性神经官能症),但正是这种对细节的极端注重造就了Slack——用某些标准衡量,它是这个星球上增长速度最快的初创公司。
Slack在2014年2月上线,20个月之后,其用户人数超过了170万,其中48万是支付8-15美元月费的付费用户。该公司的年营收达到了4,500万美元,其付费用户转化率完胜其他采用“免费增值模式”的企业软件产品。
在70周的时间里,Slack的用户每周平均增长5%。Slack的企业用户超过9万家,其中包括Salesforce、eBay、NASA、HBO、Intuit以及Mansueto Ventures。“我们一直在考察过去一年公司逐周的增长情况,很快就会慢下来。”Slack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卡尔·亨德森说,“否则的话,Slack的用户人数都要超过地球人口了。”
不过,正是Slack取得这种惊人增长的方式解释了它何以脱颖而出。沟通是“信息经济”中的基本活动,让这种沟通保持高效是最根本的挑战。在一项又一项的调查中,数不清的知识工作者都反映说,电子邮件和会议是损害工作效率的最大元凶。很多软件公司宣称,他们让工作沟通变得更舒服和更有乐趣,但只有Slack的产品好到不用自卖自夸。
这是真的,这家公司里连一个销售人员都没有,该公司直到最近才开始打广告,其97%的新用户都是由老用户介绍过来的。人们从别人那里听说了Slack有多么好用,介绍者要么是正在用它的朋友,要么是以前用过它的同事,再要么是微博客上的某个人。
一开始,他们都是在团队内部试用Slack的免费版本,然后便欲罢不能。再然后就会用各种手段软磨硬泡,要公司的IT采购员购买付费版,否则就有他们好受的……

巴特菲尔德跟他的技术和运营工作人员交流
当我们考虑到办公软件并非一个以暖人心窝闻名的产品类别时,这一切就更让人觉得了不起了。作为一个让团队成员相互之间或者以聊天群的方式发送信息的沟通平台,Slack的创新似乎不算大。用户可以方便地搜索会话记录,灵活的架构减少了不必要的闲聊,而智能通知功能则可以让你在聚焦其他工作任务的同时不错过重要事情。
Slack能够跟其他流行的企业应用进行很好地协同工作,同时也支持emoji表情符号和GIF动画这些可爱的东西。这都是一些很好的元素,但是倒也说不上有何惊人之处。
然而,不知何故,Slack却成为那种能够让人们改弦更张的产品,通常只有In-N-Out汉堡、Zappos和维珍美国航空这些深受人们喜爱的消费品牌有此魅力。“我们在顷刻之间就看清,它比我们之前用过的所有产品都优秀。”Modest首席执行官哈珀·里德说道,这家初创公司是Slack的早期测试用户之一。
里德的团队已经不再使用内部电邮了,他在Twitter上的介绍帮助Slack获得了其他一些早期用户。“人们一般不会对公司产生这种感觉,更不会对对自己使用的工作工具产生这种感觉。”Slack的客户支持主管阿里·瑞利说道。
Slack堪称当下某种潮流的经典例子,分析人士称之为“企业技术的消费化”。其中的想法是:智能手机和流行应用,比如Facebook、Instagram和Candy Crush这样的大规模普及已经改变了人们对于软件外观和功能的共同期待,从而为那些消费应用直观和对用户友好的企业应用创造出巨大机会。
不过,从“对用户友好”到“受用户推崇”,这是巨大的飞跃。在《疯赞:以真诚的社交互动激发消费者对品牌的持续追捧》一书中,《广告时代》的资深专栏作家鲍勃·加菲尔德探讨了特定的品牌比如Patagonia和Krispy Kreme,是如何在消费者中制造出宗教式崇拜的。
他说,最强大的品牌不仅仅受到人们的喜爱乃至自发宣传,同时还能让他们产生一种身份认同。“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在自己的汽车贴上公共电台的贴纸。”他如是说。
Slack用户感觉跟这个品牌有一种情感上的联系,这绝非偶然。从公司一开始成立,巴特菲尔德就跟几个创始人定下了大方向,除实用性之外,还要确保作为产品和公司的Slack要有趣、周到、人性化、异想天开以及博学多才。
当你打开Slack应用,它会用一句欢迎词迎接你,比如“多么美好!在如此阳光灿烂的一天,有什么事情不能做成呢?”或者是,“你今天看起来不错。”用户可以把自己的奇思妙想加入其中,办法是修改可编程的主机Slackbot。在Modest公司,它被设置成在门铃响起时向员工发出提醒;
通过跟登录软件Envoy进行整合,它还可以在会议开始前发送关于访客的档案。“那些跟Slack互动的人,他们会非常非常非常快地考虑使用Slack的产品,而且还会向自己工作的单位以及朋友推荐它。”里德说道,他是奥巴马总统2012年竞选团队的技术负责人,“那真是匪夷所思。”

Slack的员工队伍现在已经达到300人左右,该公司的增长速度实在太快,以至于不得不在过去15个月两度为旧金山办公室寻找新址。现在的办公室已经接近4500平方米,,即便如此还是显得太过拥挤,巴特菲尔德打算再租一片大约3000平方米的办公空间。
管理一家每小时都在不断增长的公司,这是一件让人肾上腺素飙升的工作。巴特菲尔德把它比喻成跑酷运动。“如果你慢下来,你就会跌倒。”他说,“你得不断观察周围场地,寻找一个可以借力弹跳的窗台,或者一面可以在上面跑过去的墙,或者是一个可以支撑自己翻过去的扶手。”
去年5月,Slack通过Social Capital和其他顶级风险投资公司完成了一轮1.6亿美元的融资,并获得了28亿美元的估值,由此加入硅谷的“独角兽”俱乐部。你问Slack究竟有多强?证据就是,无论是大到微软、谷歌、Facebook等公司巨头,还是数不清的小初创,如今都想要从Slack的手里抢走一杯羹。
当微软在9月份发布最新版本的Office软件时,该公司市场营销负责人重点宣传了协作和聊天功能,并满怀期待地称之为“Slack杀手”。办公沟通服务公司Basecamp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杰森·弗莱德称赞了Slack所取得的增长,但也发出警告,称Slack式聊天“不是进行周密和充分讨论的好办法,它催生出很多焦虑以及害怕错过的情绪。”
巴特菲尔德虽然不至于傻到忽视这些威胁,但他也没有怕得汗流浃背。“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对作为一家企业的我们来说,Slack仍然是好样的。”他说,“人们总是会想要知道你到底能达到什么样的一种高度,但至少眼下我们是万无一失的。”
当谈到企业软件时,42岁的巴特菲尔德不是你能够联想到的那种人。他成长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农村地区的一个群居公社,身为嬉皮士的父母为他取名“达摩”。巴特菲尔德拥有哲学硕士学位,他养的小狗名为LMNOP(爱需要付出耐心),他还会弹一种叫乌克丽丽的四玄小吉他。
巴特菲尔德就读于维多利亚大学,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哲学教授。然而,在攻读硕士学位的中途,他发现自己那些念完博士的朋友很难找到工作,而那些掌握编程技能的朋友却在上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泡沫中活得有滋有味。当时在暑期做网站制作兼职的巴特菲尔德改变了自己的主意。
2002年,巴特菲尔德拉起一支队伍来开发《Game Neverending》,这是一款带有社交媒体元素的建设类网络游戏。他的合作伙伴包括埃里克·科斯特洛、谢尔盖·莫拉科夫和亨德森——他们四人后来成为了Slack的核心成员——另外还有卡特丽娜·菲克,她当时是巴特菲尔德的女友,后来变成了妻子,再后来变成前妻。
当时的经济环境并不适合开发一款大型网络游戏:互联网泡沫已经破灭,安然和世通的破产事件让经济环境变得更加风声鹤唳。“我们差不多是注定会完蛋。”亨德森回忆道。
巴特菲尔德酝酿了一套计划,把我们为游戏编写的一部分代码分离出来,做成一款图片分享工具,他的想法是把它单独剥离出来以获得收入。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奏效了,于是诞生了图片和视频分享网站Flickr,它的增长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让巴特菲尔德他们无力负担每周都要进行的服务器扩容。
“你今天看起来不错。”——Slackbot
当雅虎提出以2,500万美元收购Flickr时,看起来问题找到了一个完美的答案。然而,在出售不久之后,Flickr被重组到一个跟自己不搭调的部门。在Flickr渐渐失去活力的时候,Facebook和YouTube迅速后来居上,夺走了最大社交网站的头衔。“我们的感觉自己被花言巧语忽悠了。”亨德森如是说。
巴特菲尔德咬着牙在雅虎坚持了三年时间,后于2008年离开了这家公司,他准备好重新来过。他召集了原来的搭档们,并着手开发一款名为《Glitch》的大型网游。这又是一款带有社交元素的幻想游戏,故事涉及巨人和时间旅行。Glitch得到了加速合伙公司和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提供的1,700万美元投资。
但这次的时机同样不理想:在用户开始向移动设备迁移的时候,巴特菲尔德他们却在打造一款桌面端游戏。经过一番艰难的讨论,巴特菲尔德跟伙伴们在2012年10月做出了关闭Glitch的决定,他含着泪水把消息告诉给公司员工。Glitch提出把剩余的约500万美元资金退还给风投,但后者却让他们留下钱,并建议他们尝试组织骨干人员开发其他产品。
他们把积累起来的创意拿出来,看中了一个好想法,它是如此显眼,以至于已经没有人记得是谁首先提出来的。在开发Glitch的过程中,团队人员一直利用互联网中继聊天进行交流,这种聊天技术能够把会话组织成频道。对他们来说,一款高效的通讯工具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科斯特洛身处纽约市,莫拉科夫和亨德森则分别在温哥华和旧金山。
在巴特菲尔德辗转温哥华和旧金山两地的情况下,所有团队成员很少处于同一个时区。多年来,他们已经编写出自己的IRC应用,并一次又一次地改进它,以满足自己的需要。“我们确信,不管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都肯定需要一款类似的辅助通讯工具。”亨德森说道。也许这意味着其他公司可能也希望能用上这类工具?
有一天半夜,巴特菲尔德灵光乍现,想出了Slack这个名字。他把它想象成一根松弛的绳子把两个铁罐连接在了一起。“沟通是会在组织机构中制造紧张关系的事情之一,我们希望让它放松下来。”他说道。其他几个人几乎都讨厌这个名字,他们指出,Slack(松懈)是工作的反面——这对生产力软件来说简直就是在打自己的脸。
巴特菲尔德很喜欢这个词所蕴含的厚脸皮意味以及它的读音,并且生造了一个逆向首字母缩拼词来证明它的合理性:所有通讯和知识的可搜索日志。最后还是让他得逞了。
在接下来的17天里,巴特菲尔德写了一份演示讲稿,以解释Slack会是什么样子:一个统一的通讯平台;一个可以随时随地使用的平台;一个“最大程度发挥其他应用比如Excel或PowerPoint,功效但又不寻求复制它们的平台。这份讲稿后来成了Slack的产品路线图,几乎是一个字都没改。

Slack旧金山总部的员工队伍
这种没有走弯路,完全直线式的进步是很罕见的。“在软件设计方面,总是要不断提出猜想,不断进行尝试,然后从经验中学习。”巴特菲尔德说道。他认为,自己跟其他几位创始人打造出了一款完美的产品,因为他们根本不是把它当成一款产品来对待。
“为了它,我们已经完全放弃了自我意识。”他说,“于是那段时间的情况就变成了,‘搜索功能不管用了,真该死’,或者是‘我无法在iOS设备上发信息了,真该死’,然后,我们就会用最短的时间,比如几分钟内,把问题解决掉。”
“这并不是一定是你想创办一家公司的方式,但它的这种自发性、内生性所发挥的作用确实可圈可点。”加速合伙公司的安德鲁·布拉西亚说道,他是Slack的董事会成员。
此外,Slack提供客户支持的独特方式也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负责这块工作的瑞利是Slack最初的八名员工之一;她的团队现在是公司规模最大的团队。
瑞利的工作就是确保,把常常是最令人沮丧的用户体验——在遇到故障时试图找到答案——变成最令人愉快的体验之一。“我们一直认为,Slack不仅仅是在电脑或手机上打开的一款应用;它还是用户跟我们进行的每一次互动。”瑞利说道。
“努力工作,然后回家”是Slack办公室的一则座右铭,该公司将在明年推出的新功能之一是:请勿打扰模式。
在思考自己希望这种互动是什么样子的时候,瑞利参考了那些最以激发客户忠诚度而闻名的公司,比如维珍美国航空以及Zappos。不过,她看重的是一辆名为Señor Sisig的菲律宾卷饼餐车。
在Slack,家庭式午餐是一项传统,而当Señor Sisig在周四来到附近的街区时,公司员工都会排队去购买那些卷饼。不知怎的,在餐车上工作的女员工似乎记得每位常客要点的东西。“那种极具个人定制感的体验——对递给我卷饼的人来说,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瑞利说道。
为了重现这种体验,瑞利尝试聘请一些具备情商高且文笔好的客户支持代表。技术知识可以传授,但个性化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是一家非常文艺范的公司。”瑞利说,“需要让客户觉得自己是在跟一位读过几本书、在工作之外兴趣广泛的人进行交谈,只不过眼下恰好是在聊着关于Slack的事情。”
现在是下午6点30分,巴特菲尔德就在闲聊,谈到了关于Slack的事情。他读过的书可不少,昨晚刚看完了塔那西斯·科茨的作品《世界与我之间》,接着又在开始阅读贾德·阿帕图的《脑子有病》后进入了梦乡。现在,在结束了12小时的工作之后,他有点精疲力尽。
Slack成长正当其时,巴特菲尔德也有与之匹配的焦虑情绪。银行账户里屯着大笔现金固然是好事一桩,但随之而来的还有人们的高期望。一些人辞去了在谷歌和优步的好工作来为Slack效力,因为他们认为这家公司仍然能够成长到更大的规模。
“这种期望,倒不是每个人都希望能把几百万美元捧回家。”巴特菲尔德说,“而是他们希望自己没有做出一个累及家人的愚蠢决定。”如今,巴特菲尔德自己已经减少了开发产品方面的工作,更多地在于交流价值观。
随着Slack的扩张,他害怕公司会出现组织偏离的问题,而避免这一切的唯一办法是“不断提醒人们”Slack代表着什么。因此,也就有了他提出来的那些可教原则。巴特菲尔德甚至聘请了拥有教育学博士学位的人,让其监督公司内部培训。
作为一个经历过两次创业失败的人,巴特菲尔德都已经不奢望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抓到如此大的机会。不过,刚到傍晚的这个时候,Slack办公室里差不多已经没有人了,这正是巴特菲尔德希望看到的情景。
在Flickr时期,他每周要工作60小时以上,并希望其他人都能跟上自己的步伐。在那以后,他已经变成了一种不同类型的老板。
他跟合作伙伴都已经为人父母,他们一直小心地把Slack打造成能让有生活的成年人感觉“找到了组织”。“努力工作,然后回家”是Slack办公室的一则座右铭,该公司将在明年推出的新功能之一就包括勿扰模式。
有没有注意到这其中的讽刺?Slack让团队能够无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来展开工作,但他们自己却认为,当团队成员聚在一间办公室,在一起享用午餐,然后按时下班回家,这才能实现最好的工作效果。
“大多人都拥有几个小时的高效工作时间,这些时间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跟其他人的高效工作时间发生叠加,这种综合效应将更具有冲击力。”巴特菲尔德如是说。
将沟通中制造的紧张关系消灭掉,这是个很有诱惑力的前提。因为一旦能做到这点,那就能够完成更多工作任务,更好地理解团队其他成员,以及更加热爱自己的生活。
正如巴特菲尔德及其团队通过自己使用产品开发出了Slack,他们正在通过亲身实践来创造一种能够推及其他人的公司文化。
Slack的成功秘诀是什么?
答案就在它的名字里。

Source :
《Inc.》
本文由造就|翻译 整理,其他媒体如有转载需求请留言征询,谢谢!
投稿请邮件:alisawang@xingshuchina.cn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