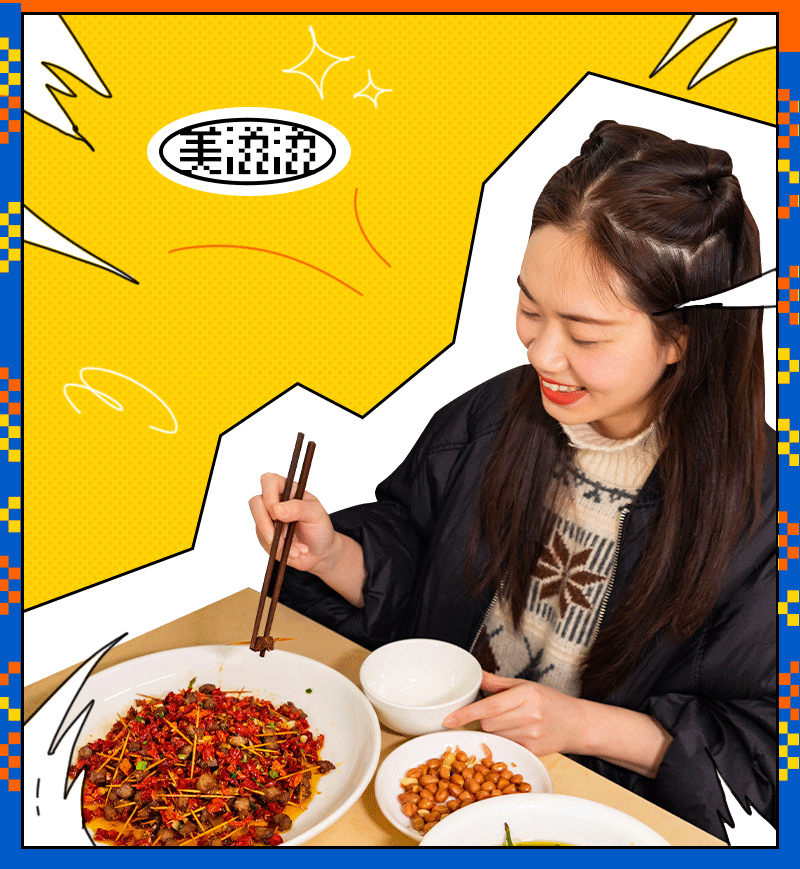一碗豆腐散文(磨豆腐散文)

(节日朝阳\作者摄影)
磨豆腐(散文)
李朝俊
过年磨豆腐,在我们四邻八乡,是天经地义的事,几乎家家都要磨的。这是慢工活儿,不是啥难事。黄豆地里种的,水从井里挑的,石磨豆腐坊是老亲旧眷的,提前打好招呼搭点人情,使劲用力就能吃上白白嫩嫩的豆腐。
少年郎磨豆腐,一天下来就是感到累,累在挑豆、挑水、挑柴,最后还得往家挑豆腐。
豆腐坊在后金楼表舅家,出自家庄南下条槐树沟,翻上半坡下到堰埂,绕过弯牛角状的竹杆园,磨坊就从竹林绿叶中露出门脸。
两个村庄直线距离,不长不短约二、三里地,一个在金楼山下,一个在梨园山下,一南一北斜调角,一庄建在坡边平地上,一庄筑在山洼台阶地中,好在两山都不大,路也不算远,在山里就像一个庄一样。这庄望见那庄,站在山坡一声高喊,人们能大声对话说事。
山里路,高高低低,弯弯曲曲,脚下石头,路旁树枝,到处都是坑坑洼洼,到处是枝立巴杈的长条短丫。空手走路不觉得碍事,担挑负重一上一下走,累了换个肩都费事。别说那树枝刺条,时不时碰下挑子,让人防不胜防,若不低头长眼看脚下,摔个跟头洒下粮食,也是常有的事。负重爬坡过涧,山里人都习惯了,办法是爬坡前,先站着歇一小会儿,身上的汗消得差不多了,顺手紧紧裤带,紧紧鞋带,脱下厚衣,弯腰举勾担上肩,爬坡上坎不敢停下,路窄坡陡,无处可歇,全凭意志,一鼓作气弓身慢行。又期待又害怕的是,那将将下坎又爬坡,让人高兴劲刚兴起,头疼的问题冒出来。担挑下漫坡,碎步稳走感觉轻松些,不用换肩就到了沟底平路;负重爬坡,大口喘气,心跳加速,热气炸肺,双腿打飘,左右摇摆,狠命苦撑,一步一挪。心想快到平地了吧,汗水眼缝一瞄,愿望总是落空,总爬不到坡顶,那个难受劲不是苦不堪言,是力不从心还得负重前行,心都快崩溃了还要没事人一样,无助地挑起担子总要爬上坡顶。
我半大小子叫累,父母腰弯背驼也不吐半句累。磨过年的豆腐,豆子提前在自家泡好,用水桶装上挑到豆腐坊去磨。母亲头天用大瓷碗,从穴子里盛出黄豆,用筛子筛选一遍,用簸箕簸一道,用井水淘一淘,将黄豆当天夜里一、二点钟,就早早地泡在清水桶里。父亲喂饱拉豆腐磨的健牛,捆好烧豆腐锅的柴禾,准备担水担豆腐的挑子……
过年磨的豆腐,有大小豆腐之分。大的要用黄豆二十五、六斤,小的十来斤黄豆就足够了。年下磨小豆腐,是用小磨人工拐的。蒲团形状的小石磨,也是上下两扇磨盘,功能与牲口拉的大石磨一样。只是这小石磨,轻巧方便可手。上磨盘上有手握木柄,棒劳力伸手抓木一推,盘动磨响,左手用盛饭铁勺,连豆带水舀上一勺,往磨孔里放,左拐右推,玩杂技般拐动。在小石磨“哧溜、哧溜”、“咕噜、咕噜”转动中,在拐磨人汗水浸湿衣背中,在两人轮换拐磨中,生豆浆慢慢磨好,很快轮转到下个做豆腐程序。
我家人多客多,母亲爱磨大豆腐,年年要用牲口拉大石磨。十三、四岁的我,挑豆到磨坊后,先给牛戴上兜嘴、捂好蒙眼,套上磨备好料,挥鞭成了牛监工。
老牛出蹄,石磨拉动,一圈又一圈。湿漉漉的黄豆,堆如山丘,牛走磨盘转,鼓胀黄豆纷纷塌陷入磨孔,经上下磨盘粉碎,浓稠的生豆浆沙漏般流淌。磨顶上有四根绳子,垂吊瓦制水瓮于空中,瓮底插个小姆手指粗,半尺长的青竹节管子,滴水源源不断地注进磨眼孔,润滑石磨黄豆拼挤出豆汁。很快白中透淡青色的生豆浆汁,从上下磨盘中滚滚涌出,你挤我我推你,小溪入海流的气势,顺水磨沟槽泻进铁桶里。我瞪大眼睛看牛拉磨,还有给磨顶水瓮注水、给磨盘孔加黄豆的使命。
父亲和表舅,此刻都穿单上衣,高高地挽起袖子,头上冒着热气,双人合作,四手紧握滤单架子摇把。这滤单摇架悬在房梁下,两根一米长短木制摇手,铁轴居中交错穿过,四角系上滤豆浆的白稀布,生豆浆汁放入其中,加水反复摇荡,直至把生豆浆汁都过滤尽,只剩滚圆的豆腐渣为止。父亲和表舅配合默契,一边不紧不慢干活,一边前三皇后五帝的说笑。那滤单摇架,被摇晃得“吱扭,吱扭”声响,直摇得生豆浆汁,一桶又一桶入大铁锅,黄豆渣一包又一包的清出。
说话间,活儿干到午饭时辰,二十六斤黄豆磨尽,老牛卸磨牵到外边拴好,表舅母饭菜已端上桌,一声高一声低的笑喊:“豆腐坊的爷几个,干大半天活儿肚子还不饿?快洗手吃饭吧!”都是亲戚熟人,相互也不见外,父亲和我,表舅一家,在舅母热情张罗中围桌而坐。
因抢时间做豆腐,端碗就吃,丢碗就干活。滤好的生豆浆汁加水,倒入一口可供百人吃饭的大铁锅,我大火一阵阵猛烧,满灶柴禾燃烧,满屋豆腐水气,满锅浆香冒出缕缕白雾。轻松下来的表舅和父亲,各自两手不使闲地清理装豆腐脑的水缸,叠包豆腐滤水的布单,准备固定豆腐包的大竹筛子………
一切准备就序,豆腐匠表舅,转身用力推开巨大的木锅盖,趋前看热浆火候,大声说“火烧得差不多了。”让我不要再添柴禾,锅底余火烧尽就大功初成了。十几分钟后,表舅拿根长长的细竹杆,轻轻探入豆浆锅里,从锅这边入到锅那边出,手动杆起浆水响,抓出一张白中透黄,黄中闪亮,亮中滴白浆的豆油皮。这豆油皮往小竹杆上一凉,如同一面小彩旗,上宽下窄飘动在阳光下。铁锅涨豆油皮,是民间祖传绝活,是饮食文化精品,是生态文明之物,只有豆腐匠才能把握好时机,诀窍运用自如涨豆油皮。一般一锅可涨三张,头张锅开后十多分钟就成了,后两张因豆浆精华被反复抽取过,油皮形成速度渐慢,时间各要半个小时左右。若生手去抓豆油皮,不是抓个稀烂,就是手被浆烫个红印迹。豆油皮是豫南地方名吃,可与菠菜、小油菜、大白菜混炒,可配以多种佐料,煨出绝佳美味的香汤。老家的豆油皮,城里超市里说是豆筋、油皮,只是没有豆油皮好吃地道,有点橘生淮河南北的意思。三张豆油皮出锅后,热豆浆被盛进豆缸。豆腐匠表舅,忙中有序,嘴说眼示,指挥众人。只见表舅端起电焊护脸罩大小的木瓢,将满瓢的石膏水,天女散花样的倾入缸中,父亲用大铁勺子将热浆不停地搅动,使卤水散漫开来,达到点成豆腐的最佳效能。一阵技术操作之后,压上缸盖,擦汗擦手抽旱烟,鲜嫩嫩的豆腐脑,一两袋烟的时间就可出缸。
传统古法磨出的豆浆,烧做成的豆腐脑,嫩滑细软,洁白似雪,品质如玉。父亲会给我舀上一勺,倒入碗中,上面洒点白糖,有时放点精盐,清香甘甜,口味适中,含到口里怕化了,咽到肚里肠胃通畅,感觉好吃得天下第一。
磨豆浆是慢活儿,压豆腐包是快活儿。这时,一米方圆,半尺来高的大竹筛子派上用场。将筛子正面向上,放到锅角旁的压豆腐木架上,把滤单布铺入其中,大瓢将热豆腐脑,一一盛进筛子滤布里,三、四人七手八脚拉动,四根滤布角上绳子慢慢趋紧,热浆水哗哗从豆腐包滤出。随之绳子交叉拴牢在竹筛底部,众人用力倒扣豆腐包于木架板上,轻轻解绳子,拿开竹筛,再紧好绳索,压木板横卧在豆腐包上,木板之上重压铁石之物,豆腐上压下顶作用力中,热流清水渐渐从豆腐内挤出,排漏在滤包布外,从哗啦哗啦到嘀嗒嘀嗒,需要时间等待。让包中水自然压出流尽,城里人说的豆腐,也就做成了。
人们没闲功夫管这水响,又忙着压千张豆腐,也就是城里说的豆腐皮。千张豆腐同打印纸大小,簿簿的双面表层都是细细的花纹,这花纹功夫是时间“雕刻”出来的。千张豆腐制作木模具,尺把长,半尺宽,四指厚,形象抽屉,间有夹层,功能如漏斗,方便出水,灵活抽取。别小看这“抽屉”,算是豆腐坊的老物件,有点“镇馆之宝”的地位。表舅出手,滤干布顺序入“屉”,勺舀豆腐脑,均匀倒入,裹好滤布,上压下挤,一屉屉千张上架,很是壮观震撼。压千张豆腐费力费时,十斤八斤出量,用时三、四个钟头。
乡村过年磨豆腐,豆腐坊总是多家排队,压茬跟进,彼此帮忙,从不窝工。平时不常见的姑娘小子,各家都是得力帮手,常常会在豆腐坊里无意见面,并由生疏变成熟人,干活中就有了说笑。热心的嫡亲厚友长辈,觉得两家大人厚道,孩子不信不傻,就悄悄搭桥说亲。每年豆腐磨好后,总有几对“豆腐姻缘”结成。说这豆腐坊,磨出的是文化,磨出的是亲情,磨出的是幸福,一点都不假呢!
(2020年1月11日于西城区枣林前街70号)

(远眺故乡村庄\摄影玉海)

(今日小山村\摄影玉海)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