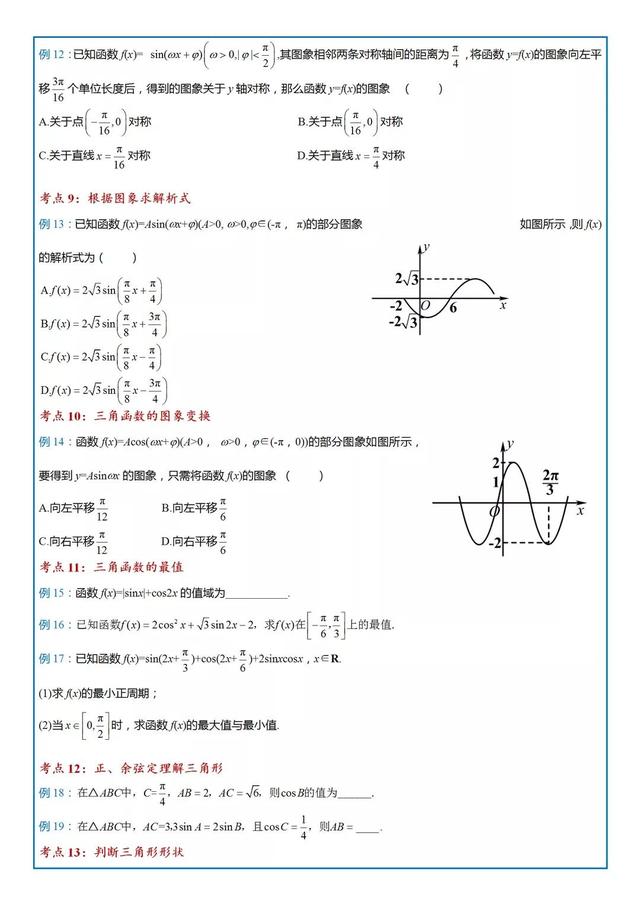逃离不幸的家庭英文(逃离不幸的家庭)
#我的生活也是#

女性出走,去新世界冒险
迄今为止,孟梦的人生经历过三次出走。
第一次是2010年,在职校第二年开学报到的下午,这个被迫学了航空管理的女孩扛着所有行李冲出校门,从此一去不回头,她不愿过如何学做一名高端体面的服务生的生活。第二次在2012年,辍学后的孟梦在重庆发传单,做模特,维持不被认可,也不被在意的生活。远方工作的母亲打来电话,用重庆话大骂,“难道你想跟你爸一样死在那个烂地方吗?”愤怒之下,她决定继续出走,去海口,去广州,到更远的地方,见更大的世界。
现在是第三次,孟梦嫁给了一个美国丈夫,并跟随丈夫的脚步在异国构建新生活。但这个过程并不容易,至少在来美国的前两年,孟梦打心底讨厌这个陌生的国度——因为语言的障碍,她甚至无法独自去超市买菜,她仿佛陷入一种封闭的聋哑状态。诸多担忧曾在出发前浮现,如今也一一应验,可孟梦还是选择出走,把生活推向更辽阔的可能性。
三次出走,各有不同的契机,也夹杂着运气与环境等诸多因素,甚至嵌套在过往的母女关系里:自打孟梦十岁起,母亲便无法忍受父亲的不断出轨,和姐妹一起去南非做了床垫生意,此后八年再没回过国。儿时的孟梦曾对母亲有许多怨愤,可如今她理解了母亲的选择,“这是她求生的过程。”
孟梦的出走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故事,属于她,属于她的母亲,也属于成千上万的、不甘于狭小世界的普通人:她们要向外走,向更良善文明的世界出发,赢得尊重与新生。
一
构建新生活
2019年,我跟随丈夫来到美国。我们俩在广州相识,恋爱,步入婚姻的殿堂。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这里工作六年了,我们结婚以后,他觉得在中国的发展有天花板了,外国人就只能到这了,就想回美国发展。那时我一直没什么稳定的工作,做做代购,摆摆摊什么的,我觉得我过一天是一天的,所以他想去哪,我肯定跟着他去哪。
但来到美国以后,我经历了非常艰难的适应期。语言不通是最大的障碍,像美国这边的人,他们非常习惯于那种口头聊天,不管认不认识,都会随便跟你聊一下天气什么的。我那时特别害怕买单的时候收银员跟我聊天,他们说什么我都听不懂,所以我根本不敢自己去超市买东西,也不敢去咖啡馆点单。
这已经不止是语言问题了,当我没有办法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我仿佛是个精神上的聋哑人,就像一个小婴儿一样,曾经在国内建立的一些个人价值,身份感,引以为傲的生活经验,都得全部推翻,重新再来一遍。我像是站在风中摇摇欲坠的最后一根树枝。

到美国后我厨艺飞涨,中国菜可以喂养我生理和心理的归属感,烧菜也变得治愈
我在加州待了半年以后,找了一家奶茶店上班。虽然奶茶店的老板是个中国人,但它90%的客户都是美国本地人,我的同事也都是在美国长大的小孩,这是我真正了解这个社会的开始。
其实我当时差一点就放弃了,去上班的第一天,老板就拿了好大一个菜单给我,上面有7、80种奶茶,我得在三天之内把基本的名称背下来,在一个月里学会制作所有的饮品,但我拿的又是加州最低的工资,我就不想做了。但我后来想了一下,难道我不做了,就一直这样在家里待着吗?
我挺感谢自己当时跨出了第一步,然后强迫自己坚持了下来。我开始了解美国亚裔群体的生活,他们怎么看待美国的政治,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份。

半年后,我跨出第一步到奶茶店打工
可就我个人而言,在奶茶店上班让我有些看不起自己。我身边的同事其实都还挺年轻的,二十二三岁,刚刚大学毕业,或者没有读大学的,他们是有迷茫的资本的。但我已经组建了家庭,可还是做着这种重复的、机械的,并不稳定的工作,这跟我理想中的自己是背道而驰的,好多人会以为你去了美国,生活就是怎样光鲜的,可其实没有。我一边觉得自己很差,看不起自己做的事情,一边又推着自己融入,我知道这是我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刚来美国的前两年,我对生活产生过很大的怀疑,当时我完全依附于丈夫才能生活。加州的生活费其实挺高的,我在奶茶店一个月也赚不了多少钱,只有几百美金,房租全靠他在支付,吃饭的费用也基本是他在承担。我们虽然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但也没有多余的闲钱,比如我们会算着这个月不可以出去吃饭,现在我也几乎没办法回国,因为机票太贵了,我要是回来的话,会对我们的经济状况造成很大的影响。
我有一种作为女性完全放弃自我的焦虑,那时很没有安全感。其实来美国前的两个星期,我跟他说,我不想去美国了。现在回想,当时的情绪更多是忐忑,你要搬到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焦虑,说出来就成了我不想去。
但实际上,我对外面的世界还是有向往的,我希望自己可以走出去看一下,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是一种对可能性的向往。
我完全无法想象,来美国两年后,只有初中学历的我,会跟刚刚高中毕业的学生们坐在一起读大学,这完全像做梦一样。
二
母亲的出走
出国生活的一部分底气,或许来源于我的母亲。我妈是那种有点爱闯的性格,她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去了再说,再怎么样都可以搞定。
她在我10岁的时候,便去了国外打工。
但她走的时候,没有给我任何交代,甚至骗我说她去的是云南,去三四个月就回来。有天我姨夫问我,我妈在哪?我说她去云南了。我姨夫就很生气,把我打了一顿,说我很坏,连着我妈一起骗他们。我那时才知道,原来她已经出国好几个月了。
我妈一走就是八年,中途也没有回来过。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她是很生气的,而且那种生气没办法表达,一直被压抑着,它会从生活的其他方面钻出来。比如我妈说一句话,其实那句话可能也没什么,我身边十个人跟我说我都不会生气,但如果是我妈说,我也不知道那个愤怒是从哪里来的,我就会跟她大吵一架,以前我俩是没办法相处的。

我家住在嘉陵江边,这座嘉陵大桥是重庆过去二十年经济发展的证明,可是我们家这么多年了还是没有修电梯,爸爸说他已经爬不动六楼了
去年不是出了一个电影叫《The Lost Daughter(暗处的女儿)》,里面讲一个妈妈,组建了家庭后觉得自己不甘于传统的生活,她在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中一点点迷失了自己,结果她放弃了自己的家庭出走了。我看完电影以后,其实对我妈有更深的理解,那时她在家里的生活那么痛苦,又一直不被自己的老公尊重,老公也不是真的爱她。我站在她的角度,觉得她并不是在抛弃我,她只是在寻找自己,这是她求生的过程。
我妈其实已经忍了很多年了。我爸30多岁的时候就病假退休了,每个月拿以前单位的退休金,我妈在我姨夫的电器店里做收银员,家里的开支都是靠她的收入,吃饭、打扫、管我学习也基本都是她一个人。而且我爸一直在外面出轨。家里人也不会避讳着我,我记得我三四岁的时候,我妈就会拉着我去捉奸,和我父亲对峙。其实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大的阴影,影响了我对婚姻的憧憬,和对亲密关系的信任。
那时候,她大概是觉得跟我爸的婚姻走不下去了,于是她就彻底离开了。

我小时候最喜欢去的市场,卖菜,锅碗瓢盆,衣服,什么都能买到,这是一家旧货二手书店
我妈离开以后,家里就没有人管我了。刚开始我爸把我送到小学的数学老师家里托管,那个老师非常苛刻,我洗澡洗得久了她会说我,做饭的量也特别少,我总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后来我外婆看我可怜,把我接去姨妈家里住,但我姨一家很不喜欢我们一家,他们觉得我妈是穷光蛋,因为我一直没人管,他们怕我把表妹带坏了,旁敲侧击让我爸把我接走。
初中我基本一个人住了,后来也没考上重点高中,被家人强迫着去一所职业学校,每天就是学怎么把餐巾折成千纸鹤的形状,怎么倒红酒不会滴到桌布上。那时老师让我们好好学,以后就能到重庆比较好的邮轮或者酒店里做服务员。但我根本不想成为一个在高端酒店工作的服务员。
第二年开学的时候,赶在学校5点关门前,我把被子、行李全都带着就走了,再也没回去过。
那时我刚满17岁不久,开始了自己养活自己的生活。我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 发传单,做模特,开服装店。做模特的时候,我基本走一个秀就能赚500多块钱,最多的一次,我做模特负责人,三天赚了7000多块钱。那时候我还不到20岁,我对自己特别骄傲,那些高中毕业的同学没一个比我能赚钱。

家乡的老城步行街,过年时的样子
直到我18岁的时候,我才又见到了我妈一面,那时我已经认不出来她了,记忆里她一直是个高大的能保护我的母亲形象,结果那天我才发现,原来她那么瘦小。我妈回来待了一个月又回南非了,我继续我的兼职野模生活。后来,我忘了是因为什么事,我们俩在电话里吵了起来,她是那种特别直接的人,在电话里用重庆话骂我,“难道你想跟你爸一样,死在那个烂地方吗?”
这句话完全激起了我反叛的斗志,挂了电话以后,我问朋友有没有外地的工作介绍,我不想再待在重庆了。
三
外面的世界
最开始,我被朋友介绍去海口卖房子。说白了就是做销售,也是这时我真正感受到,没有学历的人,只能从最底层开始做起,连大公司的门槛都够不到。当时,我每天要坐一个小时大巴车去市中心,到保险公司还得唱《我相信》那首歌,好像给你打鸡血一样。那时我的业绩也不好,后来就没再做了。
在海口断断续续待了一年,我也没什么朋友,当时真的很孤独。2014年的时候,跟我关系好的几个朋友聚在了广州的一个酒吧,看世界杯决赛,给我打电话。从小没有父母和家人照顾,朋友就代替了家人陪伴在我身边,他们就像我的家人一样。当时我就想,我可以依靠的人全都不在我身边,再这样下去我就要疯了。凌晨四点我就买了机票,七点的飞机,从海口飞到广州,之后再没有回过海口。

我在广州大桥上拍的珠江新城
也是这时我开始思考,自己究竟想追求什么样的事业。我想做一名心理咨询师。
其实我对心理学的兴趣起源很早。小时候,我总在过察言观色的生活,看大人的脸色来决定我该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我对身边人的情绪非常敏感。12岁的时候,我们班上好多人都在看《恶作剧之吻》之类的小说,但我在书店买的书叫《怎么变乐观》,或许是某种求生本能让我形成了同理的能力,那时班上情窦初开的同学也很愿意找我聊天,让我出主意,我也很愿意扮演倾听者的角色。
那时候我有很严重的PTSD和焦虑症,但我并不知道,只是会读很多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它们让我对一个人的动机和行为,包括如何产生心理疾病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我想了解心理因素如何影响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延伸到社会。
后来我认识了一个朋友,她在读大学的时候考了心理咨询师的证,我知道有这个职业,但是从来没有感觉可以离我这么近。她告诉我,拿了这个证,就有可能做心理咨询师——这对我来说就好像一把钥匙,我要首先拿到,才能打开这扇门。我不知道门后面有什么,但我一定要拥有这把钥匙。
2017年,我考过了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的证。
当时是1月份,我一个人在电脑面前查成绩,其实我考的不是特别好,刚过分数线两三分的样子。在电脑面前我就哭了,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一直被父母、老师、姨夫和姨妈瞧不起,没有人相信我可以做成什么,但我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拿到一个证书。这是我活了23年以来最大的一个成就,我好像得到了某种认可。这是一种安全感,一种被信任感,是我从小到大都没有体验过的。
等我拿到证书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五月份了。我很难去描述拿到证的感觉,好像你脱离了过去,看到了一点曙光,未来会产生一些改变。我一个人坐在外面,看着那个证,它似乎给我的生命增加了一点色彩,即便我的整个生活还是黑白的。
在我拿到咨询师证不久之后,我得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坐办公室的工作,在广州的一家心理学机构当课程助教。当时我的工作主要是帮忙对接课程老师和学生,主要工作是招生,当时心理卫生在国内不是很发达,我待的机构也不是很正规,它的收费实在是贵得可耻了,我觉得它在消费一些有心理需求的人,我在这里也待得不是很开心。

2019年5月23日,离开广州去美国那天,这是我们住了三年多的卧室
后来我意识到,这张证书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用,没办法用来定义我是谁。
在这之前,我曾在一家心理学机构求职失败,对方拒绝得很直接,不能接受我从模特到咨询师助理的身份跨度,甚至直接评价我太爱打扮了。可能在国内的工作系统里,一个女性太爱打扮,就会被看成是很招摇,不太稳定的角色。
但学历还是最重要的因素,那时,我便发现只有传统大学教育出来的学生,才能受主流心理学界的认可。如果我真的想从事心理学方向的职业,一个心理咨询师证实际上是没什么用的,这对于科班出身的人来说可能是简历上的装点,但大家最看重的远不止这个。我必须走得更远。
四
真正的冒险
来到美国以后,我丈夫帮我制定过一个七年的学习计划,他是个很爱帮别人做计划的人,加州的教育资源又非常好,免费的社区大学的师资、教材跟普通大学都是一样的。那时我规划前三年学英语打基础,后两年在社区大学学心理学专业,两年后转到普通大学学社工。
我对学历始终是有执念的。很现实地讲,在美国你也一定要是科班出身,至少硕士毕业,才有可能成为心理咨询师,不然我只能做一些自己没有那么满意的销售型工作。但更深层的原因,或许是我自己的童年创伤,小时候老师说我笨,父母觉得我笨,我身边所有人都觉得我很笨,不是学习那块料,我自己也觉得自己很笨。可我辍学以后,我慢慢意识到我对知识是有渴望的,我这么喜欢看书,就好像隐隐地在向以前那些贬低我的声音证明,其实我不是很笨,我是学习的那块料。

第一次看到金门大桥的时候,我大喊:“虎门大桥!” 虎门大桥是广东虎门镇的一座连接广州和深圳的桥
可我的内心始终在摇摆。前两年我在社区大学学英文的时候,都是吊儿郎当的,我觉得我学英语只是为了在美国可以日常生活,能买个菜,能看懂路牌,就这么简单,我根本不相信自己可以读大学。
去年秋季,我报了一个学分可以转到正规大学的学分课,学习初阶的学术写作。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认真上一门课。那时候,我英语还没有多好,口语只是还过得去,阅读水平也不好,刚刚开始尝试看第一本英文书。但我在那门课的成绩出奇优秀。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篇文章,写跟家人一起度过的有意义、深刻、快乐的时间,我们班上20多个同学全写的是过年过节,但我想了一下,我们家根本就没什么一起度过的很快乐的时间,全家能聚在一起的日子,就是一起去给我爷爷奶奶上坟,于是我便写了这个。
老师看完我写的文章后,把我叫到一旁,问我愿不愿意直接跳级到三级写作,如果我愿意,她很乐意帮忙写推荐信。她说很喜欢我的文章,她都看哭了,那篇文章也是我哭着写完的。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一直给她鞠躬,说话都说不清楚了。

给我爷爷奶奶上坟的地方
学术写作课给了我很多信心。这种信心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体会过的。那天以后,我第一次相信我是一个可以制定计划,并且付出努力去完成它的人。我开始相信努力真的有用。
上学期,我报了我最恐惧的数学课,其实是统计学。我从小数学就特别差,初中数学就再也没有及过格了,初二的时候老师一直劝我退学,怕我拉低班里的平均分。但如果我要学心理学,这门课是必须的。
上课那天我特别紧张,听讲的时候,我还感觉我都听懂了。结果一做作业,五道题,做了两个小时,一道题都没做对。那天我又哭了,我又一次感觉自己的梦想破碎了,原来我并没有我以为的这么聪明,我还是那个初中毕业,没有文化的小混混,我都已经28岁了还想读大学,就感觉自己特别傻,不自量力。
我也和一个也在美国读书的女生聊过,她知道我打算学心理学或者社工,一直奉劝我不要学文科,说了很多可能会失败的丧气话,觉得我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的感觉。但我就是喜欢,不管别人怎么泼冷水,我都会坚持自己想做的事。
我开始花很多时间去做一道题,可能写10道题要花六七个小时,一直做到我会为止。我第一次刷题的时候,那几个章节可能刷了100多遍,最后考试的时候,我们的考试时间是1小时15分钟,我花了20分钟就把所有题都做完了,做完以后,我还重头做了第二遍,40分钟交了卷。我每次考试都是100分。到最后一次考试前,因为老师会抹掉最低分的一次成绩,所以我根本不需要参加最后一次考试,即便是0分,我还是拿A。

我终于开始系统地学习心理学了
我是最近才开始喜欢上美国的,之前我很讨厌这里,我感觉它就像一面镜子,光线太强烈了,一直刺痛着我。其实它只是照出了我本来的样子。
我以前一直觉得自己很牛逼,虽然我没有学历,但我很聪明,虽然我没有一个好的工作,但我有很多知识储备。但其实就是因为太自卑了,我才会不断地用这些来包裹自己的自卑。这两年在美国的生活,被迫让我开始面对自己的那些裂痕。
说实话,我的成长背景非常影响我感知未来的能力,我那时离开学校,离开重庆,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就觉得我要这样做。我从海口去广州,再从广州来到美国,我做每个决定的时候,都没有考虑过未来要如何,我觉得那是不可控的。或许是因为我小时候老是觉得每一天都过得不好,所以现在我形成的观念是,我必须要保证我现在过得好,我也不想以后会怎么样。
现在,我已经29岁了,跟我同班的同学们才高中毕业,而我的冒险刚刚开始。
作者 门罗 | 内容编辑 何晓山 | 微信编辑 李心意
(摘编自微信公众号看客inSight)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