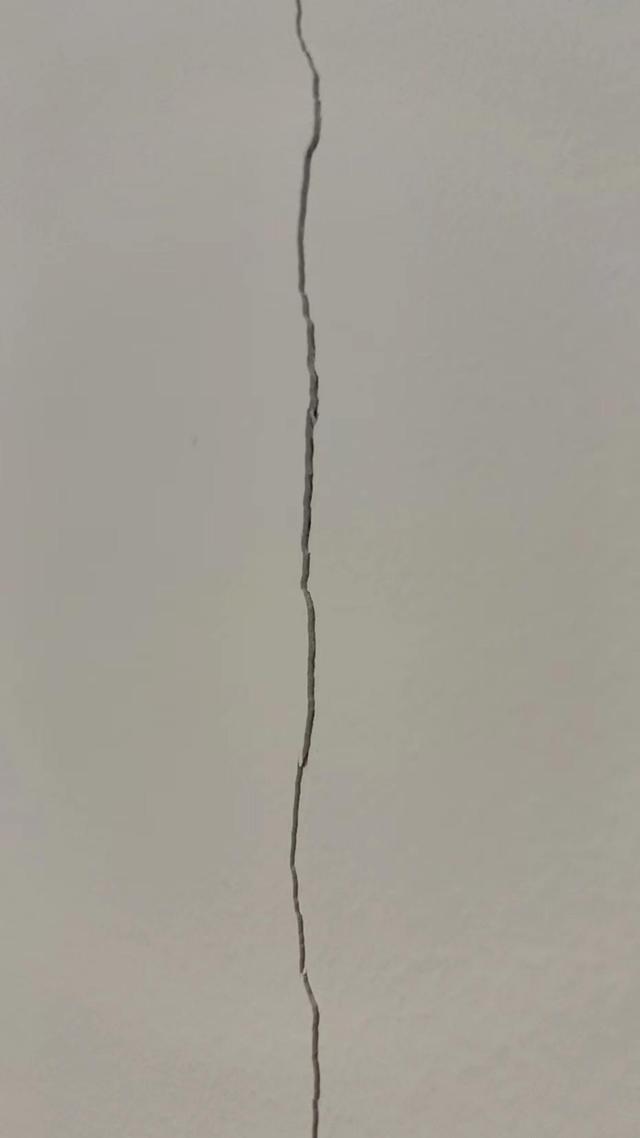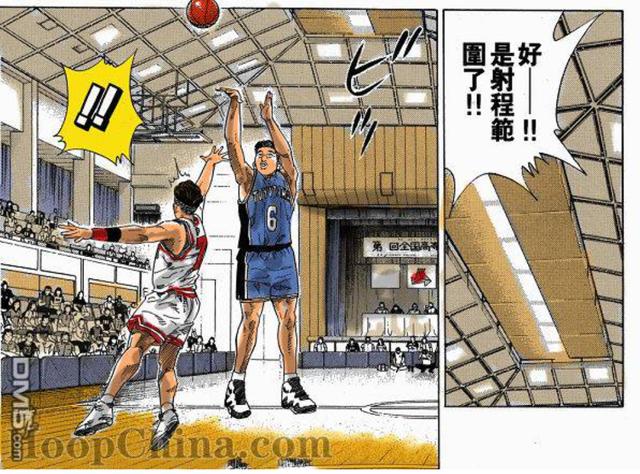苏轼因为乌台诗案几次被贬(乌台诗案身陷囹圄)
#创作挑战赛#

苏文忠公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率先摘引苏轼《湖州谢上表》中“新进”、“生事”等语上奏,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暗讥朝政。
何正臣的弹劾,只是给乌台诗案起了个头,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想给苏轼定罪,那帮御史们,深深知道,这是不可能、也是行不通的。
偏偏凑巧,也活该苏轼倒霉,当时出版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dǎn)经过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苏轼说:
“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马上,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脚后脚杀到,他们纷纷历数、指控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轼极刑。他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接着说苏轼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乃讥讪权要。再次,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冀其改过自新,但是苏轼拒不从命。最后,虽然苏轼所写诗之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臣叨预执法,职在纠察,罪有不容,岂敢苟止?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慝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
于是,朝廷派出的钦差皇甫遵去湖州拘捕苏轼。“乌台诗案”,正式立案。

御史台院内
山雨欲来风满楼,乌台诗案苏轼慌。其时,苏轼的好友驸马王诜,知道乌台诗案案发这个消息,快马加鞭派人去南京,给在南京做官的苏辙送信,苏辙马不停蹄派人去湖州告诉苏轼,朝廷派出的钦差皇甫遵也同时出发,但苏辙的人先到,苏轼知道消息,立即请假,由通判祖无颇权摄州事。
皇甫遵到时,湖州太守官衙的人慌做一团,深知天威难测,谁也不知会有什么事发生,也不知何以应对、何以解忧。苏轼吓得不敢出来,与通判商量,通判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需出见之。”苏轼一听,就准备出去。祖无颇连忙提示:“衣服,衣服。”苏轼说:“既有罪,不可穿朝服。”祖无颇提醒道:“未知罪名,仍当以朝服相见”。于是苏轼穿上官衣官靴,面见钦差皇甫遵。
苏轼首先说话:“苏轼自来疏于口舌笔墨,着恼朝廷甚多,今日必是赐死。死固不敢辞,乞归与家人诀别。”
皇甫遵淡然道:“不至于此。”命士兵打开公文一看,是份普通公文,不过是以苏轼以诗文讪谤朝廷,传唤进京而已;要苏轼立即启程。
太守官衙的人全都吓得手足无措,个个躲躲藏藏。苏轼途经扬州江面和太湖时,多次想跳水自杀。因不知道要判什么罪,并且怕他的案子会牵连好多朋友。等再一想,真跳了水,又会给弟弟招致麻烦。家里烧了他大部分与友人的通信和手稿,家人到了安徽宿县,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们的行李,找苏轼的诗,书信和别的文件。后来苏轼发现自己的手稿残存者不过三分之一。
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被正式提讯。“乌台诗案”,正式查处。

苏轼画像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苏轼下狱后未卜生死,面对审讯者通宵达旦的审问,巨大精神压力,一日数惊。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远亲代劳,却忘记告诉远亲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远亲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
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苏轼自知诗作写好之后,必定是要上呈给皇帝的。想着只要耽搁了两天,说不定可以使皇帝收回成命。

苏轼
乌台诗案遇贵人,苏轼九死遇一生。大约从十二月起,“乌台诗案”进入了判决阶段。陈睦的“录问”完成后,交给大理寺审判,大约十二月初,大理寺进行了初判。大理寺的判词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则其要点概括为: “当徒二年,会赦当原。”换言之,大理寺官员通过检法程序,判定苏轼所犯的罪应该得到“徒二年”的惩罚,但因目前朝廷发出的“赦令”,其罪应被赦免,那也就不必惩罚。
但是,御史台本意欲置苏轼于死地,御史台当然反对大理寺审判结果,大理寺的初判显然令御史台非常不满,《长编》在叙述了大理寺“当徒二年,会赦当原”的判决后,续以“于是中丞李定言”、“御史舒亶又言”云云,即御史中丞李定和御史舒亶反对大理寺判决的奏状。他们向皇帝要求对苏轼“特行废绝”,强调苏轼犯罪动机的险恶,谓其“所怀如此,顾可置而不诛乎”?不过李定和舒亶的两份奏状并不包含司法方面的讨论,没有指出大理寺的判词本身存在什么错误,只说其结果不对,起不到惩戒苏轼等“旧党”人物的作用。
不过,审刑院支持大理寺审判结果。审刑院是干啥子的呢?其关键作用,在案件审核中起到复核作用。从《重编东坡先生外集》所载“审刑院本”的结案判词可以看出,审刑院支持了大理寺“当徒二年,会赦当原”的判决,并进一步强调赦令的有效性。其结案判词可以被梳理为三个要点:一是定罪量刑,苏轼所犯的罪“当徒二年”;二是强调赦令对苏轼此案有效,“会赦当原”,也就是免罪;三是根据皇帝圣旨,对苏轼处以“特责”。
谁也没想到,生死关头,当时当朝居然多人为苏轼求情,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
但是,关键时候,一锤定音者,还是太皇太后曹氏,她把宋仁宗搬出来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
最后,宋神宗听取了太皇太后曹氏的劝阻,没有诛杀苏轼。十二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
苏轼,身陷囹圄,诚惶诚恐,本以为自己“两头不讨好”的性格,定会招致“墙倒众人推”的悲惨命运,心想新党定会将自己置于死地,哪成想连王安石都出面保他,这时候,苏轼恐怕应该会感动得痛哭流涕吧!不过,苏轼还真应该感谢他们,如果没有宰相吴充、卸任宰相王安石的求情,恐怕也感动不了太皇太后曹氏,以至于在关键时刻,她搬出宋仁宗遗旨来救苏轼一命。正所谓,“乌台诗案遇贵人,苏轼九死遇一生”!

太皇太后曹氏坐像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