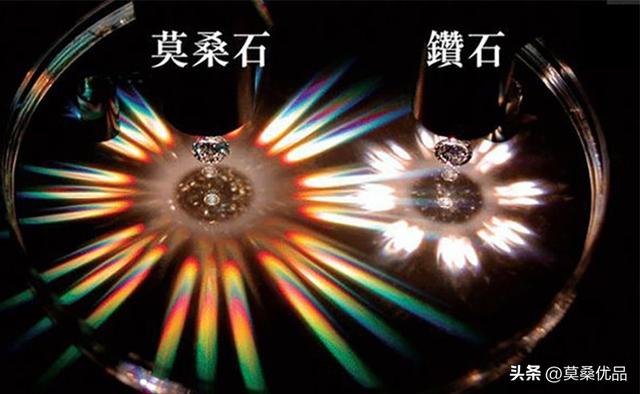老家母亲河(故乡大岔河)

泾河发源于宁夏泾源县老龙潭,是一条古老而富有传奇的河流,自古就有“泾渭分明”的传说。那清凉的水流,穿过崆峒峡谷,缓缓地流进陇东古城——甘肃省平凉市,就在它平静地穿越平凉市区时,突然,有一条小河融汇了进来,形成了泾河上游的一个岔口。应该说,这条河也算是泾河的另一个源头,就是这条河,流淌出了一片美丽的河滩,那就是我的故乡——大岔河。
童年的记忆里,大岔河两岸长着稀稀拉拉的一些柳树,柳树最多的要数我们村子,因此,我们村得名柳树沟。河滩上的石头特别多,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爷爷喜爱这些石头,常常回家路过就背回来一个,所以我们院子里到处都是石头,有的充当板凳,有的充当桌子,也有的供人观赏。以至于后来我出生时,爷爷就给我起了个“石头”的名字。记得小时候,我不喜欢这个名字,觉得太“土”气了,偷偷地改过几次,但没有改过来,因为这个名字太好记了。长大后才知道,名字不过是人的代号而已,叫什么都一样,况且,我的名字由于特别一些,很容易被别人记住,也是好事,所以也就渐渐地喜欢上这个名字了,再后来,更是敬佩爷爷,他老人家真是独具匠心啊。
泾河不像黄河那么浑浊而湍急,而是清亮而平缓的,大岔河清澈见底,无论是上游还是下游,都可以掬一捧饮用,大岔河水的甘美,是远近闻名的。到了夏天,河滩就成了我们小孩子的乐园。每天午饭后上学前,小伙伴们便瞒着大人,相约溜到河边。嬉戏玩耍,到了河滩上,用最快的速度脱光衣服,把衣服随意地扔在沙滩上,就欢跳着扑进河里,去享受沉浸在凉凉的河水里的感觉,非常惬意。
那时,河滩上也不光是我们小孩子,也有许多洗澡的成年男人,所以,每逢中午,河滩里就看不见洗衣服的女人。尽管这条河流域的村庄全是回族,但那时正值文革后期,清真寺还没有开放,庄户人家里,又没有单独洗澡的地方,所以,每逢星期五(主麻日),村子里的大人们基本上全在河里洗澡(乌苏里),洗完了就悄悄钻进附近的玉米地里礼拜,那个时代,所有是宗教活动都是暗中进行的。
有时,我们会在浅滩中挖出很粘的潮泥,去岸上筑出一道几米长的滑道,就像公园里的溜溜板,然后光着屁股坐下去,嗖的一声,身子就从滑道上滑入了河水里,激起一阵浪花。有时,我们会把银沙和水调成“糊糊”捧在手中,让“糊糊”慢慢从指缝往下滴,滴成各种造型,有的像高塔,有的像山峰,然后用水冲掉又来。有时,我们会在浅水中打水仗,猛烈地往对方脸上戽水,直到对方睁不开眼,认输。不过这时自己的眼睛也差不多睁不开了。
在滔滔流淌着的河水里,我们尽情地玩耍,玩够了,带着满身湿漉漉的水珠跑上岸去,晒太阳;有时候,也偷偷的跑到大人们礼拜的地方,悄悄地跟在后面礼拜,我们不会念词,只是模仿大人们鞠躬叩头这些动作。也许正因为那时不允许礼拜,人们反而更显得很虔诚,几乎全村子的人没有不去偷偷参加礼拜的,大人们偷着学经,我们小孩也一样,晚上悄悄地学习阿文字母“哎里夫、别、贴、些”,还有《清真言》《做证言》,直到最后自己能读全部常用“读哇”。
在大岔河的怀抱里,在银色的沙滩上,我度过了一年又一年快乐的时光。到了八十年代,河滩开始悄然变化,裸泳的人少了,女人们洗衣服的也少了,大岔河的水也少了,河岸边开始建工厂,河水也渐渐地变了颜色。银色的河滩开始被一些露天石灰窑蚕食,成堆的垃圾出现在河畔。而这时,我也告别了少年时代,再也没了下河游泳的兴致,只是经常傍晚路过河滩,却也顾不上欣赏风景了。
至今,我仍然爱着那片河滩,记忆中,它是那样的美丽。在八十年代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经常晚上怀里揣着经本,顺着河边往返于我家和我舅舅家,当时不敢走大路,怕被人发现了(当时是不许学经)。我家附近的阿訇不敢教,舅舅他们村子里有一位阿訇每晚给十几个孩子教经,所以,我每晚都要往返十几里路去那里学习。
家乡的大岔河已经融入了我的生命,它伴随着我的童年,给了我无限的欢乐;我至今常读的几个短“索热”(《古兰经》章),和阿拉伯语单词都是在这条河边边走边背记下来的,多少次阿布待斯(小净)就是在这里洗的,洗完了就在河边礼拜,这条河曾经就是我的清真寺,我的成长和它分不开,对它的感情自然是异常的深厚。
后来,我离开了大岔河,离开了故乡;再后来……一切都改变了。去年秋天我回到故乡,眼前的景和事都让我很遗憾,大岔河已不再是梦中的模样,河道几乎干枯了,变成了一条断断续续的小溪。为什么会这样?后来听弟弟说:最近几年种庄稼不划算,村里的人们都纷纷的在河道两旁烧起了石灰,石灰窑散发出来的滚滚浓烟遮天蔽日,庄稼也很难成长。最悲哀的是,尽管每个村子都已修建了华丽的清真寺,寺里也都配备了宽敞的淋浴室,而坚持礼拜的却只是几个老年人而已,村子里的人们再也没有当年钻玉米地礼拜的那个精神头了,河滩里也不见了戏水的孩子们。
我特意去寻访当年和我一起念经的伙伴们,有的在做小生意,有的在石灰窑上打短工,也许是不参加拜礼的缘故,脸上也没有了当年那吉庆的光彩,望着那些满脸污垢的烧石灰的汉子们,心里真不是滋味。有位老人拉着我的手说:“唉!如今咱们这里的每个寺里都有开学阿訇,而小孩们却都不学经了,教门已不像你小时候的那个样子了……”。我绕过富丽堂皇的清真寺,艰难地来到曾经充当过礼拜大殿的老窑洞前,踯躅在老阿訇当年住过的那间小木屋的残砖破瓦中,回忆着恍若隔世的旧景,不禁怅然以悲。
一阵惆怅,难道在不经意间,我们真的要和那些美丽的情景告别?想到此,我决定今年秋季带孩子回一趟老家,我想站在那伴随我成长的地方,给孩子讲一讲曾经发生在这里的故事。我也要久久地站在河边,睁大眼睛看看那片河滩上大大小小的青石。尽管我无力改变什么,但也要深情地捧起一捧银沙,闻一闻那沙土上熟悉的气息,那气息早已深深地植入我的骨髓,成为终生的记忆。
初稿于2002年3月12日
m318688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