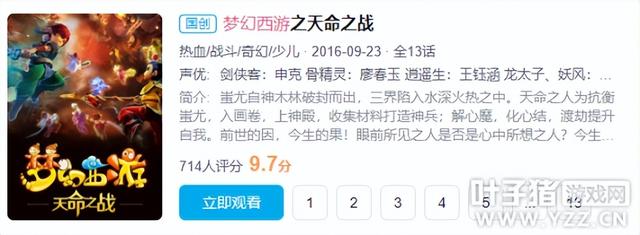孙玉霞记忆中的那些乡村农活(记忆中的那些乡村农活)
拾柴火20世纪七八十年代,捡拾烧水做饭的柴火是个大事初冬,是我们拾柴最火热的季节那时,农村孩子八九岁,就可以帮衬家里拾柴火了拾柴火也叫作“拾柴禾”,就是拾取柴草,捡拾的大多是田间地头庄稼收割后留下的残根,也叫“茬子”,玉米根最多秋天,玉米辦完后,秸秆沿根被砍下,成排晾晒在地里,等干燥后捆成一个一个的捆,拉回家立在后院墙上,冬天喂羊,留在地里的玉米根,就是我们要拾的主要柴火吹晒干的玉米根顶部有镰刀砍伐或铁锨铲后留下的茬口,比较尖锐锋利,一不小心,会划破手指那时没有手套,所以手划破的事很平常,我们不留意三五成群的伙伴们,只要看到有“大方”一些的人家扔在地里的成排的玉米茬,就很兴奋放下筐子,看准一棵茬子,从侧面几铲子挖下去,用力镐起,连同埋在土里的根须一下子被掀起来,顾不得扬在脸上和嘴里的土,敏捷地拾起,在鞋帮或者铲子上磕打,去掉沾连在根上的土坷垃,码在筐子里运气好的话,不用转移地方,在田埂下,还能捡到因根部粗壮不能连根拔起而直接被砍剩的麻头根,上面土少,肌肤光滑,有的还像千年老参,身材臃肿,不到半个时辰就可以拾满满一筐把柴火背进家门的时候,刚好是母亲准备喊我们吃饭的时间拾下的柴火专门堆在伙房的窗台下,半个月的时间,我和妹妹战绩辉煌——柴火已经超过了窗台,快堆到门口了,占领了父亲放农具的地方,妨碍我们进出伙房我和妹妹看到小山似的柴堆,似乎骄傲的很,更加乐此不疲父亲只好把柴火转到了后院的草房里,腾空了地方慢慢地,村里有的伙伴们已经不再满足于捡拾地里的“茬子”、偶有“漏网之鱼”的秸秆了印象深刻的就是那年冬天,那天是周末,太阳刚升起来,但不是太明亮,还有丝风邻居二婶家的福子和他妹妹小兰来叫我,福子压低声音说:“今天我们去拾真正的柴火”我看看天,迟疑地说:“好像有风,太冷了吧”他说:“我爹昨天说了,大队林场里有干白杨条,还有红柳,我们能掰来当柴烧,而且比茬子耐烧”听了他仗义的“邀请”,我很快就收拾好了工具那儿果然大有收获红柳长在沙丘上,冬天红柳条干燥易折,有的红柳露出了黑褐色的根,盘虬卧龙,用力一扯,就拉出来了林场离庄稼地远,白杨树一年四季靠雨水,有的白杨树树枝枯干了福子二话不说,直接爬到树上,掰断低处的小枯枝,再用小树杈勾着更粗更壮一点的枯树枝,只听“咔嚓”一声脆响,粗大的枯枝应声掉落,我和小兰再抽下来,避开尖利的地方,小心地放在膝盖上,抬起膝干,两手一用力,“啪,啪”撅成几截没多久,两捆柴火就捆好了福子用力一甩,我就听到了他嗷嗷的大叫声,原来树枝扎到了他的脖颈上,他呲牙咧嘴地说:“疼死了疼死了”我们骄傲地扛着“沉重”的柴捆,哈着气,顶着风,歪歪扭扭地走在崎岖逼仄的水沟沿上,一不小心,连人带柴摔到了沟里最后,我们绕到刘家庄和张五南面的土路上,像拉车一样把柴捆拉回家一路上,灰尘像一条云龙,柴捆腾云驾雾,十分壮观父亲看见柴捆,先是愣了一下,接着神色严肃起来,不由分说就在我额头重重地指了两下,说:“拾柴拾到公家的林场里了,这就是偷生产队的东西没柴烧,也不能偷今天不准吃饭”说着,父亲轻飘飘地提起柴捆,径直走向我们家斜对面的生产队我摸着隐隐作疼的额头,意识到错了,也在想福子和小兰是不是也受到他们父亲的责骂和惩罚了原来,君子爱柴,也得拾柴有道如今,天燃气进入千家万户,微波炉、电磁炉、电烤箱等新科技成果运用于生活,方便简单,省时省力柴草垛,乡村这道独特的风景,淡出了我们的视线可还是有很多人觉得柴火很亲切,喜欢吃柴火饭,总觉得柴火饭的味道才是家的味道,现在小编就来说说关于孙玉霞记忆中的那些乡村农活?下面内容希望能帮助到你,我们来一起看看吧!

孙玉霞记忆中的那些乡村农活
拾柴火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捡拾烧水做饭的柴火是个大事。初冬,是我们拾柴最火热的季节。那时,农村孩子八九岁,就可以帮衬家里拾柴火了。拾柴火也叫作“拾柴禾”,就是拾取柴草,捡拾的大多是田间地头庄稼收割后留下的残根,也叫“茬子”,玉米根最多。秋天,玉米辦完后,秸秆沿根被砍下,成排晾晒在地里,等干燥后捆成一个一个的捆,拉回家立在后院墙上,冬天喂羊,留在地里的玉米根,就是我们要拾的主要柴火。吹晒干的玉米根顶部有镰刀砍伐或铁锨铲后留下的茬口,比较尖锐锋利,一不小心,会划破手指。那时没有手套,所以手划破的事很平常,我们不留意。三五成群的伙伴们,只要看到有“大方”一些的人家扔在地里的成排的玉米茬,就很兴奋。放下筐子,看准一棵茬子,从侧面几铲子挖下去,用力镐起,连同埋在土里的根须一下子被掀起来,顾不得扬在脸上和嘴里的土,敏捷地拾起,在鞋帮或者铲子上磕打,去掉沾连在根上的土坷垃,码在筐子里。运气好的话,不用转移地方,在田埂下,还能捡到因根部粗壮不能连根拔起而直接被砍剩的麻头根,上面土少,肌肤光滑,有的还像千年老参,身材臃肿,不到半个时辰就可以拾满满一筐。把柴火背进家门的时候,刚好是母亲准备喊我们吃饭的时间。拾下的柴火专门堆在伙房的窗台下,半个月的时间,我和妹妹战绩辉煌——柴火已经超过了窗台,快堆到门口了,占领了父亲放农具的地方,妨碍我们进出伙房。我和妹妹看到小山似的柴堆,似乎骄傲的很,更加乐此不疲。父亲只好把柴火转到了后院的草房里,腾空了地方。慢慢地,村里有的伙伴们已经不再满足于捡拾地里的“茬子”、偶有“漏网之鱼”的秸秆了。印象深刻的就是那年冬天,那天是周末,太阳刚升起来,但不是太明亮,还有丝风。邻居二婶家的福子和他妹妹小兰来叫我,福子压低声音说:“今天我们去拾真正的柴火。”我看看天,迟疑地说:“好像有风,太冷了吧!”他说:“我爹昨天说了,大队林场里有干白杨条,还有红柳,我们能掰来当柴烧,而且比茬子耐烧。”听了他仗义的“邀请”,我很快就收拾好了工具。那儿果然大有收获。红柳长在沙丘上,冬天红柳条干燥易折,有的红柳露出了黑褐色的根,盘虬卧龙,用力一扯,就拉出来了。林场离庄稼地远,白杨树一年四季靠雨水,有的白杨树树枝枯干了。福子二话不说,直接爬到树上,掰断低处的小枯枝,再用小树杈勾着更粗更壮一点的枯树枝,只听“咔嚓”一声脆响,粗大的枯枝应声掉落,我和小兰再抽下来,避开尖利的地方,小心地放在膝盖上,抬起膝干,两手一用力,“啪,啪”撅成几截。没多久,两捆柴火就捆好了。福子用力一甩,我就听到了他嗷嗷的大叫声,原来树枝扎到了他的脖颈上,他呲牙咧嘴地说:“疼死了!疼死了!”我们骄傲地扛着“沉重”的柴捆,哈着气,顶着风,歪歪扭扭地走在崎岖逼仄的水沟沿上,一不小心,连人带柴摔到了沟里。最后,我们绕到刘家庄和张五南面的土路上,像拉车一样把柴捆拉回家。一路上,灰尘像一条云龙,柴捆腾云驾雾,十分壮观。父亲看见柴捆,先是愣了一下,接着神色严肃起来,不由分说就在我额头重重地指了两下,说:“拾柴拾到公家的林场里了,这就是偷生产队的东西。没柴烧,也不能偷!今天不准吃饭。”说着,父亲轻飘飘地提起柴捆,径直走向我们家斜对面的生产队。我摸着隐隐作疼的额头,意识到错了,也在想福子和小兰是不是也受到他们父亲的责骂和惩罚了。原来,君子爱柴,也得拾柴有道。如今,天燃气进入千家万户,微波炉、电磁炉、电烤箱等新科技成果运用于生活,方便简单,省时省力。柴草垛,乡村这道独特的风景,淡出了我们的视线。可还是有很多人觉得柴火很亲切,喜欢吃柴火饭,总觉得柴火饭的味道才是家的味道。
铲草
酷暑一到,地里、田埂上、水渠边的野草肆意生长;立秋后,野草成熟结籽。所以,从夏天开始至秋天野草结籽变黄,铲草喂猪喂羊、喂牲口也是我们这些十三四岁孩子们干的重要农活。最先铲草,其实就是清除田地里的杂草,以免欺了庄稼,也叫薅草。那时候,庄稼播种成长时,不打农药,和庄稼苗一齐发芽生长的灰条草、打碗碗草、狗尾草、麻苣苣、稗子等野草,都是手拔、铲子挖的。为防止野草复生,薅草一般是地里浇水后第三四天进行,要将杂草连根拔掉,拾掇干净,好斩草除根。等下午太阳落下,我们就将薅下的草一起清理出地垄,打捆背回家去喂牲口。记忆中,真正铲草的乐趣和成就感是夏末初秋的“偷草”。放了暑假,我们对铲草怀着一种向往。早上露水大,大人害怕露水伤了手脱皮,一般是不打发我们出去的。好不容易挨到吃过午饭,太阳还毒辣辣的,我们就挎着筐子,拿起铲子出发了。早早出去,名义上是割草,其实主要是玩。村子南头、刘家庄后面有一条宽约3米、长约100米的大沙沟,是专门用来冬天挑好了浇河水用的。沟沿上有成排的白杨树,两面大多种植籽瓜、西瓜、玉米等农作物。一到目的地,我们就脱了鞋,在沙沟里疯跑,你追我我追你,满头是汗,或是下腰、打滚,鼻子里、嘴里都是沙子,等玩累了,就有胆大的男孩子蹑手蹑脚进人家的瓜地偷人家的瓜吃,或者在树荫下抓来屎爬牛,刨一个沙坑,将它们扔下去,看它们挤挤挨挨、争先恐后、笨头笨脑地往上爬,玩厌了,就很残忍地用沙子掩埋掉,再踏上几脚。等太阳落下去,大人们陆续回家,我们就开始“偷草”。哪种草羊爱吃,哪种草猪爱吃,哪种草牛羊不理,我们一清二楚;谁家地里草多,谁家地里草少,我们到来时就做了侦查。有些草叶上长满刺儿,如刺秆,越长刺越尖锐,既不好铲,猪羊吃了还可能扎嘴;灰条,一种叶片上有银灰色或紫色的草,羊吃多了拉稀。这个节气,籽瓜基本成熟,瓜秧萎靡不振,但攀附在瓜秧上的打碗碗草如野火,开始燎原般地旺势疯长,高高地铺在瓜秧上,远远看去,就像规格整齐的绿带子。我们猫着腰,扑到隔壁邻居“老队长”家的瓜地里,一扯一大把,等扯满了一抱,迅速地跑出去,再猫着腰折回来,再扯。有的瓜趟上伤痕累累,瓜秧翻到一边,露出了比我们头都大的籽瓜。一溜烟的功夫,笈笈筐就塞得严严实实、装得满满当当。到了第二天,“老队长”发现了,也只是说我们这班小鬼,偷了草,又不肯好好偷,踩破了坠在瓜沟里的籽瓜,黑瓜籽都挤出来了。我们佯装不知,从“老队长”身边四散跑开。羊最爱吃的草是稗子、麻苣苣、狗尾巴草等。“刘虎子”是个光棍,好吃懒做,他们家玉米地里的麻苣苣、稗子最多。在他家地里“偷草”,我们最坦然,总觉得给他帮了大忙,可“刘虎子”偏偏不买我们的账,只要发现有人进了他家的地,他就会面带微笑地骂骂咧咧半天。即使这样,我们也不怕,只要瞅准了时机,照偷不误。那天下午吃过饭,我们看见“刘虎子”踢踏着露出两个脚指头的破鞋到大队闲逛去了。我们一群伙伴,吆二喝三飞也似的来到他家地里。玉米行里的稗子贴着地皮长出肥壮的叶梗,向四周伸展开,像一把扇子,葳蕤青绿,棵大茂密。我们蹲在地里,顺着地皮对着根用铲子轻轻一铲,根就铲断了,还不连土,铲几下便可拾掇一大把。埂坡下的麻苣苣一团团、一簇簇,青嫩蓬勃。铲麻苣苣要小心一点,不能直接捋。先得将叶子拢到手心,捋到一边,看清楚根的深浅,带点根铲下来,不然,叶子上苦涩的奶汁全粘在手上,不一会儿手掌就变黑了,黏糊糊的,不容易洗掉,一连几天吃饭时都能闻着苦味。我们几个弯着腰,撅着屁股,顺着地埂,七手八脚,一会儿便把“刘虎子”家玉米地里的好草铲光了。填满筐子,正准备钻出玉米地时,忽然就听见“刘虎子”一边骂着脏话一边拨拉开玉米叶子走来的声音。“刘光棍来了,快跑!”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我们急忙提起筐子,猫着腰,磕磕绊绊向另一头跑去,出了玉米地,气喘吁吁,回头一看,却不见“刘虎子”追来,细细一听,地里静悄悄的。原来,“刘虎子”拾到了我们在慌乱中丢了的两把铲子,已经得意扬扬地踢踏着破鞋回去了。而我们,因为丢了铲子,怕大人发现,一直熬到天黑才背着草筐回家。自此,我们就多了个心眼,进“刘虎子”家地里偷草,一定安排两个年龄小点的在地头放哨。就这样,一夏天割的草牲口都吃不完,还能晒下一大堆干草,那种成就感似乎可以和庄稼丰收后的喜悦相媲美。现在的农业生产从播种到秋收,实现了机械化;畜牧养殖场的建设如火如荼,牧草种收规模化,野草自然失去了用武之地。每当看到被扔在墙根下,风吹日嗮,缺把少底的笈笈筐和路旁地头积得厚厚的、水灵灵的野草,我不免心生怅惘。
看瓜
六月,赤日炎炎,南风一吹,西瓜渐渐地熟了,父亲就在地头搭起瓜棚。几根手腕粗的白杨杆搭建起三角形的主体,再加上一层白杨树枝或寻一些破旧的编织袋篷在上面,略略地抹上泥,里边摊上一层厚厚的麦草,瓜棚就好了,日里遮阳,夜里挡露。暑假到了,西瓜熟了,我们看瓜的日子也来了。走进瓜田,瓜蔓铺满了瓜趟,青白色锯齿样的瓜叶像一只只伸开的大手,贪婪地吮吸着阳光。一个个青皮绿纹的西瓜挺着圆溜溜的肚皮悠然地躺在瓜蔓之间,闪着光,带着香,我们眼热地用手挨个敲过去,“嘭嘭”“噗噗”“当当”,动听诱人。看瓜人吃瓜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事儿。口渴了,肚子饿了,不渴不饿想吃瓜了就去田里挑选。可俗话说“满箩里挑瓜,挑得眼花”,有时敲瓜掐皮,左挑右挑,打开一看,半生不熟,就再挑一个。被糟蹋的西瓜没处藏就挖个坑埋起来,用脚踏实;或者甩开膀子扔到玉米地里,就听到“砰”的一声,西瓜粉身碎骨。时不时地被大人发现了也难免挨骂,不过,看瓜的活儿还是照干,西瓜挑走眼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当然,吃瓜归吃瓜,我们可从未忘记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看瓜。其实,那时候村子里基本上家家种瓜,看瓜也就是做做样子,看瓜次数数不清,但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大人偷瓜的。同宗邻居,乡里乡亲的,即使没有种瓜,按照风俗,都会照例给他们家送的;田间劳作的人口渴了,摘瓜也都会打招呼的,看瓜的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也会热情招呼他们尝尝自家的西瓜。那些赶路的外村人,顺手扯个瓜,摘个果,三瓜俩枣的,乡亲们也是不介意的。至于年龄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小孩子,因为顽皮,漫山遍野地闲逛,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摸到别人家的瓜地里摘个瓜吃,大人们是不会看重的。即便如此,瓜还是要看的。看鸟。主要看乌鸦、喜鹊、麻雀啄食西瓜。鸟儿们很聪明,比我们更懂得西瓜的生熟,它们啄的都是熟得正好的瓜,那么漂亮的西瓜被啄个洞,红瓤黒籽,看着真让人可惜。而且,啄开了又不好好吃完,喜新厌旧似的,趁人不备,又去啄食好瓜。父亲用我们不穿的旧衣服做了一个“稻草人”,一开始对鸟儿还有震慑作用,没过多长时间,鸟儿就识破了真相,不再惧怕,甚至还挑衅似的落在“稻草人”的头上。所以,我们看瓜时,看有鸟雀下来,就要拿一根绑着颜色鲜艳的布条的棍子,到地里舞弄耍动,制造动静。看瓜是个悠然快乐的活儿,但我后来再也不敢去瓜地里看瓜,是因为生产队里传说的刘四爷的事。那年,我们村里种瓜的农户大多把西瓜种在刘家地。刘家地在村庄的西南方向,属于村子里土质最好的地块,种啥成啥。出了村,西走200米左右,有一条大沙沟,将村子里北边孙家的田地和南边刘家的田地分开。沟的两边各是平整出的土路,方便转运农作物。让孙家人生忌和闹心的是刘家坟地就在地西头不到100米的地方,晚上地里浇水心生惧惮。所以,夜里小孩子是不能单独留在瓜棚里的。如果谁家的小孩哭闹着要跟大人去,大人就拿刘四爷的事吓唬他。刘四爷是生产队里的一个老把式,特别喜欢种瓜种菜,人又特别朴实厚道,所以村集体的瓜园也往往交给他来看管,他还掌管着生产队里分瓜的事,等按工分分完了西瓜、甜瓜,剩下的歪嘴劣蛋就吆喝我们一群孩子们挑着吃。在大人们和孩子们的眼里,刘四爷是个好人。可谁也没想到刘四爷80岁的时候,疯了,老说些不着边际、古怪恐怖、没来头的话,听得瘆人。慢慢的,村子里就传开了这样离奇的故事:刘四爷晚上看瓜时,看到一个穿着白衣白裤、披头散发的姑娘从他们刘家坟地走过来,要抓刘四爷的手,刘四爷大骇,挣脱开跪地磕头,等他抬起头,却只看到一轮月亮明晃晃地悬在头顶。从此,刘四爷一到晚上,就满头大汗,胡言乱语,精神一天不如一天,家里人用驴车拉他到城里看病,也没看出什么问题。三个月以后,野草黄了,瓜田渐渐地败了,杂草盖过了瓜蔓。大西瓜几乎已经摘完,小西瓜俗称“秋瓜蛋”也长不熟了,刘四爷也死了。刘四爷死后好几年,村民们都不在刘家地种瓜了。时光荏苒,村子里种瓜的老把式都不在了,年轻人带着美好的憧憬离开家乡,去外面的世界闯荡,种瓜和看瓜早已经成为了故事。水果店里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到各色各样的瓜,但承载着我们儿时欢乐的家乡和土地,却像藤蔓上的西瓜,在我们的心里无穷无尽地生长。
打场
每年盛夏的麦收时节,村子里的打麦场成了全村最热闹、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快割快打,麦粒不撒。”早上10点左右,打麦场上人头攒动,要摊场了。大人们还没说摊多少捆麦子,我们六七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就已经攀着麦垛,拽着草葽爬上了麦垛顶,开始往下扔麦捆,那样子和动作颇有点古战场上防守城墙时,将士们居高临下往下扔石头的气势。大人们手提肩扛,车拉杈挑,有些招架不住,仰头嗔怒“慢慢拆!慢慢拆!”我们哪里肯听,手脚并用,左扯右撕,一会儿就将麦垛拆掉了三分之一。直到小爸扬起杈把,把我们从麦垛上赶了下来。我们就开始挨个解麦捆上的草葽子,找到系扣,抓住短头,用脚一挑,抖散了麦捆,大人们用杈摊开抖匀。不到一个小时,一个两边半圆的矩形麦场就摊好了。场摊好了,让麦场吹吹风,出出潮气,晒晒太阳,各家先吃午饭。午饭后才是打场的高潮。套好牲口带好磙子后,开始打场。打场通常要打三遍。头遍叫“攘场”,磙子走几圈,场上的人在磙子打过去的地方,用杈随时翻起抖匀,麦芒压落,打遍即可,主要让摊在下面的麦子吹风晒太阳。头遍上我们最愿意牵牲口,因为嘻嘻哈哈赶着牲口跑圈,不走正道,也没人责骂。二遍叫“打头麦”,牵牲口要求比较严格。父亲或者叔伯他们牵着“大牲口”(骡马)的“单磙子”走在前面,我们赶着驴套的“双磙子”,手里拿着白杨条或鞭子,吆喝着紧跟在后面,不停地转圈压场。单、双磙子一个走里沿,一个走外沿,不能走错道,否则,场容易打“花”,麦子不容易打“熟”,如果老走不对道,或者跟不上父亲、叔伯他们,就会被罢免,跟母亲或婶婶她们去做用杈把、扫帚收拾场边,垫场口这种无聊的活儿。慢吞吞的,一会儿,我们就开始打嗑睡,一个趔趄,嘴差点合到驴屁股上。等麦秸压成了明晃晃、金灿灿的麦草时,头麦就打完了。卸了牲口,把它们拉到有草的地方,免得进了周围的庄稼地糟蹋了庄稼。母亲、婶婶她们一边说着闲话一边刮麦草。我们抱麦草,你追我赶,你把他推到麦草堆里,他把麦草扬在你的头上;谁抱的麦草多,谁偷奸耍滑,七嘴八舌,一个不饶一个。太阳毒辣辣的,麦场上人声鼎沸,热火朝天。刮完麦草后要翻场,即把没有打熟的麦秸、没有脱尽的粮食,用杈翻抖拨匀,让太阳暴晒。期间人们开始休息,吃晌午。树荫下,有吃西瓜泡馍馍的,有干馍馍就茴香茶的。吃喝完了,父辈们抽袋旱烟,就套好牲口,准备第三遍“打二麦”。“打二麦”的程序和“打头麦”是一样的,只不过花的时间比较短。等麦穗压软了,麦壳粉碎了,麦粒纷纷脱落,麦场上铺上了一层饱满厚实的麦被时,就该起场了,一天的打场工作也就接近了尾声。“起场”是打场中节奏最快、参与人数最多、场面最壮观的。父亲选好了场中心起印堆的地方,场上的男女老少就紧赶着把粮食往印堆上拢。用簸箕运的,用木锨铲的,用推板推的,用扫帚扫的,用拉板拉的,推拉在前,铲扫在后,边拉边扫,边扫边推,整个打麦场上工具齐响,草屑飞舞,麦尘飞扬,一派欢腾。木锨铲起粮食和扬出时发出的“刺啦”声,推板推动粮食和用力压住拉板的“咯吱咯吱”声,扫帚扫起粮食时的“唰啦唰啦”声,大人们开怀的大笑,小孩子们的嬉闹喧哗声,编织成了热闹的劳动交响曲。渐渐地,麦场中心的印堆越来越大,像小山一样,饱满、圆润;场边堆起的麦草垛,像波浪一样,高低起伏,它们彼此守望,静默在夕阳的余晖里,渲染成了一幅最美的画卷。吃过晚饭,一场不焦不躁的东南风来了,麦场上又忙碌起来,扬场了。扬场是借助自然风力把麦粒和麦糠分开,是粮食归仓前最后一道工序,是个技术活,大都由父亲或叔伯来承担。父亲先看好风向,拿着木锨站好位置,母亲围着头巾拿着新栽的大扫把站在一边,准备打掠扫。父亲手持木锨,一锨一锨扬着,“唰……唰……唰……”,不疾不徐,不轻不重,节奏和谐。麦粒随着扬起的木锨在空中飞扬、散开、落下,像一道彩虹,又像一股飞溅的瀑布。手起手落,麦壳和麦芒随风而去,沉甸甸的麦粒,却划出一道弧线落下来,不高不低,不远不近,在父亲脚下滚动、聚集、成堆。母亲趁这个间隙,不紧不慢,左右开弓,用长长的扫把尖轻轻把麦糠和麦秆掠到两边去,留下了颗粒饱满的麦粒。我们围在一边或躺在麦草垛上,痴痴地看着父亲和伯父挥舞着手里的木锨,将麦粒舞出一弯弯漂亮的月牙,伺机过过扬场的瘾的念头蠢蠢欲动,待他们歇息抽烟的当儿,我们立刻跑过去,拿起木锨,“唰……”,麦粒从头顶灌到了脖子里,钻到衣领中,又从衣襟下滚出来,脸上飞了一层又痒又呛的麦糠,就逃也似的钻到麦草堆里玩去了。“麦上场,快快扬。”在一年四季的农活里,麦场上的日子是最为短暂的。农人一年的忙碌辛苦,就是祈盼庄稼有个好收成。只有把地里的庄稼变成粮食,他们的心里才踏实。从收割进场,到颗粒归仓,短短十来天,场院又恢复了沉寂,静静地等待下一个丰收季节的到来。今天,农业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新农村建设日新月异,脱粒扬场“一锅出”。半天工夫,几十亩地的麦田变成了晾晒在房前屋后水泥地板上一大堆一大堆的粮食。留够自家吃的,装袋过秤,算账点钱,一年的收入到手了。一个个寄托着农人希望,见证着农村从贫瘠到富裕,从富裕到辉煌变迁的打麦场失去了昔日的喧嚣与繁华,沉浸在时间里,定格成了满满的乡村年代记忆。时间的流逝总是在不停地记录社会经济的发展、时代文明的进步。新陈代谢,吐故纳新,永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柴草垛、笈笈筐、瓜棚、打麦场,这些乡村的原始生命符号,穿越了时空,正在用全新的姿态迎接乡村振兴的明天。
作者: 孙玉霞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