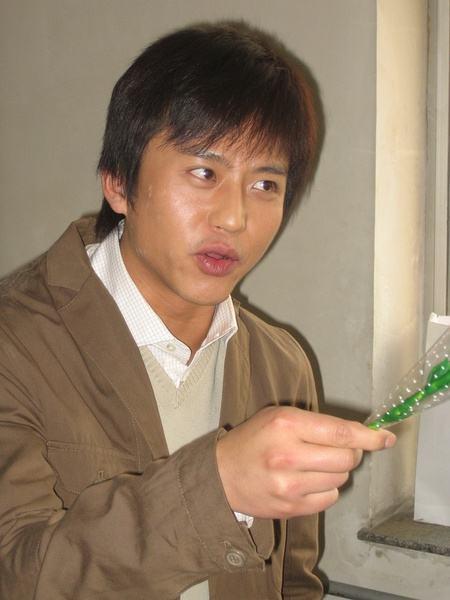过年打花糕的技巧(传说中的打禾炮)
打禾炮,是家乡方言即爆米花。小时候,进入冬天的湘南乡村,常常有进村入巷的打禾炮师傅不时地吆喝着“打禾炮,打禾炮啰”。我们这些小毛孩一听到这种吆喝声,立即跟在打禾炮人的身后,等待打禾炮人将“武器”摆放在某个背风又空旷的地方,或是一条宽阔的路边,或是晒谷的禾坪上。有的小孩也会跑回家,向父母报告,说“打禾炮的人来了,我们家也去打点禾炮吧!”在征得父母的同意后,从米坛子里弄几杯米,交给打禾炮人,装一袋爆米花回家。
打禾炮,一炉熊熊的火焰,打禾炮人慢慢地翻滚着外形如炮弹一般漆黑的爆花机,黑黝黝的被炉火映红的脸膛,以及空气中弥漫着的令人陶醉的玉米花的香味,一切尽是如此贴切,如此似曾相识。那时候,尽管物质比较匮乏,但人们都会想方设法变换着法则,让传统的春节过得热闹又有味道。每逢过年,爆米花是许多农家必备的过年年货。大年初一拜年时,许多农家的餐桌上都会有洁白的爆米花。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九七五年的一个冬日。“小雪”过后,这天刚好是星期日,天气十分晴朗,村子里来了一个打禾炮的老汉,他说的是资兴话。年龄大概五十多岁,披着一件打了补丁的旧棉袄,下巴上长有一小撮胡须,黝黑的脸膛,脸黑手黑。在禾坪上支起炉子,烧起炭火,坐在一条小矮凳上,他一边抽着短烟斗,一边拉着风箱,摇着酷似一个压腰葫芦圆鼓鼓的小黑锅也即爆花机,小黑锅上还连着一个表盘一样的东西,后来才知道那是一个温度计。让我不明白的是,小黑锅还链接着一个拖拉机的外胎。

图片来源:时刻新闻
随着浓烟升起,村民们便三三两两地或用布袋装着大米,或用麻筛盛着金黄的番秀(家乡土话即玉米)来爆米花。由于来打禾炮的人较多,需要排队而且是排长队,没有什么人维持秩序,但村民们都很自觉,按顺序排队。排队的方式,开始是人站着排队,大概是人站着时间长了点有点儿倦,不知道是谁先用物品代替人排队,大伙儿便跟着用物品排队。这些物品是布袋、麻筛,各自在自家的布袋、麻筛标上记号,站在大老远的地方就能够分辨出来。
我见到众人打禾炮排队的情景,于是,便赶紧跑回家,将有人来我们村打禾炮的事告诉母亲,母亲说:“今年年成好,过年多打点禾炮,两个品种,大米、番秀都要打。”听母亲这样说,我心里非常高兴,过年的年货丰盛,我们这些小孩有口福,很有可能过了元宵节还有年货吃。母亲用一个旧军袋装了几杯米,用一个小布袋装了几杯番秀,吩咐我拿去禾坪排队。我将两个袋子紧挨着,容易识别。与村民们的布袋、麻筛排在一起,等待打禾炮。往年打禾炮的原料只有大米,而这年增加了番秀。番秀是自家自留地里种的,而且种得很好,用句官话说是大丰收。所以母亲决定打禾炮除大米外,还增加番秀这个品种。
众人围观老汉打禾炮,有人拉起家常,有人议论该买什么年货,帮小孩缝制新衣服。老汉他在手摇爆花机时,偶尔也会在人们谈话时插上几句话,表明几句自己的观点。他说的是资兴话,与我们村说永兴话不同,不过,我们都能够听懂。原因是我们村地处资兴、永兴交界处,边界地段的人们交往密切。我不仅能听懂,而且还会说资兴话。我母亲是资兴人,她在家里都是同我们说资兴话,家里很多亲戚也都是资兴人。久而久之,我们家的人都会说资兴话。
打禾炮有一个流程。开打前是装原料,只见老汉将其专用计量工具一搪瓷缸,将大米或玉米倒入黑黝黝的爆花机中,拧紧盖子,放到炭火上慢慢滚动着,使里面的大米或者是玉米粒受热均匀。约七八分钟后,待爆花机手柄上的压力表指针达到指定的刻度,米花就可以爆了。此时,老汉戴上厚厚的棉手套,以防烫伤。一只手提着手柄,一只手把着另一端,将爆花机在炉子上拿下来放到铁箱上,用铁棍插进盖子上的铁鼻子一撬,只听“嘭”的一声,随着一股乳白色的气浪,像棉花一样洁白的爆米花便被送进了麻袋里。我们这些小孩捂上了耳朵,胆子小的连眼也不敢睁开。出炉时那个黑黑的机器炸响声,吓得一位来凑热闹妇女手中的婴儿哇哇地哭了起来,老汉说“带婴儿看打禾炮,容易吓坏婴儿的。”女人说“没什么,没什么,这种声音同家里那些鸡鸭鹅的叫声差不多。”她轻轻地拍了几下受惊吓的婴儿,嘴里不停地念着“崽子崽子,不要哭,不要怕,妈妈护着你呢!”很神奇,婴儿在女人的轻拍摇晃下,果然不哭了。

图片来源:时刻新闻
打禾炮在出炉时,会有一种强劲冲击波,随着巨大的冲击力,也会有小部分米花通过铁箱散热的小孔撒到地上。此时此刻,我们的鼻子里钻进一阵香气。小伙伴们随即雀跃着蜂拥而上,捡起热乎乎的松软的米花放进嘴里,嘴里放不下时就装进兜里,脸上洋溢着得意的欢笑,让我们有一种沉醉的感觉,一边吃一边等待着下一轮的收获。爆米花时人们总是挑选个头最大最饱满的玉米粒,有的再添加些许白糖,这样爆出的米花香酥脆软,又大又好吃。
等了将近两个小时,终于轮到我们家打禾炮了。根据母亲提供的大米、番秀数量,我们家要打两次。先打大米,再打番秀,两锅打出来的结果十分完美,米花既大又香。在给老汉付加工费时,我用资兴话同他交谈,他有点吃惊,想不到我的资兴话说得那么好,本应收取两元加工费,只收取我一元五毛钱。这年,我们家的年货较多,家人似乎是过了一个“肥年”。特别是这两大袋的爆米花,让我们吃到了元宵节。
打禾炮,童年的往事,尽管过去了几十年,但其中的乐趣至今让我难以忘怀。(文/肖飞)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