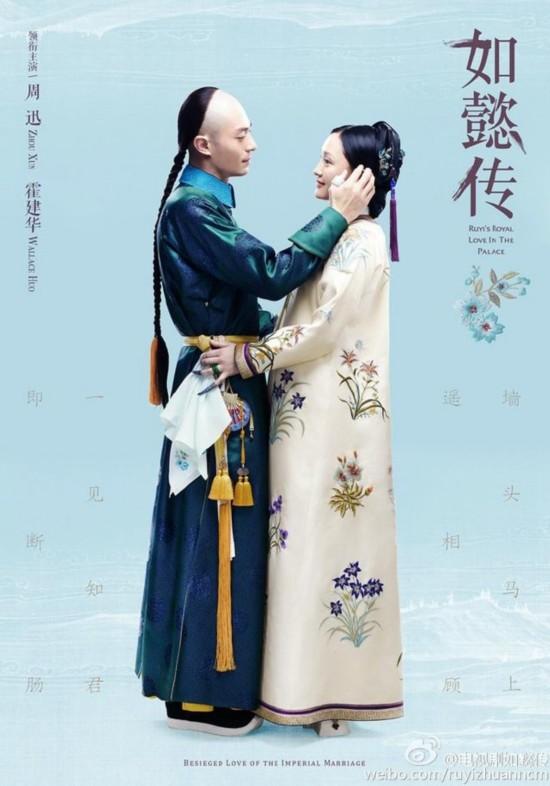北大老师对学生的教诲(北大课堂的传统)

《半百上学堂:北大家书集》33
上回跟您抱怨北大有许多怪客,还有许多怪声。然而那终只是片面。这里的男声大半还挺好听的!
女儿早已过了异性相吸的年龄,如此评价与荷尔蒙作用全然无关。大陆人,尤其北方人讲话普遍比台湾人阳刚许多,从一般女生口中出来,总觉得稍过强悍,可这种气质反映在男生的口语表达,自有别样的魅力。女儿很喜欢在上下课途中,或是在食堂凝神倾听不经意飞来的男声。北大学生在课堂里的发言难免炫技,夸夸其谈,有时甚或是大放厥词,听得女儿直皱眉头。可若是这种不经心的讨论,女儿可喜欢了。一来是对话中的含金量颇高,二来是避开了争取高分的现实利益,呈现的是更为真诚的情感。女儿虽然面无表情,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可心里常偷偷喝采。
今天是星期五,照例有陈平原老师的课。真要说他的课精彩到无与伦比,就像先刚老师赞美黑格尔那样,是金字塔上无可匹敌的尖儿?也不尽然。女儿在他课堂上的收获,有更大的比例是来自他精神的感召。他就是有办法让你觉得:这才叫真正的读书人,远非一般汲汲名利的大学教授可以望其项背。
他是文革十年后重新开放高考的第一代考生。1977年开始连着三年高考登第的莘莘学子,日后在许多专业领域大放异彩,至今依然屹立不摇。老师虽然也属于这个圈子,却能翻出樊篱审视其中的不足。那三年入学的学子,年龄从16岁到36岁不等,大约涵括了两代,等同父子一同上学。文革错失的十年光阴,让他们格外心急,这一路走来始终都有赶路的心态。积极进取不是坏事,但忙着往远方大步前进的结果,必然错失了沿途许多可喜的风景,从而作出来的学问也就无可避免地少了点什么,就像民初小品大家周作人对于北京茶食的批评一般:既不够从容,厚实与丰腴也一并从缺。

陈老师真诚的自我批判是一回事,现实的场景却是这批学者至今依然活跃在学术舞台上。老前辈引领风骚数十年,从某个角度看是老当益壮,诚然可喜可贺,高瞻远瞩的陈老师看到的却是后继乏人。这个“奇迹”的背后,要嘛是上一代学者仍“赖”在台上,新一代无有上台的空间;要嘛就是年轻学者产能不足,无有上台的本事。
如果把知识看作共同体,是国家民族发展的命脉所在,那么理当长江后浪推前浪,不断推陈出新。陈老师一直有个深切的自觉,学者活到某个年纪,应该有意识地带领后辈学者上台,至于如何带领,技术操作的细节当然得再琢磨,否则只怕又是另一个温情脉脉的乌托邦而已。
爸爸记不记得很久很久以前,大学教授曾是最受尊敬的行业?这几年呢?声望下跌到有点不堪的地步。这个景况,不独台湾如此,大陆更是。尤其是政府介入大学研究经费补助之后,恶化尤烈。稍有自觉的人早就知道暗潮汹涌的学界无异于险恶的江湖,或者说更有过之。把原该清净如水的学界搅成污浊的泥沼,学者本身当然有责任,更直接的因素,则在制度的设计。
先前在台湾也曾报导得沸沸扬扬的王立军,在事发后被《南都周刊》掀出底来。这位有“学者”头衔的老兄原来只有初中学历,从军后通过自学与成人考试,取得大专文凭。随着官场青云直上,学术头衔居然也水涨船高。事发当时,王立军已经是二十九所大学、研究中心的兼职教授,从硕士导师、博士导师到主席等等不一而足。这还没把只有口头聘请,尚未举行正式聘任仪式的高校算进去。
陈老师说,王立军要不是“及时”出事的话,恐怕连北大、清大、人大这种一级名校都要跟着沦陷。
高等学府在赠予王立军学术荣衔一事上,表现得倒是非常“长江后浪推前浪”,唯恐落人一步。根本的原因就在王立军手上握有大权,大学为了争取经费,透过这种“合作”关系,方便取得补助。相较之下,企业家捐赠大笔资金,换取校园建筑的题名,反而显得可爱多了。陈老师说,那至少不影响专业。阁下爱名,学校要钱,双方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大学的清望跌到什么地步?说个真实的“笑话”给爸爸听。陈老师应邀到东北的某高校访问,与校方高层谈起招生。对方说新生入学,要嘛是高官,要嘛就送钱,当然是大笔大笔地送,不然就是直接带教授到车厂,看教授中意哪一部。陈老师听得目瞪口呆,对方意识到了,反问他:“难道你们北大没有?”陈老师赶紧声明:“不但没有,连听都没听过!”结果对方“惊呆”了:“什么?那你们怎么招生?难道是看成绩?”

北大的确存在不少问题,但至少招生是干净许多的。女儿可以作证!
真要说现今学界的丑闻,那可有的讲。老师引用一笔资料,2013年11月7日,《南方周末》有一篇报导,标题是“给我一篇假论文,我能骗倒半个地球”,有位教授故意假造一篇论文,所谓假造,是有意地引用大堆艰深的名词与理论,拼凑成一篇逻辑,甚至语法都不通的论文,投给304家期刊,同意刊登的,居然有157家!部分编辑曾经提出修正意见,全在语法打转,没有人发现这篇论文的内容一无是处!
换句话说,如果有心,真想在学术界招摇撞骗,难度其实也没那么高。
好啦,说来说去,大环境既然如此恶劣,置身其中,个人当如何修为呢?自命清高,所以不随波逐流,不寻求获奖,也不申报课题(大陆这玩意近似台湾的研究项目,通过后会有官方的经费补助,而且数字大到让人眼红),不谋求晋升,全凭个人兴趣读书写作。这样行吗?也行!不过近似自我放逐的结果,必然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的天职也就无从着力,无从发挥了。
老师的结论,引用古人的“取法乎上,仅得乎其中”,既有的学术典范从来不少,不必忙着在不堪的现实中与人比烂。“达则兼善天下”的理想或许太过高蹈,至不济,也还可以“独善其身”。一席话说得女儿热血沸腾,频频点头。活在这个时代,不仅学术如此,为人也是哪!
今天让女儿动容不已的课堂其实从一个不大寻常的起点开始:点名。老师挑了选课名单上十三个名字点完,说其他的日后再抽样点名。北大点名?不只是作为博士班新生的女儿从没听过,老师的说法,这根本违背北大传统。北大课堂的传统是什么?据说是“来者不拒,去者不追”,旁听的尽管来,溜课的尽管去,反正对点名嗤之以鼻。去者之所以不追,预定的假设是学生如果不在课堂,就是在图书馆。现在呢?超高的缺课率,表明学生的确不在课堂,可去了哪儿呢?不知道。所以只得被迫点名。教现代西方哲学的赵敦华老师大概不久之后也会跟进,他上一次上课,已经预埋伏笔,劈头就说:“老师有义务帮助学生学习,所以学生如果无法主动学习,老师就得善尽义务。”这话说得漂亮,然而意思明显不过:爱逃课的得准备接招了。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英文听力课是大班上课,集结所有学生在大教室看视频(台湾叫视讯),当场点名第一有技术上的困难,第二则是把诚实当作第一守则的外籍老师推定北大学生会遵守互信原则,出缺席是事后在口语课上让学生自动划记。女儿明明听到同学嘴里嚷着(当然是用老师听不懂的汉语)缺课,可又毫无愧色地在出席单上打勾……
什么地方都一样呀,什么人都有。套句陈老师的话:“既有终南捷径,也有杀人放火后招安的传奇。”反正别人是别人,自己是自己,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最重要。对不对?爸爸。女儿相信您会这么说,当然也是这么做的呀。女儿可是从小就把爸爸当作实践典范的!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