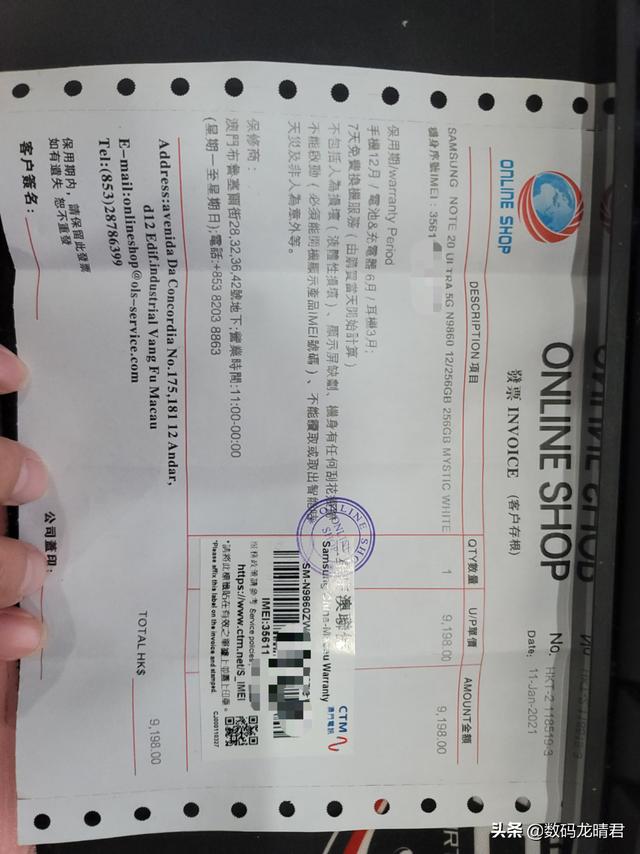回忆儿时旧时光的句子(时光回声故乡的模样)
柳树,是很普通的树种,天南地北随处可见,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回忆儿时旧时光的句子?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参考一二希望能帮到您!

回忆儿时旧时光的句子
柳树,是很普通的树种,天南地北随处可见。
在济南的一些公园里,比如大明湖、趵突泉、五龙潭、护城河等等,就生长着很多婀娜多姿的垂柳。人过中年以后,于风和日暖、柳絮飞扬的时节,我很喜欢去这些地方看柳。出差在外,每当看到枝条繁茂的柳树,我的心情也会格外清爽熨帖。
刚开始的时候,我这么做纯属一种下意识的行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当爷爷和父亲过往的言行、故乡的点点滴滴,越来越频繁、越清晰地在脑海中回放之后,我似乎明白了自己这么做的缘由。
我的故乡,是北方平原的一个普通乡村。所以,那里也有不少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柳树。
故乡那个村子,大致分东、中、西三个部分。村子东头,以李氏家族为主聚居。中部,村民多为魏姓。我们老王家,则占据了村子的西头。爷爷离休以后回到故乡,在老王家聚居处盖了三间房子住了下来。于是,故乡便成了我每年寒暑假,乃至下乡插队的目的地。
记得儿时的故乡,村子四周还残存着一段段古时修筑的土围子。那些土围子,在小时候的我看来,像一道道又高又陡的坡。坡上野草青青,坡顶柳树葱茏。坡下沟里,水清鱼嬉。在它们时断时续的包裹之下,整个村庄就像一个大家园,有些团圆、有些安详、有些神秘,当然也有些封闭。
爷爷盖的房子,靠近村子西头的出口附近。村子的西口外面,有一个东西长、南北窄的椭圆形池塘。池塘的水面不算小,大概总有十几亩地那么大。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池塘里的水深而且清。即使是在干旱之年,也从来没有干涸过。
在池塘的周围,遍布枝繁叶茂的柳树,其中多为垂柳。其中最古老的那棵,粗大的树身两人不能合抱。它位于池塘的最东头,夹在村子西出口两旁的土围子中央。流逝的岁月,已经在树干中间掏出了一个大大的朽洞。风霜和雨雪,压弯了它那苍老的腰身。从我与它相识之时起,它的躯干就是斜倒着伸向水面的。它是那么地粗大,倾斜得又比较厉害,以至于我们这些小孩子们躺在树身上面,都不会掉到水里去。
老树年年发新枝。每当春风吹来的时候,这棵老迈年高的垂柳,总会如期绽放出一派盎然的新绿。茂盛的枝条,如流瀑般垂向宁静的水面。有些,已经可以与池水亲密接触。微风轻摇柳枝,柳枝微抚池水,那水面泛起的一圈圈涟漪,看上去透着说不尽的温柔。我觉得,这棵老柳树,就像一位鹤发童颜、长髯飘飘的德高长者,率领着自己的子孙们,默默地守护着这方池水,守望着这个村庄。
爷爷抗战之初从军,离乡背井三十多年。叶落归根之后,他常常拿个小马扎,坐在这棵大柳树下,或者跟乡亲们拉拉家常、或者下下棋什么的。不过,他似乎更喜欢笑嘻嘻地看我们这帮小孩子,嬉闹着在树上爬上爬下,玩水钓鱼套蛤蟆。不知道这样的情景,是不是让爷爷的思绪,又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时光。
爷爷会做柳哨。从树梢上取一截半指长的柳条嫩枝,去掉中间的硬芯以后环切整齐,便是一只柳哨了。爷爷做的柳哨,吹起来清亮亮、脆生生,很有穿透力。我也跟爷爷学着做过柳哨,但是吹出来的声音,却怎么也没有爷爷做的好听。记得有一回,我吹着爷爷给我做的柳哨,一遍遍爬上老柳树,噗噗通通地往池塘里跳。爷爷在树下看着,一声叹息:“这孩子,跟他爸爸小时候一样‘皮’”。在我的故乡,人们形容小孩子调皮捣蛋,通常都用这个“皮”字。
我父亲1946年参军,走的时候还不满十六岁。也就是说,他离开家乡的时候,在那棵老柳树上爬上爬下所留下的气味和体温,还没有从身上褪去。我不知道,他走的时候,嘴里是不是也衔着一个柳哨。在外东奔西走四十多年,由于工作、身体等种种原因,他回故乡的次数并不是很多。每次回去,也大都是来去匆匆。我不知道,回到故乡以后,他会不会专门去看看那棵老柳树。但是我记得,在他病重住院以后,有一次有些伤感地对我说,“咱们村西头那棵老柳树,不知道还在不在了。”还没等到我为他问清楚这件事,他就离开了人间。
父亲去世的第二年,爷爷也走了。庆幸的是,在爷爷去世前不久,我回故乡看望过他老人家。在故乡期间,爷爷有一天幽幽地对我说:“那棵老柳树没了,‘西湾涯’(故乡方言称池塘为‘湾涯’)也快被填平了。”那时的我还太年轻,不懂得爷爷的伤感,需要我的共鸣。听了爷爷的话,我竟然无动于衷。我也没有意识到,爷爷和父亲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念叨起那棵老柳树。因而我也就没有问问爷爷,这棵老柳树是什么时候没的,又是怎么没的。我想,它死于人为原因的可能性,大约更大一些。毕竟,它顽强地生长了那么多年都没有死掉。至于那些土围子,此时早就不见了踪影。村口那条弯曲的小路,也已被扩宽拉平。这样一来,村子的封闭感是没有了,但那种与此相伴生的祥和团圆感,也就一同消失了。
在故乡那个村子的东头和中部,分别生长着一棵老榆树和老槐树。它们跟那棵老柳树一样,也都是年深日久的老树精了。在这两棵老树底下,同样经常聚满了魏家和李家的乡亲们。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想,这三棵大树,也许是村中王、魏、李三姓的祖先们,在村庄的初创阶段,出于各自的喜好不同,而分别栽下的。久而久之,它们于不知不觉间,慢慢地成为了乡亲们关于故乡、关于家园、关于宗族的标志或者图腾,尽管他们未必能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
不用问我也知道,那棵老榆树和老槐树的结局,一定跟老柳树一样令人唏嘘。但是我不知道,当它们的寿命被终结的时候,又有多少人像爷爷和父亲一样,为之伤感或者牵挂。对于同自己朝夕相处的草草木木,人们往往会习惯性地视若无睹。爷爷和父亲在自己的孩提时代,跟那棵老柳树朝夕相处、尽情玩耍的时候,大约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要离它而去,并为之牵肠挂肚的。
故乡的美丽,也许在背井离乡之人的眼中,才会更加清晰生动。我也是在年过五十以后,才开始怀念起那棵给了我很多欢乐的老柳树,明白了自己喜欢去看柳的个中缘由。老魏家和老李家的人们,在离开了故土之后,大约也会跟榆树和槐树格外亲切的。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树木也一样。相同的树种,外观看上去似乎很相像,其实却有着各自不同的容貌和性格。异乡的柳树,我并不熟悉,它们也不会认识我。看到它们,虽然能引发我的一些联想,但却闻不到故园泥土的芬芳,感受不到家乡亲人的温情。当然了,也无法从中寻找到自己儿时的身影。所以,地处北方故乡的粗笨柳树,也许不如江南水乡的柳树那般潇洒秀丽,但是它们在我的心中,已经不再普通。
如今,故乡的那些美丽,大都渐次成为了我的梦境。亲爱的故乡,已然渐行渐远… …
壹点号谷荻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