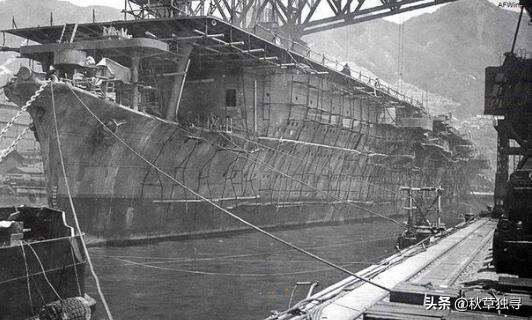杨升庵在云南有官职没(杨升庵的B面与历史的疼痛)
文:温星/2020-03-21云南日报·读书版

作者:聂作平
版本: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12月第一版
活跃于当代文坛的聂作平,当属最优秀的历史写作者之一。他以诗歌出道,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便进入历史领域,成为浸淫历史随笔或曰“大历史文化散文”的最早的中国作家之一。其代表作《历史的B面》《1644:帝国的疼痛》,我认为,皆能进入该领域最富有个人风格与代表性的作品行列。
《青山夕阳:大明文宗杨升庵》,应该是聂作平的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由杰出的历史随笔写作,而进入长篇历史小说,这是水到渠成,也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毕竟,在文学的各类体裁中,空间最大、也最考验作家闪展腾挪综合写作能力的,一定是长篇小说。而其中,最具难度的,又是历史题材长篇小说。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府新都县(今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但在自庄蹻开滇以来的云南的历史尤其文化发展史上,他绝对是一座里程碑。

嘉靖三年(1524年),名满天下的状元公杨升庵与时居首辅高位的父亲杨廷和一道,卷入“大礼议”事件,整个家族命运由此急转直下。他本人两次被廷杖,疾患终身,残命半条,被流放到蛮荒的不毛之地永昌卫(今云南保山地区),并直至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于此终老。后半生近三十年,可以说,杨升庵是“云南人”。
关于明史人物的文学及影视作品很热,作为明朝三大才子之首的杨升庵,却一直冷门。我想,大约是因为他的史料记载太少,写起来难度很大。长期以来,云南人谈历代文化必推崇杨升庵,却拿不出一部稍具影响的关于杨升庵的作品来,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从这个角度来说,云南人应该感谢聂作平。
这部《青山夕阳:大明文宗杨升庵》并非人物传记,而是基于极为有限的文献资料,在一个极具创新意义的架构之下,延展发挥创作而成的长篇历史小说。
相信读者们最先留意到的,便是结构。小说由甲编(他们说)、乙编(杨慎曰)、附编(作平记)三部分组成,以三类视角来铺开关于杨升庵的故事。其中,甲编(他们说)分量最重,占了30多万字篇幅的约3/4。这部分,又分别由七个讲述,依次为大太监王有根、滇中说书人柳麻子、杨升庵夫人黄峨、嘉靖皇帝、杨府管家杨敬修、内阁首辅杨廷和(即杨父)以及土匪头子丁黑牛。
七人身份迥异,与杨升庵的关系也迥然不同,以此顺序登场,感觉有些混乱?其实不然。比如,太监王有根率先“登场”,是因为他奉旨行刑时“放水”,才让杨升庵得以保命。廷杖的场景作为整部小说开篇,不但极为生动、紧张,更是抛出了一个关乎杨升庵及家族命运最大的悬念,让人不由立即就会去猜想:杨升庵究竟犯下何等大逆不道之罪,让嘉靖皇帝如此忌恨,非要在朝堂之上当众让他皮开肉绽?
这部分,小说以实权太监之口,对廷杖这一皇帝威慑和惩治朝臣的手段进行讲解,更是道出了大明宫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明规则、潜规则。
接着,聂作平自然不会直奔已成功营造起来的悬念的答案。第二位讲述者是永昌地区(即今保山)的说书人,因为,在高中状元已然名满天下却又遭受“屈辱之刑”后,杨升庵成为了明朝最大的“传说”,进入了许多民间艺人的作品中。
然后,则是杨夫人闪亮登场。这是一位能与杨升庵心灵相通的才女,他们的婚姻生活平淡而又多舛,甜蜜而又忧伤。杨升庵的满腹柔肠和一些爱欲小心思,得以呈现。虽已带残疾且始终在贬谪困苦之中,但他还是娶了两房妾,都是在今天的昆明安宁。所以,可以说,作为“新云南人”的杨升庵,同时也是“云南姑爷”。安宁,给了杨升庵平生中难得的一段安宁时光,这方面,小说中是可以有更多表现的。安宁市至今仍奉为其第一城市形象标签的“天下第一汤”,据传,便是杨升庵在一次惬意泡汤后所题。但于此,小说中并未提及,我以为,算一个小小的缺失。

昆明安宁,“天下第一汤”,据传,为杨升庵所题
铺垫至此,终于轮到嘉靖皇帝。“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率土之臣莫非王臣”的极权统治制度,“伴君如伴虎”的臣下残酷境遇,在嘉靖的喜怒无常中逐渐展开,杨氏父子失宠乃至蒙难的根源也清晰了起来。
原来,以兄终弟及的方式登上皇位的嘉靖,按祖制和礼法,应当追认死去的皇帝(其伯父)为父亲,而改称其生父为叔父。嘉靖坚决反对。面对坚持“礼”并带领群臣直谏的杨氏父子,嘉靖终怒不可遏。其实,嘉靖之所以能登大宝,杨升庵之父杨廷和功不可没。但君王秉性,怎可能念你旧情?
七位讲述者,其思维方式和视角皆存在极大差异,这也就使得他们所讲述的杨升庵呈现出了多张面孔、多种姿态、多样人生。但,这每一个不为他人所知的“B面”,显然都仅仅只是一个向度上的杨升庵。七者拼合起来,是否就能成为一个血肉丰满的杨升庵?
聂作平显然并不满足于此。于是,他在“分饰”七种角色、以七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讲述后,又将笔触直接探入了“本尊”杨升庵内心深处,这便是第二部分乙编(杨慎曰)。这部分,篇幅仅占全书1/5。
待正式登场之前,杨升庵的形象已然非常丰满,但颠沛人生的心路历程,非夫子自道不可。这里,植入了一条动人的感情线。杨升庵遭遇土匪,被苗族少女阿妮救入苗寨,彼此情愫暗生。但这段在小说而非传记里原本可以展开渲染的线索,处理得非常克制,杨升庵弥留之际仍为此抱憾。这种克制的处理方式,我认为是与杨升庵的性格相契合的,也兼而体现了聂作平严肃的创作态度。
对于打击报复、并放过许多特赦机会始终不愿宽宥自己的皇帝老儿,在贬谪的前半段岁月中,杨升庵一直心存希望,幻想着总有起复的那一天。在主角第一人称讲述的这部分,杨升庵的天真与率性、坚持真“礼”的迂腐与愚衷,也都得到了生动的表现。

对杨升庵又爱又恨的大明朝嘉靖皇帝
所有篇幅中,都不时穿插着杨升庵各个人生阶段及各种心境遭遇之下所创作的相关诗、词、文,其冠绝大明近三百年的文学造诣,在小说故事的推进和大明体制的剖析之中,不断闪现,绽放着耀眼的光芒。
当然,人最难做到的事情就是正确认识自己,此理古今皆然。从这个角度来说,杨升庵所讲述的自己,其实,极可能也只是历史真相中的一个侧面,仅此而已。我依然很乐意用聂作平代表作之一《历史的B面》所“发明”的“B面”这个概念,来看待这样一副形象的杨升庵。这些B面,其实都是大历史中的一些伤痕与疼痛,共同构成了某个真实的人物,也共同构成了某段真实的历史。
若整部作品就此戛然而止,无疑,已经是一部非常独特而又优秀的长篇历史小说。但别忘了,作品还有最后一部分:附编,即《作平记》。一定会有人不以为然:不就是一个后记?
聂作平追忆与杨升庵的奇妙缘分,其源头,与绝大多数人别无二致,都是那首被置于《三国演义》卷首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后来,聂作平结识杨升庵研究者郑先生,并在云南保山寻访到了杨升庵后裔。这段缘分,渐渐演变出了一丝“奇幻”的成分——当年,苗族少女阿妮亲手雕刻、并赠予杨升庵的那支充满情殇意味的木鱼,隔着近五百年的历史沧桑,竟遗赠到了聂作平手里,而且,冥冥中,似乎一直等的就是他。
显然,附编虽具有一定后记的意思,但究其本质,是这部小说有机的组成部分。我想说,它更是这部小说非常高明的一个“豹尾”,将作品的时空和精神指向拉到了当下,从而让作品具有了更为厚重和深邃的历史与人文价值。
最后,我想引聂作平的一句话,来作为本文结尾。
聂作平说:“当杨慎远贬滇南,并没有就此沉沦,而是以文化的力量、文学的力量,既支撑起了自己残破的人生,也为当时落后的云南进行了一次生机勃勃的输血,留下了关于云南的海量著作。”他表示,创作这部作品,其实,就是为了向杨升庵致敬。
详见2020-03-21云南日报·读书版,主编郑千山,略有删节
yndaily.yunnan/html/2020-03/21/content_1334851.htm?div=-1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