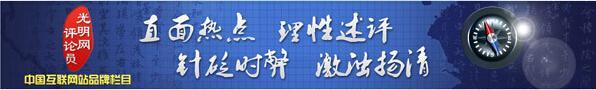浩然的读音和意思 浩然的读法

浩然代表作在近年的集中再版是当下文坛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1)这表明,自1978年的“浩然重评”现象至今,浩然的文学时代虽然已经结束,但他并没有真正离场。如何理解浩然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难题。而遗憾的是,研究者大多以浩然为材料印证自己预设的观念,结果一次次落入站队式研究的模式。浩然被抽象为一个文学符号,成为不同知识立场缠绕的扭结点。作为曾经被树立为文学样板的“一个作家”,他的遭遇实则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文学研究的普遍问题。
面对浩然现象,无论是程光炜提出的整合“新时期文学视角”和“七十年代视角”,“从七十年代再出发”的方案,(2)还是贺桂梅寻找的“在‘金光’或‘魅影’之外谈论浩然的方式”,(3)无不提醒我们走出狭隘的历史观,走出新启蒙范式设置的文明和愚昧的冲突,“地上”和“地下”的对立,在广阔的历史视野中理解浩然以及70年代文学。受此启发,笔者试图通过引入“阅读史”的理论与方法,规避在“文学”内部无法调和的矛盾,转而以“阅读浩然”这一历史现象和社会行为作为研究的切入口。
阅读史是西方近30年来新兴的研究方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其一是关心书籍的生产、流通以及最终到读者手中的方式;其二是将阅读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讨论阅读的方式和读者的心态;其三是分析阅读对于个体、社会和历史的影响”。(4)本文即试图以这些问题为导向,探讨浩然在70年代如何被阅读,以此勾勒支撑浩然作品广泛传播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体系,呈现70年代阅读史的复杂面向。
一、作为“地上文学”的浩然作品
1972年5月7日,叶圣陶在给叶至善的家书中写道:“昨夜浩然来,谈了一小时许。《金光大道》中旬可出,印数惊人。‘人文’和‘北京人民’两家共印一百万册。有十三个省、市、区订了纸型,每地以十万计,即为一百三十万册。”(5)由此可见,《金光大道》仅初版的印数即可达230万册,整个70年代,《艳阳天》《金光大道》均是一再重印,其最终的发行数量是今天的读者难以想象的。
笔者关心的是,这么大规模的图书如何能够在短时间内印制完成?这些书籍又如何到达全国的读者手中?这关系到对书籍制作、流通环节的考察,通常不在文学研究的视野内,却是阅读史研究所要回答的问题。相对于书籍的内容,阅读史研究更关注书籍的物质形态。它不仅涉及传统文献学的范畴,还意味着把书籍的制作和流通看成社会分工的结果,设想了一套涵盖作者、出版人、印刷人、运输方、书商、读者的传播线路系统。(6)目前对70年代文学的研究,不论是情感还是理论上,重心都在挖掘反叛性的“地下阅读”和潜在写作,而往往以简单的价值判断的方式处理“地上文学”。其实,对于理解70年代的书籍传播线路系统而言,具有历史合法性的“地上文学”反而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这一套体系如何运转,就隐藏在叶信“十三个省、市、区订了纸型”之说里。
通过《金光大道》初版本版权页可知,承担一版一印任务的印刷厂全部集中在北京。70年代的出版物种类不多,但政治学习材料以及类似的畅销文学作品印数极大,动辄以百万为计算单位。若只由北京供应全国,既不能适应需要,也会增加图书运输、发行的成本。这样,区域出版生产力与全国性的出版物需求以及图书发行的成本之间就出现了较大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供需矛盾,国务院出版口1972年8月专门下发文件,推行跨地区租型,分区协作印制的办法。叶圣陶所讲的,正是出版史上这一特殊现象。
《金光大道》第一部的印刷早于出版口的文件,或许带有试验的成分。不久后,分区协作印制的政策在正式文件中被落实下来。图书取自中央出版单位出版的全国需求量很大的部分图书,北京之外,另设上海、山东为印刷点,并将全国分为8个“协作印制区”,每个区推出一个省负责与中央出版单位联络,召集本区的印制计划。供型书目发出前,中央的出版单位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商定每种书的印数,再分配到其他印制区。文件要求分区协作印制的数量要除去北京发行所的分配数,即印制北京发行所供应不足的那一部分。(7)
为了标示“身份”,记录版本时,租型印制图书的版次按照原出版者的记载,记载原出版者和重印者的名称,如“1972年5月北京第1版/1972年7月山西第1次印刷”。这种版本的印刷时间并不统一,且略晚于一版一印本。据笔者查阅的版本,山西、四川完成于7月,辽宁、安徽在8月,河南在9月。《金光大道》第一部出版后,“各省出版社租型印刷都供不应求”,(8)想来各省读者接触的多是此类本子。中央供版、地方租型、协作印制,实质上是通过中央出版社让渡部分版权的方式,实现了国家行政权力对印刷生产力的调度。
印刷问题解决之后,接下来便要考虑如何把书籍从印刷厂运送到书店,进而送交到读者尤其是工农兵读者手上。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可以重新审视普通读者的阅读记录,这些隐藏在各类回忆性文章中的“边角料”,因为可以揭示接触书籍的情境,反而变成了具有研究价值的材料。
在笔者梳理相关材料时,两位边疆小读者格外引人注目。其中一位蒋晓华70年代生活在“新疆兵团农四师六十五团场最偏远的八连,图书这种资源十分匮乏,找书十分困难”。他在团部住校的姐姐每周六从学校图书室借阅小说带回家,周日下午带回去。他凭借这种方式,在小学和初中时期阅读了包括浩然作品在内的许多流行小说。(9)而另一位小读者潘小松少年时期“在闽北的一个前线小岛上随父亲过着军营生活”,小岛上有一家公社一级的新华书店,当时公开出售的只有《艳阳天》《金光大道》等为数不多的文学书籍,他因此对阅读浩然记忆深刻。(10)从北国边疆到前线小岛,从学校图书馆到公社书店,这种散点式的阅读个案并发,显然不是遵循西方世界“书商”的商业法则,而体现着一套依托于国家行政力量的发行体系在井然有序地运作。
在当代中国的书籍传播线路系统中,发行方新华书店始终是一个固定项。1958年,除保留极少的外文书店、古旧书店外,私营书店全部并入新华书店。为了扩大农村的发行网络,根据当时的文化部与供销合作总社1956年的联合指示,新华书店依靠基层供销社和部分零售点进行图书发行工作,最终形成了“以国营新华书店为主渠道,以供销社书刊门市部为支渠道”(11)的全国图书发行网络。“文革”期间,发行工作以工农兵读者为重点服务对象,工作重心由此向农村和边疆倾斜,并通过全国供销社合作售书点拓宽发行渠道。
鉴于我国幅员辽阔,当时的交通网络又远不如现在健全,即使出版口指示印刷分配数量适当照顾边远地区,但在一个“协作区”内部,如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以及跨度更大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图书发行难度依然很大。汽车需要一个星期才能把图书从乌鲁木齐运到南疆和田地区,边疆、沿海地区还有骆驼驮运、帆船运输的方式,西藏曲水县书店的两名工作人员则是轮流骑马下乡卖书。即使地处沙漠边缘的巴伦别立公社供销社,书店亦可以做到备有图书七八十种。(12)通过国家权力的毛细血管,“地上文学”得以渗透到最基层的读者手中。在此意义上,读者所面对的书籍,便不单纯是作为审美对象的文本,更是一套被建构起来的文化秩序。
除了书籍形态的传播之外,《艳阳天》《金光大道》等小说被改编为电影公开上映。根据浩然作品改编的连环画达百余种之多。《艳阳天》则被改编为评剧、话剧、京剧、黄梅戏、眉户剧、吕剧、锡剧等多种艺术形式。(13)浩然作品为其他艺术形式提供了底本,相应的改编也扩大了阅读行为的范畴。在诸多外溢的文本形式中,笔者拟对电台的小说连播略做梳理。
“小说连续广播”是中央广播电台的经典栏目,在当代文学作品的传播和经典化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节目在1966年后一度中断,1974年重新开播,1977年的节目时间表显示,栏目的播出时间固定在每天12:30—12:50。(14)据《建国以来全国电台〈小说连播〉节目录制重点书目汇总表》记录,《艳阳天》集数为100,制作台有中央台、天津台、鞍山台;《金光大道》集数为70,制作台有中央台、黑龙江台、鞍山台。这两部前面都用符号△标记,代表这是70年代受欢迎的节目。(15)
鞍山广播电台于1972年首先恢复了“评书连播”的录制生产和广播,录制者系艺术家杨田荣。不过,由于电台覆盖范围的影响,传播度最广的并非鞍山台,而是曹灿在中央广播电视台播讲的节目。曹灿的风格以朗诵加评述为主,声音条件优越,擅长对人物性格的创造和对外部环境声音的模仿,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收听《艳阳天》也是李敬泽对70年代的一个特殊记忆。“每一句中宣喻式的煞有介事的起始重音和暗示性的拖音,在庄重和引逗之间滑行。”曹灿的男中音给他留下了了深刻印象,以至于“至今翻出一页《艳阳天》,我仍能在内心按照曹灿的语调诵读,我认为,那就是浩然本人的声音,奇怪地混杂着造作与生动”。(16)
书面阅读以阅读者的意愿和能力为先决条件,但是没有人能够拒绝声音。彼时的乡村,“各个大队都有广播喇叭,家家户户都有小喇叭”,(17)农村广播网的建立和普及赋予“声音”以政治的意义。每当公共高音喇叭响起,不论听众意愿如何,都在客观上被纳入读者群中。这种方式也使得浩然及其作品在70年代家喻户晓,沉淀为无数普通人生命中的一段记忆。出身、年龄、地域、教育程度、文学趣味千差万别的普通读者共同组成了浩然作品的接受主体。因此,浩然作品是在一个时代的精神生活中留下刻痕的社会性文本,“在作家作品—批评家—文学史家这个圈子里打转,很少关注圈子之外普通读者的反应”的“内循环式研究”(18)显然不足以应对它所蕴含的问题。
二、“教材型”读法——如何组织与引导“阅读”
70年代书籍传播线路系统的政治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只是,在本质主义的判断之外,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如何引导阅读、个人读者如何接受当时的文学作品等问题,依然有待于学理性的讨论。《金光大道》出版、《艳阳天》《金光大道》被改编为电影在全国上映后,“阶级斗争教育的生动教材”(19)“农村基层干部的好榜样”(20)等类似字样直接被用作文章的标题。“教材”作为一个关键词,引导出阅读浩然时“教材型”读法的规范。
作为“政治教材”,传播浩然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当时基层政治思想工作的一部分。据报道,北京市亦庄管理区在1972年底开始启动讲革命故事的活动。他们选择《艳阳天》等十几部长篇小说和浩然的《新媳妇》等十几个短篇故事,“利用管理区广播站,每天占用半小时广播时间,向全管理区一万零一百多口人播讲革命故事”。(21)这种做法被《人民日报》树立为“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农村的思想文化阵地”的先进事迹。
在先进事迹的示范作用下,浩然作品的教育作用在公开的材料中被放大,小说中的人物事迹在基层治理中被转换为现实社员的行为规范。黄社章是湖南秦家坳生产队的图书管理员,针对队上弃农经商、搞副业单干、蚕食集体土地、损公利私等资本主义倾向,他向社员推荐《金光大道》《艳阳天》等图书,帮助基层党支部克服了这种不良倾向。(22)黑龙江某奶牛场大队里有个干部主张高价售出剩余的谷草,文艺评论骨干便给大家讲评萧长春拦车的故事,以此实现对干部的社会主义教育。(23)类似的阅读个案只有在文化工作向农村倾斜的时代,在将文学作品等同于现实生活指南的时代,才有可能以这种方式进入公众的视野。1972年前后,部分公共图书馆开始恢复活动,提供借阅或开架阅览。囿于当时的出版环境,可供公共图书馆采购选择的书目很少,于是只得加大每种图书的采购量,由此造成了购书品种稀少而复本极高的现象。因此,《艳阳天》《金光大道》在各级别图书馆都有极高的馆藏复本。据查,成都市图书馆、天津市河西区图书馆复本量均在100册以上。(24)即使是公社一级的图书馆,如苏家屯区陈相公社图书馆,复本也可达二十几册。(25)重新开放的图书馆构成了一个阅读文学作品的公共空间,大量的馆藏则保证了浩然作品的可得性。余华的文学阅读便是在这样一个小环境中展开:1973年海盐县图书馆重新开放,余华在父亲和哥哥的帮助下得到一张借书证,自称“把那个时代所有的作品几乎都读了一遍”,他所举篇目中,便包括了《艳阳天》和《金光大道》。(26)
公共图书馆除了供给书籍,还通过开展读者座谈会、作家交流会等形式组织、引导读者的阅读。当时的北京市延庆县文化馆(1974年恢复,1975年建县图书馆)曾陆续邀请包括浩然在内的文化名人为文艺爱好者讲课36次。(27)黄石市图书馆在70年代还为小说《艳阳天》《沸腾的群山》等举办了读者座谈会,为《冷月英》《鲁迅杂文》《金光大道》等组织了读书辅导活动,并有专题讲座等录音报告会。(28)长春市图书馆于1973年2月、1974年5月分别组织《金光大道》小说报告会和《艳阳天》小说报告会。(29)公共图书馆作为一条重要的阅读渠道,它们的活动为读者以“教材型”阅读浩然作品提供了外部环境。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试行以“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方式招收工农兵学员。借助于“政治教材”的合法性,浩然作品随着大学招生的恢复,进入到中文系的教学环节。“一个时期的文学经典的秩序,最终需要在文学教育和文学史撰写中加以体现和‘固化’,以实现其合法性,并在教育过程中普及和推广。”(30)随着文化精英群体在阅读趣味和人员构成上的工农兵化,浩然作品在大学课堂上的着陆,意味着完成了来自专业和权威的认定,而这是“经典”确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1974年春天,当时的文化部写作组到北京大学中文系,组织师生撰写评论《艳阳天》的文章。这件事落在由林志浩和洪子诚任教的1973级工农兵学员身上。一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和学生读作品,读资料,分组讨论多次,然后规定师生每人各交一份作业。最终,统稿后的论文有三分之一的篇幅被初澜采纳。(31)复旦大学中文系为组织“现代文学专题课”教学,选择以长篇小说《金光大道》《虹南作战史》《牛田洋》《江畔朝阳》作为教学内容。“教师先介绍社会上评论这四部小说的各种意见,并讲解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短篇小说创作的新特点,然后组织学生分头到工厂、农村、中学和文化馆进行调查,听取工农兵群众对这些作品的意见。”(32)作为教学成果,署名“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金光大道〉评析》一书于197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高校中文系的教学需要同时催生了第一本浩然研究专集的诞生。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资料室编辑的《浩然作品研究资料》一书,于1973年4月初版,次年修订再版。再版本分为“浩然简介”“浩然谈创作体会”“浩然作品评介选载”“附录”四个部分。虽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入选文章多带有时代风格,不过附录中的《浩然著作目录》《浩然作品评论资料索引》却颇具资料价值。《关于浩然作品中部分方言词的解释》一文由浩然好友杨啸解释作品中不易理解的北方方言词汇。
这也让我们意识到,浩然作品的文学性很大程度上来源其民间、民俗色彩,尤其是生动鲜活的北方农村语言。
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文化部写作组的认可、各种形式的改编、贴近真实生活的内容、基层组织的阅读、大学的文学课堂……促成文学作品“经典化”的诸多要素在浩然作品的接受中日渐齐备。只不过,这种由政治主导的文学评价并不稳定,随着新时期的到来,浩然的“定评”受到挑战,成为一个被“重评”的作家。
三、70年代文学的弹性空间——个体阅读行为一瞥
对于浩然的“定评”,表现了70年代主流的阅读规范。问题是,当阅读行为落实到个体的层面上,历史上的真实读者果真会亦步亦趋地追随这种规范吗?
阅读史理论认为:“历史环境变动不居,各色读者都有不同的规范和套路引导他们阅读,任何一个文本,没有任何意义是固定不变的。读者再造文本,从中抽绎出他们自己的意义,与作者、出版者的意图可能相差十万八千里。”(33)总体来看,80年代的“浩然重评”,问题在于将70年代对浩然的阅读窄化了。对于浩然政治化写作的批评意见以及以“图解政策”为旨归所做的文本分析,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出发点:将70年代设定为一个没有缝隙的“极权社会”,而从人性/人道主义/纯文学等概念出发,谈论读者所受到的压制。其视野的盲区恰恰是忽略了读者感受力的能动性,因先在的价值观念预设,而遮蔽了对历史上真实读者的阅读行为的考察。真实读者/历史读者指的是“真的接触过书籍,读过其中的文本,并且生成了自己对文本的阐释”的读者,以便于同“文本和副文本暗示的读者”,以及“作者和批评家想象的读者”区别开来。(34)对真实读者的关注,意味着重视读者的阅读自主性和历史性,由此探寻当时的读者究竟是如何阅读浩然作品的。
从这一角度进入阅读史的研究,首先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沉淀在中国人阅读记忆中的“地上文学”是《艳阳天》《金光大道》,而非集体写作的《虹南作战史》《牛田洋》等。1964年,《艳阳天》第一卷出版不久,孙犁便赞赏其是“有生活、有情节、有语言、有人物的作品”。(35)汪曾祺亦曾和浩然接洽,拟将《艳阳天》改编为京剧。(36)阿城也有过“赵树理和浩然都是会写的”(37)这种评价。这些今天备受推崇的作家在浩然作品中看到的文学性因素,同样也会被当时的读者看到。正因此,千差万别的个体阅读行为溢出了“教材型”读法的规范,呈现出阅读的多样性。相对于把70年代文学结构化为在大时代和个人之间建立一种剑拔弩张的关系,我更愿意关注二者之间犬牙交错的中间地带及其缝隙,以70年代文学的弹性空间来想象这样一种多样和柔性的文学状态,贴近已被学院语言抽象化的时代经验。
如此一来,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之外的阅读状态,同样可以被赋予文学史的意义。如叶圣陶父子对浩然作品的阅读。叶圣陶不仅对浩然有发现、培植之情,而且是浩然作品的忠实读者。在他的影响下,叶家成员大都读过《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其子叶至善彼时在黄湖干校劳动,“本来嫌它字数太多,不想看”,不成想随手翻看两节,觉得有意思,便从头看起。只用四天时间便看完了小说,并认为“这是目前的长篇中最好的一部,也是浩然的作品中最好的一部”的说法是公允的。对于叶氏父子来说,《金光大道》可谓是寂寞文坛的惊喜之作。不仅如此,他们谈论阅读的语言与主流文坛差异很大,为我们展示出在主流话语系统之外,历史上还真实存在着另外一种谈论浩然作品的方式。比如,他们在书信中臧否人物塑造上的得失:“《金光大道》我还没有看第二遍。近日想想,这部书写高家弟兄,弟弟比哥哥写得好。写一些富农,富裕中农和思想落后些的中农,似乎也比写贫下中农好。正面人物英雄人物难写,我看是有些规律性的。高大泉在书中,长篇说白多,有些空议论,有些重复,我对浩然说了。”(38)“弟不如兄”的判断很有“中间人物论”的味道,揭示了“三突出”创作方法在美学问题上的失效。
面对浩然作品,不少阅读者为语言、人物、情节所吸引,获得愉悦的审美体验。陈晓明回忆:“少年时代读《艳阳天》而有非常生动的感受。”(39)对于年龄相仿的青少年读者而言,无处不在的思想引导不免使人厌倦,阅读浩然有时便带有逃避现实的味道。李建中70年代中期在家乡小镇中学做语文教师,他记忆中的课堂总是一片混乱,按性别分为前后两大区域,女生在后男生在前。坐在后面的女生,或者织毛衣或者读《金光大道》之类的小说。(40)对于这些不谙世事的少男少女来讲,这一方小天地就是一片“阳光灿烂的日子”。对于这样一个以年龄为主要区隔方式的社会群体而言,浩然作品几乎是那个时代最具文学性的公开读本了。阅读浩然也成为赵勇“少年时代一段不折不扣的文学记忆”,“一套《艳阳天》颠来倒去读了许多遍,继而再读《金光大道》,又读《西沙儿女》,浩然似乎就打发了我少年的不少时光”。(41)
对于这些青少年而言,萧长春与焦淑红的爱情虽然描写得含蓄、克制,经过了阶级话语的层层包裹,但男女主人公之间千丝万缕的情愫还是可以透过纸面,让懵懂躁动的青春期少年为之心旌摇曳。如易光所说:“政治读者或许瞩意阶级斗争的风云变幻,鹿死谁手,更多的读者,则依了自己的兴趣,注目于家长里短,民情风习,尤以男女情事最为上心。”(42)在那个文学匮乏的年代,《艳阳天》支撑起了70年代青少年的爱情想象。李大龙和他的少年伙伴便为小说中“尤为美丽动人的女主人公”倾倒,“发誓今后非得找这样一位‘偶像’当老婆”。(43)在爱情启蒙的年纪,青年们总是能够在政治的缝隙中放置对异性的想象。
单独来看,以上所引材料不过是一些琐屑的阅读个案。然而,相似的阅读风格和阐释策略却让一个“阐释共同体”渐渐明晰。上述阅读记录大多基于“青少年视角”,阅读者多是50年代前后出生的一代人。彼时的他们有阅读的渴望,但是由于特定的时代氛围,所能接触的文学书籍很少。尤其是对于那些远离权力中心的普通少年来说,可接触的读物中,浩然作品便显得愈加珍贵,成为在生命中刻下印迹的书籍。如程光炜所说,这一代人“其实是从一个非常弱小和可怜的个人记忆的基础上,是从一个精神生活的低端上来‘重新’看待浩然的‘价值’的”。通行其中的诠释策略,是“我们那代人接近于零的一个低端的文学教育”。(44)
然而,恰恰是这种“低端的文学教育”,以及更广泛的70年代经验,构成了这一代人的“内面”。只不过,阅读浩然的行为在80年代之后一度被“遗忘”,取而代之的是对“地下文学”、西方思潮的阅读。借由2008年浩然去世的契机,个人经验中被尘封的“浩然”才逐渐被照亮。时至今日,这一代人已成为当代文学的创造者和书写者,他们身上的70年代质素如何被清理、转化、沉淀,不仅仅是一个代际群体的问题,同时也是如何理解70年代与80年代的历史联系的问题。
对于新时期作家而言,阅读浩然应当是他们文学起步阶段的必修课。何立伟于1975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他的文学训练便是“找来报纸学了划甚么主语谓语和宾语,或是一行行地读《金光大道》”。(45)劳马亦曾表示10岁阅读《铁道游击队》《艳阳天》《金光大道》《喜鹊登枝》等文学作品,“心中崇拜的作家仅浩然一人”。(46)如同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人之于80年代文学的意义一样,浩然在70年代也曾一度扮演着“作家中的作家”的角色。诸如路遥、曹文轩、莫言等从70年代进入新时期的作家,浩然以及70年代经历在他们的创作中具有起点性的意义。他们如何处理从“浩然”到“马尔克斯”的转换,断裂的两个时期有哪些一以贯之的文学质素,此类研究目前似乎还不够。
孙郁曾同笔者讲:“浩然是‘文革’文学里保留人性最浓的一个作家,‘左’的错误观念指导的写作下面,依然保留了人性中善和温暖的一面。他的文本的存在使我们不能一下子否定那个时代所有人的书写。面对生活,他能够坚持真善美的标准,有我们这个民族里面可贵的东西。过去我们觉得浩然简单,今天看来浩然是复杂的。”(47)这里不乏对作家的“同情之理解”,以及重新建立理解浩然的坐标系的趋向。对于浩然的认识从“简单”到“复杂”,使得今天的浩然形象的知识范式由此开始被撼动。
结语:“读书无禁区”
“到了一九七八年春夏之交,一个不寻常的现象发生了。门庭冷落的书店,一下子压倒美味食品和时式服装的店铺,成了最繁荣的市场。顾客的队伍从店内排到店外,排到家岔路口,又折入另一条街道。”(48)李洪林在《读书无禁区》一文中描绘了70年代末“文艺复兴”时节,民众渴求阅读的社会现象。阅读的民主权利诉求,呼应了时代的改革气息和“拨乱反正”的实践。从“一个作家”到“读书无禁区”,社会土壤的更新、文学观念的变革,松动了使浩然作品畅销全国的机制。对于阅读的记忆,也在这样一种历史转型中被后来人重述。
以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为代表,围绕着“地下文学”,一批精英知识分子群体的阅读生活占据了主流的视野。不可否认,地火涌动的反叛阅读、持灯先行的文化英雄是一种值得敬重的历史事实。但我们也要意识到,这种由新时期的启蒙论创造的阅读神话,将70年代笼罩在意识形态的魅影之中,有可能使我们陷入以历史叙述覆盖历史事实的境地。如此一来,仿佛阅读皮书、手抄本便是时代的先觉者,阅读“地上文学”则变成一件令人羞愧的事情,与此相关的阅读记忆便受到有意压制。这就有可能造成对历史的新的遮蔽。读书无禁区,阅读行为本身并不存在高下之分的等级序列。无论是“地下”还是“地上”,都是一个时代国人精神生活的记录,也都应该平等地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和文献资料。
“怎样找到一个理论框架把这些发现加以整合性的总结”(49)是进行微观阅读史研究的棘手之处。本文立意在这个层面上对浩然的“读法”进行一次研究尝试,同时亦感到存在呈现大于研究的问题。如此处理材料,目的是希望通过阅读史的钩沉寻找一种从70年代再出发的可能。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钩沉差异性的个体阅读,并没有超历史地拔高浩然作品文学性的意图。如果我们将真实读者的阅读行为与当时推行的阅读规范理解为二元对立的紧张关系,用文学性推翻政治性,看似完成了对浩然的“解放”,实际上只是又一次陷入逻辑陷阱。因此,我更愿意将它们当作70年代的内部视角,当作手抄本或是“地下阅读”之外的维度,以此重新进入被意识形态判断简单化了的70年代文学和历史。
文/邵部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