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话怎么讲(百年前的厦门话和现在不一样)

建筑高度的背后,往往代表的是一座城市的发展速度。在建设者们的打造下,厦门朝着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的目标一路高歌猛进。与此同时,厦门话的生存空间似乎正遭受着挤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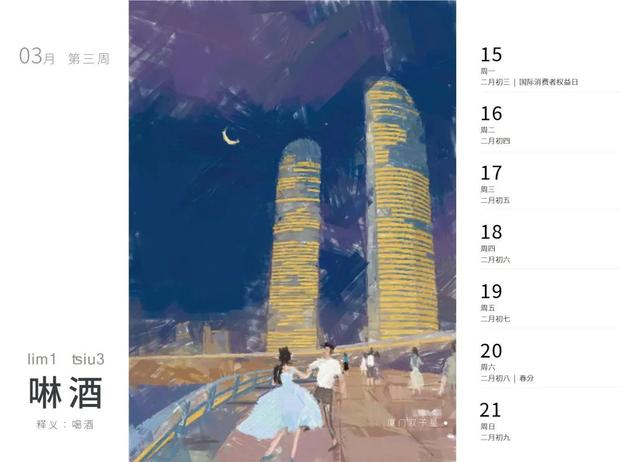
©说咱闽南话2021周历
厦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从唐代开始,厦门岛就隶属于泉州府同安县管辖,唐宋称嘉禾屿,明代称中左所,清代称厦门。从人烟稀少的小渔村到如今灯火璀璨的繁华之都,厦门翻天覆地的变化始于厦门港的兴起。

一个港口的没落,通常伴随的是另一个港口的兴起。因明末清初实行迁界禁海,漳州月港逐渐没落。1684年,清政府在厦门设立海关,厦门港正式取代了漳州月港的海外贸易地位。1842年,厦门被迫开埠通商,逐渐成为闽南地区对外的门户。

清代厦门港位置图 ©《地道风物·闽南》
鸦片战争结束后,1902年《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章程》签订,鼓浪屿被辟为“万国租界”,西方人陆续在岛上修建教会学校、医院、教堂、书局和领事馆等。这个草木葱郁、幽静隐逸的岛屿也吸引了不少泉州、漳州早期下南洋打拼的华侨华人,他们在岛上斥巨资造了一座又一座别墅,在骑楼街上开了数万家店面。
随着厦门经济的发展,泉、漳两地居民持续涌入,他们共同开发建设厦门,几乎是倾全闽南之人力、财富,合力打造了这座港市。他们带来的漳州腔、泉州腔的闽南语在这里杂糅出了一种“半漳半泉”的闽南语——厦门话。

在此时期,西方传教士陆续进入南洋群岛和闽南地区、台湾地区,他们在马六甲首先遇上语言沟通的障碍。在闽南人移民海外的浪潮下,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很早就形成了闽南人的聚居地,闽南语也成了当地的通行语言。传教士们意识到,在他们学会使用方言之前,口头传教很难在闽南地区广泛开展。为了让传教士更快地学会闽南语,1815年,美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英华书院研究拟定了一套厦门话罗马字方案并完成编写《罗马化会话手册》,这是厦门话教会罗马字(即闽南语白话字)的起源。

马六甲英华学院 ©网络
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来到闽南地区最早到达的地区便是厦门。当地绝大部分人不能流利使用普通话,多使用闽南方言,甚至不识字。为克服语言障碍在闽南地区传教,传教士们在鼓浪屿创制并推广了记录方言的厦门话教会罗马字(如鼓浪屿“Kulangsu”、厦门“Amoy”),帮助当地人拼音识字。据《厦门宗教》记载,“白话字”创设于1851年,创设者为美国三位牧师,打马字、罗帝、宾为霖,他们共同编集简明易懂的《白话字典》(即为《厦门音个字典》,1894年出版)。
20世纪30年代,中国开展大众语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1936年,厦门成立“闽南新文字协会”,开办新文字夜校,掀起学习白话字热潮。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因教育的普及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推行,它的传播范围日渐缩小而式微。

在西方传教士来厦传教期间,先后编印了多种与厦门话相关的方言字典、学习手册等书籍,其中在19世纪下半叶影响最大的有1853年出版的《翻译英华厦腔语汇》(简称《语汇》),1871年出版的《英华口才集》(简称《口才集》)及1873年出版的《厦英大辞典》(简称《辞典》)。除了西方传教士编著的厦门话工具书外,厦门人自己也写作出版了多部字典。如1892年, 在厦门出版的卢戆章所著《一目了然初阶》(简称《初阶》);1894年出版的以厦门音为主、混合漳泉腔的闽南语音韵学书籍《八音定诀》(简称《八音》);1930年出版的研究现代闽语厦门话的奠基之作《厦门音系》(简称《音系》)。

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网络
对比现在的厦门音,从这些书籍资料中可窥见百年来厦门话语音系统和词汇的演变。整体上,150多年前厦门话的音系与现今并无太大差别。
从声母系统上看,变化只在于柳、入二母混同,即浊声母“dz(j)”混入了”l”,例如“日”字,[jit]变为了[lit]。这与如今的泉州话(除永春、惠安、安溪等部分地区外)一致,漳州话则柳、入有别,因此厦门话柳、入混同很可能是受到泉州话的影响。

声调对比表 ©徐睿渊
从韵母系统上看,最明显的变化在于“参”韵的消失。在西方传教士编著的词典中,人参等参类药物中的“参”字均读为[som]。而现代厦门话中,“参(om)” 韵已混入“公(ɔŋ)”韵。漳州话的“参”韵至今仍读为[om],泉州话则读为[əm]。

声母对比表 ©徐睿渊
从声调系统上看,厦门话的声调系统百年来没有发生音类上的变化。

声调对比表 ©徐睿渊
百余年前的厦门话与现今相比,在词汇方面差异最大。一方面,保留了一些原有的词汇。另一方面,有一部分词汇发生了变化,有的词语退出日常使用范围,成为历史;有的词汇经过精简合并,原有说法或消失、或已淡忘;有的词汇义项或增或减……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旧制度的消亡与旧事物的消失,有些词汇退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清政府的推翻和封建制度的废除,使得一大批官吏职位(如衙门中勘查偷盗事件的走卒“马快[be3 khoai5]”)、称谓(如尊称文人或师爷“相公[sĩũ5 kaŋ1]”)和服饰相关词(如官员上朝时所带礼帽“朝帽[tiau2 bo6]”)等退出口语。
厦门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也导致了一系列词汇的增减。厦门过往以渔、农业为主要产业,1981年厦门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厦门经济特区,从小渔村一跃发展为海峡西岸重要的现代化港口城市。农业和渔业几乎退出了厦门人的生活,与之相关的词汇(如缉[ʦʰip7],指的是一种竹篾箍边的渔网)也逐渐不再使用,相应地,现代港口行业及商贸相关词汇逐渐丰富,但还是有些旧词(银分[gun2 hun1],指分量和质量不同的货币之间的价值差别)随着时代发展而消失。

1981年厦门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厦门经济特区 ©网络
二是教育的普及使得人们认知深化、观念改变。一百多年前的厦门还处于封建迷信社会,盛行鬼神之说,认为打雷闪电是神的行为,与之相关的词是“电母”“雷公电母”,对于天灾人祸也同样归结于鬼神之说或命运使然。由于厦门靠海,经常有人溺水而亡,当时的人们认为这是水鬼为了轮回而抓人替代自己,即“水鬼叫交替”。旧时厦门人还认为血是不祥之兆,与血相关的病症都要有所避讳,称“血”为“红”,例如“咳红(咳血)”“放红(便血)”等。随着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观念也发生改变,与鬼神相关的词几乎都退出了口语,对一些忌讳也不再回避,但还是有一些老一辈人会使用。
三是厦门话与外来方言或语言接触引起的词汇变化。在《厦英大辞典》里,可以发现一些与福州话和广东话相通的词条。与广东话相通的词语如“浮泛[hɔ2 hoan5]”,意指没有根据的话,流言。与福州话相通的词语如“顶四府”,指建宁府、延平府、汀州府、邵武府等地;“下南侬”,指厦漳泉等闽南人;“下四府”,指厦门周边的泉州、漳州等地。这些词到今时几近丢失,或因概念难以被认同而消失,或为普通话词或方言固有词替代而消失。

1905年英国人拍摄的厦门港 ©网络
由于海外贸易往来的频繁,厦门话中因此增加了一些外来词,如“吕宋(菲律宾)”“高丽(朝鲜)”“暹罗(泰国)”等外国地名,“大必(David)”“达摩(Dharma)”等人名,“槟榔(来自马来语betel)”“芭蕾(来自西班牙语)”“禀针(别针,来自英文pin)”等物品名,还有吨、磅等度量单位。这些外来词保留到现在的并不多,特别是地名,但还是有些日常用品的名称保留在口语里,比如“禀针”“雪文”等。
四是不同时期语言政策及语言环境的影响。1956年,我国政府正式落实推普政策。1958年周总理在全国政协委员会报告会上提出了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一方面,厦门市响应号召,全市上下争先恐后地学习普通话,厦门话虽“声势渐弱”,但在日常中仍使用闽南语交流。1986年我国再次把推普列入当时语言文字工作的第一要务,并将“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定为推普工作方针。改革开放后,厦门对外经济交流频繁,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再加上广播、电视等各种媒体的普及,工作、生活中需要使用普通话交流的场合越来越多。在这种语言环境下,学习普通话成为自觉行为,厦门话在这段时期发生了较大变化,常用词语的词汇量有所缩减。

改革开放初期厦门随处可见推普标语 ©厦门手绘地图

透过百年来厦门语音系统和方言词汇的演变,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厦门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反过来,正是社会的变迁对厦门方言词汇的变化产生了影响。
如今,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闽南语的影响力和使用范围大不如前,还面临着因老一辈人的老龄化而消逝的困境。年轻人对闽南语越来越陌生,对方言词汇的知晓、应用能力也在衰退。能流利使用闽南语交流的人愈来愈少了。试想一下,如果有一天,闽南人都不再说起闽南语,那家乡还会是我们熟悉的家乡吗?
参考文献
[1]罗攀. 中西文化碰撞的意外收获——厦门话教会罗马字的创制、传播及其对闽南社会的影响[J]. 海交史研究, 2008, 000(002):115-126,44.
[2]王朝晖, 余军. 闽南都市社会的语言文化生态调查——以厦门为个案[J]. 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 2012(11):45-46.
[3]《中国新闻周刊》杂志社. 乡音无改 方言保护与传承[J]. 中国新闻周刊. 2020,(954): 14-25.
[4]李如龙, 徐睿渊. 厦门方言词汇一百多年来的变化——对三本教会厦门话语料的考察[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01):86-93.
*本内容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本平台立场。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