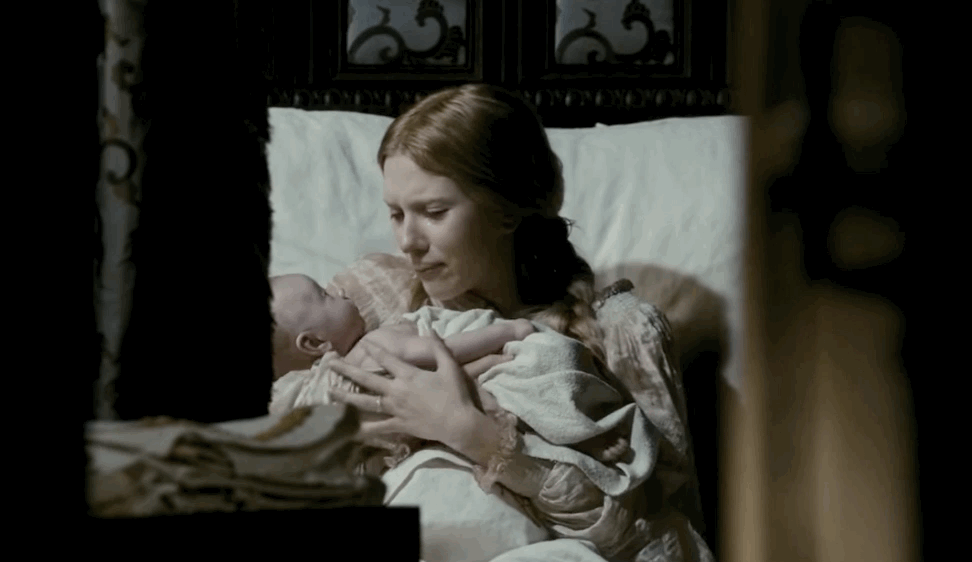苏东坡与苏小妹佛印的故事(琢玉郎与点酥娘)
文/老徐

在苏东坡的朋友里,我最喜欢王定国。
作为反对变法的保守派,苏东坡看似一直被攻击、被打击、被贬官,可是,作为北宋文坛盟主,他身边的好朋友一个比一个有名。
苏门六学士就不必说了,富弼、张方平、吕公著、范镇,都是做过卿相的人物,文与可、米芾、陈季常都是艺术上的大家,参寥、惠勤、佛印、大通,都是名重一时的高僧。可是,苏东坡觉得最对不起的一个人,就是王定国。
定国是他的字,他的名叫巩。他的爷爷是名相王旦,父亲也当过工部尚书。这个人的先天条件好得不得了,既出身世家大族三槐王氏,又是名门之后、卿相之子。
不用说他也喜诗善画工书,所以才能跟苏轼兄弟都结为好友。
苏轼之所以觉得最对不起他,起因在乌台诗案。他自己被抓进大牢不算,好多朋友也受牵连入狱,王定国就是其中之一。
最让苏轼过意不去的,是结案之后,他被贬到了黄州,而王定国居然被贬到了岭南。
而王定国之所以被贬官,完全是因为跟他来往过密,御史舒亶弹劾王定国的奏章是这样写的:“(苏轼)与王巩往还,漏泄禁中语,阴同货赂,密与宴游。”所谓泄密和受贿,并无真凭实据,但“密与宴游”,确有其事。
苏轼知徐州时,因抗洪抢险成功,于九月九日重阳节在黄楼举行庆功宴会,遍邀各界名流到徐州黄楼聚会,王定国就是特邀嘉宾。苏轼怕其不来,又写了《次韵答王定国》诗以寄之,嘱其“愿君不废重九约”。
重阳节,王巩如约而至徐州,游山玩水,吹笛饮酒。苏轼对他道:“李太白死,世无此乐三百年矣!”两个人饮酒赋诗,王定国滞留达十日之久。归去时苏轼又写了《九日次韵王巩》一诗:
我醉欲眠君罢休,已教従事到青州。 鬓霜饶我三千丈,诗律输君一百筹。
闻道郎君闭东阁,且容老子上南楼。 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
挽留之意深情款款,可见二人感情之深。
但是,乌台诗案落幕之后,王定国被贬往岭南的宾州,比苏轼贬得更远,受罚更重。相当于现在的主犯判了三年,一个从犯却判了七年。苏轼为此,很长时间内不敢写信给王定国,担心王定国会埋怨他。
而事实上,王定国对此毫无怨言。他在广西修身养性,访古问道,作画吟诗,还一本正经地做起了学问,注疏论语达十卷之多。而且,他在此间所写的诗词,也并没有什么乖怨之气,寄给苏轼后,苏轼叹为“皆清平丰融,蔼然有治世之音,其言志与得道行者无异”。
这就是真的名士风采了: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更厉害的是,他身边的人也受到他的感染,能够做到宠辱不惊,随遇而安。
他前往宾州的时候,家中诸妓只有一个叫宇文柔奴的,自愿追随他前往蛮荒之地。他们在宾州三年,柔奴居然还给定国生了个儿子,名叫王皋。王皋后来成为南宋的中兴之臣,两次拥立宋高宗,官至太傅。

有了柔奴的红袖添香,王定国才在岭南安居无恙;反过来,因为王定国的名士风度,也让柔奴一介弱女变得强大起来。
事实上,王巩在烟瘴之地生活得并不好,他“一子死于谪所,一子死于家”,自己也差点染上瘴气死在异乡,人生陷入了最低谷。
正因为柔奴的陪伴与照顾,才让他渐渐走出沮丧悲愤情绪,身体也渐渐康复。性格越发旷达。
处于困境中的他了解到苏轼的心情,多次写信劝慰其不必因为连累到自己而愧疚,因为自己因祸得福,终于有时间“更刻苦读诸经”和创作,顺便苦修道家的长生之术。
王定国被放归的时候,苏轼设宴招待,发现虽遭此一贬,王巩却非但没有自己想象中那样仓皇落魄的样子,还神色焕发更胜当年,就连柔奴也面色红润,气定神闲。
苏轼忍不住问柔奴:“岭南风物应是不好?”不料柔奴微微一笑:“此心安处是吾乡。”
一位歌女即能通达至此,王定国之胸襟风采,可想而知。苏轼大为叹服,提笔写下一首《定风波》:
“谁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