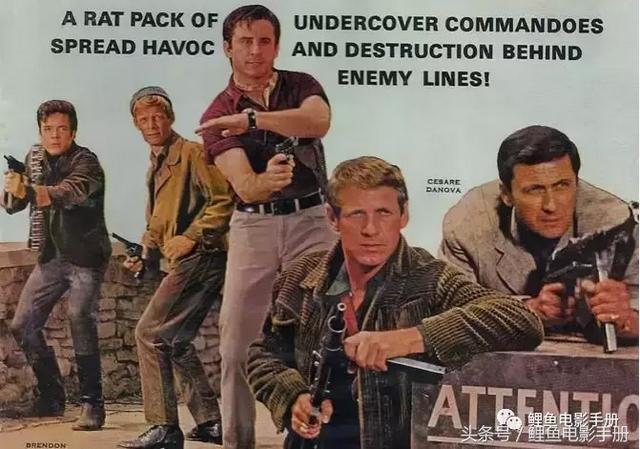马场工作者的生活(我在马场村的四十天)

马场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座落于湟中区上五镇西北部的一个山沟沟里。沟东西狭长,蜿蜒曲折,时而山重水复,时而柳暗花明。连绵数十里,山大沟深,绿水青山。沟底的硬化路和潺潺流水,如一对情侣,相互依偎,形影不离,曲折婉转地流向远方,通向外界。要不是偶尔几声羔咩犊哞,犬吠鸡鸣声外,这里寂静得无法形容,仿佛与世隔绝似的。
村庄不大,近三十户人家,大多数是回族。汉族人家不多,完完整整的不到八户(其中就有两户光棍汉)。
这里的人民勤劳、朴实,民族团结,一家有事众人帮,回汉兄弟如一家。
前几年,适逢新农村建设,村庄统一规划,统一修建,墙体美化,庭院整洁,布局合理有序。尤以村文化活动中心,幼儿园,医疗室,清真寺皆在村中心位置,粉刷装饰一新,非常漂亮。不大的广场边缘各种健身体材一应俱全,四、五位回、汉老者在凉亭下悠闲地喧着浪板(聊天)。
“绿树村边合,青山廓外斜”。整个村庄被掩映在青山绿水之中,恰似世外桃源。
马场,顾名思义就是养马圈马的地方。这里群山环绕,水草丰美,确实是天然的马厩。据老人们的咸水巴巴(不完整的述说):远古不祥,就解放前而言,这里曾是青海军阀马步芳的军马场。居住在这里的回、汉村民的先辈们大都是为躲僻战乱而流落至此的。
今年5至6月份,我有幸承揽了这个村子的人饮维修工程,热情的杨村长即使为我们施工队一行7人借给了村里闲置的一座小院。院内混凝土地坪干净整洁,可供盛放器材,三间板儿房,白墙面砖,窗明几净,里面水电设施齐全,非常干散漂亮。出门打工之人如能住上这样的房子,舒坦得简直没法说。
杨村长是个回族小伙子,三十出头,衣着朴素,与人为善,忠厚、踏实、勤快。闲谈中得知跟我儿子同岁,他有时称我阿爸(叔叔),有时叫我李师,不过叫啥我都不介意。在工作上跟我们施工队很配合,不论遇到什么难题或者搅沫沫的事情,只要一打电话,他第一时间就到现场,妥善解决处理。
在工作上他非常认真,仔细。那怕是一个极小的接头,螺丝的松紧,水阀的按装,沟槽的深浅……逐个检查,分毫不能误差,床痹大意。另外还选了两位村民代表,做为我们的监工,以防我们在施工中偷工减料。
他家养着三百多只羊,顺着这条沟往里约五公里有个叫陈家滩的地方,是他们的牧场,平时多由妻子住帐篷放牧操心。他把主要精力化在村里的公益事业上,一般尕大的事情多由他出面调解,在群众中评价威信极高。
村支书是由一个四十过不大法(四十出头)的汉族小伙担任,姓山,人称山书记。官大一品,说话特别傲慢,目中无人,辄眉辄脸(看不起人)的,接触了一两次,我就跟他冲掉缘了。据说他外出招赘多年,户口尚未迁出,一般村里没有啥重要事情多在岳父家居住。
畜牧业是这个村的支柱产业,是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大多数村民家都养着牛羊,有山里散养的,也有育肥圈养的,像杨村长这样的养殖户这个村比比皆是。说起他们的年收入,张口动辄就是数十万,令人咋舌,羡慕不已。
他们的草山是粗放式经营,没有按片区划分给农户,任由他们随意放牧。一般夏秋两季在山里啃吃青草,冬春两季在家暖棚里饲喂育肥。
农业章法(情况)不大,做做样子而已,虽然在整村推进项目中全部坡改梯,但不知啥原因尽皆荒废,唯有在低洼平缓处零星种植着几块青稞,燕麦,小油菜,且杂草丛生。
村里有位姓山的汉族老人,今年七十八岁,属猴的,长一脸落腮胡子,走路瘸三拐四的,是这个村子里回、汉男性中年岁最长的一位。老两口独门独院,相依为命,相互厮守,从他酸涩的表情显露出老人的无奈。同行的杨村长娓娓而言:
“这老汉共有六个子女,两个女儿均已出嫁,四个儿子因地区条件约束,娶不上媳妇,先后外出招赘,现皆有妻室。唉!谁叫娘老子把我们生在这个鬼地方。”
我深为老汉的孤独而同情,也为杨村长的一席话有所深思。这里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户均几百只羊,上百头牦牛,张口就是几十万,上百万的财产,比上我们下半川的人强的多啊!还装穷卖穷啥着哩?
给我们做饭的大师傅(厨师)是本村人,小我一岁,已是五十开外的人了,非常勤瑾、麻利。她是家里的主妇,平时掌柜子和儿子在山里轮换放牧着一百多头牦牛,她在家里主要照顾着七岁孙女,为其做饭,上学接送等。
谈起她的儿媳妇,她又是满脸酸涩,情不自禁地长叹一声:
“唉!说啥哩?阿妈养着不好呗,怪就怪我们这个地方。”
原来,早在前十年,她们张罗着从湟中李家山给儿子说了一门亲事,年底明媒正娶过来,婚后生有一女,凑合着过了三年,就跟上人着跑了。 大前年,她和掌柜子合计着买掉了四十余头牦牛,化了近二十万,从门源又说了一门亲事。双方都是二婚,女方的孩子暂由其娘家人抚养,约定男方每年给予其岳父五千元的抚养费,不准食言,这些条件尽皆一一答应。
“将将凑凑地又过了三年,从今年开始脾气耍着又不成了。三年来,我们视如己出,比亲闺女还当人,啥活都不让她干,衣服脏了我给她洗,饭做好了我叫他起来吃,浑天地黑地躺在炕上耍手机。前一个月猛乍乍地回娘家去了,说是要离婚,不给我们当媳妇了。”大师傅述说着,泪水早已湿润了眼眶。
“猴儿没到拔蒜处,水没到紧处。大不了豁出我的这条老命,我要把她们一家子收拾掉也划算”。谈论间,不知大师傅的掌柜子老刘啥时候站在外间铁青着脸说。
大伙连忙起身,给他让座、倒水、递烟,并开导、安慰了一番。
一天后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雹雨来不及往寝舍里跑,我们两三个人索性就近站在一家大门檐下避雨,哈巴狗的惊叫声早惊动了这家主人,热情好客的主人把我们让进屋里,又倒茶地又递烟,说出门人不要客气,甭假了多吃一点。
这是一座典型的农家小院,主房五间,全是砖混结构,全玻璃封闭,屋内装饰非常漂亮,高档家具、家电一应俱全,窗明几净,干净亮丽。透过门窗,院子里绿油油的,各种蔬菜,花卉竟相生长、绽放。一看便知这是勤俭人家。
主人姓张,独户,祖籍湟中页沟的,是解放前从爷爷的头上到这里落户的。老两口观面相都大我几岁,一家三口,养着一百多只羊,两头母牛,儿子三十多岁了,尚未婚配。
“这么好的家庭条件,尽快给儿子找个媳妇呗!”我同情地说。
“谁家的姑娘愿意嫁到我们这个山沟沟里?唉!没办法,照就(天可奈何)听天由命吧!”站在一旁的女主人一边给我们添茶,一边无精打采地说。
“要不,到城镇上买套房子,让儿子在外面见见世面,在社会上闯荡一下,总比窝在家里放一辈子羊会有出息的,说不定还能谈上个对象哩”。
“唉!之前,我们也有这个想法,不过娃娃东门未出,西门未进,连自己的名字写不来,躲过这里,到城市上咋过哩。”主人夫妇的一席话,又一次震憾了我哪颗善良而又束手无策的心。
离我们住地斜对面的一个深巷道里,住着一对年轻回族夫妇,有三个孩子,老大老二分别为一女一男,非常聪明可爱;老三是个女孩,已经五岁了,不会说话,走路颠三到四的,脚手不相连,是个重度残疾,小小年纪孽障拉拉的。据说是其母亲癫痫病发作时从怀中摔在地上伤了大脑导致的。
这对夫妇一家五口住着不大的三间砖混毛坯房,屋里的摆设极其简单。两头黑白花母牛和两头刚产下不久的牛犊子是家里唯一的主要财产。年轻的回族阿娘每天晚饭后提着个灌满牛奶的饮料瓶子(大约三斤),来到我们的住处求我们非买不可,一瓶子十元,处于怜悯,大家愿意为其消费。
从她的口中得知,她今年二十六岁,娘家在兴海县,从十六岁嫁到这里快十个年头了。十年来,从未回过娘家一次。因为患有癫痫病,掌柜子(丈夫)从不让她出远门,街上(乡政府驻地)总共去过两次。
她还说她家的两头母牛一天最少能挤三十多斤牛奶,村里的干部把浪山(旅游)的人甭禁止的话一天就能卖完,现在正是青草头上,挤下的牛奶吃不完,没处去给(哈)白白倒掉着哩。
是啊,我们是五月十六号进驻该村的,初夏的马场沟到处是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独特的自然风光吸引了西宁等地的游客,人们慕名而来,游客络绎不绝,踏青赏景,观光旅游。使原本寂静的穷乡僻壤活跃了几天,有了几分生机。
可没上两天,不知啥原因沟口上下了顶帐篷,设了卡子,挂着禁上浪山的横幅,由村里的村民轮流值勤守护。
一次闲聊中我向杨村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逗到:
“唉!我说杨村长,你们村口永久性横幅标语上写着振兴乡村经济,建设美丽乡村,那你们为啥守着金山银山受穷,甭说其它,就连二斤牛奶都卖不出去,你们怎么振兴?怎么建设?”
“你看我们既要青山绿水,又要金山银山,在优先保护生态的前提下,能否效仿邻近的乡趣卡阳,尼麻隆花海,包勒村渡假村等,依靠你们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发展生态旅游,如果搞起来,我看比他们都强。”
“唉!说啥哩?李师,说句心里话,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再说人一多,生态环境受影响,上面也不答应。”
杨村的话也有一定道理,但我认为,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像马场村,要想富,必须筑巢引凤,大力发展乡村生态旅游,如果不改变观念,不造血,不输血,愚昧地仍然坚持“闭关锁国”,这样的话穷根难拨,穷窝难移,始终根治不了贫困,群众的思想境界始终走不出大山深处。
李德玉
2021年9月4日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