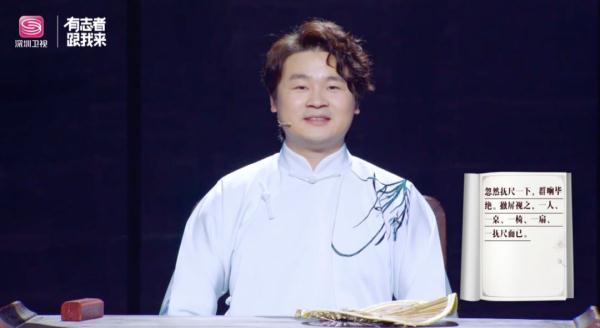阿基考里斯马基采访(你喜欢阿基考里斯马基吗)
(值此北京国际电影节之际,以此文献给爱看电影的你。)
你也不出来看看,这世上的戏都唱到哪一出了?
——段小楼(《霸王别姬(1993)》
1
上大学的时候,学校的一些社团经常会拿投影仪找个自习室播放一些免费电影。这些电影大多是从网上下载的,电影开头时屏幕上方总会出现一行滚动字幕:“请自觉在下载后24小时内删除,如果你喜欢本片,请购买正版”。
我和她就是在观看同一场免费电影时认识的。那天播放的是《这个杀手不太冷》。当影片演到小姑娘玛蒂尔德一家惨遭灭门时,她赶在那个邻家老太太之前念出了那句:What’s happening out there。她模仿得惟妙惟肖,引来了周围同学的侧头观望——这其中就包括坐在她前面的我。我笑着看了她一眼,她害羞地低下头,下意识地拿手捋了捋自己的留海。
电影放完后,通常还有电影学的研究生上台解读一番。那天负责讲解的是一个头发稀少油光满面的男人,他一上来就开始讲厄勒克特拉情结,我觉得很无聊就提前走了。走出教室后才发现她也提前出来了。我忘了是谁先搭讪的,总之我们之间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你部电影你都看过了,为什么还要再看一遍?”
“第一遍看的是情节,第二遍重点就放到表演上了。让·雷诺、娜塔莉·波特曼、加里·奥德曼都是很出色的演员。”
她一口气蹦出三个外国名字,让我觉得她很厉害。我们互留了电话号码,后来便经常相约一起去看免费电影,一来二去,我们就成了恋人。
2
这段时间的相处让我发现她是一个疯狂的电影爱好者,为了不在她面前显得那么浅薄,我开始拼命看电影和影评。跟校园里的其他恋人一样,我们经常一起去食堂吃饭。不一样的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几乎只聊电影。
我们每次在食堂楼底下见面说的第一句话都像是地下党员在交接暗号——
“罗伯特·雷德福长得实在太帅了。”
“伊莲娜·雅各布现在是我的女神。”
“你知道吗?芬兰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导演叫阿基·考里斯马基……”
“胡里奥·密谭的《北极圈恋人》你一定得看看,拍得太美了!”
……
那时候我有一种近乎变态的虚荣心,总是试图在她面前表现得技高一筹。比如当她说德国导演里她最喜欢文德斯时,我就会说赫尔佐格的电影也不错(因为我猜她没听说过这个德国导演);她说她爱上塔可夫斯基了,我就说相比而言安哲罗普洛斯的形式感更强;她说她看了一部非常极端的电影,整个电影只有一个长镜头,索科洛夫的《俄罗斯方舟》,我笑了笑说,那不算极端,德里克·贾曼的《蓝》,整部电影只有一片蓝色;她说伯格曼、费里尼、安东尼奥尼,我一定要说英格玛·伯格曼、费德里科·费里尼、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
有时我们还会拎几瓶啤酒去没人的自习室或草地上玩跟电影有关的游戏。比如我问:“日本四个字的导演有哪些?”我们就开始“寺山修司”“木下惠介”“冈本喜八”“小林正树”“是枝裕和”“沟口健二”……你一句我一句如数家珍般地说出这些导演的名字;我们还会玩导演名接龙的游戏,比如波兰斯基——基耶斯洛夫斯基——基亚罗斯塔米——米洛斯·福尔曼——曼德尔施塔姆(“曼德尔施塔姆哪个国家的导演啊?”“俄罗斯的,你没听说过啊,他拍的《时代的喧嚣》可好看了。”“好吧。”)……谁接不上来谁就喝酒。
为了更方便看电影,我们一人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学校社团播放的免费电影因其低劣的趣味早已被我们列入黑名单,那会儿我们已经不看好莱坞电影了)。我们还会相约这个星期只看北欧电影,下个星期只看伊朗电影,下个月只看纪录片等等。
我们每天下课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冲回宿舍看看自己出门前下载的电影有没有下好。
“居然又是下到99.9%就不动了!”
“罗伯特·布列松的这部电影我都下了三天了!”
“我终于把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下全了!”
“我在下莎米拉·玛克玛尔巴夫的片子,她的电影比马基德·马基迪的深刻多了!”
那时的下载工具下完电影后会发出“叮”的一声,那清脆的声音会让人精神为之一振,通常我会先跳着预览一下,根据其沉闷程度来决定什么时候开始看。
不少大师的片子在网上是下不到的,我们相约每个月去市区的碟店淘一次碟。店主是一个喜欢法国新浪潮电影的中年女子,每次去她那里,她不是在看戈达尔、特吕弗就是在看阿伦·雷乃、侯麦。我们通常下午去,出碟店时天就已经黑了。
就这样,看电影几乎成了我们唯一的娱乐,即便是偶尔出去开房,我们都要把笔记本电脑带过去看电影。有一回,她不听我的劝告,非要看吉姆·贾木许的电影,结果没看一会儿,我们俩都睡着了,一觉醒来后已经到要交房的时间了,最后只好抓紧时间做了开房该做的事情。
3
我们日复一日地看着电影聊着电影,我们看的电影越来越小众,聊的话题离人群似乎也越来越远了,但是我们都不在乎。我们就像喜欢抽烟的人一样,高兴时要看一部电影,难过时也要看一部电影。
然而毕业的日子到了,我们的好日子也到头了。我比她大一届,这意味着我要比她先一步踏入社会。反观我的大学生活,发现我基本上都是在看电影中度过的,如果不找个跟电影有关的工作似乎太可惜了,因此斟酌再三我决定投身影视圈!
“好,我支持你!”听完我的决定,她兴奋地说。
“可是我上网搜了一下发现和影视有关的工作基本上只有北京才有。”
“那你就去北京啊!等我毕业了就去北京找你。”
去北京的计划就这样愉快地决定了。我开始收拾行李,最舍不得的是我那三百多张电影碟(其中有几十张是我自己拿空白光盘刻录的),还有宿舍里一墙的电影海报。
我把电影碟片都留给了她,只带了一部西恩·潘的《荒野生存》,因为在我内心深处,其实很不想工作,我想像片中的主人公一样去流浪。对于我的这一选择,她表示很不屑:“那么多大师的片子你不选,偏选了这样一部中庸的公路片。”
临行前的晚上,我特意象征性地选了一部帕索里尼的《索罗马120天》作为大学期间观看的最后一部片子。我对她解释说,如果我能够坚持看完这部电影,那就意味着我能够直面即将到来的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那你应该看看拉斯·冯·提尔的《反基督者》或者是三池崇史的《杀手阿一》,这两部片子比《索罗马120天》残酷多了。”她笑着说。那段时间因为毕业的事而烦心,电影看得少,她的阅片量又远远地超过了我。
4
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来到了北京。我投了很多摄影师助理和导演助理的工作,也收到了不少面试通知,但是很快我发现这些约我去面试的大多都是皮包公司,一上来就要收费。
那天我决定最后面试一家电影公司,如果再不靠谱的话,我就只能“转行”了。好不容易找到那家电影公司所在地,却失望地发现那家公司居然在一个小区的居民楼里,看上去极不正规。我给她打了一个电话,讲了一下我的处境。
“你都到了,好歹试一下啊,也许这次是真的呢。”在她的鼓励下,我还是进去面试了。
没想到面试官居然还挺专业的,我去的时候他正在读伍迪·艾伦的《门萨的娼妓》,一上来就跟我讲巴赞、爱森斯坦、库里肖夫效应什么,还说自己最喜欢的导演是库布里克。我一听就来劲了,跟他大谈我对《2001太空漫游》的理解。最后面试官表示对我很满意,说我明天就可以来上班做导演助理,但是工资不高,一个月只有五千多块,没有提成。
“没关系,我刚毕业,没那么高的要求,主要是希望有一个学习的机会。”我表面唯唯诺诺实则心花怒放地回答说——这工资真的远远超过了我的设想。
“我就喜欢你这种实诚的年轻人。好,先交两百块钱的食宿费吧,我们明天就带你去顺义那边的片场。”
喜欢伍迪·艾伦和库布里克的人总不会是骗子吧,我一边这么想,一边递给了他两百块钱,出门时我就后悔了,很想跑回去跟他把钱要回来,那可是我身上仅剩的两百块钱呀!
我来到前台登记处(公司不大,但是有四五个工作人员),想记下其他来面试的人的电话号码,问问他们是什么情况,其中一个号码刚记了一半就被前台小姐一把抢走了登记簿,她怒气冲冲地说这是公司机密。
第二天我没有去报到。我没跟她讲这次悲惨的经历,只说面试官说让我回去等消息。
“今天我看了一部非常特别的电影叫《电视台风云》,是拍《十二怒汉》的那个导演拍的,名字挺难记的,不过我还是记住啦!西德尼·吕美特。”
她现在给我打电话还在聊这些,我已经没有什么兴趣听了。每天忙着找工作,也没时间看电影了,虽然电脑里还存着两百多部没看的。慢慢地,她察觉到了我的言不由衷和答非所问,她觉得我越来越不关心她,开始跟我发脾气,有时候吵完架气不过,我就直接关机了,第二天开机后会看到她打来的几十个未接电话。
终于有一天,她发短信跟我说:“我们分手吧,我喜欢上别人了。”那一刻我突然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但还是问她:“那个人我认识吗?”“你不认识,是一个电影学的研究生。”不知道为什么,我脑海中一下子就浮现出那个拿精神分析学解读着《这个杀手不太冷》的脱发男。我强忍着恶心,给她回了一个:祝你们幸福。
5
虽然分手了,但我们还保持着联系,毕竟在这个世界上要找到一个这么热爱电影的人还是挺困难的,我们偶尔还会交流一下最近看的片子。没想到的是她居然决定考电影学的研究生,一年后她还真的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系。
也许是出于嫉妒的心理,我不再回她的短信。我找到了一份书店的工作,每天浑浑噩噩地过着,直到有一天她突然打电话跟我说她学期末要拍一个短片,希望我可以出演,我心中的电影梦才死灰复燃起来,我自然是欣然前往的。
她对于这个片子的最初设想大致是这样的:一个有着导演梦的青年A,迫于现实的压力,现在在一家书店做店员(为我量身打造的角色!)。一天,一个女人来书店找一本名为“雕刻什么的”电影方面的书送人用。塔可夫斯基的《雕刻时光》,A自然很快帮他找到了。女人问A你怎么确定是这本呢?A说,是这本没错,谁的书都有可能记错唯独这本不会(接下来便是伍迪·艾伦式的吐槽或是昆汀·塔伦蒂诺式的对白)。
同时,平行蒙太奇的另一头是,一个梦想着一夜暴富的青年B,迫于现实的压力,现在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销售。一天,一个男人说他不该在他的地盘上撒野,拉他去小巷子里狠狠修理了他一顿(贾樟柯式的画面)。
片子的结局是,在地铁上,两个底层青年互相看了对方一眼(安哲罗普洛斯式的悲剧气氛)。然后,镜头移向地铁上的电视,屏幕里正在播放一条关于大学生就业困难的新闻(杨德昌常用的手法)。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遇到了种种困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青年B的演技太差,一句完整的台词都说不下来,还经常笑场。剧本便被简化成了一个有着导演梦的青年A的一天,其中有上班迟到、为女顾客查书、在厕所被主管训斥、坐地铁回家四场戏,同时穿插着一串葡萄被路人反复践踏的画面(这一段本是我受苏联导演谢尔盖·帕拉杰诺夫启发打算用在总结我的一生的自传性影片里的镜头——象征着人生的血腥和残酷——现在我无私奉献出来了)。
影片的结尾是,我下班后回到家,拿起吉他弹了一曲,隔壁新搬来的女生闻声而来,送给我一串葡萄(这串失而复得的葡萄象征着人生渺茫的希望),镜头定格在我讳莫如深的微笑上。很自然地,这部片子的名字就定为《葡萄》了。
但是,在后期制作过程中,导演(同时也是摄影师和剪辑师)发现,葡萄被踩的那段戏剪进去显得很突兀,而且她担心这样一来,整部影片会呈现出一种过于诡异和晦涩的氛围。我用伯格曼、布努埃尔、安东尼奥尼的电影观来劝慰她,但最后,她仍然坚持删掉了那段我认为颇具艺术特色的“葡萄戏”。
据说,《葡萄》上映时(当然是在她们班上上映),一直有人笑场,尤其是最后那个端着一串不知所云的葡萄的邻家女孩(是她的同学饰演的)上场时,全班哄堂大笑。其中的穿帮镜头和不专业的剪辑更是让“评委老师”勃然大怒。
6
不久后,她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着说着她就痛哭起来。
“你这个骗子,我被你骗了!”
“此话怎讲?”
“都怪你上大学时天天带着我看电影,现在才学了这个狗屁电影学,学这个根本没有出路,我真想把这一切都还给你!”
“怎么没出路?我们上次合作的电影不是挺好的吗?”
“好个屁!那部片子得分全班倒数第一,好么?!”
“那是你们老师太商业了,不懂得欣赏艺术片。”
“你够了!我就是这样被你一路骗过来的,以为看电影拍电影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意义的事情,事实上根本不是!电影根本就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你知道那时候我为了在你面前显摆一下,熬了多少个通宵看电影吗?你倒好,说分手就分手……”
“且慢!你是一开始就喜欢电影的好不好?我是为了在你面前显摆才拼命看电影的……再说,分手是你提出来的。”
“我那是试探一下你,没想到你答应得那么爽快!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你只是爱你的电影。我一开始只是对电影有点兴趣,在你的激励下才把所有时间都搭进去了。你毕业了发现电影这条路行不通就放弃了,你放弃得倒是快,我现在掉沟里了,根本爬不出来……”
她就这样对着我咆哮了半个小时。
在这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了,等我想起来给她打个电话时发现她的号码已经是空号了。
7
两年后的一个晚上,我在大望路的地铁通道里看到了她。通过一个过肩镜头,我看到她穿着工作服和高跟鞋走在我前面。光凭背影我其实不太能确定是她,但那会儿她正在接一个电话,那声音是她无疑。我本来可以走上去打声招呼的,但我却刻意放慢了脚步。在一个长镜头里,我看着她拼尽全身力气挤上了地铁。
在等待最后一班地铁到来时,我在想,如果我跟着她上了这趟地铁会怎样,我的人生会因此发生改变吗?
“呐,你这个想法汤姆·提克威在《罗拉快跑》里不是已经表达过了吗?”以前的她一定会这么回答我。
而我会说:“是的,不过就同一个主题而言,我觉得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机遇之歌》拍得更深沉一些。”
想到这里,一种电影落幕时的凄凉感突然击中了我,我的眼前闪现出各式各样的片尾字幕——
完
终
剧终
The End
FIN
FINE
……

△市川昆《缅甸的竖琴》(1956)

△小津安二郎《秋刀鱼之味》(1962)

△希区柯克《惊魂记》(1960)

△布努埃尔《沙漠中的西蒙》(1965)

△安东尼奥尼《红色沙漠》(1964)

△杜琪峰《阿郎的故事》(1989)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