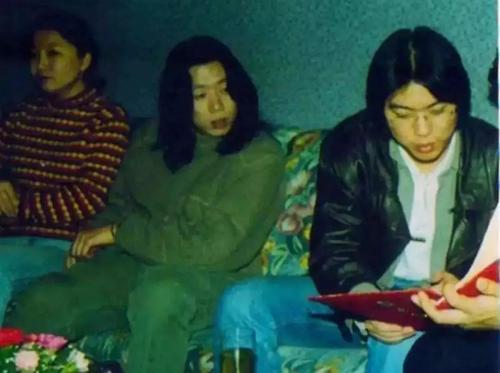潮汕祠堂讲究(人生的起点与落点)

很多关于童年的回忆,都绕不过村里的祠堂。
祠堂是一个严肃的地方,但对孩子们来说,更像是一个乐园。他们在祠堂里追逐玩耍,在柱子之间像鱼儿一样穿梭,欢笑声回荡在庭院之间。要是祠堂关上了,孩子们就在祠堂前面空旷的大埕丢手绢、弹榄核、拍纸片、滚铁环。
有时候到河边挖来黏土,在祠堂一角围坐成一圈,把黏土捏成小动物、小手枪、小汽车等造型。小伙伴们经常玩的一个游戏就是摔泥泡,把黏土捏成碗状,碗口朝下猛地一扣,随着“噗”的一声响,泥碗破了一个大洞。你用拍扁的泥巴来补我的洞,我也一样用泥巴来补你的洞,洞破得大的得到的“补丁”越多,算是胜方。类似的游戏,还有很多。
捏糖人的老头喜欢把担子放在祠堂的门楼,用剪刀把一小团麦芽糖剪出造型,然后拉出一根管状的糖丝,嘴巴一吹,一只公鸡或者一只猴子瞬间膨胀起来,活灵活现。
还有那些换锅底的、修木桶的、修伞的、磨剪子戗菜刀的,都喜欢在祠堂门楼角落干活,因为可以遮风挡雨。孩子们围观在四周,睁着好奇的眼睛。

大概是1985年前后,村里给祠堂添置了一台彩电,自此,祠堂成为全村老小向往的娱乐场所。
那可是村里第一台彩电,进口的日立牌啊。为此,村里还郑重其事地让人在祠堂后墙上安装了一个电视柜,关机就上锁,锁匙由专人管理。毕竟那时候电视机很金贵,偷彩电的传说时有所闻。
那时候刚好村口国道扩建,道路两旁的树木砍伐之后,算作村里的公家财产。在树干中找出比较周正的,由村里木工制作成十条长约两米的长凳,在电视机前面摆成五排,气气派派,一个简易的播放厅就此告成。
一般说来,白天是不开电视机的。通常是晚上六点半,负责播放电视的愈贤老叔会准时打开祠堂侧门,然后再打开电视机。吃饱晚饭的小孩子鱼贯而入,要是有好节目就抢位子看,要是播放新闻就嬉闹追逐。
晚些时候,大人们陆续进场,有些是纯粹瞎转悠的,有些是等心爱的节目的,比如说有些人就等星期二晚八点的潮剧专场。
电视频道非常少,只有中央台、珠江台、岭南台、揭阳台四个频道。能够选择的节目非常有限,娱乐节目根本就没有。晚上七点到八点这一个小时,基本都是新闻,先是中央台的新闻联播,接着是省台新闻,然后是本地新闻。还好八点之后就是连续剧了。

我那时候也就十岁左右吧,也跟在人群中凑热闹。我看过《庚娘》,非常清楚地记得是南通电视台拍摄的。断断续续看过墨西哥的《诽谤》,没觉得剧情多好,就觉得墨西哥女人的眼珠子又圆又大的。此外,还有《济公》《射雕英雄传》《铁道游击队》《红楼梦》《夜幕下的哈尔滨》等连续剧。最激动人心的是播放《西游记》的时候,整个“播放厅”人头攒动,密密麻麻都是人,凳子不够坐就站着看。
有一年春夏之交的一个夜里,天气湿热,我正在看电视,一条虫子悄无声息爬进我的裤管,在大腿咬了两口,疼得要命 。脱掉长裤,抖了抖,赫然掉出一条斑斓的蜈蚣。
因为祠堂里有全村唯一的一台彩电,晚上到祠堂看电视成了全村小孩的第一选择。可是明天要上课啊,所以经常有父母到祠堂逮小孩回家睡觉。
掌管着电视柜钥匙的愈贤老叔是个单身老头,得过麻风病,手脚都异于常人,走路有些摇晃。村里为了照顾他,给了他这么一个闲职。愈贤老叔平时喜欢喝两口,有时候喝过头了就站在天井骂娘,骂社会不公平,骂一切看不惯的东西。有时候大家明明看电视看得好好的,忽然后面传来一阵叫骂声,不由嘀咕一声,愈贤老叔又喝多了。
2

村里的祠堂,建立于清末戊戌年间。祠堂在不同时期发挥不同作用,比如做过学堂,也做过粮仓。我父亲小时候就在祠堂念过小学。大部分时间里,祠堂一直是议事议政的地方,祠堂东侧厢房,充当过相当长时间的村公所。祠堂屋顶有一个高音广播喇叭,一旦有要事通知,广播喇叭便响彻全村:“通知通知,各位村民同志请注意……”
年底年初,在祠堂里拜神,这个传统从以前到现在,一直不变。
我的细老叔,也就是我爷爷最小的弟弟,在乡里扮演的角色类似于古代的“祭酒”。
他深谙各种祭祀仪式,从“跋杯”(掷杯筊)、解签、择日到迎神、送神,各个环节都熟稔于胸。凡是涉及到拜神,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三牲、五果、斋菜、粿品、纸钱的讲究。须知吾乡拜神环节之繁复,可以上升为一门学科,仅纸钱一项,可以分为“说话钱”、“福钱”、“大金”、“大钱”、“银锭”、“小金”等等,各有用途,令人迷惑。
到了年底,细老叔的事情就多了起来。
他要到庙里“跋杯”择日送神,选好日子后就在墙头贴出告示。送神之日前一天,要安排人手将庙里的神位护送到祠堂正中间的香案之上。
正月里迎神,他要将神位请到祠堂供村民跪拜。村里新婚的后生,或是准备添丁者在神前许愿,希望今年求得麟儿,然后向细老叔领取糖狮子一只。若是遂愿,来年要送上一只更大的糖狮子,即为还愿。
以细老叔为首的几位老人,组成了一个小规模的“拜神理事会”。祠堂里忙上忙下的那几个老人,他们操持着村里的各种拜神仪式。他们要准备好各种材料,要安排人手帮忙,要登记各种收支,要在某个准确的时辰完成某项神秘的仪式。

我的四老叔,是村里公认最有文化的人。
他是中学语文老师,做过校长,会写毛笔字。他退休回家后,试图将文化的火种播进我们这个只有700多人的村子。
四老叔说服村领导,把祠堂打扫一番,再把墙壁刷得雪白,然后在墙壁上写上很多大字,比如爱国、民主之类。四老叔先在玻璃上写上字,在夜里用手电筒一照,投射在墙上的字体陡然变大,描出轮廓后再刷上红色油漆,斗大的字就这样写出来。果然是读书人办法多。四老叔又说服村领导,在祠堂厢房一边再隔出一间小屋子,办成一间小小的图书馆。他将自己的藏书奉献出来,又让村里出钱买一部分书。四老叔还出一个主意,动员村民捐书。那时候我已经读初中,觉得家里的小人书已经过时,就一股脑捐了出去。
就这样,一个小小的乡村图书馆就在祠堂里落成了,馆长当然是四老叔。
上面对我们村走在前头的文化建设表示满意,还特意发了奖状。

图书馆开始还有人凑热闹,借几本闲书看看,到后面借书的人就渐渐少了。一是图书馆的藏书量有限,二是村里爱读书的人真的不多。
四老叔过世后,图书馆很快被拆掉,里面的书籍也不知所踪。一想起这回事,我就后悔当初捐那么多书。
我读高中的时候,毛笔字写得还可以,于是接过四老叔的“文化事业”,过年时候给村里写春联,再贴到各个门楼、巷口。还有就是在正月里的祠堂门口,举办灯谜竞赛。可惜我们村子太小,有几个读书的也不见得有多喜欢猜谜,结果造成的局面就是,我出的谜语村里人猜不着,倒是外乡人来的人猜了不少。
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一房也算是在祠堂里留下了一点印记。
3

村里要是有人过世,祠堂便成了议事厅。
早在逝者弥留之际,一个非正式的治丧委员会已经准备得差不多,通常是由族里有声望的长者和得力后生组成。祠堂大门打开后,桌椅摆开,茶炉烧起来,各位主事人陆续坐下,丧事各项细节便提上议程。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得,丧事是一项非常考验主事人能力的事情,它关系到组织、统筹、接待、协调等管理能力。
首先,丧事是一件非常严肃的大事,有着各种各样的严格仪式,那些繁复礼节只有老人们才懂得。通常,吾乡葬礼一般要经过换寿服、上厅、发讣、报地头(向本地神庙告知)、买水(带上锅钵茶壶到河边,丢下硬币“买”回水,为死者举行沐浴礼)、入殓、成服、祭灵、戴孝、做功德、出殡、安葬、回灵、食“清洁桌”(相当于解秽酒)等诸多环节。那些该做,那些不该做,都有明确的边界。有些事情做错了,可能会影响到后面的吉凶运程。宗族里的老人在这一刻,充满权威感。

丧事也是一个和解的机会,对于那些平时和死者一家有龃龉的人,到祠堂送上一份纸仪,算是尽了一份心意。有的人会留下来,帮忙做一点事,或者坐着聊一会天,都是一种示好的姿态。自此,两家人的恩怨算是了结了。帮忙的人多,吊唁的人多,说明办事这家人面子大,人缘好。
出殡当天一大早,各路人马聚集到祠堂,被迅速动员起来,分工行事。
负责联系火葬场的、负责买菜的、负责接待的、负责端菜洗碗的、负责记录收支的……各种分工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出殡归来后,众人回到祠堂坐着,就等着吃饭。祠堂里坐满了人,大家喝茶抽烟聊天,很多平时联系少的人又碰面了,不由寒暄起来。大家开始还略有憾意地谈起逝者,言及其生前的种种事迹,慢慢的,话题转向了工作、股市、楼市、升学等日常话题。

午饭通常在十点多就开始,菜一上,祠堂马上变成一个大食堂。大家找相熟的人凑到一块,找不到熟人的就随便坐,十几张台一下子坐满了人。渐渐的,气氛开始热烈,大家的注意力转到饭菜上,对厨师的手艺评头品足。在我们村吃过“死人饭”的都赞不绝口,一是我们村素来大方,二是厨师手艺好。凑到一起的年轻人,有的开始喝酒,啤的白的都有。酒一进肚,酒精迅速发挥作用,那一两桌的年轻人声音开始变大,甚至有人大笑喧闹起来。
祠堂里一扫之前的压抑气氛,甚至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快,孩子们开心地喝着饮料,大人们卸下了悲戚的心情。就是那些逝者的至亲,也不见了之前的悲哀,换之的是疲惫。毕竟,绷紧的弦总要放松的。偶尔也有一两个悲伤至深的人,依然在强作欢颜。
酒过三巡,现场看来有些荒诞,有些戏剧化,悲伤的悼念活动仿佛一下子变成欢快的聚餐。
其实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

人总是要回归到正常的生活的轨迹上,情感上需要一些释放,需要一些过渡,更需要一些弥合。没有人愿意在丧事结束后还见到哭哭啼啼的人,想想逝者泉下有知,也是这般想法吧。及早从悲伤中抽身出来,回归正常的情绪,才是正理。
吃饭的间隙,主事人会给在场每位亲友发放回礼,通常是一个红色塑料袋,袋里包着一条毛巾、四颗糖果、一根红丝线,有时也会多一对“大吉”,即是柑。
饭后散伙,也有讲究,千万不可以告别或说“再见”,这是非常不吉利的事情。正确的做法是径直走掉就是。
曲终人散之后,就是收拾残局。炉头灶具、锅碗瓢盆洗刷完毕,和凳子椅子一起归类放进祠堂厢房。地上的垃圾在几把扫帚的努力下,一扫而光。两条水管接上水龙头,一阵冲刷,地面恢复清洁。
嘎吱一声,祠堂门关上了,一切又恢复平静。
4

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在不断提醒,你就是这个村子的人。
外出的或者是住在城里乡亲,很多人会在送神、迎神等大日子赶回来。同村的一个朋友,每逢送神迎神之时,都不辞劳苦地开四五个小时的车,从外地风风火火赶回来。进香的人,在祠堂中厅神位之前虔诚跪下,向看不见的神明祈求庇佑,然后在香炉里郑重插下三炷香。
那一刻你明白了,无论你走得再远,你依然是这个村子的孩子。
年底送神,正月迎神,庙里的神位被请到祠堂中厅香案上面,进香的人络绎不绝。祠堂前面的大埕摆满了桌子,一张桌子代表着一户人家。一到天微微亮,拜神的乡亲挑着担子,把供品摆满桌子。天渐渐亮了,人渐渐多了,相熟的人打着招呼,平时各顾各的,现在有机会拉一会家常。一些新嫁娘被婆婆拉过来作介绍——这是某某老婶,这是刚娶过门的儿媳妇,来来来,猛猛叫老婶。虽然都是同一个村子的,依然看到很多陌生面孔,毕竟年轻人越来越多,人与人的距离越来越远。

拜神活动结束后,纸钱都集中在一个地方燃烧,成扎成捆的纸钱被扔进火堆里,火光冲天,热浪逼人。围观的人笑呵呵说:旺就好啊,旺就好啊。好像是整个仪式最后的升华,火越来越旺盛,气氛越发的热烈。纸灰在热空气的作用下,四处飘散,余韵袅袅。
端午节划龙舟,分散在各地的年轻人像飞鸟归巢一般赶回来。出发之前的清晨,全部人到祠堂神位之前进香,然后围坐在祠堂前面大埕上吃“龙舟饭”。饭后众人列队,村领导发表鼓舞士气的讲话,锣鼓响起,口号震天响……那一刻,是何等的热血沸腾,何等的激动人心。你坐的那条龙舟,也许认识不到一半的人,但你有强烈的归属感,你就是这个村子的一份子,不管谁来挑战,你都会拼尽全力。

大部分时间里,祠堂是安静的。
现在的祠堂,更像一个社区活动中心。村里购置了桌椅、茶具、乐器,可以打乒乓球和羽毛球,墙角的书柜里放着崭新的书籍。老人们有时会带着自己的孙子来祠堂转转。现在的祠堂对孩子并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他们不会玩泥巴、弹榄核、拍纸片,更缺少一起抓迷藏、丢手绢的玩伴。
无所事事的老年人,每天只能到祠堂找老伙计喝茶、聊天、下棋、打牌、拉二胡,就像小时候到祠堂找伙伴玩一样。人生阶段的最初和最后,竟是如此惊人的一致。
有的居住在外地甚至是外省的老人,在垂危之际说什么也要赶回老家。因为在村子之外身故,遗体是不允许进村的,那样不吉利。有的老人甚至吸着氧气躺在救护车里赶回来,可谓是争分夺秒。为的是能吊住一口气,好让家人穿寿衣,接着进厅堂、做法事,然后在祠堂里大摆宴席,风风光光做一次人生的告别。

前厅墙壁上,嵌有石板做成的芳名录,那是重修祠堂热心捐款的乡亲名字和金额。里面有的人平时并没有在村里住,甚至几十年都没有回来过,但他们捐起钱来,异常慷慨。中厅墙壁上,挂有相框,里面有乡亲们在各种活动的留影。
他们有的还在,有的已经不在了。
闲聊的老人,有时会提起从前的某个片段、某件事情、某个人物。那些远去的人,像愈贤老叔、四老叔、细老叔,在某次闲谈中又一次清晰起来。
我不禁想了想,过了二十年,我会不会也和他们一样,一样到祠堂来找老朋友聊天,聊小时候弹榄核、拍纸片、玩泥巴的事情,聊那条莫名其妙咬伤我的蜈蚣。
祠堂像一座时光驿站,贯通着从前、现在、以后,那些来来往往的人,在祠堂里留下匆匆的身影,最终融进了祠堂的历史。
有人说,人的一生,都走在回家的路上。
很多人看似渐行渐远,但人生的起点和落点,却在祠堂不约而同地交汇。
他们的一生,有意无意间被祠堂概括了。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