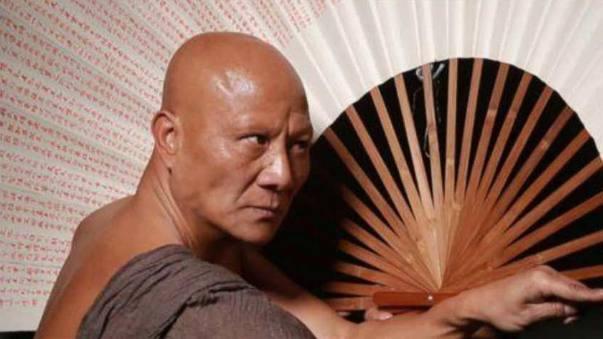水浒传的主要三个情节(纪德君口头传统规约下的水浒传叙事)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是从说唱文学中脱胎而出的,对那些直接受说唱文学孕育而产生的白话小说,不妨称之为“说书体”小说。
长期以来,我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说书体”小说当作文人创作的书面文学来研究,对《水浒传》的研究也多半如此。
当我们孤立地分析、评价《水浒传》的叙事特征时,往往一面惊叹其写人叙事的高超成就,一面又难以对书中诸多不合理的描写和叙述(如韵文散语的因袭套用、回前诗与正文内容的脱节、水浒人物的血腥暴力、叙事单元的前后重复、征战场景的重叠敷演以及时空描写的反常错位等)作出合理的解释。
近20年来,《水浒传》研究在版本源流、成书时代、翻译传播以及文化内涵的阐发等方面有所推进,但上述问题并未解决。究其原因,这与我们不够重视民间口头传统对《水浒传》叙事的规约有很大关系。
倘若我们立足民间口头传统,适当借鉴西方口头程式理论,重新审视《水浒传》叙事,那么不仅能对上述问题作出较有说服力的理论诠释,还可以为“说书体”小说的研究在视角、方法与思路上打开一点新局面。
一
让我们先从《水浒传》中韵文散语的因袭与套用说起。
《水浒传》中但凡写到庄院、酒店、城池、庙宇、山林、风雪、湖泊等,往往便以“但见”引出一段韵文,而这些韵文有不少还是雷同的。
书中一些骈词俪语也是多次重复使用。其散文叙事也同样存在遣词造句的重复现象。进一步调查,还可发现这些反复套用的韵文散语多见于宋元话本或元代戏文。如果从作家书面创作角度去看,这种现象未免不可思议。
一个作家即便文学创作才能再不济,也不至于翻来覆去自我抄袭或抄袭别人。不过,如果从口语文学的角度看,那么韵文套语的频繁使用,正是口头叙事的主要特征。
西方口头程式理论认为,处在口头传统中的诗人,是以程式的方式从事史诗的学习、创编和传播的,而韵文套语在口传文本中的反复出现,就是程式化叙事的产物。
对此,我国学者也有体察,如侯建在《有诗为证、白秀英与<水浒传>》一文中分析指出:
“口语文学,在传述的时候……纵有诗、文之分,其全凭说者的记忆则一,如果逢人逢事都要具体、不同的描述,则不仅说书人记忆起来过分吃力,听书人也同样要艰于记忆。
说书人哪里有停下来,想上半天,再继续下去的道理?听众所要找的是娱乐,也不可能聚精凝神,一气到底地静听。两者都要借助若干套语,遇到适当场合,略加更动,就套上去。”
(《中国小说比较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版,第76页)
的确,就书场演说而言,艺人说书只要事先背诵一定数量的专门描绘亭台楼阁、酒店旅馆、山川江河、风雨雷电等的诗词韵文,或是为各类人物开脸用的赋赞,或是形容疆场打斗厮杀的套语等,书中说到某处某景、某人某事或某场打斗时,只须拿现成的韵文赋赞往上一套,便可省心了事;如果想更应景一些,也只须在语词语序上略作调整,便可应付裕如。
对于口传文学这种创编特点,如果我们不甚明了,在研究《水浒传》时仍习惯于以作家个人创作的眼光去审视之,那么不仅难以对书中韵文散语的因袭、套用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甚至还会导致一些误读或错判。
如有学者发现《水浒传》与《平妖传》至少有13首写景状物的赞词是雷同的,据此认定两书作者同为罗贯中。
实际上,《水浒传》与其他说部之间出现诗词韵语的雷同,乃是因为它们都源自民间口头传统,都是因说话人相互影响、彼此取鉴,将一些韵文套语运用于不同说部导致的。
这种现象也出现于《西游记》与《封神演义》等小说中。
就口头说唱而言,程式化的诗词赋赞属于一种公有的文化资源,民间艺人不管是说“水浒”、说“平妖传”,还是说“封神”、说“西游记”,均可以共享,因此当艺人的说唱成果被记录、加工为不同的小说文本时,它们之间出现诗词赋赞的互文现象,实不足为怪,我们既不能据此认定某些小说同出于某个作家之手,也不能用来说明甲小说是否抄袭了乙小说,或者乙小说可能抄袭了甲小说。
还有学者以《水浒传》中的韵文为据,考证作者籍贯问题。如林冲雪天上梁山,来到岸边,“但见:山排巨浪,水接遥天……”;
又如隆冬季节,杨雄来到翠屏山,“但见:远如蓝靛,近若翠屏……”,这些韵文所写显然违背气候常识,论者据此认为施耐庵是不熟悉北方气候的南方人。
可是如果了解民间说书的特点,就会明白这大概是艺人说到水泊山川时随口将程式化的韵文往上一套所致,似不宜以写实的眼光视之。
另有论者指出《水浒传》第七十八回开头的赋赞,理应概括本回内容,但它描绘的却是梁山的险要与众头领的性格、特长等,因此放在本回并不合适;赋中说“黑旋风善会偷营”“燕青能减灶屯兵,徐宁会平川布阵”“小旋风弓马熟闲”与书中描写不符;
赋中提及“杀辽兵”“擒方腊”,本回并无此内容;赋云“千年事迹载皇朝,万古清名标史记”,分明是小说的结束语,将后面的事情超前叙述,明显不当(《水浒传·前言》,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7页)。
看来,这也是以“量体裁衣”的眼光来审视、苛求入话诗赋。其实,《水浒传》每回前的入话诗赋,有不少与正文所叙不相干,它们多半不是为特定情节量身定做的,而是一种程式化的韵文套语,常被说话人用来候坐、静场,因而对其所述不宜做胶柱鼓瑟式的理解。
如这一篇赋赞描绘梁山泊气象的部分,就与元杂剧《鲁智深喜赏黄花峪》《黑旋风双献功》第一折中宋江的开场白雷同。
赋赞中将主要好汉的性格与才干概说一遍,也是为了强化听者印象。
而赋中夸赞某些好汉的才干与小说所写不合,则反映了说书人使用赋赞的随意性,其所说“跃洪波,迎雪浪,混江龙与九纹龙;踏翠岭,步青山,玉麒麟共青面兽。逢山开路,索超原是急先锋;遇水叠桥,刘唐号为赤发鬼”等,明显就是从“龙”“麒麟”“兽”“先锋”“鬼”这些字眼上生发的;而“善会偷营”与“偏能劫寨”,“减灶屯兵”与“平川布阵”等,也是两两对应的套语。
至于该赋将后文之事超前叙述,这也是说书人的惯伎。
《水浒传》第五十一回入话诗,也将全书内容概说了一遍,徐朔方指出它“不折不扣地包括了整整一部《水浒传》!如果不是由说唱艺术本身的特点所规定,有什么必要在标目是‘插翅虎枷打白秀英;美髯公误失小衙内’的第五十一回前面来这么一大套呢?”(《从宋江起义到<水浒传>成书》,《中华文史论丛》 1982年第4辑)
因此,认为“将后面的事情超前叙述,明显不当”,这也是忽视说书特点的一种误解。

《水浒传》
二
据史书记载,《水浒传》所写人物本来是一群流寇,他们的故事之所以见于街谈巷语,并成为说话人演说的对象,大概曾有扶危济困、反贪除暴的义举。
不过,能将一群江湖流寇演说成万民喜爱、有口皆碑的英雄好汉,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那么,说话人是怎么做到的?追溯水浒人物故事的流变,揆诸民间说书的特点,下述编创方式颇值得关注。
一是“捏合”,也即把本来不相干的人和事加以聚合,并辅之以编造与想象,这是宋元“说话”艺人的拿手好戏。
一些研究者早就指出,南宋时民族矛盾尖锐,北方忠义军活动频繁,汉族人民痛恨奸臣贪官,崇拜草泽英雄,说话人为了顺应民意,遂将抗金忠义军的故事附会、捏合到宋江等人身上。
不仅如此,说话人还编造了水浒好汉征讨辽国,迫使辽国纳表称降的故事,并将平定方腊也说成是宋江等人的功劳,如此便将水浒人物的“忠义”行为坐实了。
而这样一来,宋江等人便由“剧盗”逐渐转变为“忠义之士”,不仅洗去了盗贼之名,而且成了汉族民众喜闻乐见而文人士大夫也能认同的英雄。
二是“攀附”。当“说水浒”还是无名小辈时,“说三分”等早已风靡于市井瓦舍。
于是“说水浒”的艺人便千方百计攀附“说三分”等,以期增强水浒故事的吸引力。
其攀附之法,或是直接袭用,如《水浒传》第九十回就将“说三分”的精彩关目“刮骨疗毒”攘为己用;或是有意效仿,如《水浒传》中司空见惯的兄弟结义,便效法“桃园结义”;
或是援引比附,如《水浒传》中多次援引“火烧赤壁”来比附其所写的火攻;或是刻意附骥,如让水浒好汉与“说三分”“说隋唐”“说五代史”以及“说杨家将”中的英雄人物发生关联,以此改变他们秉承的文化基因,提升其知名度与影响力。
三是“夸大”和“神化”。从书场接受的角度看,夸张的、冒险的、令人惊悚的、神奇化的人物,无疑更易耸人听闻。
美国学者沃尔特·翁指出,在口语世界里,英勇而非凡的“厚重”人物最有助于记忆,而没有色彩的人物则不可能流传、保存下来(《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2页)。
就水浒人物塑造而言,说话人正是通过“夸大”和“神化”来凸显其人物的非凡武勇和过人智能的。诸如倒拔垂扬柳、只手打猛虎、剖腹剜心、生吃人肉等。有不少学者对水浒好汉的血腥、暴力行为往往过于苛责。
实际上,“对暴力的热心描绘常常是口传故事的显著特征……赤裸裸的暴力在许多史诗和其他口语样式里处于核心的位置”(《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第33页)。
《水浒传》讲的是江湖传奇,其所说的虐杀滥杀、剜心吃肉等恐怕主要不是写实而是为了耸动受众听闻。
试想,如果水浒好汉所作所为不是这么超常、惊悚,那么又如何凸显其狂野不羁的英雄本色和快意恩仇的精神性格?又如何能制造一种惊险、刺激的效果,让人过耳不忘?
《水浒传》讲杀人吃人,之所以并不引人憎恶,武松、李逵等还是民众很喜爱的英雄,恐怕一是因其所杀多为滥污官吏、流氓无赖、淫贱荡妇,虐杀他们,可以痛快淋漓地宣泄民众的仇恨情绪;
二是因为说书人有意把血腥、残暴行为戏谑化、程式化了,如宋江多次死里逃生、李逵吃李鬼之肉、用斧头剁碎一对偷情男女等,都经过了戏剧化的处理,使人闻听不由地开怀一笑。
另外,说话人为了凸显水浒人物的卓荦不凡,还将他们神异化了,说他们是天罡地煞下凡,其领袖宋江还幸遇九天玄女面谕天机、授其天书,公孙胜则能呼风唤雨,荡邪除魔。
神话原型批评学者弗莱曾说:“传奇越接近神话,主人公的神祇属性便越多,仇敌也具有越多神话中的魔怪特征。传奇的主要形式具有辩证性:
一切事情都集中在英雄与其仇敌的冲突斗争上,而读者的一切价值期待又都寄托于英雄一身。因此,传奇中的英雄十分类似从上界降临到凡世的神话般的救世主,而其敌手则如同下界的魔怪。”(《批评的解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70页)
《水浒传》中与梁山好汉敌对的高廉、贺统军、郑魔君、包道乙等,就善使妖法,魔性十足,不过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他们最终还是败于梁山好汉之手。
当梁山好汉完成“替天行道”的使命后,他们便重登紫府,回归神界,受人庙祀。通过如此这般的“夸大”和“神化”,说话人终于将水浒人物说成了受民众崇拜的神话式的英雄。
四是“排座次”“起绰号”等。水浒人物经由说话人的演说,由少到多,如滚雪球般发展为一百零八将。
为何不多不少就是一百零八将?这显然是借用了道教三十六天罡与七十二地煞之说,不仅把水浒人物神奇化了,而且数字化了。
沃尔特·翁说,在口传文学中,“公式化的数字群体也有助于记忆”,比如七雄远征底比斯、美惠三女神、命运三女神等(《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第53页)。
水浒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之说,无疑也有助于人物故事的记忆与传播。
水浒一百零八将虽然个个神奇非凡,但聚在一起,其武勇才能等毕竟有高下之分,而受众出于好奇心也想弄清谁强谁弱,排位谁先谁后,于是说话人便为好汉排座次,前后大大小小排了7次,并且将他们分为马军、步军与水军,马军又分为五虎将与八骠骑等。至于将人物分为兄弟档、夫妻档、叔侄档、师徒档、同事档,以及让一些人物配对行动,自然也有助于口头记忆与传播。
另外,便是给人物起绰号,以此凸显人物外貌、才能、性格、脾气等方面的鲜明特征。
不仅如此,艺人说“水浒”,还初步构建了“六位一体”的人物关系模式,即左右书情发展的核心人物宋江、制约核心人物的领袖宋徽宗、活跃书情的喜剧性人物李逵、为宋江出谋划策的军师吴用、与水浒好汉作对的奸贼高俅,以及辅佐宋江的其他次要人物。
这种人物关系模式在“说三分”等讲史中已见雏形,《水浒传》当效“说三分”而为之,我们在宋江、李逵、吴用、高俅等人身上不难看到刘备、张飞、诸葛亮、曹操等人的影子。显然,正是借助将水浒人物数字化、特征化、类别化等手段,说话人才能确保其书场演说有条不紊,而受众也才能了然于胸,甚至有了茶余饭后的谈资。
总之,水浒人物本来是一群流寇,如果说话人不将他们与南北宋之交北方抗金忠义军关联起来,那么就难以荡涤他们身上的匪盗习气,赋予其忠君爱国的正义色彩;如果不将他们与市井小民崇拜的英雄人物关联起来,也难以改变他们的形象,扩大他们的影响;
如果不将他们的武勇才能夸大化、神奇化,也难以让市井小民肃然起敬,产生崇拜之情;如果不将他们数字化、特征化、类别化,也难以让市井小民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
而经过上述这样的改造,水浒人物不仅脱胎换骨,变成了妇孺皆知的忠义英雄,说“水浒”也后来居上,并进入文人视野,得到思想和艺术上的加工、提升,为其经典化奠定了基础。

三
当然,说“水浒”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也与说话人善于运用程式化的“主题”与“故事范型”进行叙事密切相关。
所谓“主题”,是口头程式理论常用的一个重要概念,洛德将其定义为“诗中重复出现的事件、描述性的段落”(《故事的歌手》,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页),也即“母题”与“场景”。而“故事范型”,则是指具有组织、建构故事之功能的叙事框架或曰情节套路(朝戈金《口头史诗诗学的几个基本概念》,《民族艺术》2000年第4期)。
程式化的主题与故事范型,是艺人记忆、建构、演述、传承其所说故事的秘诀,艺人必须积累一定数量的主题与故事范型,才能在说书场中游刃有余。
就说“水浒”而言,善于化用口头传统中流行的“母题”,乃是说话人取得成功的奥妙之一。
宋元说书场中有一些情节关目,因受听众的喜爱而反复出现在不同题材的“说话”名目中,久之便成为艺人共知共享的“母题”,诸如比武、打擂、打虎、结义、得天书、劫法场,等等。《水浒传》中不少精彩的叙事单元就脱胎于这些“母题”。
至于书中常见的一些“场景”描写,如两军交战、出奇设伏、偷营劫寨、摆阵破阵等,也不脱讲史熟套。
从阅读角度看,这种程式化的描写固然陈陈相因,单调乏味,但这正是说话伎艺的突出特点,说话人掌握了这些基本程式后,只要稍加变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演述不同人物在相异的时空中进行的各种战斗,而在场上演述时,说话人又可以凭借其说学做打等本领,将战斗演说得惊心动魄,因而并不给人以老调重弹的感觉。
值得注意的是,《水浒传》中还不时可见某些情节关目的重复运用。
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曾说:“如武松打虎后,又写李逵杀虎,又写二解争虎;潘金莲偷汉后,又写潘巧云偷汉;江州城劫法场后,又写大名府劫法场;何涛捕盗后,又写黄安捕盗;林冲起解后,又写卢俊义起解;朱仝、雷横放晃盖后,又写朱仝、雷横放宋江等。正是要故意把题目犯了,却有本事出落得无一点一画相借。”(陈曦钟等辑校《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
在他看来,作者是故意“犯中求避”,以展示其非凡的叙事才能。不过,从口头程式理论的视角看,这分明是同一“母题”的灵活套用,说话人不过是利用“替换律”做了一些因时、因地与因人制宜的改造,而基本程式是类同的。
由此说到口传文学的创新问题。沃尔特·翁指出,在口传文学中,“其叙事创新并不表现为编造新故事”,而是“给老故事引入新成分……它们的创新基本上局限在套语式、主题式思想的简明框架里”(《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第31页)。
《水浒传》产生于口传文学,很擅长在旧套子中翻新出奇,并能青出于蓝。同样是比武,林冲棒打洪教头胜于《杨温拦路虎传》所写杨温棒打马都头多矣;
同样是打虎,武松打虎远迈《残唐五代史演义》所写李存孝打虎;同样是劫法场,《水浒传》所写比起《五代史平话·梁史平话》的相关叙述,简直是化腐朽为神奇。
《水浒传》的成功,不取决于情节关目、场景描写等是否独出心裁,而在于推陈出新。
如果不明白民间艺人口头创作与文人作家书面创作的差异,一味地以“新颖性”“独创性”苛求包括《水浒传》在内的许多“说书体”小说,那么就会因这些小说中程式化“主题”等的大量存在,而指斥它们“千篇一律”(丁柔克《柳弧》卷四“小说通病”,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52-153页),甚至嘲笑作者“恬不知羞”(天游《小说闲评》,黄霖编著《历代小说话》,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第2316页)。
如果从“故事范型”的层面来看,《水浒传》的主要故事框架也是程式化的,这就是研究者们从水浒主要人物故事中总结出的“官逼民反,逼上梁山”叙事模式。
《水浒传》所写的林冲、武松、宋江、朱仝、卢俊义等人的故事,遵循的是“犯罪→发配→历险→落草”叙事模式;史进、鲁智深、杨志、石秀、杨雄以及晁盖、吴用一伙人的故事,没有“发配”这一环节,而是直接流亡江湖,遵循的是“犯罪→流亡→历险→落草”叙事模式,两者虽略有差异,但基本模式大体一致。
《水浒传》围绕“犯罪——落草”这一故事范型组织、建构故事情节时,由于以书中主要人物的命运播迁作为主线,叙述其流亡、历险和磨难,因而既可以灵活地适应书场分段演说的实际需要,又便于随时安排大大小小的“扣子”,抓住听众,使听众不断地为主人公担忧,从而激起强烈的求听欲。
《水浒传》在众多好汉聚义梁山后,又围绕招安与反招安,敷演了“两赢童贯”“三败高太尉”这样的重头戏,这其实也是一种故事范型,主要包括“挂帅征剿→两军对垒→布阵设伏→粉碎征剿”这四个要素序列,其阵战叙述前后重复,只是在陆战、水战、火攻、埋伏等战法上略有变化。
至于梁山好汉招安后,又开启了征辽、征方腊这种“征讨”故事模式,围绕攻城打寨,改换地名人名,将阵法兵机重叠敷衍,这也是按套路说书的体现。

《历代小说话》
四
如果我们放开视野,再将《水浒传》与明清“说书体”小说关联起来考察,还会进一步加深对“说书体”小说口头叙事特征的认识,进而改变我们的评价标准。
前文指出,说话人为了把水浒人物故事说出名气,说出影响,很善于把本不相关的人物故事捏合、附会在一起。
而当《水浒传》问世、民间说“水浒”名声大噪后,那些“说岳”“说唐”的艺人,也依样葫芦,攀附“水浒”。
《说岳全传》不仅让一些水浒人物重新出场,还写他们的后代活跃于抗金战场,而岳飞与林冲、卢俊义的师父同为周侗。
至于人物性格,岳飞类似宋江,而牛皋又活脱脱是李逵的化身。可见,攀附经典说书中的名人名将,制造看点,已是说书人惯用的伎俩。
《水浒传》通过“夸大”和“神化”来凸显人物的超凡出众,清代说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说唐》中的主要英雄,不仅力大无穷,武艺超群,而且多为星神下凡。
《水浒传》有一百零八将,《说唐》则有贾家楼三十六友。《水浒传》对好汉排座次,《说唐》也为主要英雄排名次。
《水浒传》给好汉起绰号,《说岳》也给一些英雄起绰号。
《水浒传》设置“六位一体”人物模式,清代以来说书人则将该模式固化,名之为书领、书胆、书筋、书师、书柱和书贼,其中帝王如赵构、李世民等为遥控主帅的“书领”,主帅如岳飞、秦叔宝等是统摄群英的“书胆”,军师如徐懋功、刘伯温等是运筹帷幄的“书师”,福将如牛皋、程咬金等是活跃书情的“书筋”,权奸秦桧、庞洪、敌寇兀术等是与正面人物作对的“书贼”。
可见,将英雄人物数字化并且排位次、起绰号、定类别等,也成为民间说书的惯例。
《水浒传》中许多精彩关目,如比武、打擂、打虎、结义、得天书、劫法场等,本来源于民间“说话”,后来更成为民间说书中经久不衰的“公用段落”,我们在《说岳全传》《说唐全传》《说唐后传》《反唐演义传》《粉妆楼》《飞龙全传》《绿牡丹》等书中就不时可见这些关目的反复出现。
这说明在民间说书领域中,只要某些情节关目很叫座,就会变为一种“母题”,而被说书人频繁地套用在不同题材的书目中。
《水浒传》建构的“犯罪→流亡→历险→落草”与“三打某某地”“三败某某人”等叙事模式,也传递给了明清说书人,因而屡见于“说岳”“说唐”等系列说书体小说;
特别是《水浒传》通过描写梁山好汉征辽、征方腊确立的“征讨”故事范型,在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罗通扫北、狄家将征西与平南等故事中被反复运用,以至于“攻不完的关隘,打不完的城池”等变成了一种司空见惯的叙事套路。
由此可见,基于口头传统而产生的说书体小说,尽管也或多或少地经过写定者的整理、加工与改造,渗透了文人的某些思想意识和审美趣味,但其口头叙事特征依旧灼然可辨:
它们惯用夸大化、神奇化、特征化、类别化等方法塑造人物,不会讲求、甚至基本无视历史上或现实中人物性格的个性化、真实感与复杂性,因此我们便不能用个性化、真实性、典型性等美学尺度去加以品评,否则就会指责其人物描写简单化、不真实、类型化甚至脸谱化;
它们喜欢利用听众熟悉的母题与情节套路展开叙事,而不太在意人类社会矛盾斗争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而是刻意追求用惊险、曲折、奇异、可怖的故事去耸人听闻,因此我们也不宜用文人书面文学创作的标准,指责它们缺乏新颖性与独创性;
它们惯用程式化的韵文套语描景状物,而不太考虑是否与所说对象完全吻合,因此我们也不能用“写真”的眼光,或苛责它们文不对题,或以之作为考证小说作者籍贯、辨析不同文本之间先后关系等的依据。
既然如此,那么应该如何评价说书体小说呢?我们认为,评价的前提是不能将它们与文人书面创作的小说混为一谈,而要从民间说书的角度,充分考虑口头记忆、即兴创编与听众接受等实际因素的规约,在认知、理解其口头叙事规律与特征的基础上评价其艺术质量的优劣。
拿韵文套语的评价来说,从“说——听”角度看,韵文套语给听者的感觉,不仅不嫌重复,反倒觉得“游词泛韵,脍炙人口”(钱希言《戏瑕》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97册,第13页)。
不少韵文套语经过“说——听”的反复检验与艺人的不断加工,凝聚了民众的经验智慧与审美趣味,书场说唱,自然脍炙人口。
就人物形象来说,说书体小说写人是否成功,不取决其性格的个性化、真实感与典型化,而在于其是否顺应民众的道德情感,贴合民众的生活、心理和想象,由此出发,去设法模塑理想化、传奇化、类型化的人物形象,不仅不是一种缺陷,反而是其深入人心,让人喜闻乐见的主要原因。再就故事情节的评价来说,说书体小说以口述故事为本位,不可避免要用程式化的“主题”和故事范型进行叙事,其叙事水平的高低,不在于其是否新颖、独创,而在于是否能从民众的生活、情感与愿望出发去推陈出新,引人入胜。
如《水浒传》中的智取生辰纲、武松打虎、江州劫法场等,多半都有宋元话本中类似的情节描写作基础,但是《水浒传》所写更加精彩动人,后来居上;即便是在文本内部重复使用某些“母题”,如金圣叹所说,也能翻新出奇。
总之,对于《水浒传》等说书体小说,只有调整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立足于它们依托的口头传统,联系口传文学的创编规律,才能对其叙事特征作出较为确切的阐释和评价。

《民间说唱与古代小说交叉互动研究》 纪德君 著

文章作者单位:广州大学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刊于《文学遗产》,2022年第4期。转发请注明出处。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