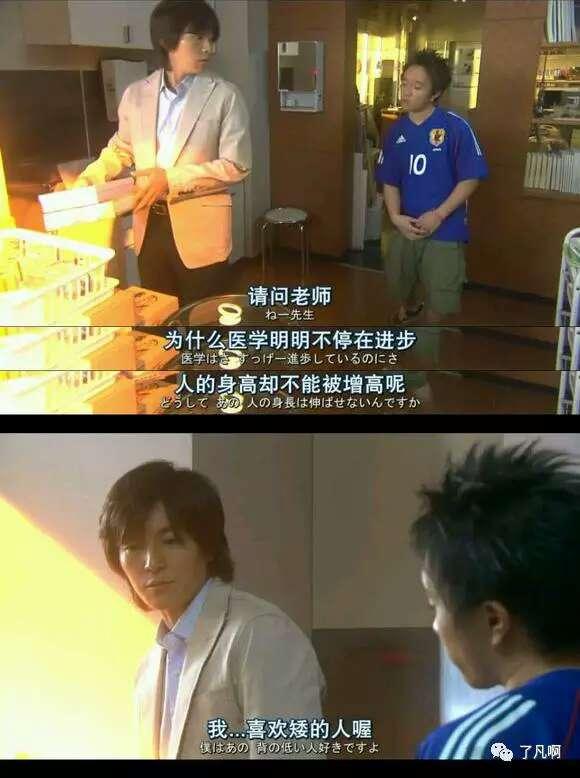周中明论金瓶梅的讽刺艺术(周中明论金瓶梅的讽刺艺术)
《金瓶梅》具有讽刺艺术的特色,这是前人早已说过的。如明代万历本《金瓶梅词话》前面廿公写的〈跋〉中,说它「曲尽人间丑态」,「盖有所刺也」。鲁迅也说它「幽伏而含讥」。[1]
香港有的研究者称:《金瓶梅》的讽刺艺术为「《儒林外史》的先河」。[2]可惜,他们皆语焉不详。
《金瓶梅》的讽刺笔法究竟表现在哪里?它有哪些特色?具有哪些优点和缺陷?认清《金瓶梅》的讽刺艺术,对于我们有着什么意义?它对于《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又有什么影响?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作深入的探讨。
一、《金瓶梅》讽刺笔法的具体表现
《金瓶梅》的讽刺笔法具体表现在哪里呢?
(一)前后映照。
如西门庆听说潘金莲与奴仆琴童有奸情,便怒气冲冲地「取了一根马鞭子拿在手里,喝令:『淫妇脱了衣裳跪着!』那妇人自知理亏,不敢不跪,倒是真个脱去了上下衣服,跪在面前,低垂粉面,不敢出一声儿。」
作者说这是「潘金莲私仆受辱。」(第 12 回)可是紧接着下一回,作者就写潘金莲发现西门庆私奸李瓶儿,她便
「一手撮着他耳朵,骂道:『好负心的贼!你昨日端的那去来?把老娘气了一夜!又说没曾住你,你原先干的那茧儿,我已是晓的不耐烦了。趁早实说,从前已往,与隔壁花家那淫妇,得手偷了几遭?一一说出来,我便罢休。但瞒着一字儿,到明日你前脚儿但过那边去了,后脚我这边就吆喝起来,教你负心的囚根子,死无葬身之地。……』
这西门庆不听便罢,听了此言,慌的妆矮子,只跌脚跪在地下。笑嘻嘻央及说道……」
两者都因偷情而受责备,两人都跪在地下。
一对奸夫淫妇,既然本是一路货,他们又有什么理由互相斥责,有什么权利要求对方忠贞不二呢?可是他们却说得振振有词,做得煞有介事。
两者前后映照,更显出了他们那恬不知耻的卑劣灵魂,毫无人的尊严的丑恶形骸,叫人感到实在可鄙而又可笑!
前后映照,既不是两个相似的故事情节简单并立,也不是两个相类的人物形象机械重复,而是既要揭示出故事情节的必然发展,又要进一步丰富人物的典型性格,使作品的思想意义得到深化,在艺术上也更富有魅力。
如西门庆对潘金莲与琴童的奸情的审问,尽管凶神恶煞,气势逼人,但最终却被潘金莲的花言巧语蒙混过去了。而潘金莲对西门庆与李瓶儿的奸情的审问,却轻而易举地就迫使西门庆供认不讳。
因此这两者的前后映照,给人毫无重复累赘之感。它既反映了故事情节的进一步发展,又活画出各自不同的典型性格─潘金莲的偷情似乎理应受辱,而西门庆的偷情却可满不在乎;潘金莲的下跪是畏惧、无奈、可怜,西门庆的下跪则是装佯、撒娇、可鄙。
它使读者在对这一对奸夫淫妇感到可耻可笑的同时,不能不进而深切地感受到:在旧社会,妇女的命运实在是尤为悲惨的。
类似这种前后映照的笔法,在《金瓶梅》中是屡见不鲜的。如潘金莲和李瓶儿先后皆遭西门庆用马鞭子毒打;宋惠莲的金莲赠送给西门庆,潘金莲的金莲则遗失给陈经济;有个潘六儿,又有个王六儿,李桂姐拜西门庆为干女儿,西门庆又拜蔡太师为干儿子,这些加以前后映照,都无不具有讽刺的意味。
它使对象既丰富化,又深刻化,使那些本来易于被忽略而溜过去的东西,变得惹人注目和发人深思起来。
诚如张竹坡在第五十五回批语中所指出的:「写桂姐假女之事方完,而西门假子之事乃出,递映丑绝。吾不知作者有何深恶于太师之假子而作此以丑其人,下同娼妓之流。文笔亦太刻矣。」
这种「下同娼妓之流」,显然是由前后映照所生发出来的意蕴,这种文笔的「太刻」,也正是前后映照所产生的讽刺效应。

皋鹤堂本
(二)是非颠倒。
如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曾孝序,经过一年的调查访问,在给皇帝的参本中指出:
「理刑副千户西门庆:本系市井棍徒,夤缘升职,滥冒武功,菽麦不知,一丁不识。纵妻妾嬉游街巷,而帷薄为之不清;携乐妇而酣饮市楼,官箴为之有玷。至于包养韩氏之妇,恣其欢淫,而行检不修;受苗青夜贿之金,曲为掩饰,而赃迹显著。」
是「贪鄙不职,久乖清议,一刻不可居任者也。」(第 48 回)尽管曾孝序的参本「颇得其实」,但是经过西门庆向蔡太师行贿后,不但曾孝序被撤职「除名」(第 49 回),而且在兵部的考察官员照会中,名为「尊明旨,严考核,以昭劝惩,以光圣治事」,实则竟颂扬「理刑副千户西门庆,才干有为,英伟素着,家称殷实而在任不贪,国事克勤而台工有绩,翌神运而分毫不索,司法令而齐民果仰,宜加转正,以掌刑名者也。」(第70 回)
「菽麦不知,一丁不识」,被称为「才干有为」;「滥冒武功」,被颂扬为「英伟素着」;「赃迹显著」,被说成是「在任不贪」;「贪鄙不职」,被描绘成「台工有绩」;「一刻不可居任者」,顷刻变为「宜加转正」,提拔重用的对象。
混淆黑白到如此地步,颠倒是非至这般程度,不仅对那个封建黑暗统治是个莫大的讽刺,而且它以鲜明的对比,有力的反衬,足以引起读者心灵的震惊,激起愤怒的火焰,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
好在作者还用颠倒是非的讽刺笔法,生动地刻画出了被讽刺者的形象。
如西门庆在获悉曾孝序的参本而派人赴京行贿后,跟西门庆狼狈为奸的夏提刑,特地前来感谢西门庆的「活命之恩」,说:「不是托赖长官余光,这等大力量,如何了得!」而西门庆竟笑着说:「长官放心。料着你我没曾过为,随他说去便了,老爷那里自有个明见。」(第49 回)
分明是因贪赃枉法、胡作非为被弹劾而去行贿的,而西门庆却装得很坦然地说:「你我没曾过为,随他说去便了」;事实是因受贿而蓄意庇护,而西门庆却称颂为这是老爷自有「明见」。
如此颠倒是非,而又泰然自若,它不仅对那个腐朽黑暗的社会是个有力的讽刺,而且以西门庆本人的寥寥数语,就把他那个无耻之徒的卑鄙灵魂和有恃无恐的丑恶嘴脸,都惟妙惟肖地刻画出来了。
因此,这种是非颠倒,绝不是作者任意颠之倒之,故作惊人之笔,而是看似荒谬透顶,实则适度得体。
因为它文笔透骨地活现了作者所要刻画的那种丑恶的人物性格,洞隐烛微地再现了作者所要反映的那个黑暗的时代,所以它能够在激起我们的愤慨之余,以一种极其真实、强大的力量叩动我们的心弦,似乎在从一个最黑暗、最可怕的幽灵身上,要把人类的本性和良知召唤回来。

绘画 · 西门庆
(三)表里不一。
如西门庆到王招宣府去勾搭林太太,作者特地写了那个王招宣府外表如何标榜节义;
「正面供养着他祖爷太原节度邠阳郡王王景崇的影身图,穿着大红团袖蟒衣玉带,虎皮校椅坐着观看兵书,有若关王之像,只是髯须短些。傍边列着枪刀弓矢。迎门朱红匾上『节义堂』三字;两壁书画丹青,琴书潇洒;左右泥金隶书一联:『传家节操同松竹;报国勋功并斗山。』」(第 69 回)
住在这个王招宣府的女主人林太太,「诚恐抛头露面,有失先夫名节」,而实际上却「是个绮阁中好色的娇娘,深闺内的菩萨。」
她通过媒婆文嫂牵线搭桥,滥肆淫欲。明知西门庆「是个富而多诈奸邪辈,压善欺良酒色徒」,她却「一见满心欢喜」,顷刻勾搭成奸,还教其子王三官拜西门庆做了义父,要西门庆凡事指教他「为个好人」。
作者随即作诗感叹道:「三官不解其中意,饶贴亲娘还磕头。」「不但悖得家声丧,有愧当时节义堂。」(第 72 回)
这种表里不一的鲜明对照,把封建礼教的虚伪、堕落,讽刺得该是多么剔肤见骨啊!
把西门庆和林太太那种臭味相投,表面上极力打扮成正人君子,实际上却是彻头彻尾的男盗女娼,揶揄得该是多么妍媸毕见、令人瞠目啊!
这种表里不一的讽刺笔法,不是停留在对社会丑恶现象的谴责上,不是满足于个人愤怒情绪的发泄,而是揭露了那个时代礼教已经虚伪的通病,从被讽刺者身上反映了那个社会腐朽的阶级根源,给人以一种深广而真实的历史感。
如林太太之所以那么淫荡无度,西门庆那样的淫棍所以能横行无忌,作者都不只是停留在对他们个人的谴责上,而是与《金瓶梅》开卷第一回所写的潘金莲的出身经历相呼应的。
潘金莲「从九岁卖在王招宣府里,习学弹唱,就会描眉画眼,傅粉施朱,梳一个缠髻儿,着一件扣身衫子,做张做势,乔模乔样。」
潘金莲的淫荡性格,可以说就是王招宣府培养出来的。张竹坡在〈金瓶梅读法〉中便指出:
「王招宣府内,固金莲旧时卖入学歌学舞之处也。今看其一腔机诈,丧廉寡耻,若云本自天生,则良心为不可必,而性善为不可据也。吾知其自二、三岁时,未必便如此淫荡也。
使当日王招宣家,男敦礼义,女尚贞廉,淫声不出于口,淫色不见于目,金莲虽淫荡,亦必化而为贞女。奈何堂堂招宣,不为天子招服远人,宣扬威德,而一裁缝家九岁女孩至其家,即费许多闲情教其描眉画眼,弄粉涂朱,且教其做张做致,乔模乔样。
其待小使女如此,则其仪型妻子可知矣。宜乎三官之不肖荒淫,林氏之荡闲踰矩也。招宣实教之,夫复何尤。」
可见这种表里不一,道德败坏,实肇始于王招宣本人,而不只是其遗孀和儿子;罪魁祸根是在于王招宣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本身已经腐朽溃烂,以致流毒四溢,贻害无穷。

《新刻金瓶梅词话》
(四)言行相悖。
西门庆有六个妻妾,还到处奸人妻女,先后被他淫过的妇女多达二十人。妓女李桂姐被他每月三十两银子包着。诚如妓院李虔婆所说的:「你若不来,我接下别的,一家儿指望他为活计。吃饭穿衣,全凭他供些籴米。」
可是当李桂姐接了客人丁二官,西门庆便「大闹丽春院」,「一手把吃酒桌子掀倒,碟儿盏儿打的粉碎,喝令跟马的平安、玳安、画童、琴童四个小厮上来,不由分说,把李家门窗户壁床帐都打(第 20 回)后来获悉王三官一伙人又与李桂姐鬼混,西门庆更进一步利用职权,碎了。」
捉拿王三官的同伙,说:「你这起光棍,设骗良家子弟,白手要钱,深为可恶!既不肯实供,都与我带了衙门里收监,明日严审取供,枷号示众。」回家后,西门庆与吴月娘谈起王三官嫖妓女李桂姐一事,还一本正经地议论:
「人家倒运,偏生出这样不肖子弟出来。你家父祖何等根基,又做招宣,你又见入武学,放着那名儿不干,家中丢着花枝般媳妇儿,─自东京六黄太尉侄女儿。
─不去理论,白日黑夜,只跟着这伙光棍在院里嫖弄,把他娘子头面都拿出来使了。今年不上二十岁,年小小儿的,通不成器。」
月娘当场就揭穿他:「你不曾潜胞尿看看自家,乳儿老鸦笑话猪儿足,原来灯台不照自。你自道成器的,你也吃这井里水,无所不为,清洁了些甚么儿?还要禁的人!」
以西门庆本人的行为,揭穿他的本性「原来灯台不照自」,─自己同样嫖妓女,不仅有脸禁别人,还有脸摆出一副「自道成器的」架势。这把西门庆的恬不知耻,讽刺得简直无地自容!难怪作者写道:月娘「几句说的西门庆不言语了。」(第 69 回)
好在这种言行相悖的讽刺笔法,并不是径直让被讽刺者夸夸其谈,撒谎吹牛,而是传神入化地刻画出那自身遍体疮痍,而又指责别人嗜痂逐臭的被讽刺者的形象。
作者为了催人以他所塑造的被讽刺者作为一面镜子,照照自己,特地安排了个「磨镜老叟」来西门家磨镜的情节,还生动地刻画了又一个「灯台不照自」的陶扒灰的形象。
当众人都在围观韩道国妇人与小叔因通奸而被人拴做一处时,有个老者
「便问左右站的人:『此是为什么事的?』旁边有多口的道:『你老人家不知,此是小叔奸嫂子的。』那老者点了点头儿,说道:『可伤!原来小叔儿要嫂子的,到官,叔嫂通奸,两个都是绞罪。』
那旁多口的,认的他有名叫做陶扒灰,一连娶三个媳妇,都吃他扒了,因此插口说道:『你老人家深通条律,想这小叔养嫂子的便是绞罪,若是公公养媳妇的却论什么罪?』那老者见不是话,低着头,一声儿没言语走了。」(第 33 回)
可见「灯台不照自」的,绝不只是西门庆一个人,而是在那个社会带有一定普遍性的病症。
陶扒灰之被羞得低头无言,赧然而去,对于某些人来说,犹如当头棒喝,使其不能不猛醒;犹如一架明镜,使其不能不照一照自己的原形。
以上几种讽刺笔法的共同特质,皆不是简单地肤浅地罗列一些可笑的怪现状,加以斥责或谩骂,而是利用现象和本质、理想和现实、真理和谬误、对人和对己等等社会生活中固有的矛盾,以这一思想和那一思想的脱节,这一感情和那一感情的冲突,这一表现方式和那一表现方式的雷同,来达到使其曲尽丑态、原形毕露的讽刺效果。
因此,这种讽刺笔法能够极其清醒、深刻、准确、犀利地揭穿被讽刺者的本质,既不同于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的嬉笑怒骂,又有别于居高临下、庄严肃穆的揭露、批判。
它是愤怒和轻蔑的结合体,在鄙视中进行愤怒的挞伐,在挞伐时又给人以幽伏含讥、不屑于顾的轻松之感。

《金瓶梅的艺术》
二、《金瓶梅》讽刺艺术的鲜明特色
由于运用了上述种种讽刺笔法,这就使《金瓶梅》具有讽刺艺术的鲜明特色。
用平常人、平常事、平常话,来曲尽人间丑态,这是《金瓶梅》讽刺艺术的显著特色之一,也是它的讽刺艺术达到现实主义高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我国,「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3]但总「不离于搜奇记逸」。[4]
《西游补》《钟馗捉鬼传》所塑造的精魅鬼怪,更是以奇幻为讽刺特色的。用平常人、平常事、平常话来进行讽刺,实在是《金瓶梅》的一大创造,是《金瓶梅》对中国小说历史发展的杰出贡献。
因为它用的是平常人、平常事、平常话,这就更加具有真实感。正如鲁迅所说的:
「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发阴司』,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
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
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5]
《金瓶梅》的讽刺艺术便具有这个特色。如它写西门庆正当与潘金莲打得火热的时候,一听媒婆薛嫂来介绍寡妇孟玉楼如何既有钱又漂亮,便把娶潘金莲的事抛在一边,迫不及待地「就问薛嫂儿:『几时相会去?』」薛嫂儿随即领他到孟玉楼处相亲。
「西门庆把眼上下不转睛看了一回。妇人把头低了。西门庆开言说:『小人妻亡已久,欲娶娘子入门为正,管理家事。未知意下如何?』」
此时孟玉楼不作正面回答,而是反「问道:『官人贵庚?没了娘子多少时了?』」这看似叉开话题,实则既曲折地活现了她的忸怩作态,又隐约地表明了她对嫌她年龄大的耽心。
西门庆答道:「小人虚度二十八岁,七月二十八日子时建生。不幸先妻没了一年有余。不敢请问娘子青春多少?」
孟玉楼说:「奴家青春是三十岁。」
西门庆道:「原来长我二岁。」虽未明说,但话语之间已流露出大为惊讶的口气和有所不满的神态。因为薛嫂向西门庆介绍孟玉楼的年龄是「不上二十五六岁。」
由比西门庆小二岁变成大二岁,这已把媒婆薛嫂惯于扯谎的嘴脸暴露无遗了。
然而这时薛嫂却不但毫无羞愧之色,反而巧舌如簧地「在傍插口道:『妻大两,黄金日日长;妻大三,黄金积如山。』」
说着,又「慌的薛嫂向前用手掀起妇人裙子来,裙边露出一对刚三寸恰半扠,一对尖尖趫趫金莲脚来,穿着大红遍地金云头白绫高底鞋儿,与西门庆瞧。」
这既迎合了西门庆爱财如渴的贪婪心理,又契合他那偏爱妇女金莲脚的低级趣味,自然使「西门庆满心欢喜」。
当场西门庆就拿出宝钗、金戒等定婚礼品,孟玉楼便问:「官人行礼日期?奴这里好做预备。」
西门庆道:「既蒙娘子见允,今月二十四日,有些微礼过门来。六月初二日准娶。」(第 7 回)一桩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人物、事情和语言,无一不是平平常常,字字句句皆令人感到真实可信。
然而,写平常人、平常事、平常话,这是一般现实主义作品共同的特色;《金瓶梅》的独特之处,是在于它能以此「曲尽人间丑态」,从平常之中写出不平常的「可笑,可鄙,甚至于可恶」的人物性格来。如西门庆的贪婪和庸俗,一听「黄金积如山」,一见「尖尖趫趫金莲脚」,猝然就由惊变喜,已经够引人可笑的了,更令人可鄙的是他的虚伪和卑劣,明明自家有妻有妾,却对孟玉楼谎称:「小人妻亡已久,欲娶娘子入门为正。」
薛嫂在谎言被事实揭穿后,还厚颜无耻地以她那如簧之舌和「掀起妇人裙子来」等丑恶表演,使这桩婚事得以当场撮合,岂不也显得很可笑么?
孟玉楼的表现像煞很赧颜、持重,实际上她听任薛嫂掀起自己的裙子,当场急于询问:「官人行礼日期?」这已经把她的赧颜、持重,瞬间化成了忸怩作态,显得很可笑了,何况她初次与西门庆相见,连西门庆已有妻妾全不了解,便乐于接受他的婚礼,草草定下婚事。因此,她给人的感受,确属「虽非蠢妇人,亦是丑妇人」。[6]

戴敦邦绘 · 孟玉楼
讽刺艺术,必须像《金瓶梅》这样建立在极平常的如实描写之中。
对于这条宝贵的艺术经验,并非已经为后代作家所普遍理解和接受了,追求「怪现状」的谴责小说之不能与讽刺小说同伦,便是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金瓶梅》的这种讽刺艺术特色,虽然平常、真实得「似真有其事,不敢谓为操笔伸纸做出来的。」[7]
但它又绝不是生活的实录,而确实是「操笔伸纸做出来的」,只不过它是以日常的真实生活为基础,并且需要作家有很敏锐的眼力和很高超的写实技巧才能做到的。正如果戈理所说的:
「那些每天围绕我们的,跟我们时刻不离的、平平常常的东西,只有深厚的、伟大的、不平常的天才才能觉察,而那些稀有的、成为例外的,以其丑陋和混乱引人注意的东西,却被中庸之才双手抓住不放。」[8]
鲁迅也说:「在或一时代的社会里,事情越平常,就越普遍,也就愈合于作讽刺。」[9]
在谈到果戈理的《死魂灵》的讽刺艺术时,他还说,「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10]可见越是平常、越是难写,而又越是具有普遍的典型意义。
寓庄于谐,悲剧的实质,而又具有喜剧的色彩。这是《金瓶梅》的讽刺艺术的又一显著特色。
《金瓶梅》是怎样做到寓庄于谐的呢?它在诙谐的喜剧性的形式中,寄寓着庄严的悲剧性的思想内容;以对丑恶事物的嘲笑、耻笑、讪笑、冷笑,来寄托作者给予无情鞭挞和悲愤痛绝的感情。谐趣有理趣、情趣、意趣、语趣等多种。
《金瓶梅》作者正是利用不同的谐趣,来引起不同感情色调的笑,达到既「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又「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11]其具体表现:
(一)用以正衬反的理趣,来进行辛辣的嘲笑。
如西门庆抨击他的上司夏提刑说:「只吃了他贪滥婪的,有事不问青水皂白,得了钱在手里就放了,成什么道理!我便再三扭着不肯,『你我虽是个武职官儿,掌着这刑条,还放些体面才好。』」
可是正当他发表这个高论之时,他却正在和应伯爵一起喝着受贿的木樨荷花酒,吃着受贿的糟鲥鱼等佳肴,感到「馨香美味,入口而化,骨刺皆香。」
接着他又徇情枉法,包庇通奸的叔嫂韩二和王六儿,反把捉奸的四人「打的皮开肉绽,鲜血迸流。」(第 34 回)作者以西门庆的卑劣行为和他所讲的大道理相对照,岂不使他显得很滑稽可笑么?这是辛辣的嘲笑。
它不只是针对西门庆一个人,而且也是针对着整个封建官僚阶级。正如张竹坡在该回的回批中所指出的:
「提刑所,朝廷设此以平天下之不平,所以重民命也。看他朝廷以之为人事,送太师;太师又以之为人事,送百千奔走之市井小人。
而百千市井小人之中,有一市井小人之西门庆,实太师特以一提刑送之者也。今到任以来,未行一事,先以伯爵一帮闲之情,道国一伙计之分,将直作曲,妄入人罪,后即于我所欲入之人,又因一龙阳之情,混入内室之面,随出人罪。是西门庆又以所提之刑为帮闲、淫妇、幸童之人事。
天下事至此,尚忍言哉!作者提笔着此回时,必放声大哭也。」
可是作者这种「放声大哭」的感情,其表达方式,却不是以令人声泪俱下的悲剧性场面,而是通过以正衬反的喜剧性冲突,把他笔下的人物刻画得非常滑稽可笑,从而达到对其进行辛辣讽刺的目的。

《鲁迅全集》
(二)用以雅衬俗的情趣,来进行奚落的耻笑。
如西门庆要和宋惠莲在潘金莲房里奸宿一夜,潘不肯,西门庆又说:
「我和他往那山子洞儿那里过一夜。你分付丫头拿床铺盖,生些火儿那里去。不然,这一冷怎么当?」
「金莲忍不住笑了,『我不好骂出你来的!贼奴才淫妇,他是养你的娘。你是王祥寒冬腊月行孝顺,在那石头床上卧冰哩!』」(第 23 回)
王祥是古代著名的孝子。他因为母亲要吃鲤鱼,便不惜卧冰求鲤。
这种「孝」的感情,在封建社会是很高雅的。因此它成为我国民间流传千古的美谈。而西门庆为了与奴才妻子宋惠莲奸宿,则不怕石头的冰冷,睡在山洞里,其感情的庸俗、卑下,已足以令人嗤之以鼻,再加上通过潘金莲嬉笑他是王祥卧冰,以雅衬俗,更在盎然的情趣中,达到了作者对西门庆进行奚落地耻笑的艺术效果。
(三)用譬喻、象征的意趣,来进行鄙夷的讪笑。
如潘金莲被吴月娘撵出西门家,在王婆家等待发卖的几天之中,却又和王婆的儿子王潮儿刮刺上了。
「晚间等的王婆子睡着了,妇人推下炕溺尿,走出外间床子上,和王潮儿两个干,摇的床子一片响声。被王婆子醒来听见,问那里响。
王潮儿道:『是柜底下猫捕的老鼠响。』王婆子睡梦中,喃喃吶吶,口里说道:『只因有这些麸面在屋里,引的这扎心的半夜三更耗爆人,不得睡。』
良久,又听见动旦,摇的床子格支支响,王婆又问那里响。
王潮道:『是猫咬老鼠,钻在炕洞底下嚼的响。』婆子侧耳,果然听见猫在炕洞里咬的响,方才不言语了。」
接着,作者写道:
「有几句双关,说得这老鼠好:你身躯儿小,胆儿大,嘴儿尖,忒泼皮。见了人藏藏躲躲,耳边厢叫叫唧唧,搅混人半夜三更不睡。不行正人伦,偏好钻空隙。更有一桩儿不老实:到底改不了偷馋抹嘴。」(第 86 回)
这里作者显然是以老鼠的好「搅混人」,「偷馋抹嘴」,比喻潘金莲的偷淫;以老鼠的丑态,象征和讽刺潘金莲的卑劣。
令人感到颇有意趣的是,它不同于一般诗文通常那种对比喻词语和象征手法的运用,而是巧妙地把所谓老鼠的活动,纳入到他们掩盖偷淫行径的具体情节之中,使读者在幽默的意趣之中,对潘金莲的偷淫成性,不禁发出鄙夷的讪笑,给予刺骨的讥讽。

《金瓶梅词话》
(四)用打诨、解嘲的语趣,来进行愤怒的冷笑。
如西门庆与他的亲家陈洪等人一起,被人向朝廷控告为「皆鹰犬之徒,狐假虎威之辈,揆置本官,倚势害人;贪残无比,积弊如山;小民蹙额,市肆为之骚然。乞勅下法司,将一干人犯,或投之荒裔,以御魑魅;或置之典刑,以正国法,不可一日使之留于世也。」
西门庆闻讯后,急忙派人赴京,给主办此案的右相兼礼部尚书李邦彦送上五百两银子。
作者既不说西门庆送礼金,也不云李邦彦受贿赂,而是写道:「邦彦见五百两金银只买一个名字,如何不做分上,即令左右抬书案过来,取笔将文卷上西门庆名字改作贾庆;一面收上礼物去。」(第 18 回)
明明是贪赃纳贿,目无王法,包庇犯罪,却竟以打诨、解嘲的口气,写成「五百两金银只买一个名字」,这语句该是多么滑稽有趣!而在这看似打诨、解嘲的语趣之中,实则却寄寓著作家愤怒的冷笑,令人对这般奸臣赃官欲杀、欲割,犹难解恨。
妙在这种打诨、解嘲,绝不是作者外加上去的,而是既符合特定人物的性格,又达到了作者给予愤怒冷笑的目的。
又如西门庆死后,他店里的伙计韩道国跟他的老婆王六儿商议,要把西门庆家的一千两银子「拐了上东京。」
韩道国说:「争奈我受大官人好处,怎好变心的,没天理了。」
他老婆道:「自古有天理倒没饭吃哩!他占用者老娘,使他这几两银子不差甚么。」(第 81 回)
天理良心,向来是人们所追求的,而王六儿却说:「自古有天理倒没饭吃哩」,这该是多么滑稽可笑而又富有惊世骇俗的语趣啊!这不只是王六儿对拐银行为的辩解,更重要的是作者以极其悲愤之情,对那个黑暗社会的有力鞭挞和嘲讽;它所引起的是一种令人无比愤怒的冷笑。
这些寓庄于谐的讽刺艺术特色,不仅好在荒唐滑稽的形式之中寄寓着严肃深刻的思想内容,使诙谐滑稽耐人寻味,发人深省,而不是庸俗、油滑,使人生厌;
更重要的,它还好在既塑造出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被讽刺者的形象,又显示了讽刺者尖锐、犀利的目光和幽默、写生的艺术才能,而不是停留在对奇形怪状的社会现象的谴责和谩骂上。
因此,它能使现实丑恶、令人悲愤的不快之感和艺术美的快感相沟通。《金瓶梅》所描写的人物,几乎都是丑恶不堪、令人不快的。
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
「丑在滑稽中我们是感到不快的;我们所感到愉快的是,我们能够这样洞察一切,从而理解,丑就是丑。既然嘲笑了丑,我们就超过它了。」
「那种不快之感几乎完全被压下去了。」[12]
三、《金瓶梅》的讽刺艺术存在的缺陷
用平常人、平常事、平常话,创造寓庄于谐的讽刺艺术,这在《金瓶梅》以前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既然是首次独创的新生命,它在令人欣喜、庆幸之余,就难免还存在着许多的稚气,乃至严重的缺陷。
我们在充分肯定《金瓶梅》的讽刺艺术成就的同时,对于它在讽刺艺术上所存在的严重缺陷,也必须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
首先,由于作者世界观的矛盾,大大削弱了《金瓶梅》讽刺艺术的思想深刻性。如作者一方面同情妇女被蹂躏、被玩弄的命运,认为:「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第 12 回、第 38 回)「堪悼金莲诚可怜。」(第 87 回)
另一方面,又受「女人是祸水」的封建历史观的影响,宣扬「由来美色丧忠良。纣因妲己宗祀失,吴为西施社稷亡。」(第 4 回)「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第 79 回)一方面讽刺了一夫多妻制所造成的重重矛盾,另一方面又不否定一夫多妻制。
一方面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认为世上农夫、商人、兵士最怕热,皇宫内院、富室名家、琳宫梵剎最不怕热;另一方面,又肯定封建等级制度,认为「尊卑上下,自然之理。」(第 89 回)
一方面对世俗的许多丑恶现象,进行了尖刻的讽刺,如常时节得钞傲妻;另一方面,作者本人又未免陷入世俗之见,如在讽刺陶扒灰不能灯台自照之后,却又写道:「正是:各人自扫檐前雪,莫管他家屋上霜。」(第 33 回)
作者世界观上的这种种矛盾,就必然使他的讽刺锋芒难以触及到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本质,而往往停留在酒色财气等社会现象上。
用《金瓶梅》作者的话来说:「色是伤人剑」,「积财惹祸胎。」(第 79 回)「妾妇索家,小人乱国,自然之道。」(第70 回)
因此他所讽刺的对象,主要是「妾妇」和「小人」,「财」和「色」,而不是社会制度和反动阶级的阶级本质。《金瓶梅》中所以充斥着淫秽色情的描写,除了鲁迅所说的在当时「实亦时尚」[13]
之外,我看这跟作者把好色这种社会病态,错误地当作社会病根,把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堕落,错误地归咎于商品经济的繁荣─「财宝祸根荄」(第 56 回)这种形而上学的唯心史观,是分不开的。
在他之后一个多世纪产生的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虽然也不可能把讽刺的矛头指向整个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阶级,但它毕竟是把讽刺社会丑恶现象上升到否定封建科举制度的高度,在作家的思想高度和讽刺的深刻性上,毕竟比《金瓶梅》前进了一大步。

《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
其次,由于作者缺乏鲜明、强烈的爱憎感情,在他的讽刺对象中,有一些是属于某些基本上善良的普通人或被压迫者,讽刺得未免过于冷酷和尖刻,使人不是产生快感,而是感到痛心,甚至对其真实性产生怀疑。
如荒淫不堪的陈经济残酷迫害他的妻子西门大姐,「一把手采过大姐头发来,用拳撞、脚踢、拐子打,打得大姐鼻口流血,半日苏醒过来,这经济便归娼的房里睡去了,由着大姐在下边房里,呜呜咽咽只顾哭泣。」
半夜,「用一条索子悬梁自缢身死,亡年二十四岁。」连作者也说:「可怜大姐」。
可是作者接着写次日早晨,陈经济骂西门大姐:「贼淫妇,如何还睡,这咱晚不起来!我这一跺开门进去,把淫姐鬓毛都拔净了。」
此时,却用戏谑、讽刺的笔调,写丫头「重喜儿打窗眼内望里张看,说道:『他起来了,且在房里打秋千耍子儿哩。』又说:『他提偶戏耍子儿。』」(第 92 回)
对一个被迫害而上吊自杀的善良妇女,怎么能用这种语言来讽刺她呢?这岂不比陈经济对她的毒打和摧残更令人可恶么?
如果说丫头重喜儿说这种话是由于在窗眼内未看清楚,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作者对西门大姐的被迫上吊自杀是看得很清楚的,又为什么要让重喜儿说出这种冷酷无情而又令人极其反感的话来呢?这就使人不能不怀疑,西门大姐的被迫自杀,究竟是可怜还是可笑?
讽刺的生命是真实。而要真实,就必须根据讽刺的对象,正确掌握讽刺的分寸,绝不能不分对象,乱加讽刺,使亲者痛,仇者快。在《金瓶梅》中,便存在着这种缺陷。
如第五十八回写有个磨镜老叟,在替孟玉楼、潘金莲磨完镜子,收了工钱之后,还只顾立着不去。
玉楼便叫来安问其原因,老汉哭着说他已经六十一岁,家有五十五岁的老妻,因儿子赌钱,「归来把妈妈的裙袄都去当了,妈妈便气了一场病,打了寒,睡在炕上半个月。」
「如今打了寒才好些,只是没将养的,心中想块腊肉儿吃」,街上又买不到。因此,孟玉楼就送了他一块腊肉,潘金莲也送了他二升小米,两个酱瓜茄。
这一切在我们看了都感到真实可信、深表同情的时候,作者却指出,原来「他妈妈子是个媒人,昨日打这街上走过去不是,几时在家不好来!」
因而他通过来安当场讥笑磨镜老叟:「你家妈妈子不是害病想吃,只怕害孩子坐月子,想定心汤吃。」
如果说在这个磨镜老叟身上,寄寓著作者对磨镜者自己却不用镜子照照自己,干着扯谎行骗的勾当,这对揭示全书的寓意还有其一定的作用的话,那么,书中并未写他的老伴有什么丑行,为什么又讥笑他那个五十五岁的老妈妈子「害孩子坐月子」呢?这就未免是对于讽刺的使用不当,而使读者产生反感了。
《金瓶梅》的有些讽刺描写,显得过于浅露,这也使人感到不够真实可信。如写有个太医,竟然会在病家面前自道:
我做太医姓赵,门前常有人叫。只会卖杖摇铃,那有真材实料。行医不按良方,看脉全凭嘴调。
撮药治病无能,下手取积儿妙。头疼须用绳箍,害眼全凭艾醮。心疼定敢刀剜,耳聋宜将针套。
得钱一味胡医,图利不图见效。寻我的少吉多凶,到人家有哭无笑。(第 61 回)
世上尽管有这种靠行骗为生的医生,但绝不会像赵太医这样「自报家门」。这是作者为了制造讽刺的笑料而杜撰出来的。
可惜这种笑料不仅过于浅露,而且已落入油腔滑调,够不上讽刺艺术了。
《金瓶梅》还有些讽刺描写,虽然没有油腔滑调的弊病,但由于作者未能抓住客观事物本身固有的矛盾,为讽刺而讽刺,这也必然使人感到不够真实。
如在「群僚庭参朱太尉」的场合,作者让五个俳优,面对贪赃枉法的群僚和朱太尉,唱了李开先《宝剑记》第五十出的一套曲词,在曲词中痛骂,
「你有秦赵高指鹿心,屠岸贾纵犬机。待学汉王莽不臣之意,欺君的董卓燃脐。但行动弦管随,出门时兵杖围。入朝中为官悚畏,仗一人假虎张威。望尘有客趋奸党,借剑无人斩佞贼,一任的忒狂为。」
「南山竹罄难书罪,东海波干臭未遗。万古流传,教人唾骂你!」
「当时酒进三巡,歌吟一套,六员太尉起身。朱太尉亲送出来,回到厅,乐声暂止。」(第 70 回)
始终无人对唱这套曲词提出任何责难。这对那些官僚的昏愦、麻木,贪赃枉法而自觉若无其事,固然是个辛辣的嘲笑。
然而这又毕竟使人感到太失真了,因为那班官僚怎么能听任自己挨骂而装聋作哑或颟顸无知到如此地步呢?这如同疯狗挨打而一声也不狂吠那样,令人太难以置信了。
讽刺是以带喜剧性的艺术手段揭示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因此,作家首先必须把握住生活中矛盾的实质,才能使讽刺艺术具有真实动人的力量。
同时,还必须对于丑恶事物有满腔的仇恨,才能燃起讽刺的烈火;必须对于美好事物有必胜的信念,才能产生对丑恶事物的极度蔑视;必须有鲜明、强烈的爱憎感情,掌握好对不同对象、不同性质问题的分寸,才能使讽刺艺术得到恰到好处的运用。

《宝剑记》
再次,由于作者缺乏高尚的审美趣味,使《金瓶梅》中还有一些讽刺描写,显得过于粗野、低级,甚至沦为庸俗、下流,读了不仅难以引起美感,而且反而令人恶心。如西门庆在和李瓶儿淫乐时说:「我的心肝,你达不爱别的,爱你好个白□□儿。」这话被潘金莲偷听到了。
当西门庆要用茉莉花肥皂洗脸时,作者就通过潘金莲讽刺道:「我不好说的,巴巴寻那肥皂洗脸,怪不的你的脸洗的比人家的屁股还白。」(第 27 回)
这无异于讥讽西门庆爱李瓶儿的白□股,就如同爱自己的脸一样;虽然讽刺得很尖刻,但已未免流于形同粗野的谩骂了。
还有一次,西门庆、应伯爵和妓女韩金钏等一起在郊园饮酒作乐。席间,
「那韩金钏吃素,再不用荤,只吃小菜。
伯爵道:『今日又不是初一月半,乔作衙甚的。当初有一个人,吃了一世素,死去见了阎罗王,说:我吃了一世素,要讨一个好人身。阎王道:那得知你吃不吃,且割开肚子验一验。割开时,只见一肚子涎唾。原来平日见人吃荤,咽在那里的。』众人笑得翻了。
金钏道:『这样捣鬼,是那里来!可不怕地狱拔舌根么?』
伯爵道:『地狱里只拔得小淫妇的舌根,道是他亲嘴时,会活动哩!』」
因李瓶儿病重,西门庆被书童叫回去了。接着作者便写:
「一个韩金钏,霎眼挫不见了。伯爵蹑足潜踪寻去,只见在湖山石上撒尿,露出一条红线,抛却万颗明珠。
伯爵在隔篱笆眼,把草戏他的牝口。韩金钏尿也撒不完,吃了一惊,就立起,裩腰都湿了。
骂道:『贼短命,恁尖酸的没槽道!』面都红了,带笑带骂出来。伯爵与众人说知,又笑了一番。」(第 54回)
万历词话本原回目是「应伯爵郊园会诸友」。「第一奇书」本特地把它改成「应伯爵隔花戏金钏」。
张竹坡并在回批中指出:
「盖伯爵戏金钏,明言遗簪坠珥,俱是相思,隔花金串,行当入他人之手,是瓶儿未死已先为金梅散去一影。然瓶儿一死,亦未尝不有隔花人远天涯近意。是此一回既影瓶儿,复遥影莲摧梅谢。」
这是从象征、影射的角度来看的,未免有深文周纳、不切实际之嫌。
我看这不是属于象征手法,而是讽刺手法,是韩金钏对应伯爵讥笑她假吃素、会亲嘴的反击,是以妓女撒尿尚有槽道,来反衬、讥刺应伯爵「恁尖酸的没槽道」。
且不管是象征或讽刺,用妇女撒尿来加以戏谑,这实在是太低级、下流了!无论象征得多么寓有深意,或讽刺得多么尖酸刻薄,叫人看了都只能感到是个恶作剧,而绝无美感可言。
讽刺艺术是打击社会中的丑恶现象的有力武器。并且它不是一般地揭露和鞭挞丑类,而是要更为清醒、更为理智地解剖丑类。
因此,它是严肃的艺术,需要有崇高的审美理想,对丑类的灵魂具有洞察秋毫的透视力,这样才能不仅更有力量,而且也更为轻松愉快地给予丑类以深刻的讽刺。
可笑是由轻松愉快而引起的。因此,这种轻松愉快不是轻佻浅薄,更不是轻狂下作,而是一种力量的表现。它显示了美的优越和丑的渺小,需要经过作家化丑为美─由生活丑转化为艺术美的艺术创造。
看来《金瓶梅》作者由于自己未能完全摆脱低级趣味的影响,审美情趣不够高尚,这就使他的讽刺艺术难免存在着粗俗有余而雅洁不足的严重缺陷。
即使把其中描写淫秽的字句统统删去,其在讽刺艺术上的这个缺陷,仍然丝毫改变不了。

《强 盗》 (德) 席勒著
四、认识《金瓶梅》的讽刺特色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我们对于研究《金瓶梅》的讽刺艺术的意义,不应低估。
只有不仅从一般的揭露、批判,而且也从讽刺艺术的角度,我们才能更加全面、透彻地了解《金瓶梅》的思想意义和艺术特色。
如万历本《金瓶梅词话》第四十九回回目「西门庆迎请宋巡按」,「第一奇书」本改为「请巡按屈体求荣」。
文龙则在对此回的批语中指出:
「此一回斥西门庆屈体求荣,窃不谓然。此宋乔年之大耻,非西门庆之耻也。
一个御史之尊,一省巡抚之贵,轻骑减从,枉顾千兵(户)之家,既赴其酒筵,复收其礼物。心之念念,有一翟云峰在胸中。
斯真下流不堪,并应伯爵之不若,堂堂大臣,耻莫大焉。西门庆一破落户而忝列提刑,其势位悬绝,纵跪拜过礼,亦其分也。
周守备等尚在街前伺候,谓之曰荣可也,亦何为屈体乎?至若献妓于小蔡,究与献姬妾不同,而又非其所交之银、桂也,其宋、蔡二御史,屈体丢人,西门庆沾光不少矣。」
一个说是西门庆「请巡按屈体求荣」;一个则认为「宋、蔡二御史屈体丢人,西门庆沾光不少矣。」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尖锐对立的看法呢?其实,如果我们把握住《金瓶梅》的讽刺笔法和特色,就不难发现,无论是西门庆或宋、蔡二御史,都是本回所要刻画的被讽刺者的形象,而完全没有必要在究竟谁「屈体」上纠缠不清。
西门庆跟蔡御史早有交往,他要通过蔡的关系来结交刚离京至本省上任的宋御史,因此他早就派人打听他们的行程,「出郊五十里迎接」,「先到蔡御史船上拜见了,备言邀请宋公之事。」
蔡御史心领神会,说:「我知道。一定同他到府。」
次日,蔡御史约请宋御史一起到西门庆家去,宋称:「学生初到此处,不好去得。」
可是当他一听蔡说,「年兄,怕怎的!既是云峰分上,你我去去何害。」便「分付着轿,就一同起行。」
翟云峰是太师蔡京的管家,西门庆因给他娶了个妾,而攀为亲家。原来蔡、宋二御史之所以接受西门庆的邀请,皆看在「云峰分上」,这难道不是颇有讽刺意味么?
上回曾御史刚刚弹劾西门庆是「市井棍徒」,「赃迹显著」,「贪鄙不职」,此回蔡御史便颂扬西门庆「乃本处巨族,为人清慎,富而好礼。」
宋御史也恭维地说:「久闻芳誉」,「幸接尊颜」。这无论对西门庆或对吹捧他的蔡、宋二御史,难道不都是个辛辣的讽刺么?
西门庆既已「赃迹显着」,难怪宋御史起初不敢登门,蔡御史劝他「怕怎的!既是云峰分上」,他们也就不怕了,这难道不是一语穿透了蔡、宋二御史的灵魂,可笑之至么?
西门庆迎请蔡、宋二御史,除了以「费勾千两金银」的酒席款待之外,又送「共有二十抬」礼品;
「宋御史的一张大桌席,两坛酒,两牵羊,两对金丝花,两匹段红,一付金台盘,两把银执壶,一个银酒杯,两个银折盂,一双牙箸。蔡御史的也是一般的。都递上揭帖。
宋御史再三辞道:『这个,我学生怎么敢领?』因看着蔡御史。
蔡御史道:『年兄贵治所临,自然之道。我学生岂敢当之?』
西门庆道:『些须微仪,不过乎侑觞而已,何为见外!』比及二官推让之次,而桌席已抬送出门矣。
宋御史不得已,方令左右收了揭帖,向西门庆致谢,说道:『今日初来识荆,既扰盛席,又承厚贶,何以克当?徐容图报不忘也。』」
这种对受贿既羞羞答答,故作推辞,又公然把它说成是「自然之道」,难道不是绝妙的讽刺么?受贿而不忘「图报」,似乎就扪心无愧了。可是他们究竟「图报」什么呢?

崇祯本《金瓶梅》插图
曾御史弹劾西门庆「受苗青夜贿之金,曲为掩饰」,如今谋财杀人犯苗青已被捕获,受西门庆之托,蔡御史对宋御史说:「此系曾公手里案外的,你管他怎的?」「遂放回去了。」
西门庆又利用蔡御史任「两淮巡盐」的职权,要蔡御史对他派往扬州贩盐的伙计「青目青目,早些支放。」
蔡即表示:「只顾分付,学生无不领命。」「我到扬州,你等径来察院见我,我比别的商人早掣你盐一个月。」
如此滥用职权,使杀人犯和赃官得到庇护,并进一步大肆渔利,这种「徐容图报不忘也」,又该是多么可笑、可鄙、可憎啊!
西门庆那样盛情款待蔡、宋二御史,究竟是情乎?礼乎?利乎?他名为「情」和「礼」,实则赤裸裸的为了「利」,蔡御史却把他说成是「富而好礼」,那样贪赃枉法、卑劣不堪的蔡御史,作者却说他「终是状元之才」。
这一切难道不皆是以正衬反的讽刺笔法么?其讽刺意义,显然不只是谁「屈体」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嘲笑和鞭挞了封建吏治的腐败、黑暗,从堂堂的御史到执法的提刑官,竟然如此狼狈为奸,灵魂卑劣异常,行为丑恶不堪。
如果不从讽刺艺术的角度来看,人们不仅难以认清《金瓶梅》所蕴藏的深广的典型意义,而且连对其中的某些具体描写,都会感到无法理解。
如第七十一回「提刑官引奏朝仪」,作者写道:
「这帝皇果生得尧眉舜目,禹背汤肩。若说这个官家,才俊过人:口工诗韵,目览群籍;善写墨君竹,能挥薛稷书;道三教之书,晓九流之典。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商王;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
明代天启、崇祯年间刊印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对这段描写的眉批曰,「称尧眉舜目,忽接到孟商王、陈后主,又似赞,又似贬,可见败亡之主,何尝不具圣人之姿?即孟子所谓尧舜与人同之意。」
这段描写,果真「即孟子所谓尧舜与人同之意」么?否!它为什么「又是赞,又是贬」呢?难道是为了正面说明「败亡之主,何尝不具圣人之姿」么?否!
它显然是运用赞与贬的不和谐,描绘出一幅讽刺图像,讥讽这位皇帝名为尧舜禹汤一般圣贤,实则是孟商王、陈后主那样的荒淫之徒和亡国之君。
《金瓶梅》的全部描写,都可证明:只有掌握和理解它的讽刺笔法,才能领悟其深刻隽永的真谛。
只有认清《金瓶梅》的讽刺特色,我们才能更加全面、准确地评价《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金瓶梅》对我国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的发展,及其对于《红楼梦》的影响,这是众所公认的,而《金瓶梅》作为批判现实主义的特色,及其对于《儒林外史》等讽刺小说的影响,则往往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它所描写的,几乎没有什么理想的正面人物,而把笔墨主要集中于讽刺、批判形形色色的反面人物,或种种丑恶的社会现象。
作者着力于从大家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和平凡琐细的事件中,发现其丑恶和荒诞的实质,从丑恶和荒诞的偶然性中,揭示出其得以在社会上风行的必然性,
从而形成了尖锐的讽刺。讽刺的实质,就是更尖刻而轻松的批判。因此,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
「在俄国美文学中持久地贯彻讽刺─或者说得更公允一点,所谓批判倾向的功勋,却应当特别归给果戈理。」[14]
主要以讽刺笔法来进行批判,不是追求塑造理想的英雄人物,而是热衷于「把罪恶的一切丑态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出来,并且把罪恶的巨大形象展示在人类的眼前。」[15]
在这种种方面,我认为《金瓶梅》跟果戈理的《死魂灵》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是颇为相像的。我们理所当然地也应把贯彻讽刺和批判倾向的功勋,特别归给《金瓶梅》的作者笑笑生。
应当看到,不只是《金瓶梅》的写实艺术对《红楼梦》有明显的影响,同时,它的讽刺艺术对《儒林外史》也有直接的影响。
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把讽刺手法建立在对日常生活的严谨的写实上。如鲁迅早就以
「《金瓶梅》写蔡御史的自谦和恭维西门庆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军之高致矣。』」跟「《儒林外史》写范举人因为守孝道,连象牙筷也不肯用,但吃饭时,他却『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圆子送在嘴里。』」
并为例证,论定「这分明是事实,而且是很广泛的事实,但我们皆谓之讽刺。」[16]
从极平常的写实中进行讽刺,使之具有「很广泛的事实」做基础,这就使讽刺有了强大的生命力。
正是在讽刺的生命─真实这个问题上,《儒林外史》与《金瓶梅》是一脉相承的。
其次,还表现在《金瓶梅》犀利地抨击封建腐朽统治的战斗精神,也给了《儒林外史》以及近代的谴责小说以明显的影响。
它们都共同揭示了封建官僚吏治的黑暗,封建伦理道德的堕落和科举制度的腐败,甚至连「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等某些语言,都如出一辙。
《金瓶梅》所写的「富贵必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邓通成。」(第 30 回)「囊内无财莫论才。」(第 48 回)以及蔡状元、温秀才等被讽刺者的形象,都不愧为《儒林外史》的先河。
当然,《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不仅对《金瓶梅》有继承和借鉴的一面,更有新的重大突破和发展。
认清《金瓶梅》的讽刺艺术特色,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也有一定的借鉴和启发作用。如作家的主观动机和作品的客观效果必须统一。
《金瓶梅》作者的主观动机,无疑地是要讽刺和批判当时的社会现实,其全书的主要篇幅也确实讽刺得颇为出色,批判得相当深刻。
但由于作者对荒淫的性生活以及其他一些丑态的描写,比较低级、庸俗,缺乏高尚的审美情趣,就使它的社会效果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严重的消极影响,以致使它那本应产生积极影响的讽刺艺术和批判精神,也受到「株连」,险遭湮没。
这是一个多么沉痛而又具有现实意义的历史教训啊!
至于《金瓶梅》作为讽刺艺术的其他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存在的缺陷,上面已经作了比较充分的阐述,它们究竟有哪些值得借鉴之处,读者自会得出结论,这里就不用赘述了。

《小说史话》 周中明 吴家荣 著
注 释: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九篇。2孙述宇:《金瓶梅的艺术》(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
5鲁迅:〈什么是「讽刺」〉,《鲁迅全集》(1958年),第六卷。
6文龙:《金瓶梅》第七回批语,见《文献》1985年第 4 期。
7张竹披:〈金瓶梅读法〉。
8转引自耶里札罗娃:《契诃夫的创作与十九世纪末期现实主义问题》。
9鲁迅:〈什么是「讽刺」〉,《鲁迅全集》(1958年),第六卷。
10鲁迅:〈几乎无事的悲剧〉,《鲁迅全集》(1958年),第六卷。
11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见《鲁迅全集》(1956 年),第一卷。
12《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年),中册。
13同注 1。
14《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 年),上卷。
15席勒:《强盗》第一版序言。
16鲁迅:〈论讽刺〉,《鲁迅全集》(1958 年)第 6 卷。
文章作者单位:安徽大学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刊于《周中明<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转发请注明。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