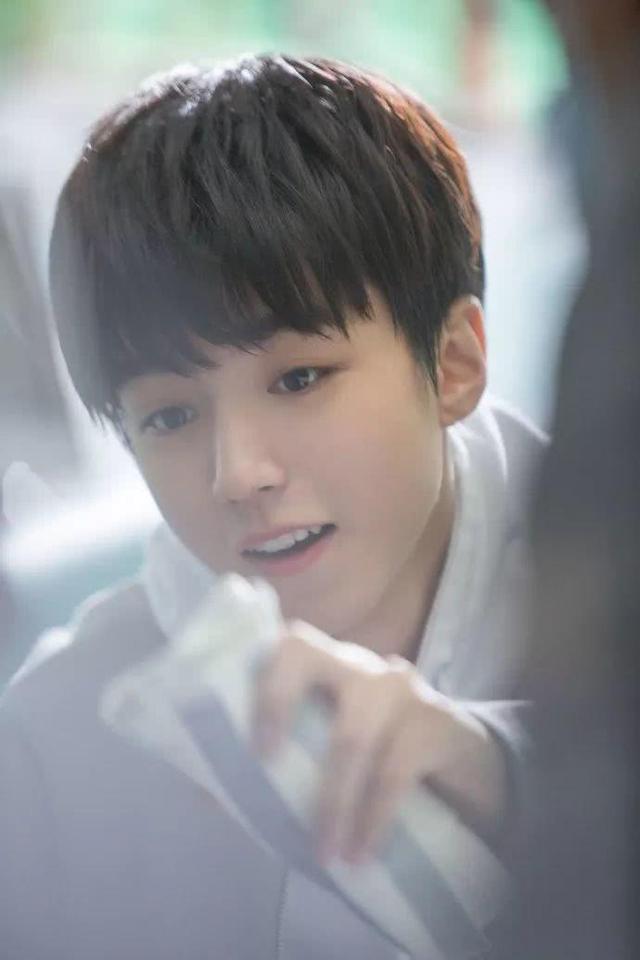暗影1美洲豹(卢修斯谢帕德)

作者 / [美]卢修斯·谢帕德 翻译 / 李鸣弦
插画 / 九代火影
因为妻子欠了电器商奥诺弗里奥·埃斯特韦斯的账,埃斯特班·卡阿克斯终于进了一次城。距他上次去城里,时间已经过去快一年了。他喜爱乡下的静美胜过一切:白日平静的农夫生活给予他无限的活力;夜里围坐炉火旁说笑话讲故事,或仅仅躺在妻子茵卡纳西恩身旁,就能给他莫大的快慰。至于波多莫拉达那种热闹地方,水果店老板没命地吆喝,狗儿蔫趴趴的,酒吧里高声播放着美国音乐,对他来讲就像瘟疫一样,唯恐避之不及。的确,从他位于山巅的小屋向下俯瞰,山坡构成昂达湾的最北岸,而围绕海湾的一座座生锈的锡屋顶,就像垂死之人嘴唇上出现的干血疤。
然而,在这个特别的上午,他还是不得已进了城。茵卡纳西恩背着他在奥诺弗里奥的店里赊了一台用电池的电视机,老板于是扬言要牵走埃斯特班的三头奶牛抵那八百伦皮拉的账。而且老板不同意退货,但又托人捎了话,说愿意商量另外的支付方式。假如没了牛,埃斯特班的收入将不足以糊口,那样他只得重操旧业,那可比务农艰苦多了。
他走下山坡,经过一座座以枯枝搭建、与他家小屋别无二致的茅草棚,沿着一条蜿蜒小径穿过香蕉林里被太阳晒得焦黄的矮灌木丛,心头想的不是奥诺弗里奥,而是茵卡纳西恩。娶她时他就知道她天生少根筋,而等到他们的儿女相继成人之后,他们之间的差异竟愈加明显,赊电视一事便是标志性的反映。她逐渐以洞察世事自诩,嘲笑埃斯特班是乡巴佬,还以资深元老的身份号令着一群以寡妇为主、总是一副深谙世事模样的老妇。每晚她们都聚在电视机周围,边看美国侦探节目边对其评头论足,力争以犀利言辞胜过他人;而这时埃斯特班则会坐在棚屋外头,阴郁地思索着自己的婚姻状况。他认定,茵卡纳西恩之所以与这些寡妇厮混,是有意暗示她想早日穿上黑裙,搭上黑披肩——他既已完成父亲的责任,就别再碍眼赶紧去死。虽然她才四十一岁,比埃斯特班小三岁,却已懒得去追求感官的欢愉,他们很少做爱。他确信,这也部分地体现出她对岁月给予他的优待而感到愤恨。他生就一副帕图卡古部落民的模样——身材高大,面容棱角分明,眼距较开,不仅古铜色的皮肤上皱纹相对较少,连头发也依然乌黑;而茵卡纳西恩的头发已经染上了花白的颜色,臂腿的光洁健美早就埋没在了层层脂肪之下。他从未期望她容颜永驻,也曾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不仅爱年轻时的她,也爱当下的她。可惜当下的她正渐渐远去,被波多莫拉达的瘟疫传染,也许他的爱也要渐渐远去了。
电器店所在的那条街灰尘漫天,街道一直延伸到电影院和海上马戏酒店的背后。埃斯特班望向街道背海的一侧,只见昂达圣玛利亚双塔钟楼的塔尖从酒店屋顶上探出来,如同巨型石蜗牛头上的一对触角。年轻时他曾遵从母亲的意愿做过牧师,在塔楼脚下的修道院里度过了三年,接受贡萨尔沃老神父的教导,为进入神学院做准备。那是他此生最后悔的时期。在他将各门神学科目烂熟于心的同时,似乎徘徊于印第安世界与当代世界之间,无法找到归宿。他在心底依然笃信父亲的教诲——魔法的原则、部落的历史、自然的传说——无法拂去将这些古老智慧视作迷信,认为其不足挂齿的心理。塔楼的阴影投在教堂门前的鹅卵石广场,也牢牢印在他的灵魂上,一见到它们,他就不禁垂下眼帘,加快脚步。
沿着街道继续走,便来到阿托米卡酒吧,城里有钱的年轻人喜欢在此聚会。酒吧对面就是电器店了,那是一座黄色的平房,安装的卷闸门每逢夜里便会放下。店铺正面绘着一幅壁画,理论上是为了展示店内的商品:簇新的冰箱、电视、洗衣机,画面下方的男女小人露出惊讶的神情,高举着双手,将这些电器衬托出硕大无朋的视觉效果。但实际上,店内的商品根本没有这么华丽,主要是一些收音机和二手厨房设备。波多莫拉达没有多少人出得起钱,而出得起的人通常会上别处光顾。奥诺弗里奥的客户基本上都是穷人,每月被他催着还款。他的财富则主要来源于将电器反复回收出售、无数次转手的差价。
埃斯特班进门时,莱蒙多·埃斯特韦斯正倚在柜台上,这个肤色苍白的年轻人脸颊臃肿,眼皮厚重。他不屑地撇撇嘴,假笑一下,吹了声刺耳的唿哨。没过几秒钟,他的父亲就从后堂出来了:身材滚圆,皮肤比莱蒙多还要苍白,根根白发柔顺地贴在布满斑点的头皮上,肚子将瓜亚贝拉衬衫撑得绷紧。他笑容可掬地伸出手。
“幸会幸会。”他说,“莱蒙多!给我们搬两把椅子,再煮壶咖啡。”
埃斯特班虽然不喜欢奥诺弗里奥,却也没有理由失礼,便和他握了手。莱蒙多故意把咖啡洒在杯托上,椅子拖得哐哐响,为不得不伺候一个印第安人而气得直瞪眼。
“凭什么不让我退货?”埃斯特班坐下后便劈头盖脸地问道。然后他又后悔失言,补上一句:“你不打算继续骗我们印第安人了吗?”
奥诺弗里奥叹了口气,似乎觉得跟埃斯特班这样的傻子解释起来太累太辛苦。“我从来不骗你们印第安人,还常在买卖合同的规定之外另开绿灯,同意你们退货也不走法律程序。但是,对于你这件事,我想了一个办法,可以让你既把电视留下,又不用续交货款。咱们的账可以一笔勾销。这也算骗?”
跟奥诺弗里奥这种逻辑牵强、自说自话的人争论毫无意义。“说吧,你要什么。”埃斯特班说。
奥诺弗里奥啜了一口咖啡,嘴唇呈现出生香肠的颜色。“我想让你去猎杀卡罗林纳区那头美洲豹。”
“我已经不再狩猎了。”埃斯特班回答。
“这印第安人是个胆小鬼。”莱蒙多凑到奥诺弗里奥背后说道,“我早告诉过你。”
奥诺弗里奥挥挥手打发开他,继续劝说埃斯特班:“道理不是这样讲。假如我带走你的牛,你还不是又得去狩猎?而你接受我这个条件的话,只需要猎一头就够了。”
“但那头已经咬死了八个猎人,”埃斯特班放下咖啡杯站起身,“它可不是普通的美洲豹。”
莱蒙多轻蔑地笑了,埃斯特班狠狠瞪了他一眼。
“啊!”奥诺弗里奥讨好地微笑着说,“但他们都不会你的绝活。”
“抱歉,奥诺弗里奥先生。”埃斯特班摆出郑重其事的模样,“我还有别的事要忙。”
“除了勾销欠账之外,另付你五百伦皮拉。”奥诺弗里奥说。
“为什么?”埃斯特班问,“恕我冒昧,我可不信你还关心治安问题。”
奥诺弗里奥肥胖的喉咙动了动,脸色阴沉下来。
“当我没说。”埃斯特班道,“不过这点钱不够。”
“很好,那加到一千。”奥诺弗里奥表面上不动声色,话音里却透着掩饰不住的焦虑。
埃斯特班突然来了兴趣,他想知道奥诺弗里奥究竟焦虑到何种程度,便漫天要了个价。“一万,”他说,“而且是预付。”
“可笑!这么多钱我都能雇到十个猎人了!甚至二十个!”
埃斯特班耸耸肩。“但他们都不会我的绝活。”
奥诺弗里奥坐了一会儿,十指交叉,不停地松开握紧,好像考虑什么神圣的难题。“好吧。”他唇齿间终于挤出这句话,“一万就一万。”
埃斯特班顿时看穿了奥诺弗里奥对卡罗林纳区的兴趣所在,他明白,这笔费用相比于由此带来的利益仅是九牛一毛。但他禁不住去想象,一万伦皮拉意味着什么:一群牛、一辆运农产品的皮卡车,或者——他越想越觉得,最叫他开心的是,如果买下茵卡纳西恩心心念念的克莱茵区的那座小砖房,也许就能使她回心转意。他注意到莱蒙多一直盯着他,脸上带着自鸣得意的冷笑;而奥诺弗里奥虽然对这价码骂骂咧咧,却也露出一丝心满意足,整了整身上的瓜亚贝拉衬衫,捋一捋本就平顺服帖的头发。面对轻易就能雇买自己的父子俩,埃斯特班自觉没趣,为了保留最后一点尊严,他转身向门口走去。
“容我考虑考虑。”他扭头丢下这句话,“明早给你答复。”
那天晚上,茵卡纳西恩的电视上特别播映了一个美国光头男演员主演的《纽约谋杀小队》,寡妇们盘腿坐在地上,把整间小棚屋挤得满满当当。为了让后来的人也能有清晰的观看角度,只得把木炭炉和吊床都搬了出去。埃斯特班站在门口,在他眼里,这个家仿佛被一群戴着头罩的大黑鸟侵占。它们围坐在一颗熠熠闪光的灰色宝石旁,从中汲取邪恶的教诲。他耐着性子从她们中间挤过,前往电视机后面墙上钉着的壁架,伸手到最上层取下一个报纸包裹的细长物件,纸上沾满了油污。他眼角的余光瞥见茵卡纳西恩正望着他抿嘴微笑,那笑容在埃斯特班的心上戳下一记伤痕。她知道他要做什么,而且还很高兴!一点不为他担心!也许她早知道奥诺弗里奥打算猎杀那头美洲豹,便和奥诺弗里奥串通一气,给他下套。他顿时怒火中烧,快步从寡妇当中冲过,任由她们吵吵嚷嚷,兀自走进自己的香蕉林,在林中一块石头上坐下。夜空点缀着云彩,从香蕉叶的裂纹之间露出几点星光;风吹得叶片沙沙作响,一头牛的鼻息声传入他的耳朵,伴着牛栏里浓烈的气味。日子仿佛不能再踏实地过下去了,他孤零零一个人,品尝孤独的苦涩。他承认自己没能好好经营婚姻,但死活想不出自己到底做了什么,竟会让茵卡纳西恩流露出那种可恶的微笑。
坐了一会儿,他打开报纸捆,抽出一把薄刃弯刀,就是用来砍香蕉串的那种。他要用它来杀美洲豹。仅仅将刀握在手中,他便重燃了信心,感觉浑身充满力量。虽然已经四年没有狩猎了,但他知道,这门技艺没有丢。他曾经重书父亲的荣耀,被誉为新艾斯帕兰萨省最伟大的猎人;他转行并非因为年老体弱,而是因为美洲豹十分美丽,它们的雄美使他再也找不到理由下手。卡罗林纳区这头美洲豹也是如此:它从未对任何人产生威胁,只是反击那些来猎杀它、进犯它领地的人;它的死只会便宜一个卑劣小人和一个没事找事的老婆,外加传播波多莫拉达的瘟疫。更何况它还是一头黑豹。
“黑豹乃月之生灵。”他父亲曾告诉他,“它们会变化形象,有自己的魔法使命,凡人不得干涉。千万勿要猎杀它们!”
他父亲从没说过黑豹住在月亮上,只是说它们拥有月的力量,但埃斯特班小时候却梦见黑豹在月亮上的象牙森林与银色草地之间奔跑,迅疾如流淌的黑色的水;当他把梦讲给父亲听的时候,父亲说这样的梦是某种事实的隐喻,至于事实本身,他或早或晚会接触到。埃斯特班一直相信梦里的景象,即使茵卡纳西恩的电视上的那些科普节目将月亮描述为没有空气的岩石星体。被揭秘的月亮依旧如梦,只是那梦变得平淡,神秘现象都被阐述成了科学知识罢了。
埃斯特班这么想着,突然意识到,猎杀这头美洲豹或许就能解开他的心结:如果违背父亲的教导,抹杀自己的梦,抹杀自己的印第安世界观,也许就能向妻子靠拢了;他在两种世界观之间徘徊得太久,终于到了选择的时候。其实算不上真正的选择,毕竟他住在这个世界,而非那美洲豹的世界;倘若杀死一头魔法生物就能让他欣然拥有电视机,愿意去看电影,并买下克莱因区的砖房,那他对这个办法有信心。他挥舞弯刀斩过夜色中的空气,朗声大笑。茵卡纳西恩的愚蠢、他的狩猎技艺、奥诺弗里奥的贪婪、美洲豹、电视机……环环相扣,如同咒语的各个元素,使得魔法被摒弃,使得那腐化了波多莫拉达的非魔法信条得到发扬。他再度放声大笑,随即又骂起了自己:既然要抛弃魔法,岂能以“咒语”作譬喻!
第二天,埃斯特班早早地叫醒茵卡纳西恩,硬逼着她陪自己去电器店。他的弯刀插在皮鞘里挂在腰间,肩上扛了一麻袋干粮和狩猎用的草药。茵卡纳西恩一路小跑,跟在他身旁,脸藏在披肩里一言不发。来到店里,埃斯特班让奥诺弗里奥在账单上盖了“现金收讫”的字样,然后把账单和钱都交给了茵卡纳西恩。
“我要去猎杀美洲豹,不是它死就是我亡。”他冷冷地说,“这些都归你。要是我一周之内没有回来,就可以认为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她退后一步,脸上表露出惊吓的神色,仿佛重新认识了他,也明白了自己鲁莽行事的后果。可他迈出房门时,她却没有上前阻拦。
街对面,莱蒙多·埃斯特韦斯正靠在阿托米卡酒吧的墙上,和两个身穿褶边衬衫配牛仔裤的女孩聊天;两个女孩手打节拍,随着酒吧里传出的音乐跳舞,在埃斯特班眼里,她们比他即将要去猎杀的生物还要异类。莱蒙多看到他,立刻对两个女孩低语了几句,她们便回头偷看一眼,哈哈大笑。埃斯特班已经被茵卡纳西恩气得够呛,哪里受得住火上浇油,便强忍着怒意过街来到他们旁边,一手按在弯刀刀柄上,狠狠瞪着莱蒙多。这一下他才发现,自己是如此缺乏威慑,如此没有存在感。莱蒙多下巴上长了一团青春痘,脸上坑坑洼洼,像是被银匠用小锤砸出来的,他根本不理会埃斯特班的视线,眼睛在两个女孩之间瞟来瞟去。
埃斯特班的愤怒转为了厌恶。“我叫埃斯特班·卡阿克斯。”他说,“我亲手修建房舍,开荒锄地,养育了四个孩子。今天我要去猎杀卡罗林纳区的美洲豹,就为了把你和你老子养得比现在更肥。”他上下打量着莱蒙多,语气中充满嫌恶地问道:“你算哪根葱?”
莱蒙多怨忿不已,臃肿的脸拧成一团疙瘩,但没有回话。两个女孩“咯咯”笑着,蹦蹦跳跳从酒吧门口进去了,埃斯特班听见她们边笑边向别人描述这件事,他继续瞪着莱蒙多。又有几个姑娘从门口探出头来,时而偷笑时而窃窃私语。僵持一会儿,埃斯特班转身走开,身后几人立即爆发出肆无忌惮的狂笑,一个女孩学着他的声音说道:“莱蒙多!你算哪根葱?”其他人也纷纷掺和进来,汇成一段杂乱无章的吟唱。
卡罗林纳区其实并不算波多莫拉达的一个区,它位于马纳比克海角以南,是海湾的最南岸,拥有一道天然棕榈林屏障和全省最美丽的沙滩。一条蜿蜒狭长的白沙邻接着翠绿似玉的浅湾。四十年前,这里曾是水果公司实验农场的总部所在地。该项目涵盖多种经营,乃至在农场区逐渐形成了一座小镇:一排排装有纱窗门的白色盖瓦木屋,俨然画报上美国乡村的那种景致。公司将这个项目吹捧为国家未来的基石,并放出豪言壮语,要培育出高产农作物消除饥荒;但1947年,海湾沿岸霍乱流行,小镇元气大伤,便逐渐废弃了。等到霍乱散去,公司已经在国家政治风云中站稳了脚跟,无须再去塑造利国益民的形象,项目随即关停,土地也完全荒废了。直到埃斯特班决定退出狩猎的那一年,才又有开发商买下这块地,计划打造大型度假村,黑豹就是在那时候出现的。虽然它从没杀过一个建筑工人,却把他们吓得不轻,一度拒绝开工。猎人们先后被派去,无一不被黑豹杀死。最后那批猎人甚至配备了自动步枪,动用了一切科技辅助工具,但黑豹还是将他们逐个击破,新项目又只得宣告破产。据说这块地最近又卖了出去(埃斯特班现在知道金主是谁了),兴建度假村的想法再度提上日程。
从波多莫拉达一路走来,又热又乏,一到卡罗林纳区,埃斯特班便在一棵棕榈树下坐下,吃了一顿冷香蕉馅饼。牙膏沫一样的浪沫在海岸上溅开,岸上没有一丁点人类垃圾,只有枯叶、浮木和椰子。房子几乎都被丛林吞没了,只有四座在外面露出一角,半隐半现,像是墨绿的草木之墙上四扇发霉的门。即使在明亮的阳光之下,它们也散发着幽森的气息:纱窗撕裂了,木板被风雨染成了灰色,藤蔓像瀑布一般从正墙垂下。有一家门口长了一株野生芒果树,野鹦鹉在树上啄它的果实。他上次来这个区还是小时候,当时令他害怕的残垣断壁的景象,此时看来竟如此迷人,自然法则在这里宣誓着主权。想到自己将为虎作伥,改变这个地方,他有些黯然神伤:此后这些鹦鹉将被链条拴在栖枝上,美洲豹将成为桌布的图案,海湾将变成一座大浴场,游客们抱着椰子吸椰汁。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吃完午餐后开始探索这片丛林,很快便发现了黑豹行过的踪迹。一条狭窄的小径,蜿蜒着穿过藤蔓遮覆的房屋之间,延伸约半英里之后,终止在杜尔塞河畔。河水比绿海略混浊,弯弯地流过丛林,黑豹的足迹遍布河岸,在一个距水面五六英尺的草墩上尤其密集。埃斯特班百思不得其解。在那高处根本喝不到水,它也不可能在那里睡觉。他思索了一会儿,最后干脆打消苦想,回到沙滩上,在棕榈树下打个小盹,养精蓄锐以便夜里观察黑豹的动静。
几小时后,大概三点左右,他突然从梦中惊醒,原来有个声音在喊他。一个高挑而苗条、古铜色皮肤的女子正向他走来。她身上的墨绿色长裙几乎与丛林混为一体,胸部曲线丰盈。随着她越走越近,他发现她的五官虽有帕图卡人的特征,但皮肤上宝石般的光泽却是部落少有,就像戴了一张精致打磨的美丽面具:颧骨饱满,脸颊微微内收,嘴唇丰如雕琢,双眉如同乌黑浓密的羽饰,眼睛好似白玛瑙镶黑玛瑙,浑身散发着夺目的美丽光芒。她胸上蒙着一层细密晶亮的汗珠,一绺黑发垂至锁骨,好像故意放下的一样,为她愈添风致。她蹲在他身旁,面无表情地盯着他,埃斯特班被她狂野的性感搅得意乱情迷。海风吹来她的体香,甜甜的麝香味,让他想起阳光下自然熟透的芒果。
“我叫埃斯特班·卡阿克斯。”说着,他突然闻到自己的汗味,窘迫不已。
“我听说过你,美洲豹猎人。”她说,“你来这个区,是要杀黑豹吗?”
“对。”他说着,有些耻于承认。
她抓起一把沙子,望着沙粒从指缝滑落。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如果我们做了朋友,我就把名字告诉你。”她说,“你为什么非得杀那头黑豹?”
他便向她讲述了电视机的故事,而后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向她倾诉起了他和茵卡纳西恩之间的矛盾,解释说他多想向妻子靠拢。这种话题原本不适合与陌生人讨论,但他禁不住想与她亲近;他对她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这也促使他把婚姻生活描绘得比事实更加灰暗。虽然他从未对茵卡纳西恩不忠,此时却十分乐意接受这样的机会。
“这是头黑豹。”她说,“黑豹不是普通动物,它们有自己的魔法使命,凡人不得干涉。你肯定知道吧?”
听到她嘴里说出父亲曾告诫他的话语,埃斯特班吓了一跳,但他断定这只是巧合,于是答道:“也许吧。但它们的使命跟我没有关系。”
“其实是有的。”她说,“只是你故意视而不见罢了。”她又捧起一把沙子,“你打算怎么杀它?你连枪都没有,就一把弯刀。”
“我还有这个。”说着,他从麻袋里掏出一小包草药递给她。
她打开包裹,闻了闻里面的东西。“草药?啊!你打算给黑豹下药。”
“不是给黑豹,是给我。”他拿回包裹,“这种草药能降低心率,让身体看起来像死了一样,使服药者进入神游状态,但又能随时自行清醒。我嚼碎草药吞下之后,就躺在黑豹夜里捕食的必经之路上。它会以为我死了,但不会马上吃我。它会先确定我的灵魂已经离开肉体。因此,它会坐在我身上,感受灵魂脱离身体的气息。只要它一坐下来,我就马上抛开神游状态,用弯刀戳它胸腹。只要我手不抖,它立刻就能断气。”
“万一你手抖了呢?”
“我杀过将近五十头美洲豹了,”他说,“不怕手抖。这是一项家传秘技,传承自古帕图卡部落,就我所知,从没失过手。”
“但是黑豹……”
“黑豹斑点豹都一样。美洲豹是依赖本能行动的生物,猎食的时候并没多大差别。”
“嗯。”她说,“我不能祝你好运,但也不咒你倒霉。”她站起身,拍拍长裙上的沙子。
他想请她留下,却又拉不下这个脸。她笑了,仿佛知道他的心思。
“咱们也许还有机会再聊,埃斯特班。”她说,“不然就太可惜了,今天说了这么多,还是觉得意犹未尽呢。”
她快步走过沙滩,变成一个小小的黑影,在热浪的涟漪中荡漾。
那天傍晚,埃斯特班为了找个便于观察的地方,特意挑了一幢朝向沙滩的小屋,撬开纱窗门,进了前廊。几只变色龙匆忙逃到墙角。一头鬣蜥从缠满蜘蛛网的生锈沙滩椅上爬下,钻进地板的裂缝不见了。屋内一片漆黑,令人望而却步,只有卫生间因为没了屋顶,从上方藤蔓交错的间隙之中洒下几缕灰绿色的暮光,裂开的马桶里盛满了雨水和昆虫的尸体。埃斯特班感觉有些不适,回到前廊,擦擦沙滩椅,坐了下来。
远方海天一线之处笼罩着迷蒙的银灰,风已经止息,棕榈丛静止不动如同雕塑,一行鹈鹕低低地飞过波涛之上,仿佛在拼写神秘黑色音节组成的句子。然而他却对这诡异的美景视而不见,他一刻不停地想到那个女子,脑海中一遍遍播放着记忆里她离去时那薄薄长裙下摆动的臀部。而他越是想集中精力对付手边的事,那记忆反而来得越是强烈。他想象着她的胴体,她臀部肌肉的颤动,不禁欲火难耐,来回踱起了步,不顾那地板吱吱嘎嘎地提醒他的重量。他无法理解她对自己的吸引力为何如此巨大。他想,也许是因为她力保黑豹,也许是因为她唤起了他抛诸脑后的过往……然后,他一个激灵,好像冰冷的殓尸布突然裹在身上一样。
帕图卡人通常认为,如果一个人即将遭受意外孤独死去,死神会预先派使者到访,代替家人朋友引导其直面死亡。埃斯特班此刻十二分地肯定,那个女子就是死神的使者,刻意装扮得如此迷人,以引诱他的灵魂走向近在眼前的厄运。想到这里,他瘫在沙滩椅上,呆若木鸡。她清楚他父亲的教导,谈话的内容多有蹊跷,加上与他一见如故的亲密感,都与传说完全吻合。一轮凸月升上天空,将沙粒照得银白,他仍坐在那儿,因为惧怕死亡而挪不动脚。
他呆望了好几秒之后,才意识到黑豹已经出现在眼前。起初他只觉得像是有一小块夜空掉落在沙滩上,被忽起忽停的海风吹动。很快他便看出那就是黑豹,正缓缓前行,仿佛在跟踪什么猎物。接着它高高跃入空中,翻腾转身,开始在海滩上狂奔:如同一道黑色的水流过银色沙滩。他从未见过美洲豹独自嬉戏,不由得产生了几分好奇。但最令他惊奇的是亲眼见到童年时代的梦境成为现实,就像在远远偷窥月亮上的银色草地和那草地上的魔法生物。眼前的景象渐渐打消了他的恐惧,他像小孩子一样,鼻尖紧贴着纱窗,眼睛一眨不眨,生怕错过了某个时刻。
最后,黑豹嬉耍够了,转身悄无声息地穿过沙滩前往丛林。从它耳朵的下垂角度和步伐的摇摆幅度来看,埃斯特班断定它在捕猎。它来到距小屋约二十英尺的一棵棕榈树下停住脚步,昂起头嗅嗅空气。棕榈叶间筛过的月光给它后腿涂上了流溢的光泽,它的双眼闪耀着介于明黄与莹绿之间的颜色,好像那眸子背后燃烧着可怕的火。这头黑豹美得令人窒息,犹如无瑕的自然准则的化身——埃斯特班随即联想到雇主那丑陋的苍白,以及驱使其雇用他的丑陋的准则,两相对比,他怀疑自己根本下不了决心杀它。
翌日,他为这个问题纠结了整整一天。他盼着女子再来找他,因为他已经否定了她是死神使者的念头——他想,那种观点一定是受到了这个区神秘气氛的影响——他觉得,如果她再来探讨黑豹的话题,自己情愿听她的劝。可她没有出现,他坐在沙滩上,望着傍晚的落日沉过昏黄和淡紫的云层,海面上的粼粼波光激荡跳跃。他再次明白,自己别无选择。不论黑豹是否雄美,不论那女子是否承载着超自然的使命,他必须明白这都是虚妄。这次来狩猎的意义原本是要破除神鬼迷信,而在童年旧梦的迷惑之下,他险些错失了方向。
他一直等到月亮再次升起才服下草药,然后躺在黑豹前一晚曾逗留过的棕榈树下。蜥蜴悉悉窣窣爬过草丛,沙蚤跳上他的脸,但他浑然不觉,在草药作用下渐渐陷入朦胧的意识深处。头顶的棕榈叶在月光下呈现灰绿的颜色,沙沙摇曳。羽毛状叶片之间透出的星星疯狂闪烁着,好像微风在煽动它们的火焰。他一点点融入周围环境,品鉴着海滩方向吹来的咸腥与腐叶味,意识也跟随那气味漂荡;当他听到美洲豹足上的肉垫落在地面的轻响,顿时警觉起来。借助眯缝的双眼,他看见它坐在十几英尺之外,一团庞大的黑影,脖子朝他的方向伸来,辨识他的气味。过了一会儿,它开始绕着他转圈,一圈比一圈小,每次它走出视线,他都要尽力压下丝丝缕缕的恐惧。然后,当它离得足够近了,绕到向海那一侧时,一丝气味飘进他的鼻孔。
甜甜的麝香味,让他想起阳光下自然熟透的芒果。
本文来自:科幻世界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