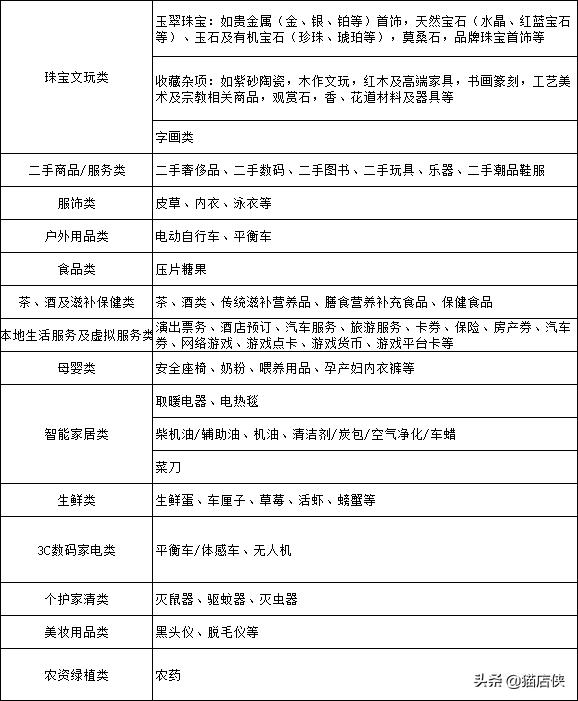她不小心把铁叉插在了自己的腿上英文(她不小心把铁叉插在了自己的腿上)
那还是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放了学,我来到队里的打麦场上找大姐要家里的钥匙。
只见打麦场上铺满了一大片壮观的金黄,几个男老力唱着古老而悠扬的牛歌,分别赶着一头黄牛,每一头黄牛都拉着一个碌碡。悠扬的牛歌和“吱哟哟”的碌碡声组成了这个季节最动听的民歌。
碌碡滚过后,十几个识字班分别拿着一把铁叉,随后就把压实的麦秸挑起,晃动几下后再把叉上的麦秸放下,让它变得篷松。(识字班:方言,指大姑娘)
识字班们错落有致的动作仿佛在跳着一种韵味十足的舞蹈,我看呆了!

“军民,干什么的?站在那里跟打愣的鸡一样。”我十八岁的大姐扛着铁叉从麦场上走过来,对我喊着,还开起了玩笑:“俺兄弟你看上哪个识字班了?”
我羞得一下子涨红了脸,心虚地看着那些呵呵直笑的识字班们,没有好声气地回道:“胡说八道,你才看上了呢!”
大姐看我气急败坏地样子,禁不住“咯咯”地笑了起来,那些识字班们也哈哈大笑。大姐一边笑,一边把钥匙从腰带上解开,扔给了我,转身又去挑麦秸去了。
我把钥匙拿在手里,一边在打麦场的旁边走着,一边无意识地把钥匙环套在食指上,在食指上飞速地动。
谁知一不小心,钥匙脱手而出,直直地飞向了打麦场,倏忽不见了。我望着满场的麦秸,一下子懵了!
我哪里想到会出现这种意外情况,也根本没注意钥匙落到哪个地方了。
这可怎么办?
我呆了半天,实在不知道怎么办,最后只得喊大姐。我明知道喊大姐得挨大姐熊,也得喊啊:“大姐,大姐……”
大姐走过来,生气道:“喊什么的,掉魂了,没看我正忙着嘛。队长正看着呢。”
我吞吞吐吐地说道:“钥匙…钥匙…掉了…”
“掉了?这不刚给你嘛,掉哪里去了?”
“掉麦秸里去了。”
大姐扶着铁叉,瞅着满场的麦秸,懵了一下子,随即转过头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道:“熊蛋子孩,等会跟你算账。”说着拿着铁叉进了打麦场。
这时,牛把式们不再压场了,场里的十几个识字班一下一下地挑着麦秸,把麦秸集中在一个地方。
大姐招呼道:“哎,挑麦秸的都听着哈,俺家的钥匙让俺这不省心的兄弟弄麦秸里去了,大家都帮帮忙,挑麦秸的时候看着点。”
旁边的小美笑了,说:“老天,满场都是麦秸,这是哪里找?就怕找不到。”
“找找看吧,找不到也没什么办法。”大姐说着又冲着场边的我凶神恶煞道:“你等着哈,要是找不到,今晚你就等着咱娘来剥你。”
我哭丧着脸站在打麦场边,想着娘见我弄没了钥匙的凶恶模样,忐忑不安。
明知道没什么希望,我还是眼巴巴地瞅着十几位挑麦秸的识字班,盼望着出现奇迹
奇迹还真出现了,不一会儿,我就听见“当啷”一声,紧接着离我最近的小美举着铁叉大喊:“找到了,找到了。”
只见小美举起的铁钗上,一串明晃晃的钥匙挂在铁叉上。

我长出了一口气。
众人都啧啧称奇,说没想到还能找到。
我奔向小美,只见小美把铁叉放下,一只手倒拿着铁叉,一只手向下撸那串钥匙。但是很不好撸,因为钥匙上的那个钥匙环紧紧地套在了铁叉的一个叉上,很不好取。
我连忙走到她身边,说,我拿着铁叉,你来往下撸吧。
于是,她把铁叉交给我,我双手拽着铁叉柄,她双手攥着钥匙就往下撸。
可也怪了,两人都使劲,可还是撸不下来。
小美说:“咱两人再使点劲。”
于是,两人就又加了点劲。就在这时,意外情况发生了,我脚底下的麦秸突然打滑,“哧溜”一下子把我滑倒了,随即我的双手就无意识地松开了铁叉。
等我站起来,看向小美的时候,我的脑袋“嗡”的一下,空白了:只见铁叉一根叉直直地插在小美的大腿上,鲜血顺着她的裤子缓缓地往下流着。
等我意识清醒的时候,小美痛苦的哭叫声不绝于耳,她的周围已经围了一圈慌乱的众人。铁叉已经从小美的腿上拔出来了,大姐正用一个手绢按在小美的大腿上,大姐的手和纯白的手绢已经都被染成了瘆人的红色。
小美的父亲——“老油条”正是今天打麦场上的牛把式之一,但是奇怪的是,众人围着小美正商议着赶快送药房的时候,“老油条”正坐在打麦场边,拿着一张脏不垃圾的纸,放上旱烟丝,伸出舌头,把纸的边沿舔湿,不紧不慢地卷着一根旱烟。(药房:方言,当地专指农村的医务室)
队长“瘆人毛”到处撒目“老油条”,这时看见了场边卷烟的“老油条”,还以为“老油条”不知道闺女被铁叉插伤了,忙告诉他。

谁知小美的父亲眼皮也不翻,不紧不慢地点上那支刚卷好的旱烟,悠然吸了一口,说道:“不是还没死嘛。”
“瘆人毛”愣了一下,随即恶狠狠地骂道:“你个老货,你说的是人话吗?她还是你亲闺女不?”接着转身朝小美走去。
“老油条”依旧无动于衷,还是不紧不慢地吸着烟。
“抓紧去药房。王麻子,愣着干什么,赶紧把大板车拉过来。”
……
那套在铁叉上的钥匙,最后还是让队长拿烟袋敲了几下,给敲了下来,还带着小美的鲜血,给我,我还不敢拿。最后还是大姐接过去的。大姐接过钥匙后,恶狠狠瞪了我一眼,仿佛要吃我一般。
小美的伤,当时看着怪吓人,可当第二天一大早,我和大姐拿着十来个鸡蛋去看她的时候,她已经瘸着腿站在门前,对着墙上的镜子,正在梳着她那两条乌黑漂亮的大辫子。
她腿上煞白煞白的包扎布,扎眼得很!
“哎呀,小美,你不在床上躺着,这么早起来,不疼吗?。”大姐嗔怪道。
小美转头朝我们嫣然一笑,说道:“小伤,不疼。”
等我知道昨天是小美自己把铁叉从腿上拔出来时,我都有些头皮发麻。小美却毫不在意,说当时一开始被铁叉插伤时,一点儿也没觉着疼,可是等自己拔出来后,没想到怎么那么疼。
“五姐,都怨我。”我内疚地说道。小美姊妹八个,她排行老五。
“跟你什么关系,你又不是故意的。”小美说着又笑了。
小美一边说着,一边放下手中的木梳,一颠一颠地找凳子让我们坐。还说这是小伤,嫌我们大惊小怪,嫌我们见外,还拿鸡蛋看她。
“行了,你别动,你别动,我们自己找凳子——这点东西算什么。”大姐忙搀着小美坐好,还埋怨她:“你呀,伤筋动骨一百天,可得注意些,免得落下病根。”
“离心脏还差老远呢,死不了她。”在旁边扫院子的“老油条”停下来,阴阳怪气地说道。
论庄邻,我得管“老油条”叫四大爷。但是从那以后,一直到他死,我也没叫他一声四大爷。
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冷酷的父亲!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