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的英文短句(哲学如摇滚都是一个动词)
《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作者:周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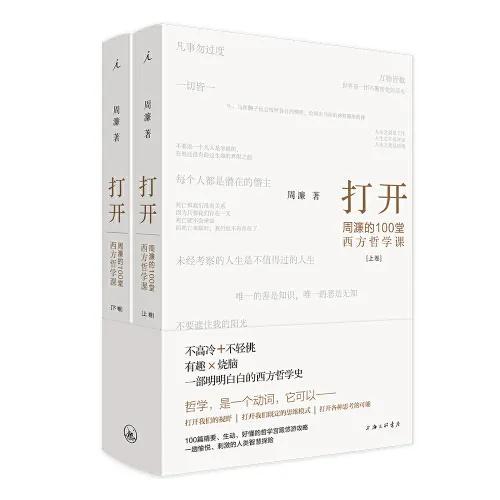
这是一本既专业又好读的西方哲学思想史入门读物,将带我们踏上一场2500年的西方哲学探索之旅。
本书作者周濂可以说是一位哲学“大牛”,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还考取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现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担任教授。2012年他曾出版书籍《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由此创造了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一时间整个文化圈几乎无人不谈“装睡的人”。
之后,周濂又“十年磨一剑”,完成了这本《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本书和《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一脉相承,因为它的主题词也是“醒来”。但是与之前不同的是,这次“醒来”则是通过哲学的视角“唤醒”我们,打开视野的深度和广度,看到世界的真实模样。
那么,一提到哲学,有些朋友或许就会不由自主地皱起眉头,觉得那些高深莫测的名词,晦涩难懂的理论,不仅难,而且和生活似乎也没什么关系,读哲学有什么用呢?
面对这样的疑惑,本书的作者周濂老师告诉我们,哲学不仅在生活中有用,而且还有“大用”,不仅不难,而且离我们的生活很近,每天都能用到。
那么,周濂老师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们可以先从认识“哲学”这个词开始。
哲学一词的英文philosophy,由philia和sophia 两个词组成。这个词来源于古希腊文,sophia的意思是智慧,而philia是爱,我们可以将哲学理解成一种温和、理性而广博的智慧之爱。这就意味着哲学之路不走极端,广博而永无止境,需要我们“上下而求索”。所以,周濂说哲学是一个动词,它会激发人们持续地进行思考。
此外,在这个日益忙碌的时代,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变”已经成为一个永久的主题,各种庞杂的信息铺面而来,把我们拽入知识焦虑的深渊。而在这些信息中,哲学可谓是折旧率最低的学问,它能帮助我们保持定力,以不变应万变。
更具体地来说,哲学能帮我们进一步打开人生视野,打开固化的思维模式,打开各种思考的可能。它让我们不武断、不盲从,能听清谁在我们耳边胡说八道,能看透谁试图割我们的“韭菜”。
这就是哲学,一门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学问,能让我们更从容地应对外部世界,更宽容地面对自己。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周濂这位思想的导游,踏上一场充满智慧与思辨的哲学之旅。
这场旅程的起点是一座古老的神庙,它就是著名的德尔菲神庙。德尔菲神庙被誉为古希腊文明的圣地,在神庙高耸的石柱上,刻着三条“神谕”,那是智慧之神——阿波罗送给凡人的礼物。它们充满神圣且智慧的光芒,曾让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终生痴迷,不可自拔。下面,我们就以这三条“神谕”为起点,开启这趟智慧之旅。
审查人生,认识你自己
德尔菲神庙上刻着的第一条神谕叫作“认识你自己”。古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曾说这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自己终其一生都在这条路上修行。那么,苏格拉底为什么如此看重这条神谕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从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讲起。
俄狄浦斯是忒拜城国王与表妹婚姻的产物。这是一段不被众神认可的结合,因此阿波罗神盛怒之下发布预言:他们生下的孩子命中注定要杀掉父亲,迎娶母亲。因此俄狄浦斯出生后,国王命令牧人处死这个孩子,但牧人没忍心下手,而是把婴儿送到邻国,让他顺利地长大成人。
在一场偶然事件中,俄狄浦斯也得知了这个预言。为了逃脱诅咒,他离开了故乡,四处流浪。但是命运之神并没有放过他,在流浪的路上,他意外杀死了乔装私访的忒拜老国王,也就是他的父亲拉伊俄斯,之后,俄狄浦斯在慌乱中逃亡到了忒拜国。当时一个人面狮身的怪物盘踞在城外,它给来往的行人出了个谜题:“什么东西行走时先用四只脚,再用两只脚,最后用三只脚?”答不上来的人就会被怪物吃掉。
俄狄浦斯以自己的“聪明才智”破解出了谜底,那就是“人”,因为小孩子爬行,长大后直立行走,老了后拄上拐杖。这头怪物虽然聪明,但脾气很大,在俄狄浦斯揭开谜底之后,一气之下跳下了悬崖。俄狄浦斯也因此成为忒拜城的英雄,当上了国王,并娶了王后,也就是自己的母亲。
俄狄浦斯被誉为那个时代最聪明的人,因为他打败了一头会给人类出难题的聪明怪兽。但聪明不等于智慧。不管是怪兽,还是俄狄浦斯,都没有真正地理解“人”是怎么回事——虽然,人类要经历爬行、直立行走、拄杖而行三个阶段,但这只是生理上的特征,根本就没涉及“人之为人”的本质。
所以,俄狄浦斯并未参透“人是什么”,更没有“认识自己”。正因如此,他一直活在弑父娶母的无知中,直到后来才从盲人先知那里得知真相。此时的俄狄浦斯深恨自己愚昧无知、有眼无珠,他刺瞎了双眼,放弃了王位,选择了自我放逐。
俄狄浦斯的遭遇告诉我们“人类掌握的理性和知识是有限的,也是容易腐朽的”。然而,有意思的是,大哲学家苏格拉底通过对人生的多方审视,竟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这个被誉为雅典最聪明的人曾经说道:“我唯一知道的是,我是无知的。”
那么,苏格拉底为什么会发出如此感慨呢?
据说有人到德尔菲神庙问太阳神:“有谁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吗?”神的回答是:“没有。”这让苏格拉底诚惶诚恐,因为他知道自己“毫无智慧”。于是为了搞清楚神的真实用意,苏格拉底挨家挨户地去找雅典的成功人士对话。
一轮请教下来,苏格拉底惊讶地发现,这些人虽然一无所知,却傲慢地以为自己很有智慧,相比之下他自己还是坦诚的,因为至少自己知道自己是无知的。
最后苏格拉底终于明白,这是太阳神想通过他来告诫雅典人:“即使最聪明的人,也意识到自己的智慧是微不足道的”。
那么,对于苏格拉底自己而言,他为什么觉得自己是无知的呢?这是因为,在他看来,真正的智慧不是人类创造的,而是“神”放在了我们心中。只有承认无知,抱着谦卑甚至敬畏的态度审察人生,“关照自己的灵魂”,神赋予的这些智慧才能浮现出来,指导我们更好地生活。这也是他所主张的“一个未经考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这种说法有点危言耸听,但仔细想一下就会觉得很正常。举例来说,如果电脑坏了,我们会去找电脑工程师修理;如果身体出了问题,我们会去看医生。同理,当灵魂出了问题,我们也需要进行修理、治疗。所以说关照自己的灵魂,也是人生中的头等大事。
这种“关照灵魂”的智慧,就是苏格拉底所说的德性。在他看来,德性是一种潜能,是上帝放在我们内心深处的那样东西。我们要通过审察人生使之浮现,并发挥到极致,成为德才兼备的卓越者。如果你是一匹马,那就做跑得最快的千里马;如果你是一只鸟,那就做飞得最高的展翅大鹏。
那么,德性和无知又有什么关联呢?苏格拉底认为,德性的关键就是知识,有知者有德,无知者无德。举个简单的例子,人们戒烟为什么总会失败?对于苏格拉底来说,他不会将事情简单地归咎为这人意志薄弱,而会说他没把吸烟的危害放在心上,对这个知识点不够重视。如果在吸烟的人身旁放置一个测试仪,让他看到吸烟前后PM2.5指数的急剧变化,或许这个人的戒烟行为就更容易成功。
所以苏格拉底认为,德性有善恶、是非标准,这种标准就是知识。就这样,他在“关照我们的灵魂”和“认识你自己”两大命题间建立起了关联。
最后,苏格拉底说道:“那些能认识自己的人知道什么事情合适自己,能够分辨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由于有这种自知之明,他们还能够鉴别他人,通过和别人的交往获得幸福,避免祸患。”由此可见审察人生的重要性,它是我们走向卓越、走向幸福、走向圆满的一条捷径。
保持平衡,凡事勿过度
然而,有意思的是,哲学是一种充满思辨性的智慧,任何事情在它面前似乎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苏格拉底告诉我们,审察人生很重要,一个未经考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但凡事无绝对,这种考察并不是越多越好、越细越好。这也就引出了德尔菲神庙的第二条神谕:凡事勿过度。
对此,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他天资聪慧,12岁就考上了当时英国最好的大学之一——爱丁堡大学。18岁时他离开大学,做过军官、外交官,当过家庭教师、图书管理员。但这些职业只是他的谋生手段,唯有哲学和写作,才是他毕生的事业。
休谟是一个早慧的天才,从离开校园那一年起,他就开始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哲学的本质就是审察和思辨,非常耗神。在经过六个月高强度的研究后,休谟发现自己有点力不从心,新的思维火花不再闪烁。他以为是因为自己太懒散,于是加倍努力,结果九个月后,他的身体也出了问题。
医生诊断说,由于思虑过度,休谟患上了抑郁症。年仅18岁的他又高又弱,骨瘦如柴,仿佛一个痨病鬼。他的手上不断出现坏血点,嘴巴也不停地流口水。在医生建议下,他在学术研究上有所放松,并坚持每周骑马、散步。直到三四年后,他的病情才彻底根除,面色重新红润起来。
经过这一经历,休谟意识到了过犹不及的道理。人生的确需要考察、反思,但凡事都要有度,过度考察的人生没法持续,它留给我们的,只有无处安放的惶惑。
此后休谟开始在哲学与生活之间保持平衡。他说:我想做个哲学家,同时我也想做一个人。做哲学家,需要审察和思辨;而做人,则需要更多的烟火气。正是这样的平衡,让休谟能左右逢源,成为了真正的自己。
休谟是学界公认的英国最伟大的哲学家,站上了西方哲学发展史的巅峰。与此同时,他也是个知足常乐的胖子。比如,他曾在晚年回忆录里开心地写道,自己在36岁那年攒了1000英镑,早早地实现了经济自由;比如,他经常盘算哪本著作能让自己声名鹊起,一旦猜中就乐不可支……
这些小故事看似庸俗,却并不让休谟招人厌烦,反而透露出一股更愿意让人亲近的烟火气。休谟自己也充分享受着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他说:“我吃美食,我玩牌,我跟朋友聊八卦;享受过人生幸福后,我再返过头来看哲学思辨,就会觉得它们是那样地冷酷、牵强、可笑……”
可以说,休谟深得我们东方的中庸思想的精髓。俗语说得好,“物极必反、月满则亏”,再好的事一旦“过度”,带来的往往也会是更糟糕的体验。比如说德国哲学家尼采,正是因为对“强者”的无限尊崇,最后被纳粹歪曲、利用,沾染上“纳粹哲学家”的污名。
尼采推崇强者,仇视弱者。他认为强者的生命力强健饱满,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的希望。而弱者和失败者则躲在人群中,打着爱与同情的名义,嫉妒、怨恨甚至阻挠强者。因此,尼采说,这些弱者和失败者就是一剂毒药,消磨着整个人类的力量。
那么,尼采为什么对爱与同情的看法如此负面呢?事实上,尼采并非无条件地反对这两种情感,他激烈抨击的,是宗教宣传中的伪善。他认为宗教既虚伪又狡猾,把“软弱、无能、卑微”等消极情感进行包装,改头换面为“善良、美好、仁慈、爱与同情”,大肆宣扬,把人类带上歧路。
比如“同情”这种情感。尼采认为肤浅的同情就是一种粗暴的、无所顾忌的伤害。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痛苦,不去做深入的了解,外人就没法理解这种痛苦。但那些同情的施舍者却并不想了解别人的苦痛,而是喜欢指手画脚,给出一些轻飘飘的建议。这样的同情,不但不能让人家放松,反而会让痛苦进一步加剧。
如果从抨击伪善这个角度看,尼采的这种说法是十分中肯的;但尼采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抨击,视同情心为一种恶性。他写下这样的文字道;“人类最大的恶习是什么?就是对于失败者和弱者的同情,我们人类之爱的第一原则,就是要推动弱者和失败者走向灭亡!”
这些偏激之语暴露出了尼采思想中阴暗的一面,以及被误读的巨大可能。所以后来德国纳粹才会利用这些言论,别有用心地解读出了种族歧视、种族灭绝等内容,把大批犹太人送进了毒气室。而这显然不是尼采的本意,他在宣扬“强者哲学”时,显然未曾料到会导致这样可怕的后果!
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神谕中蕴藏的无穷智慧,感受到哲学的思辨魅力。苏格拉底告诫我们要保持人间清醒,不要浑浑噩噩、狂傲自大地度过此生;而休谟和尼采则从另一个角度警示我们,难得糊涂、适度宽容也是一种人生智慧。
从这个角度看,东西方哲学文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就像苏东坡在《定风波》中所写的:“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就是人生的最佳状态,保持几分人间清醒,同时也不会钻入牛角尖不可自拔,哪怕外面的世界风雨如晦,我们也能闲庭信步、吟啸徐行。
生存与毁灭,就在一瞬间
在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中,神曾这样警示忒拜城的子民:“凡人的子孙,我把你们的生命当作一场空!谁的幸福不是表面现象,片刻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句台词中,就蕴藏着德尔菲神庙的第三条神谕:“生存与毁灭,就在一瞬间”。
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曾借哈姆雷特之口,发出了对人生的终极一问: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如果活着,是要默默忍受狂暴命运的无情摧残,还是与深如大海的无涯苦难奋然为敌,将其击退?如果选择死,那死亡就是一场睡眠,可陷入这场睡眠中,人又会做什么梦呢?
哈姆雷特讲到了对于死亡的纠结与恐惧,那是我们无可回避的最后归途。但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一绕不过的宿命?纠结和恐惧是我们的应有状态吗?几千年里,这始终是一个哲学家们孜孜以求的研究命题。
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就开始思考如何理性应对死亡。在被雅典城邦宣布处以死刑的那一刻,苏格拉底不仅没有害怕,反而有些跃跃欲试。他说,死亡并不可怕,反而是一种福气。
他分析说,人死后有两种可能。第一是灵与肉俱灭,从此一了百了,陷入安眠无梦的大睡中,和充满苦痛的人世相比,这是一种宁静的幸福。第二是灵魂与肉体分离,灵魂脱离肉体移居到另一个世界,参加一场永不谢幕的豪华派对,和历史上那些英雄、艺术家们相会,这是一种欢乐的幸福。
此外,苏格拉底还说,真正的哲学家要一直练习死亡。当然,这并不是说哲学家每天都要变着花样残害自己,而是说他们要学习如何让肉体与灵魂彻底分离。对灵魂来说,肉体就是一个巨大的羁绊,我们可以通过练习面对死亡,以此来削弱肉身对欲望、利益、输赢的追求,进而获得渴望已久的智慧和精神自由。
在苏格拉底之后,还有很多哲学家痴迷于死亡话题。哲学家伊壁鸠鲁曾论证说当我们存在时,死亡就不会来临;而死亡来临时,我们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死亡与我们无关,并没有什么可怕。而之后的斯多亚学派更为激进,他们说要像归还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那样面对死亡,坦然地投入死神的怀抱。
等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了“向死而生”的哲学命题,令人振聋发聩、耳目一新。他号召人们通过启动死亡的倒计时,倒逼精神上的觉醒和成长,最终实现对死亡的超越。
要想了解“向死而生”的真正含义,我们得先来了解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存在”是一个与“存在者”相对应的概念。我们日常关注的东西都是“存在者”,如叛逆期的孩子、迅猛上涨的房价,等等。这些“存在者”夺取了我们全部的注意力,让我们忽视了“存在”本身。
那存在本身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把所有“存在者”剥离后剩下的东西。比如,我们常说A是B,B是C,C是D……把A、B、C、D这些主语、宾语都去掉,剩下的只有“是”这个谓语,这就是“存在”。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但海德格尔纠正说“我在故我思”,因为我的“存在”,“思”才能派生出来。
在明确何为“存在”之后,海德格尔进一步提出了人生的两种存在状态,沉沦状态和本真状态。所谓沉沦状态,就是尚未通过思考觉醒的状态,此时我们听不到内心的声音,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而本真状态,就是自我觉醒后所追求的真正生活。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就处于沉沦状态。因为对于出生,我们无法做出选择。就像一块石头被抛入水中,我们被粗暴地抛到了这个世界里。此后大量的外部信息汹涌而来,占据了我们的大脑,但很少有人会对这些信息进行思考和质疑,比如说,为什么交通规则一定是红灯停、绿灯行?为什么股票涨用红色,跌用绿色表示呢?所以海德格尔才会说,我们缺少“认识自己”的意识,懵懵懂懂地活着。
因此,我们就需要一个大事件,把陷入沉沦状态的自己唤醒。而这个大事件,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向死而生”。他认为“先来到死面前,看清丧失在沉沦状态的日常存在。此时我们就不再沉陷于日常幻想,而是立足于人生的各种可能,在向死存在中获得自由。”
所以,“向死而生”让我们能在三个层面上超越死亡。它让我们认真思考:死亡还留给我们多少时间?我们生命中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因为意识到了时间的稀缺,我们开始发掘内心真正的声音,并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在不断的选择中,本真存在开始自行显现。这是第一重超越。
向死而生的第二重超越就是采取行动,把人生的各种可能变为现实。意大利雕塑家米开朗基罗曾这样解释自己的雕塑:“我在大理石身上看到了作品,于是把那些多余的石头凿掉,作品就诞生了。”在死亡的催促下,我们会像雕刻家那样起而行之,发现、释放自己的潜能,塑造更好的自己。
向死而生的第三重超越就是战胜对死亡的恐惧。我们聚焦于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把每一天都过得热烈饱满、充满意义。我们尽情享受光辉灿烂的“存在”,不给人生留下遗憾,自然就能平静地面对“存在”的终结,即死亡的到来。因为生如夏花之灿烂,所以死若秋叶之静美。
除此之外,向死而生也是一种人生态度的选择。人生这场“存在”,一端连着我们的来处,另一端连接着我们的归途。我们无法选择出生,我们也无法选择死亡,但如何度过这两端之间的短短一瞬,其选择权却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是沉沦而迷失,还是通过向死而生,成就真正的自己?
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萨特认为: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而这种选择和行动则塑造了我们。正是选择,赋予了这短暂人生最大的意义,让我们超越了神的警示,纵使生命只是一场空,我们也要赋予这场“空”以意义;纵使幸福只是表面现象,我们也要创造独属于自己的幸福。
那么,讲到这里,或许有朋友已经意识到,德尔菲神庙的这三条神谕有着内在关联,它们首尾相连,构成了一个智慧圆融的希望之环。正因人生苦短,所以我们需要万分珍惜,认识自己、活出自己;我们要保持清醒,同时也要热爱生活。真正的英雄,就是在看清生活的本质之后,依然热爱它。
而这也是哲学最有意思的地方,它不会给我们一个标准答案,自然也不会用标准化框定我们的人生。它跟充满质疑和叛逆气息的摇滚乐一样,不但是一个名词,更是一个动词。它推着我们思考、前进,推着我们做出一次次选择,最终探索出一条富有生机、永不止息的人生之路。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