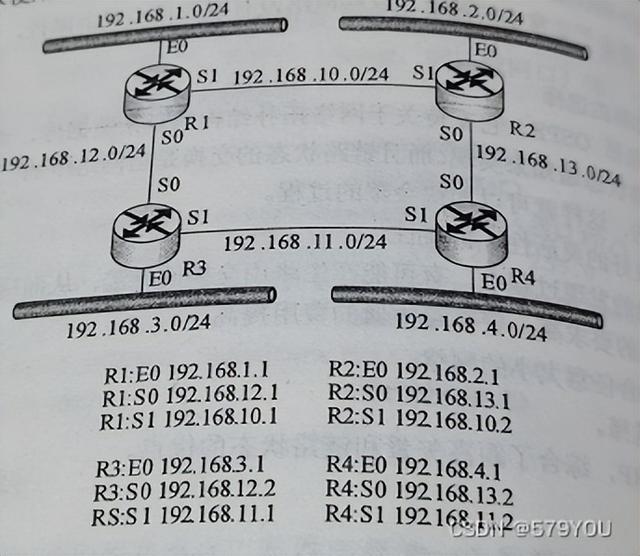文学女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加拿大文学女王)

一、周六清晨俱乐部
1946年,阿特伍德进入全日制学校读书。刚开始时,她在多伦多北部的约克公爵学校上学,那块地方尚未开发,周边是一望无际的农田。接着,一家人搬到利赛德区,阿特伍德先进了惠特尼公立小学,然后上了本宁顿高地小学。
当时的学校无论是在教学方法还是在教学态度上都视自己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前哨。教室墙壁上挂着英国国王和女王的画像,学生们要学会背诵所有国王和女王的名字,要会画英国国旗,会唱英国海军军歌《统治吧!不列颠尼亚!》。学校课本里深藏着大英帝国自鸣得意的种族主义,例如校园读本上有这样的诗句:“小小印第安人,苏族或克里族,难道你们不希望成为我。”就连爱国歌曲《永恒的枫叶》里都被注入了对英国的忠诚:“在很久以前,从不列颠海岸,无畏的英雄沃尔夫扬帆而来,牢牢插上英国国旗,在加拿大美丽的国土。”加拿大学校非常重视与英国的联系,会倡议孩子们为深受大战影响的英国贫苦家庭捐献衣物。
然而,此时的加拿大已经开始感受到来自另一个地方的吸引,那就是北纬四十九度国境线南部的美国。孩子们阅读的漫画书描绘的是像“美国队长”这样的超级英雄。在这些漫画里,坏人是德国人和日本人,好人则是美国佬。阿特伍德在回顾往事时开玩笑说:“我们知道所有日本人临死前都会大叫‘啊噫’,德国人则会喊‘阿尔格’。”此外,孩子们还看诸如蝙蝠侠、黑鹰、霹雳火、塑胶侠和惊奇队长之类的漫画。在与阿特伍德同龄的孩子眼中,漫画书里有着关于宇宙的真理。他们看完一本便相互交换,因为交换频繁,封皮都快掉了下来。对于边境线外正在进行的各种活动,孩子们充满羡慕和向往,同时也有一丝自卑,因为他们“只能观看而无法参与”。
阿特伍德的父母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女儿天资聪慧,光靠学校教育无法满足她那旺盛的求知欲,于是,他们想方设法让她参与到各种活动中去。阿特伍德九岁时,父母安排她报名参加了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周六清晨俱乐部。同时报名的还有她的好友梅格,她的父亲是希腊考古学系主任。
安大略皇家博物馆位于布洛尔大街和皇后公园拐角,当时还是一栋古老的哥特式建筑。它在1914年由查尔斯·特里克·克瑞利创建,克瑞利担任负责人期间,在埃及、克利特岛和小亚细亚半岛野外考察时收集了大量藏品。
周六清晨俱乐部的成员聚集在博物馆地下室的指定位置,各人分派一张木折凳。负责的大人将他们带到楼上的一个展品部,等大家坐下后,便开始讲解尘封在玻璃柜里的展览品:有时候是仪式使用的面具,有时候是盔甲,有时候是埃及神灵的石像。听完讲解,他们再折回地下室,用颜料、胶水、纽扣、羽毛外加想象力创造他们心目中的模型。
这个时候的博物馆尚未开始对文物展开修复工作,也还没有引入特技照明和视频等现代技术,里面的东西都杂乱地摆放着,却并不让人反感,反而能在孩子心目中造成戏剧性效果,仿佛钻进了一个时光胶囊,扑面而来的是遥远年代的气息,令人惊叹和流连。“例如,走下地窖,那里有一大组由塑料制成的印第安人,蹲在绉纸做的火堆旁,走上几段楼梯,有一个埃及木乃伊盒,盒盖开着,里面是具风干的尸体,用膏布裹着。那里还有许多武器——剑、铳和弩弓,最令人兴奋的是,那里有整整一间屋子的恐龙,那时它们是我最喜欢的野生物种,还有一群剑齿虎被困在沥青坑里的全景图。”
年少的阿特伍德徜徉在博物馆,安静地、耐心地观察里边的藏品。她最喜欢上完艺术课,和梅格一起,躲开博物馆管理人员,自个儿在里面探索:“(博物馆里的)空间似乎没有尽头,像迷宫,空无一人,只有雕塑、神像和看不见的人穿的衣服,散布着各种我只能在探险故事里才能遇见的物品——弩弓、吹箭筒、墓地掘出的项链、穴熊、颅骨。我们最喜欢的当然是埃及木乃伊,我们靠近它们,心里充斥着一种有点恶心又有点期盼的恐惧——它们会不会动起来?”
阿特伍德把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称作她的“博物馆初恋”。父母让她参加周六清晨俱乐部的初衷或许只是希望她拓展视野、结交朋友,阿特伍德得到的却远远不止这些。博物馆丰富了她的精神世界,...
二、小荷才露尖尖角
阿特伍德的学校每周都会有一位“宗教知识”老师前来上课,同学们先是大声阅读《圣经》段落,然后练习合唱赞美诗。为了能融入朋友们的圈子,阿特伍德坚持要去上主日学校,父母拗不过她便同意了。她就读的长老会卫理公会主日学校要求孩子们读《圣经》、写小论文,她写的关于戒酒的论文还获了奖。
青春年少的孩子无论对什么都怀有一种天然的好奇心,宗教形成的小圈子让阿特伍德产生了暂时的归属感,但她对宗教观念并非抱着被动接受的态度,她曾在学校就宗教中的一个问题向朋友提出挑战:“如果天堂是好地方,如果它比地狱好,为什么谋杀好人是件坏事?难道你不是在施恩于他们,因为那样的话他们会更早到达天堂?只有谋杀坏人才是坏事,因为反正他们不会上天堂。可是假如他们很坏的话,他们当然该杀。因此考虑到各个方面,谋杀好人和坏人其实都是好事;对好人来说你是在帮忙,对坏人来说是他们活该。”小小年纪的阿特伍德伶牙俐齿,无论在逻辑思维能力还是在表达能力方面都首屈一指,她那个时候便敏锐地觉察到:一旦处理不当,宗教会有失去控制的可能性。《浮现》中的女主人公描述她第一次遭遇宗教时,是在砾石水泥砌成的校园里,有孩子吓唬她说天上有个死人在看着她所做的一切,她报以反击,向他们解释婴儿是从哪里来的,妈妈们纷纷打电话向她母亲抱怨。女主人公对待宗教的态度活脱脱就有着阿特伍德的影子。
阿特伍德在小学阶段表现出色,她从六年级直接跳到了八年级,于1952年进入利赛德中学。当时有个流行的说法:见过世面的孩子上贾维斯中学,有钱人家的孩子上森林山中学。总之,两个学校的学生都有些瞧不起定位于中产阶级的利赛德中学。
利赛德中学的学生在校必须穿校服,女生是穿黑色方领束腰外衣、白衬衫,春秋季着过膝袜、冬季着黑色长筒袜。因为女孩们总是想方设法用腰带把衣服往上束,抬高下摆,校方规定,束腰外衣在膝盖上方不得短于七英寸。阿特伍德没有这些女孩子的小心机,她严格遵循校规,穿得中规中矩。
阿特伍德所在的八年级班只有八个学生,她是其中年纪最小的一个,“长得干巴巴的,其貌不扬”。她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适应学校生活。当时的加拿大公立中学仍效仿大英帝国,学生们学习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中世纪欧洲、英国和美国历史。加拿大历史得等到十三年级才开始学习,而那时已有不少学生辍学。阿特伍德一直记得中学里的加拿大历史课本——《当今世界的加拿大》,封面上画了一架飞机,内容不外乎麦子是谁种的、大家对议会体系有多满意之类。至于文学,则只有莎士比亚以降的英国文学,学生们依然要等到十三年级才能选修加拿大文学。唯一造访过利赛德中学的加拿大诗人是年迈的威尔逊·麦克唐纳德,他每年会到学校朗诵《滑雪之歌》和《红枫树》。对中学里加拿大历史和文化的缺失,大伙儿泰然处之,相信真正的历史和文学都在国外。
阿特伍德是个全面发展的学生。她学习成绩优异,代数总得满分,植物学相当出色,还选修了法语。利赛德中学年鉴的九年级集体照下有一首诙谐打油诗:“玛丽喜欢黑眼睛男生。佩吉爱学习。约翰·B专业抓苍蝇。”可见阿特伍德学习好是出了名的。她的校园生活丰富多彩,加入了校篮球队,是校“联合国俱乐部”成员,《宗族召唤》年鉴编辑,还是“三重奏”歌唱小组的一员。在十二和十三年级时,阿特伍德开始为校报《家校新闻》撰写专栏文章,她的栏目“新闻提要”旨在让同学们了解最新发生的事件:学校例会、启蒙仪式、校园选举、各个俱乐部的活动以及即将举办的舞会和体育活动。阿特伍德利用专栏报道了一些优秀女生的事迹:吉恩·马修斯和凯伦·怀特托克在《多伦多每日星报》主办的植物学竞赛中获胜;埃利诺·科布尔迪克获得了帝国石油奖学金……阿特伍德在报道时或许已暗下决心,她终有一日也将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女生,进入梦寐以求的大学深造。
阿特伍德在中学阶段就显露出导演的天赋。十二岁时,她和朋友上了一门课,学习制作牵线木偶。很快,她们便开办起“木偶生意”,为孩子生日聚会演木偶剧。有一次,一位邻居的小女儿心心念念想要一场木偶戏作为生日礼物,女孩的妈妈找不到专业表演者,便来跟阿特伍德商量。阿特伍德觉得这个想法棒极了,便摩拳擦掌准备起来。她和朋友将面粉和水调成糊状,把报纸撕成条,做成木偶脑袋,刷上糨糊,然后晾干,用蛋彩画颜料着色,做出来的木偶“绿脸,模样可怕”。她们制作了一个摇摇欲坠的舞台,用一只长筒黑袜罩住后台的灯泡,模拟夜间照明。阿特伍德写的剧本通常基于童话故事,如《三只小猪》《糖果屋历险记》和《睡美人》,但她们造出的声像效果令人毛骨悚然。两个女孩的木偶戏声名大噪,甚至有公司圣诞聚会邀请她们前去表演。
十六岁时,阿特伍德在家政课上自编自导了一出关于合成纤维织物的轻歌剧,剧名为《合成织物:独幕轻歌剧》,在学校礼堂上演。她将歌剧背景设置在合成纤维织物王宫内,国王煤炭、王后和他们的三个孩子——腈纶、尼龙和涤纶——围坐在桌边喝茶。父母讨论着卓夫特和汰渍牌洗衣液的优点,孩子们则互相拌着嘴,抢着标榜自己最成熟,抱怨父母把他们当成孩子。这时,白马王子威廉·羊毛爵士来了。他有个致命缺陷:一洗就缩水。大家建议他和腈纶结婚。他们俩结合能产生华达呢。整部歌剧以讽刺幽默的基调,嘲弄了当时社会的庸俗和奢侈。
少年时代的阿特伍德多才多艺,会唱会跳会导会玩耍。她是张扬的,一旦拥有自己的立场,便会据理力争;她又是沉静内敛的,有着独特的内心世界。学校年鉴的两段描述可以概括她这一时期的个性。在十二年级照片下面,编辑以观鸟者的视角,用讽刺的手法描述一个个同窗好友,对阿特伍德的描写是这样的:“佩吉·阿特伍德,全身羽毛——波纹头羽。叫声——让我们做点有独创性的事!”阿特伍德毕业那年,《宗族召唤》上关于她的介绍是:“佩吉的不算太秘密的抱负是写出加拿大人的小说——有那样的英语成绩,谁又能怀疑她的抱负?她的万圣节舞会通知众所周知。她写的广告歌曲《驯鹿嬉闹》是对自我的超越。”而此时,属于阿特伍德的人生剧幕才刚刚拉开。
三、博览群书的日子
阿特伍德的父母热情好客,家里经常会有客人到访,他们的到来使阿特伍德眼界大开。访客中有父亲的朋友保罗·普罗文彻和西格德·奥尔森,他们都是科学爱好者,常和卡尔·阿特伍德一起划着独木舟出去旅行。普罗文彻是森林学家和艺术家,1853年出版了《我生活在树林里》,这是一本个人回忆录和林地知识方面的作品。阿特伍德特别喜欢普罗文彻,因为他学识渊博、幽默风趣。他在饭桌上讲述自己在北部荒野的历险,能把人逗得差点从椅子上滑下去。奥尔森出生于美国,是个环保主义者,提倡保护荒野。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明尼苏达北部和安大略西北部的湖泊和森林里担当荒野向导,闲暇时著书立说,主要撰写自然史、生态和户外生活方面的文章。阿特伍德十七岁时,奥尔森出版了第一部作品《低吟的荒野》,书中体现出的对荒野的热爱使阿特伍德产生了诸多共鸣,让她感受到荒野和自然在文字中的魅力。阿特伍德从这些人身上学习到的不仅仅是对科学的激情和对知识的无限追求,还有那种为了热爱的事业一往无前的精神。
少年阿特伍德最爱的是读书。只有沉浸在书本世界时,她才最怡然自得。她如同一头杂食动物,什么内容都可以“吃”下肚。在学校图书馆,她爱读埃德加·爱伦·坡的恐怖小说。在家时,她偷偷溜到地下室,对父亲的书架“扫荡”一通。父亲是个历史迷,地下室到处堆满了历史书。于是,阿特伍德在十二岁时读了纳粹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的传记,在十四五岁时读了丘吉尔关于战争的五卷本著作。
父亲的书架上还有一类书,是关于森林知识的,有些由父亲认识的人撰写而成。或许是因为这些书与阿特伍德童年时代的生活非常贴近,能让她产生自然而然的亲切感,她总是百读不厌。它们和奥尔森以及普罗文彻的书一起,充实了阿特伍德的课外生活。
阿特伍德对两位作家的作品特别痴迷。其中一位是埃尔斯沃思·耶格,他的著作《原始林知识》是一本丛林生活指南,里面附有精美的插图。耶格对历史有着精准的描写,他深入研究了19世纪的生活,以优美的笔触描绘了那个时候的人们处理日常危险的手段以及依赖双手和智慧赢得的生存技巧。他在《原始林知识》中指导读者利用自己的技能和创造力在野外求生,其中包括如何生火,如何划独木舟,如何使用刀斧,以及如何利用手头的材料搭建窝棚。
《原始林知识》对青少年有着特殊的吸引力。耶格在书中教育小读者们千万不要在大树下搭建营地,因为闪电极其危险。他解释了冬夏季节在丛林里扎营的方法:冬天的营地最好要面对悬崖,因为悬崖能将热量反射进帐篷。他教孩子们几种生火的方式,像弓钻打火棒、泵式火钻和火锯等都非常实用;他教孩子们辨别鸟兽的“声音”,描述该怎样呼唤驼鹿、麝鼠和河狸等。书中有一章标题是“迷路”,开头写道:“记住,你没有迷路。你只是无法找到营地而已。”给野外探险的人树立信心。
书中最吸引阿特伍德的是一长串对丛林食物的描写,包括坚果、可食根和菌菇。搬到城里后,她依然有机会每年夏天随父母去丛林生活一段时间。她常常对照耶格的作品,兴趣盎然地辨认、采挖、烹煮和品尝各种天然食品。她还和哥哥试着用狼尾草的花粉做烙饼,用河泥制作陶罐。对阿特伍德而言,书本描述的世界是一回事,对知识的试验和实践是另一回事,由此可见她严谨的科学精神。这些知识在她日后的写作生涯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浮现》里的无名女主人公擅长林地生活,她是划独木舟的一把好手,能够不靠地图观察丛林状况,懂得天气变化形势,还能辨别各种类型的动植物。
阿特伍德迷恋的另一位作家是19世纪的欧尼斯特·汤普森·西顿。西顿是个造诣深厚的博物学家,爱好神话传说,他曾写过不少游记,但最出名的还是动物小说,他将神话元素和科学知识融入动物小说,这使他的作品充满魔力,各个年龄层次的读者都爱阅读,尤其吸引孩子。
阿特伍德对西顿的第一部小说《我所知道的野生动物》爱不释手,这是一本从动物视角讲述的动物们自己的故事,向读者打开了通向动物世界的神秘大门:这些动物有理智、有感情,甚至有着悲剧英雄般的气质,彰显了生命的尊严。西顿在前言中写道:“既然动物拥有想法和感情,只不过在程度上与我们的不同,它们肯定拥有自己的权利。”这句话深深镌刻在阿特伍德脑海里,对她的创作具有很大影响。她喜欢描写动物,她笔下的动物大多有着悲剧式的命运,在人类文明的匆匆脚步下走向消亡,比如《浮现》里受残害的动物:加油站油泵平台上陈列的被剥了皮的驼鹿,它们披着人的外衣,后腿用金属丝固定,以招揽顾客;森林里被杀戮的苍鹭,脚被蓝色尼龙绳缚住,头朝下吊在一根树枝上,翅膀张开,垂落下来,被捣碎的眼睛注视着过往的行人。比如《彼国动物》中的悲情动物:“在这个国家动物/具有动物的/脸/它们的眼睛/在汽车前灯的光照中闪现一下/便消失不见/它们死得并不优雅/它们的脸/不属于任何人。”阿特伍德对动物有着无法割舍的同情和关爱,这与她早年的丛林生活有关,但也不可否认西顿作品对她的熏染。
有书相伴的日子总是过得充实而愉快,阿特伍德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一点一滴地汲取书中的营养。这些书籍在潜移默化中融入她的骨血,让她的内心变得坚韧而丰盈,铸就了今天独一无二的作家阿特伍德。
四、少女艺术家的烦恼
阿特伍德十岁左右时去参加同学的生日会,同学家长请小朋友们看了场电影《红菱艳》。阿特伍德一直记得自己在电影院的感受,她的心情随着电影情节的发展而跌宕起伏。《红菱艳》讲述了女艺人维多利亚·佩姬的故事,她凭着努力和天分成为著名芭蕾舞演员,与作曲家朱利安相恋,陷入事业与爱情的两难抉择。阿特伍德为佩姬的翩翩舞姿所倾倒,同时又为她的悲剧命运沮丧不已:她冲出剧院追赶丈夫时被迎面而来的火车轧死。这部电影令阿特伍德幼小的心灵饱受冲击,她隐约从影片中得到了这样的信息:如果你是女孩,就不能既成为妻子,又成为艺术家。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北美大陆,女孩子们从十五岁起便开始考虑嫁人生子的事。当时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时尚巨擘纷纷鼓吹婚姻的重要性,有些美国大学甚至设立了婚姻系,开设婚姻课程,婚姻指导类手册在市场上卖得相当火爆。据统计,在二战后十年里,北美大约发行了一千多册此类书籍。根据书中的说法,女人的成功就是拥有成功的婚姻,她们最好在二十至二十四岁之间把自己嫁出去,生儿育女,否则就成了没人要的老姑娘。深受加拿大女性喜爱的《淑女之家杂志》和《城堡女主人》主推优雅生活类文章,里面刊登的故事大多以婚姻作为美满结局。一些妈妈对受过教育的女儿们的传统建议是:找个有稳定收入的男人,不要指望太多;任何职业都是权宜之计;既然只有美貌才是最有用的婚姻赌注,如果不是大美人,最好不要太野心勃勃……
对于自己的人生之路,阿特伍德也时常感到迷茫。她觉得自己应该有一份职业,起初,她想做画家,想当植物学家。进了中学后,她觉得应该自己养活自己。当时的指导类书籍列出了五种面向女孩的职业:护士、教师、空姐、秘书和家政。阿特伍德决定主攻家政,因为这份职业收入相较其他几种要可观些。为此,她选修了家政课,凭着自己的独创性和想象力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比如,她会拆掉所有的拉链,设计出自己的裙子;比如,当别的女生在织物上使用花纹时,她则大胆采用橘色和绿色,画上类人猿和蝾螈等动物形象……如果阿特伍德朝着这条路走下去,没准世上就多了位著名时装设计师。
然而,在内心深处,她总觉得这样的职业选择缺少了点什么。她的世界属于书,也只有书能充实她的灵魂。十二年级时,学校来了位英文老师比林斯小姐,她的文学课生动有趣,颇具特色,阿特伍德完全被吸引了,她第一次觉得自己或许可以追求一种文学生活,在这一想法的推动下,她渐渐远离了家政课。根据阿特伍德自己的描述,1956年的一天,阳光灿烂,毫无任何预兆,她“成了一名诗人”。那一天,她正走在足球场上,“不是因为我想去运动,也不是想去更衣室后面抽烟……而是因为这是我正常放学回家的路。我像往常一样悄无声息地快步走着,没有任何杂念,这时一根隐形的拇指从天而降,按在我头顶心。一首诗歌形成了。这是首相当忧郁的诗;年轻人的诗歌大体如此。这首诗是礼物——匿名人士馈赠的礼物,也因此既令人兴奋又邪恶不祥。”阿特伍德在这个意义重大的日子创作的诗歌虽然没什么价值,却具备诗歌的特征:有韵律,有格律,与拜伦和艾伦·坡的诗相似,又有点雪莱和济慈的味道。事实上,那时候的阿特伍德对20世纪的诗歌知之甚少,她几乎没有听说过现代主义和自由诗。而她不知道的事情还远不止这些,她接下去写道:“例如,我不知道自己正要跨入一整套与诗人有关的成见和社会角色之中,他们是什么样子的,他们该如何表现……我十六岁时,世界很简单。诗歌存在,因此可以将它写下来。没有人告诉过我——尚未有人告诉我——那许许多多不能由我来写诗的原因。”
当她在学校自助餐厅向几位女友宣布自己想当作家的消息时,朋友们一下子安静下来,谁也不说话。一位朋友在多年后告诉她,大家都很震惊,倒不是因为阿特伍德说了什么,而是因为她有勇气大声说出来。
阿特伍德的父母非常开明,他们觉得当时的婚姻市场完全没有道理,女孩子应该接受良好的教育,拥有自己的事业。但阿特伍德的抉择也让父母感到惊愕:她如何靠写作来谋生呢?作为经历过大萧条的一代,他们深知人需要一份正式职业,以防万一。但是,即便他们认为她的抉择从经济角度来说不明智,却并未阻止她去追求梦想。她母亲还是那句话:“没人指导佩吉。我觉得没人能指导佩吉。”
周围的其他大人却不这么想,他们无法理解阿特伍德写作的愿望,认为这只是成长阶段的怪念头,到了一定年龄自然就消失了。她母亲的一位朋友说道:“嗯,很好,亲爱的,因为你可以在家做这件事,是吧?”阿特伍德无法忍受这样的看法,她感觉到了孤立:“你觉得别人都不同意你的想法。(你被视为)疯狂、奇怪、古怪、乖僻、脑瓜子太灵光。”那个时候,她是多么希望除了父母之外,能有人支持她的写作梦啊。
少女艺术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烦恼之中:“当我开始写诗时,我没有读者,也想象不出有哪个人会成为读者……那是1956年,女孩们的正确姿态是收集些瓷器等着嫁人,尽管我身边的朋友打破了这一成规——一个想当医生,一个想当心理学家,一个想当演员——但没有人想成为诗人……我有个模糊的念头,我想写作,但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愿意读……起步时没有资质是件可怕的事。”阿特伍德隐隐明白,写作对她就像一场赌注,因为她无法证明自己是否拥有这方面的能力;此外,《红菱艳》所渲染的结局深深影响了她,电影中的佩姬命运多舛,而现实生活中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佩姬,她们是一群既不健康也不快乐的女人:“古怪(如乔治·艾略特和柯蕾特)、未婚(如简·奥斯汀和艾米莉·狄金森)、孤独(如克里斯蒂娜·罗塞蒂),或者患有临床忧郁症,到了要自杀的地步(如弗吉尼亚·伍尔芙、西尔维娅·普拉斯和安妮·塞克斯顿)。”阿特伍德在潜意识里认定,作家和结婚生子无法两全:“你不可能既为人妻母又做艺术家,因为任何一种身份都需要全身心投入。”然而,在那样一个崇尚婚姻的年代,十六七岁的她觉得自己仍无法免俗,毕竟,放弃婚姻代价太大。
到底该怎么办?阿特伍德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一条路通向作家,充满了不确定因素;一条路通向婚姻,相夫教子,平淡地走完一生。阿特伍德选择了前者,她不希望自己早早被困在婚姻里,与尿布奶瓶斗争。自打那根从天而降的拇指按在她头顶起,写作便成了“一切事情的答案,感觉棒极了”,因此,哪怕撞得头破血流,她也要努力实现梦想,写出“加拿大人的小说”。实现梦想的第一站便是大学,她要在大学里丰富自己的心灵,磨砺自己的心志,提升自己的修养。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