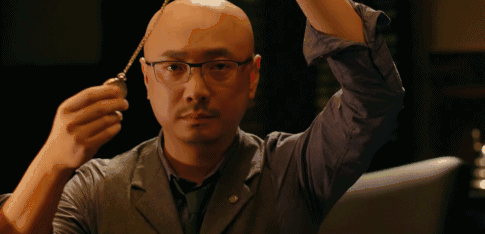第十三章蛛丝马迹(第二十三章二子乘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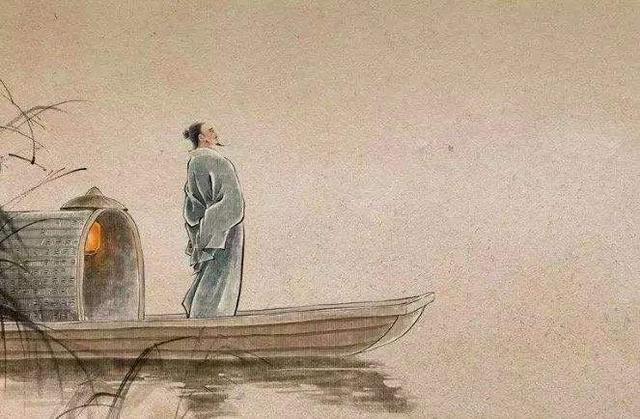
现在让我们先离开郑国的纷纷扰扰,放松一下,插一个春秋时期著名的小故事吧。
又是一个和女人有关的故事,在春秋完全是男性主导的权谋斗争、尔虞我诈中,总有那么一些有个性的女性夹杂进来,或者可爱、或者可恨、或者可敬、或者可鄙,她们和那些手握着国家命运、历史进程的无聊男性权贵们一起演绎出一幕幕动人的悲剧,从来……从来……没有喜剧。
这个故事发生在卫国,当年公子州吁创造了春秋历史上第一次弑君事件后不久被杀,前情参看郑卫相争的故事。
他死后卫国人接回了他在邢国留学的兄弟公子晋立为国君,史称卫宣公。
这哥们是个乱仑专业户,当初他和父亲卫庄公的一个小妾夷姜私通,生下一个儿子叫急子,卫宣公非常宠爱他们母子,回国当上国君后就把急子立为世子。
后来急子长大了,卫宣公就张罗着给儿子订了一桩婚事,女方是齐僖公的一个女儿叫宣姜。这也算是和齐国签订了婚姻联盟协议。
到了成婚的日子,卫宣公亲自去大门口接新娘子,准备好好给儿子操办一场盛大、喜庆、庄重的婚礼。
不料,在卫宣公见到儿媳妇的那一刹那,故事开始了。宣姜长的太漂亮了,那叫一个风姿绰约、风华绝代。她是齐僖公的小女儿,和姐姐文姜都是春秋时代著名的绝色佳人。个个妖冶淫荡,而且个个都有故事,都喜欢乱伦。真不知道这姐俩的基因工程怎么构成的。
卫宣公一见儿媳妇,顿时肾上腺素荷尔蒙大爆发,直冲大脑,破坏了脑中枢神经,导致大脑运行暂停,都不知道手脚放哪儿了,眼底肌肉彻底僵硬,眼珠子不会转了,耳内鼓膜功能消失,大厅里的所有声音都进不来了,嘴里哈喇子一个劲的流,舌头都掉出来了。
可见美女的威力是无穷的,什么都不用做,往哪儿一站就能收了男人的魂。
过了好一会儿,卫宣公的大脑勉强恢复工作后,咽了口哈喇子,把舌头收回去,当场宣布,婚约搞错啦,不是俺儿子和宣姜结婚,是俺想给齐国国君殿下当女婿。
在婚礼现场的所有人,亲戚、家人、宾客、侍者、齐国来送婚的使节、诸侯来道贺的代表、新郎急子、婆婆夷姜,大家像听了儿歌口令一样,“我们都是木头人,不许说话不许动”于是一起做呆若木鸡状,眼珠子差点瞪出眼眶、伴随着一片下巴砸在地上的声音。
卫宣公一看大家都蒙圈了,也不啰嗦,婚礼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一切都是现成的,卫宣公来了场自助婚礼。
拉着云里雾里还没醒过味的宣姜,自己唱礼拜天地、喝了交杯酒,还没忘了敬大家几杯,说了几句:“同喜同喜”。然后把自己和宣姜送入洞房,婚礼到此结束。
宾客们还在哪儿愣着呢,大家流着哈喇子看着卫宣公忙上忙下一阵头晕,等人家都把自己送入洞房了,还半天没人吭一声。
不过实话实说,这种事情在当时实在不算什么很难接受的事情,即便是近二千年后的武则天时代,大家也没把武媚娘先给老子唐太宗当小老婆,再给儿子唐高宗当皇后的事太当真。
除了骆宾王在千古名文《讨武曌檄》里骂了句“陷吾君于聚麀(读忧,聚麀,指二代公鹿共同占有一头母鹿)”以外,根本没人在乎,还是把她奉为女皇,照样山呼万岁、磕头叩拜。
还有娶了汉、唐公主的匈奴、突厥首领,老单于死后,公主又嫁给不是自己和老单于生的庶子,汉朝唐朝人也没觉得太违背礼法,照样尊重少数民族的婚姻传统。
直到南宋儒家分支“程朱理学”兴起之后,倡导去人欲、存天理的理论,从那时起到现在,理学思想主导了汉族人民的思想意识形态,才把这类事情看做是乱伦无耻的禽兽行为了,谁要是敢在南宋后做出这种事来,大家就算不打他骂他,一人吐一口口水都能淹死他,根本不能再看作人类了,就是头禽兽。
卫宣公抢儿子老婆的事,虽然显得有点急色,宾客们没想到能有这一出,有点惊喜过头了以外,倒也没太大意见。反正是你们家自己的事儿,太太儿子没意见就行。
所以愣完神的宾客们缓过劲来以后收回下巴,该送的礼照送不误,该喝的酒一滴不剩,估计闹洞房就免了,吃饱喝足,大家擦擦嘴、拍拍屁股回家了,回去给家里人又有好说的特大笑话了。
卫宣公这个禽兽的爱情观相当奇特,总结出来就一个,老婆还是别人的好,而且是亲人的老婆最好。
他把儿媳妇自己笑纳了以后,儿子急子倒没提出什么反对意见。我想不外乎二个原因,一是不值得为了一个女人和老爹闹翻,二是这种事在当时确实没那么难以接受。
我们得稍微深入分析一下那个时代的人对男女关系的看法,否则真没办法以现代人的思想去理解这一家子。
在周武王打败商纣王建立周王朝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以看过的古装电视剧的思维去认识那个时代。
那时候的中国哪有什么王朝啊,实际就是个稍微先进点的、以黄河中游地区为中心的,几千个刚从原始部落发展起来的部族国家的松散联盟体。
既然有原始部落的基因,大家就应该有点谱了。在千年以后司马迁的史学巨著《史记》里,是这么编排商纣王的荒淫无道的,说商纣王经常在朝歌用民脂民膏搭建的鹿台,也就是当时的皇家私人俱乐部里,开一种酒池肉林的联欢会。
在这个远古原始的大型皇家派对上,商纣王、妲己与民同乐,与很多年轻的男男女女在树林里一丝不挂的跑来跑去尽情戏耍,用我们现代人的观点来看,这不就是集体yin乱吗?商周王是够荒淫的,活该被灭。
但是实际上,这种集体yin乱在原始社会里,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成年男女交配繁殖仪式,根本不是纯粹的为了玩乐。就连远在偏远陕西,后来成为儒家正朔王朝的周文王部落里也没少举行这种仪式。这是因为生活在周王朝以前的史前时代的原始人是没有婚姻的。
远古石器时代一个原始部落非常穷,耕种还很落后,收成不足以保证全体人口的口粮,要靠打猎、采集野果补贴。
在这种条件下,为了生存,大家必须混居在一起,财产共有,食物平分,团结一致才能勉强维持生计。婚姻在这种时代是没有必要的,人类就和所有的灵长类动物一样,盖个大茅草屋,一个部落的所有人一起住,男女肉体共享,同代之间没有限制,根本没有兄妹乱伦这一说,生下来的娃部落所有人一起养。
婚姻真正出现,是新石器晚期到青铜时代这段时间。社会生产力提高了,私有财产开始出现,这时候一个青铜时代比较富裕的原始人,比如部落首领就会考虑,如果自己死了,自己这辈子积攒下来的财产怎么办?
捐给部落?怕没那么高觉悟。
自己交配过的女人倒是不少,这些女人生的娃也不少,可这些女人和自己交配的同时,也没那么专情,在自己忙不过来的时候,她们也会和别的男人办事。这就没法保证她们生的娃,那种是不是自己的。
自己平时省吃俭用、勤勤恳恳,为了部落的发展殚精竭虑,部落越来越富足,自己也好不容易攒下点财产,青铜工具、武器、葛布、房屋、田地、牲口……等等等等。他肯定想着得传给能确定是自己生的后代,总不能把自己一辈子的勤劳所得,便宜白送给一个不知道哪来的野种吧。
这个时候,这位聪明的原始富人,就会挑一个鼻梁没那么塌、牙齿没那么爆的原始美女,把她关在屋里养起来,不让她和部落里的其他男人发生关系,这样她生的娃肯定是自己的了,自己死了,财产就由这个娃继承,原始婚姻开始出现。
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说的一样,婚姻是因为确定的财产继承关系而产生的。
而原来那种男女混居时代的乱交传统,就一直遗留下来,直到西周初期依然存在。因为大多数底层百姓,还是很穷,没什么遗产,也就没有想结婚的念头,为了保持生育积极性,提高人口增长率,政府是鼓励年轻男女举行杂交仪式的,经常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在桑林里组织野性的狂欢派对。
甚至这种仪式直到近代仍有遗迹,比如云南丽江的纳西族分支――摩梭人,每当到了赶集、打谷的节日里,年轻未婚男男女女一起对唱情歌。互相看中的男女,当然现在文明多了,先互相介绍下,聊点有的没的,然后拜访双方老人,最后去领结婚证,这是新中国的新气象。
就在不远的上世纪解放前,互相看中了直接就钻进林子里野合啦,和商纣王他们玩的一模一样。那是相当的自由奔放。这不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恰恰是对几万年来人类社会古老传统的真正传承。
后来周公旦执政,一看统治的这都一帮什么人啊,茹毛饮血、衣不蔽体、不知羞耻、毫无礼仪,走到哪儿搞到哪儿。于是很有理想的上古时代政治家周公旦开始逐步完善《周礼》颁布全国,规范全体国民的生活习惯、日常礼仪。
其中就包括取缔这种集体乱搞的、女孩大多数时候都搞不清楚孩子他爹到底是谁的原始交配仪式。
这真不是开玩笑,据史书记载“尧舜禹汤”四位远古圣君,就是韦小宝经常念成“鸟生鱼汤”的那四位。他们的妈没一个说的清楚他们的爹是谁。怎么感觉有点绕口呢。
尧他妈过河的时候遇到一条没有公德心的龙向她吐口水,回家后生了尧。
舜他妈更奇怪,一天下雨后看见彩虹,心中有感,就生了舜。
大禹治水的禹他妈,在河边看到一颗像珍珠的石头,也不怕消化不良给吃了,回家生了禹。
汤他妈则是吃了一个燕子蛋生下了商王朝的开国祖宗。
这都什么跟什么啊,这不就是树林子里乱交回来生下的野种嘛。
周公取缔这种原始的交配仪式以后,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婚姻法》,基本和我们现在的婚姻一样了。
为了提高国民对婚姻的尊重,他不厌其烦的把婚姻的过程搞得及其麻烦,让大家都觉得结个婚真不容易啊,这辈子有一次就够啦。
具体步骤是这样的:分了七个环节,纳采(提亲)、问名、纳吉(各自回家商量一下看看八字合不合、家庭是否般配)、纳征(男方送聘礼)、请期(定日子)、亲迎(办喜事)、敦伦(入洞房,特指原配夫妻之间的性生活)。
这一套搞下来,一对未婚男女可就不能再随便去树林子里野合了。你们得把手续全部办完才能履行最后的目的“敦伦”。
以后我们现代人看过这篇文字的也可以文雅点了,别一天到晚做爱啊、makelove啊、sex啊……这么直白,你也搞点高雅的,跟女孩子你得这么说:“我们敦伦吧”。搞不好女孩子还以为你要带她去伦敦呢。
不过还得注意,周礼颁布以后,由于当时受教育资源的限制,只有国都镐京有专门教授诸侯国(各个部落)贵族子弟的学校,这么麻烦的一套要完全普及到全中国每个普通老百姓家庭,对周公旦来说那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所以《婚姻法》(周公之礼)主要针对贵族阶级。对民间的交配传统,起码在春秋初期还是允许自由奔放的林中野合聚会存在的。
这不是我瞎说的,有中国古典高雅艺术瑰宝级读物《诗经》为证。在《诗经.郑风》中有一篇《野有蔓草》全文如下: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藏。
俺的翻译是这样的:
初春的野外,青青嫩草带着露珠染绿了春色林间。有一个美人站在林中间,她的气质清新飞扬、温婉娉婷,与我不期而遇,我的愿望幸运地得到她的眷顾。(“适我愿兮”,他能有什么愿?和美女聊聊天探讨探讨人生?)
初春的野外,淡淡晨雾轻轻抚过柔弱的嫩绿草地。有一个美人走在草地上,她的姿态宛若约素、清丽淡雅,向我缓步行近,牵着我的手一同走向密林深处。(“与子偕藏”,藏起来干嘛?总不可能是二个人一起玩躲猫猫吧。)
这哥们一定是高兴坏了,做了首淫诗,居然堂而皇之的收录在《诗经》里,为我们在几千年后窥一斑而知全豹的去了解他那个时代的生活。
如我之前所说,《诗经》就是那个时代的小调,里面的yin诗多的很。诗歌要发展到了汉唐时期才算是真正的高雅艺术,基本不写yin诗了。
到了卫宣公时代,虽然《婚姻法》已经颁布四百多年了,但是传统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那个时候的人依旧很开放,远比我们现代人对性的态度开放。当然这是原始野性的残留,俺可没说这是个好作风哈。
好了,理解了那个时代婚姻生活,再来看卫宣公他们家的一塌糊涂,是不是好接受点了。既然我们接受了,卫宣公的儿子急子同志也毫无意见,虽然未必是很高兴的接受了未婚妻变成了后妈的现实,但是也无所谓啦。女人嘛,还不多的是,再找一个呗。
卫宣公和儿子的感情没有破裂,但是和急子他妈的感情出现裂痕了。“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自打宣姜过门后,卫宣公就移情别恋了;“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夷姜守了活寡了;“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不久后自杀。
过了不久,卫宣公和宣姜的色情结晶诞生了,他们生了二个儿子,长子公子寿,次子公子朔。二个儿子虽然是一母同胞,个性却完全不同,简直是二个极端。
其中公子寿和世子急子大概性格相近,都很重情重义、道德高尚,平时比较谈的来。虽然是同父异母,但是二人更像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
公子朔就不行了,年纪不大,野心不小,平时小肚鸡肠、阴险狡诈。二个哥哥都不待见他,不带着他玩。
随着宣姜二个儿子渐渐长大,卫宣公犯了一个和周幽王同样的错误,那就是想给他深爱的女人一个美好的未来,也就是给她儿子一个美好的未来。
卫宣公有这想法也很正常,宣姜本来是应该嫁给年轻英俊的急子的,他们二个年纪相当、郎才女貌,还比较般配。
没想到被卫宣公这个色中饿鬼给截胡了,宣姜虽然无力反抗、只能逆来顺受,但是肯定不是心甘情愿的。她和卫宣公的这场婚事连卫国的老百姓都编了诗歌来嘲笑他们了,再野性也没见过公然在儿子婚礼上替了儿子自己上的,国人们笑破了肚皮。
宣姜无论如何不可能像卫宣公爱她那样爱上卫宣公。
于是,为了讨宣姜高兴的卫宣公很有可能演出了下面一幕,某天和宣姜亲热的时候就满嘴跑火车了:“亲……爱的,你放心,我百……年之后,一定立你……的儿子为国君,你以后……就是国君的妈啦,你……的好日子长着呢。”
然后上下其手忙的不亦乐乎,宣姜只好为了等着他百年以后的好日子,皱着眉头强颜欢笑、半推半就了。男人啊,就这点德性,唉……
这就好比一个裂开的鸡蛋,苍蝇自然会盯上来的。这只苍蝇就是公子朔,这个小弟弟很有想法,从老妈哪里听说老爷子想立他老妈的儿子做世子,他就开始想了:“那敢情好,为啥不能是俺呢,俺也是老妈的儿子,虽然不是长子。没事,挤掉一个算一个,起码俺的继承权顺位从第三上升到第二啦。”
于是他就天天缠着宣姜:“老娘啊,你得催着老爷子赶紧动手啊,老爷子年纪大了,为了俺们娘俩的未来,这事得抓紧办。”
卫宣公在他们母子的日夜催促下,终于决定把想法转变为行动了。
这种事在春秋时期的国君之间像是一个传染病一样,随着上一代国君枕边人的变换,老是影响到国家既定接班人的命运。在以后的故事中同样的事情层出不穷、屡见不鲜。
由于世子急子年纪比公子寿、公子朔大了至少十几岁,当储君的日子很长了,国内不乏支持者。卫宣公为求稳妥,决定斩草除根,干掉急子。
虽说虎毒不食子,不过人心比虎毒。“儿啊,为了老子的下半身,你就再尽一次孝吧。”
正巧卫国有一个和齐国的双边贸易谈判,需要派个代表到齐国去参加峰会。于是卫宣公指派世子急子出使齐国,然后安排刺客等在急子必经之路上,下令:“格杀勿论,带人头回来领赏。”
这事被预订的既定获益人公子寿得知了,公子寿宅心仁厚,对于兄弟的感情看得比国君的位置更重要,于是将狠毒父亲的计划透露给急子:“大哥你还是赶快逃命去吧,别管什么出使任务了。”
急子断然拒绝:“不顾父亲的命令,要这种儿子有什么用。我无处可逃,除非这个世界上有不要父亲的国家。”
公子寿无法劝动急子,只好以给践行为理由,不停地给他灌酒,最后急子醉得不省人事。公子寿拿上急子用白色羽毛装饰的旌节(这是国家使节的信物),自己替急子走上了父亲给他们安排的不归路。
公子寿拿着白旌带着不多的使团随员乘船走到一个叫莘(读申)的地方,遇到了他爹安排的刺客,刺客们堵在水道上,一看这伙人簇拥着一个手持旌节的贵人公子,认定就是世子急子,不由分说上来就砍,公子寿慨然赴死。
过了不久急子酒醒,一看随从和旌节都不见了,立刻担心起来,忙向着既定出使路线,也坐船追了过去,在路上遇到了挑着公子寿首级的那伙刺客,急子一见公子寿的首级顿时痛哭失声,对着刺客们说:“我是世子,你们要杀的人是我,我弟弟是无辜的,现在请你们把我也杀了吧。”
刺客们面面向觎,没见过主动求死的,有点奇怪,不过最后他们还是本着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敬业精神,把急子的首级也摘了下来。(这里说“首级”二字有点早了,这是商鞅变法后出现的名词,不过为了尊重二位公子就先用用吧)。
这事后来又被爱唱歌的春秋人唱成了诗,叫《乘舟》,是《诗经.卫风》中的一首。用来纪念这二位不重名利,不惜生命,看重亲情和道义的公子。子寿和急子怎么看怎么不像卫宣公的种,只有公子朔倒是和他基因相似。
刺客们带着二颗首级去找卫宣公报功,卫宣公一看二颗人头,大吃一惊,急子该杀,子寿可是我想指定的继承人啊,怎么也被你们杀了。然后不知道是惭愧还是后悔,不到一年他也死了。
这下把公子朔高兴坏了,一次刺杀行动,死了三个挡路的,他一下子从国君的第三顺位继承人直接跨越到国君了,乐的手舞足蹈,哪里有半分丧失亲人的悲痛。公子朔继位,史称卫惠公。
这事惹恼了二个人,一个是卫宣公立急子为世子的时候指定的老师――公子泄,一个是公子寿长大以后指定的老师――公子职。一看名字就知道,这不是外人,二人都是卫国的公族大夫。
二位大叔一看本来应该是自己辅导的公子当国君的,就是因为你公子朔和宣姜撺掇着卫宣公干出这种灭绝人性的事,当然卫宣公的人性早就剩的不多了。结果俺们二个本来都有希望在自己辅导的公子当上国君后跟着沾点光的,现在全泡汤了。二人对公子朔恨得咬牙切齿。
二人忍气吞声、偷偷准备了四年,终于在郑国郑昭公第二次当上国君的第二年抓住机会突然发难,发动军事政变赶走了卫惠公,然后二公子立了世子急子的同母弟弟公子黔牟为君。这哥们没有谥号,因为最终他被当做叛贼处死的。
这段故事不是脱离中原诸侯争斗的独立故事,卫国的这次内乱,给有心参加中原争霸赛的另一个诸侯国――齐国带来了机会。理由很简单,卫惠公被赶走后,逃到他妈的娘家齐国去了,给了齐国介入卫国争端的口实。
齐襄公非常高兴,大外甥居然被二个臣子赶出来了,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是各个诸侯国最深恶痛绝的叛乱行为,人人得而诛之。
这样一来,出兵攻打卫国就名正言顺了,扶植卫惠公回国当政后,齐国还能捞不少好处。
诸侯们就像一群被困在一个笼子里、而且从不喂食的狼群。所有狼都恶狠狠的盯着其他的狼,如果有谁露出破绽或是软弱、胆怯,大家就会一拥而上把它撕碎咬烂。
人家郑国好歹还是有外国势力介入而引起动乱,卫国国君一家子自己窝里就斗上了,一个国家发生了动乱,就如同在那个狼群里露怯的狼一样,总是会引起别人的胃口的。
郑国、卫国相继发生动乱以后,中原赛区后面的十几年那叫一个热闹,堪称应接不暇。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