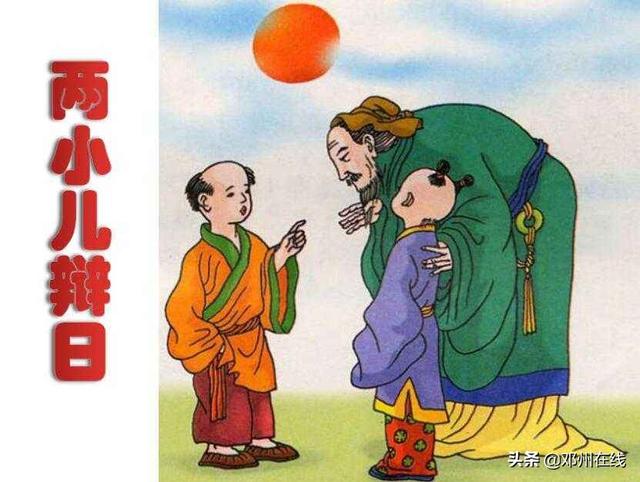北大历史系主任(北大历史系主任朱希祖)

美髯公朱希祖1926年摄于北京。
北大历史系主任朱希祖,学界美髯公剃掉大胡子之后刘宜庆
他是章太炎门下弟子,被戏称为“西王”;他是出席“全国读音统一会”的代表,在国语运动中起草的注音符号方案一锤定音;他是“某籍某系”的北大教授,先后担任国文系、史学系主任;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倡导白话文,反对封建礼教;他任清史馆的协修,获得袁世凯颁发的四等嘉禾奖章……
史学大师海盐朱希祖,一生有诸多身份,史学家是其根本。建构史学教育体系,整理历史文献和档案,编修国史,考察历史遗迹,研究南明史……每一件事中都贯注了他的爱国热情和民族尊严。他做这些事情只有两个目的:一是传承和发扬中国文化,二是唤醒国人的民族士气。
生于晚清,留学日本,民国初年进入北京大学,登上历史舞台。朱希祖一生经历洪宪帝制、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等诸多重大历史事件。朱希祖历任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教授,晚年任国民政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交游广泛,可谓政学两界的津梁。1944年,朱希祖病逝于重庆,蒋介石特颁“渊衷硕学”的挽词,葬礼“极一时之哀荣” 。“藉历史以说明国家之绵延,鼓励民族之复兴”,追昔抚远,在朱希祖逝世70年后,回望他的人生和事功,历史学家的良知和担当,令人敬仰。

朱希祖留学日本时,师从章太炎。
1919年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代理主任,教授中国文学史。不久兼任史学系主任,写成《中国史学通论》一书及许多史论。 朱希祖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这个系主任也很不一般,因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史学系的系主任。朱希祖还发起成立了中国史学会,是现代史学的开创人。
“五四”前后的北大,“卯字号”名教授,可谓北大的台柱子。所谓“卯字号”,就是几个属兔的大师级人物,两只大兔子是陈独秀和朱希祖,生于光绪己卯年(1879)。四只小兔子是新文化运动中名声鹊起的胡适,新文化运动中与钱玄同一起唱双簧的刘半农,任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曾当面顶撞蒋介石出名的刘文典,二十几岁就做北大教授、以行为怪异著称的林公铎。

陈独秀,北大“卯字号”的兔子之一。
其实,陈独秀和朱希祖是两只中兔,还有一只老兔——生于光绪丁卯年(1867)的蔡元培。“卯字号”的几只兔子,都是北大名教授。胡适不无自得地说:“北大是由于三只兔子而成名的。”这三只“兔子”指的是“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蔡是北大改革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陈、胡则是其行政上和教学上的得力助手,他们三个是当时北京大学的灵魂。不过,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的胡适之,并不入一些章门弟子的法眼。
有意思的是,“中兔”朱希祖似乎有点瞧不上“小兔”胡适。
胡适初进北大,还是末学新进,对朱希祖很尊重,朱希祖的藏书中有很多是海内孤本、秘本,胡适就经常到朱家来看看藏书,谈谈版本,请教学问。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一出版,引来叫好一片,胡适在序言中特别感谢了朱希祖,说:“对于近人,我最感谢章太炎先生。北京大学的同事里面,钱玄同和朱逖先两位先生对于这书都曾给我许多帮助。”朱希祖似乎并不领情,说此书写得肤浅,还肯定地说,胡适既不懂佛学,也不懂宋明理学,他这本《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写不下去的。

胡适,北大“卯字号”小兔子。
当然,朱希祖这番话,可能说给很亲密的朋友听。但另一位章门弟子黄侃就不同了,在中央大学的课堂上,公开讽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半部,没有下半部:“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不解,问何意?黄侃回答:“监者,太监也。太监,下部没有了。”引得学生大笑不止。
朱希祖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批评,比较中肯。后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勉强出了中册,下册果然是无疾而终。这个小插曲,并不影响两人的交情。从《朱希祖先生年谱长编》中可以看到,朱希祖和胡适的学术往来比较密切:胡适向朱希祖借书,朱希祖对胡适发表的论曹寅的文章予以补充,两人常写信交流。毕竟朱希祖是一只“温和、儒雅”的兔子,而黄侃则是桀骜不驯的野马,具有名士的范儿。胡适对待自己的批评,颇有风度,一笑了之。
朱希祖是北大的兔子,也是学界的美髯公。

1922年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编委会同人留影。左起:徐炳昶、沈兼士、马衡、胡适、顾颉刚、朱希祖、陈垣
1914年1月1日,这一年朱希祖36岁,与沈钧儒相约留胡须。于是,民国学林中,多了两位美髯公。当时,《北京大学日刊》曾将朱逖先误刊为“米遇光”,北大的同人,章门弟子,都见了他呼作“米遇光”,这个绰号有开玩笑的意味。随着朱希祖茂密的连鬓大胡子初长成,“朱胡子”这个外号不胫而走。不过,北大同人包括他的弟子,更多地称他为“而翁”。毕竟当着他的面,不好意思直白地叫“朱胡子”。“而翁”这个文言的称呼,似乎有了几分敬意。
据《知堂回忆录》,1933年暑假,时任中山大学教授的朱希祖,回到了北大。在校长室现身的他,引来一片惊呼。“这时正值北大招考阅卷的日子,大家聚在校长室里,忽然开门进来一个小伙子,没有人认得他,等到他开口说话,这才知道是朱逖先,原来他的胡子刮得光光的,似乎换了一个人了。大家这才哄然大笑。”周作人的回忆很生动,试想,一位熟悉的朋友留了近二十年的胡须,多日不见,突然剃掉了胡须,出现在朋友眼前。那种惊讶之后的恍然大悟,一定伴随着爽快的笑声。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