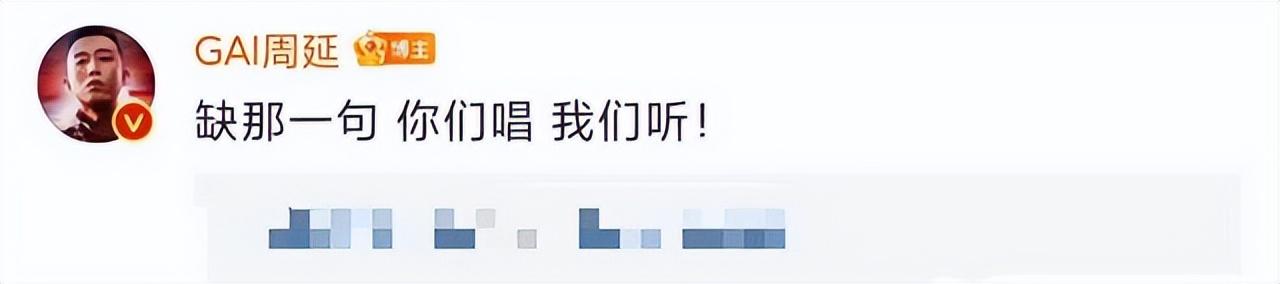乾隆三年制银锭(国宝品鉴解盐使司大安三年二月十二日)
“解盐使司大安三年二月十二日”银铤,银质,金代文物,正面通长14.5厘米,上宽8.6厘米,下宽8.8厘米,腰宽5.3厘米;背面通长13.9厘米,上宽8.2厘米,下宽7.9厘米,腰宽4.9厘米,厚2.2厘米,重1930克。1978年河南省西峡县重阳乡奎岭村出土。

“解盐使司大安三年二月十二日”银铤
1978年2月,河南省西峡县重阳乡奎岭村五组村民杨付尧等在同一地点挖出三笏(hù)银铤,“解盐使司大安三年二月十二日”银铤即是其中的一笏。银铤呈平板状,两端圆弧,束腰。正面稍微凹,周边有波纹,正面从右至左依次錾(zàn)刻铭文。铭文主要錾刻在银铤的两端及周边,中部有较深的戳记以及砸印的画押符号等。背面中部稍凸起,侧面及背面呈蜂窝状孔,周边内收,通长及两端的尺度均小于正面。在金代的官银上往往錾刻有字号、官吏职位、姓名、锤压戳记或画押。金人虽然也有自己的文字,但他们在银铤的正面錾刻重量、年月、类别、官吏名称、金银铺号等字款时,多用汉字标明。
“解盐使司大安三年二月十二日”银铤上錾刻的铭文:“解盐使司大安三年二月十二日引领牛淮朝 客人石顺 中纳银肆拾玖两柒钱 行人陶实城 秤子魏直 才 文林盐判 张 每两八十陌钱二贯 宇七 又一钱”。银铤铭文虽然只有五十八字,但其内容却显示了该银铤的性质、盐产地、盐池的管理机构、盐务职官名称及具体办事人员的名字、白银的实价及铜钱省陌规格等信息。
“解盐”,指古代产盐区之一的解州即今山西解县、安邑两盐池所出产的盐。《宋史》、《文献通考》等书载:“虽分两池,实即一池,所以通名解池。”它还包括两盐池附近的几个大小不等的盐池,即东池,在安邑境内;西池,位于东池的西部,解州境内,也称女盐泽,小盐池;六小池,是六个小盐池的总称,即永小、金井、贾瓦、夹凹、苏老、熨斗,它们位于西池的西边。宋代,“惟淮海解池,最资国用”。金代,“解盐行河东南北路、陕西东,及南京河南府、陕、郑、唐、邓、嵩、汝诸州”。
“解盐使司”是北宋专设在解池的管理机构,即“提举制置解盐司”,其职责是“掌盐泽之禁令……盐价高下及文钞出纳……”。到金代,“以解盐司使治本州”,说明解盐使司的治所仍在解州。“使司”有盐运使司和转运使司,这里当指盐运使司。它是在“提举制置解盐司”和辽代幽州“榷盐制置司”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公元1185 年)以后“惟置山东、沧、宝坻、莒、解、北京、西京七盐司”。据《金史•百官三》记载:“山东盐使司与宝坻、沧、解、辽东、西京、北京、凡士使司,一员,正五品,他司皆同。副使二员正六品。”而《金史•食货四》又有金世宗大定“十一年正月,用西京盐判宋俣言,更定狗泺(山东境内)盐场作六品使司,以俣为使,顺圣县令白仲通为副,是以岁入钱为定额。”说明盐使司的官品也有例外。其官俸由盐税收支出,但因“盐使司虽办官课,然素扰民”,于是朝廷在全国各盐池设立督察盐使司的“巡捕使”一至二人。解盐池设一人“秩从六品”由省部直接管理。
“大安”是金代“卫绍王完颜永济”年号。
“引领”是为榷货务或盐司服务的“牙保”或“保识牙人”,也称“盐牙子”,其职责是引导客人到盐务处办理入中贸易并承担某种介绍和保识任务。金代银铤有民间铸造和政府铸造之分,民间铸造的银铤,铭文比较简单,一般只有重量、行人和秤子的名字,而政府铸造银铤则沿用了宋代制度,应役的金银工匠,需要有金银行的引领、行人、铺户作保,以防作弊并负有赔偿责任。有时还要金银行会的头目为应役兑换和铸铤的各部户的金银匠作经济担保。
“客人”,即入纳银铤之人,亦即该银铤的旧主。“客”有客商的含义,常常作为商人的代名词,并有区别于本地商人的特殊意义。银铤上的客人王正、石顺当为纳税人的名字。
“行人”,从《宋会要辑稿》上记载的“……仍求良贾为之辅,使审知市易。……许召在京诸行辅户牙人充本务行人、牙人”可知,“行人”来自“行辅户”的“良贾”,既金银铺的商人。唐代时称“行首”、“行头”、“行人”等,指加入“行会”的工商人士。日本人池田温在《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一书中称“行人”制度至少在天宝年间已形成。宋代称“行头”或“行老”。《宋会要辑稿》中曾记载,“……勒行人看验,诣实分数……”作为盗窃罪依律量刑的标准。所以宋代的“行人”,就是按照当时所规定的通行含银标准,专门负责鉴定银铤的成色及其实价而承担责任的人。从近几年出土的金代银铤中可证实,南宋与金代的“行人”制度基本相同。银铤中的陶实城等,就是专司检验银子的成色职责,与“检缗(mín)钞行人”、“检钞行人”相同。在出土的金代银铤中,“行人”和“秤子”多同时并称。
“秤子”是金代官职名,主要掌管称盘、保证质量、收支官物官府差役。银铤上的田政、魏直应为当时专司银两称重的人员。
“盐判”是分治司的官员名。据《金史•百官志》记载,7个盐使司各设监判官三员,为正七品。泰和初年,宝坻、解州各设监判官二员,在盐使司和副使之下,是盐司业务的具体主办者,习惯上称为“盐判”,直接掌管盐利。
“文林”为职衔名,即“文林郎”,是吏部的下属官员,属九品文散官。
“每两八十陌钱二贯”,表明了白银的实价及铜钱省陌规格。陌,即百。在古代货币流通中陌指一百钱。省陌,按《席珍放谈》卷二“今则凡官司出入悉用七十七陌,谓之省陌是也”,即不足一百文者当一百文使用。这至迟始于东晋时期,五代到宋金均存在铜钱紧缺问题,于是相继沿用这一制度,只是省陌多寡不一而已。《旧五代史•王章传》上记载:“官库出纳缗钱,皆以八十为陌。”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民间销钱作铜、富商官豪大批隐藏铜钱造成了铜钱的短缺,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金代统治者为了解决“钱荒”问题,除严禁各种铜器输出,并逾天山北界外采铜,还“在攫取北宋解盐、青齐河朔绢的产地之后,就组织劳动力大力生产盐、绢,并把这些产品廉价倾销到南宋,换取了大量的宋钱”。在榷场贸易中,金朝政府沿用宋代的短陌之法,《金史•食货三》称,大定二十年(1180年)“民间以八十为陌,谓之短钱,官用足陌,谓之长钱。大名男子斡鲁补者上言,谓官私所用钱皆当以八十为陌,逐为定制”。可见该铤的银价为每两二贯,是八十陌钱的两贯,即两贯省,其兑换值是符合法定兑换价的。
“又一钱”戳记,当为银铤铸成后,由盐司或其它官衙加盖的。因为银铤的铸造是采用“硬砂模明浇的工艺,……从而在冶炼、铸造过程中因清除杂质数量不同,可能形成重量不统一的现象”。在收纳金银铺铸造的税银时,大约以錾文重量为准,但上缴国库或做其他支出时,则又以加盖增重戳记的手法,校正前者的重量。还有人认为,既然此类银铤是多名专职人员的监督下铸造的,就不应有这样的失误,这大约是官署舞弊的一种手法。
“宇七”中的“宇”字当为盐司在接受商人“入纳”是时按“千字文”为序的登录编号。“宇”为“千字文”中“宇宙洪荒”中的“宇”字。
“中纳银”,是客商“中买盐引而入纳”之意,即金代盐商向解盐使司购买钞引的入纳银,经过对成色鉴定后加盖的标识。铤上的刻文及戳文的押字,都是官府收纳银铤的重要戳记与记录,反映了该银铤在流通中经过多次检验。
比较研究金代官府将所得的盐税铸成银铤,即盐税银铤。盐税银铤在已出土的金代银铤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从各地出土的铸有铭文的金代解盐银铤来看,錾刻的年号有泰和、大安、明昌等。

“金明昌二年”解盐银铤
与“解盐使司大安三年二月十二日”银铤一同出土的“解盐使司泰和六年三月十四日”银铤,通长13.9厘米,两端宽8.2厘米,腰宽5厘米,厚1.8厘米,重1862克。银铤上錾刻有“解盐使司泰和六年三月十四日 引领阎太 客人王正 中纳银肆拾柒两叁钱足 秤子田政 行人口口 才 盐判李 又一两 每两二贯文 六任家记”铭文。“泰和”是金代“金章宗完颜璟”的年号。两笏银铤均出土于河南省西峡县,金朝时西峡县属邓州,恰在解盐供应的范围之内。

河南省西峡县窖藏“解盐使司泰和六年三月十四日”银铤拓片
从河南省西峡县出土的“解盐使司泰和六年三月十四日”银铤和1974年陕西临潼出土的“泰和六年八月二十八日”银铤上均錾刻有“解盐使司”铭文来看,其引领姓名相同,均为“阎太”;从西峡县出土的“解盐使司泰和六年三月十四日”银铤与“解盐使司大安三年二月十二日”银铤的上部均刻有相同的“才”字分析,这三笏银铤可能是出自同一铸地即同一分治司。
铭文中的“六任家记”指的是制作银铤的金银铺号。《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九》载:“……打造金银,自来只凭作家和雇百姓作匠承揽掌管金银等,拘辖人将造作,以致作弊,今乞将合用打作作头等,令本院招募有家业及五百贯以上人作充,仍招临安府元籍定有物力金银铺户二名委保,如有作过人令保人拘陪。”因金代沿袭唐宋两代的工商制度,将同城有实力的金银铺组织起来,支应差役和经营业务,这些金银店铺在为政府铸造俸银、税银等各种官银时,必须錾刻行人、秤子的姓名和银铤的重量等以昭信守。“六任家”应为当地信誉高、技术精的金银铺户的铺户名。出土的金代银铤的铭文中还有“张家信实记”、“留候世家”等,说明税银一项在白银流通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它促进了金代金银铺的兴旺发达。“泰和六年四月十四日”的银铤应是官府将征收的解盐税碎银交与“六任家”银铺铸成银铤,而后打上铺号戳记送还官府,再由官府及有关责任人打上银子来源、性质、重量等。
陕西省临潼出土的“泰和六年八月二十三日”银铤与河南省西峡县出土的“解盐使司大安三年二月十二日”银铤中的文林盐判姓氏相同,皆为“张”姓。两铤分别铸于泰和六年八月和大安三年二月,时间相差四年零六个月。按金制,“解盐使司”本司与分司“盐判”各仅一员,这两笏银铤的“盐判”似为同一人,应为同一分治司所铸。
将由吏部下属的直接掌管盐利的盐判等人的姓名、身份刻在银铤上,以示对该银铤的质量、成色、重量等承担责任。因金代承袭宋代盐业专卖的体制,分为官营与私营两种形式,官营中分治司和分治使司是盐使司的分支机构。解盐池主要是官营,是金代盐业的主体,故金代盐使司的银铤上,多刻有“盐判”、“承直郎盐判”、“东盐判苑”、“榷盐判管勾”和“文林盐判”等官职。
“泰和六年八月二十三日”银铤上标明重“肆拾柒两叁钱足”、“又一钱”,即四十七两四钱。“每两二贯文”印证了《金史•食货三》中,金章宗承安二年十二月,尚书省议“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直百贯……每两折钱二贯”的记载。
“泰和六年八月二十三日”银铤标明自身的重量又多一钱,即应为47.3+0.1=47.4两,实测1862克,每两相当于今天的39.28克。“大安三年”银铤标明自身的重量又多一钱,即应为49.7+0.1=49.8两,实测1930克,每两相当于今天的38.75克。在银铤上留下精确的记重铭文,至记两、记钱甚至更小的形式,是金代银铤区别与宋、元银铤的重要标志。
宋金时期,官府多有使用“千字文”进行编号、注籍的惯例。如陕西临潼出土的31笏金代银铤中,有5笏錾刻着“千字文”或干支编号。
“解盐使司泰和六年三月十四日”银铤和“解盐使司大安三年二月十二日”银铤中的铭文所錾刻的位置大致相同,只是两铤中“客人”、“行人”、“秤子”的排序有些不同。印记画押多为戳模砸印而成,不可识。其形制基本相同。
“解盐使司泰和六年三月十四日”银铤和“解盐使司大安三年二月十二日”银铤均出土于河南省西峡县同一窖藏, 两银铤的铸造时间相差仅五年,且两银铤的性质相同,均属盐税银铤。两银铤铭文均存在“引领”、“客人”、“行人”、“秤子”、“盐判”等官职的内容。从1978年在河南省西峡县出土的带铭文的两笏银铤与1974年陕西临潼出土的“泰和六年八月二十八日”银铤铭文分析,根据其上有相同官员的名字和符号,推断这三笏银铤应为同一机构铸造,但它们的铸造年代不同。
从河南省西峡县窖藏的两笏“解盐使司”银铤、陕西省临潼和四川省双流等地出土的银铤上自铭的重量和实际的重量上看,银铤不仅规格、大小、厚薄各异,而且重量也没有一个统一、严格的标准,《金史•食货三》有“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直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的记载。重五十两的银铤,约合今1900~2000克,与宋代标准官秤每两为40克左右大致相同,值铜钱一百贯。
作者简介陈娟,女,河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河南博物院文物鉴定办公室副主任、文博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古代货币、金银器、铜镜等文物的研究。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