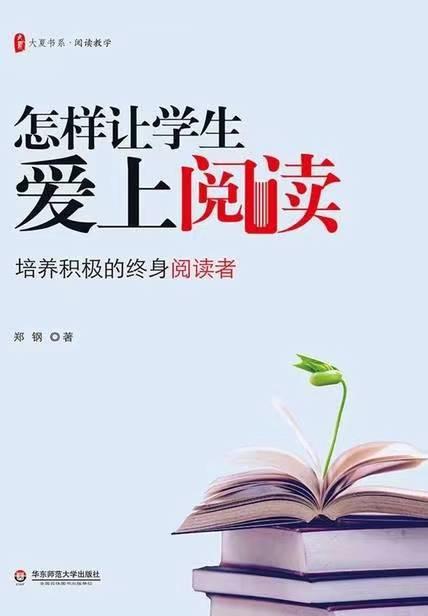两个东北人拍的80年代段子(离开东北多年以后)


采访、文|一毛/来源:陈鲁豫的电影沙发(lyyy_scndgs)
王赫泽,一个学画画的,干过摄影,开过公司,后来决定拍电影。35岁那年,他在铁岭拍摄了个人第一部长片《时来运未转》,用一出魔幻现实主义故事构建了一个残酷戏谑的世界,这是他献给故乡的东北寓言。在第16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上,《时来运未转》获得“最佳编剧荣誉推介”,回到北京后,我们与这位青年导演聊了聊整部电影的创作过程。
信仰迷途在中国北方,尤其是东北一带,萨满——这一古老的原始宗教,至今依旧盛行。萨满教相信万物有灵,人世祸福皆由鬼神主宰,神灵赐福,鬼魔布祸,而他们正是帮助人与鬼神沟通的中间者。
东北的“出马仙”正是由萨满教延续而来。狐黄白柳灰(狐狸、黄鼠狼、刺猬、蛇、老鼠)被称为“五大仙”,如若有人被“仙家”选中,就要挑日子,立堂口,召唤“仙家”上身,受用香火,替事者消灾除祸——所谓“出马”。东北“仙家”众多,许多人患上怪病或囿于困境无计可施之时,便拿些香火钱去找“仙家”问路。
也有一些人尊奉神佛。王赫泽奶奶家里就有一尊从清朝传下来的观音像,奶奶生长于战争年代,常跟人说,家里当时能够躲过一劫又一劫,多亏有菩萨保佑。一个命如草芥的时代,人人在苦海里漂泊,无处可逃时便寄望于某座灯塔,静候指引,成为信徒。
王赫泽无法像奶奶那般去看待人生,但他理解,有些信仰或许来源于苦难。贫弱者总要找出一条通道从苦难中脱身,寄托狐鬼也好,求助神佛也罢,哪里能创造希望,哪里便存在信仰,急于求成之时,谁都有可能被视为救世主。
人在困境中到底应该信谁?信什么?小人物的挣扎与现实社会中所暴露出的人性一直触动着王赫泽,让他想要去探索和表达。

出生于东北的王赫泽,八岁那年便随父母迁至秦皇岛,初中时一个人坐火车跑到北京学画画,后来考美院、工作、生活,在北京一待近二十年。故乡于他而言,更像是脑海深处的童年影像,陈旧而遥远。
小时候,王赫泽从新闻联播里看到东北正在经历国企改制,人人砸破铁饭碗,自谋生路求发展。多年以后,他回到这片土地,放眼望去,满目萧条。他觉得自己应该为故乡做点儿什么。于是,一个与信仰有关的东北故事诞生了。
在东北一座小城里,林场职工小霞(李欢欢 饰)似乎一直在走背运,事事不顺,丈夫馒头(王书仙 饰)只会混吃等死,小霞找人算命,被告知“在运上呢”。回家路上,小霞在树林中意外摔倒,附近刚好有黄鼠狼出没,小霞到家后怪事发生——她总能在睡梦中听见黄鼠狼的讨论,而它们讨论的内容总会在不久之后成真。周围人得知小霞的经历后,利用这一点为她造势宣传,将她打造成远近闻名的“二妖精”,小霞一家靠着这个噱头逐渐走上发迹之路。

故事后半段,风格急转直下,由玄奇志怪落入残酷现实:小霞收下一笔大额定金之后“神力”突然消失,夫妻二人身陷险境,而馒头为了要回投资的钱误入黑传销组织,无力脱身。小人物在困境中挣扎求生、寻找寄托,信过半仙儿也信过黑传销,最终又在“信仰”里走向绝境。

对王赫泽来说,《时来运未转》是在现实主义基调下进行的一次未知探索,也是在民间志怪故事中对于人与社会的一次反思,他想用一种更清晰的方式将这次探索与反思通俗易懂地呈现给观众。
在他看来,许多民间志怪故事里的“传奇色彩”,可能往往并不是由单一事件而来。采访过程中,王赫泽聊到拍摄《时来运未转》时剧组救助白狐的那次经历。当时所有市区戏都已杀青,剧组119人准备转场去一座山里拍摄开头和结尾的两场戏。车快开到林场时,跑出来几只白狐狸挡在车前。
当天王赫泽的父亲因为来探班也在车上,他对王赫泽说:“动物一般会躲着人,但这狐狸都饿得拦车了,你不是养流浪猫吗,那应该想办法啊,救一下这些白狐。”王赫泽就让道具组做了10个1米见方的实木房子,准备了一些食盆,又从网上买了鸡肝、狐狸粮,一并送到山上。“我计划的是还有一个月开春,这些狐狸如果每天能按计划吃两斤狐狸粮,再吃点儿鸡肝,肯定是能活过来的,但它们有没有计划我就不知道了。”


▲ 山里拍戏遇到狐狸
不久之后,王赫泽经历了一次翻车事故。当时车从水库大坝向下滚了三四圈,车上除了他,还有影片女主李欢欢和“叔”的扮演者张迅。但意想不到的,人和车都毫发无损。后来大家将这起平安无事的“车祸”与救助白狐的事件联系到一起,成为片场的一个“传说”。

▲ 翻车后合影留念
但在王赫泽看来,这只是人们在脑海中运用的一种“剪辑手法”,很多民俗故事可能都是这样诞生的——当结果出乎意料时,人们愿意从过往经历中摘取自己认为有关联的部分视其为“因”,再与现有的“果”组合在一起,赋予它某种精神层面的意义。
《时来运未转》中所谓的“出马仙”也是如此,它其实只是一个小人物在困境中寻找的寄托而已,在王赫泽的故事里它并没有真实存在,而是他人利用其进行敛财的一个载体。王赫泽将自己长久以来的观察置于虚构的“真实世界”中,借鉴民俗故事里的灵异元素来展现小人物的挣扎,思考人在绝境之中的信仰问题。这是一幅信仰迷途的众生相,在这里见人欲、见人心、见人性。
“我思索自己的作品,已经拍完的再到后边要拍的,其实我所有的故事都是寓言,是以现实世界的行为准则和生活场景为素材,重新组织成一部探讨人与社会的寓言,单看一个点好像很写实,但是整体看又不是完全写实,这好像是我创作的核心。不是有人说过吗,一个导演一生只拍摄一部电影。如果是这样,这可能就是我人生选择的方向。”
我想拍电影2016年春节前夕,王赫泽带着发小前往伊春,准备为自己第一部电影谈投资。路上他接到一个朋友打来的电话,聊天过程中朋友得知王赫泽想要拍电影,叫他先来铁岭看一看。朋友是铁岭民间艺术团的演员,在其介绍下,王赫泽结识了团长赵秀。
赵秀是70年代生人,比王赫泽年长十几岁,曾是一名舞蹈演员,97年与赵本山、范伟等人一同参加过央视春晚表演《红高粱模特队》,后接管铁岭民间艺术团担任团长。王赫泽与赵秀初次见面是在一个星期五,赵秀问王赫泽:“你有什么诉求?”王赫泽说:“我想拍电影。”赵秀又问:“需要我们做什么?”王赫泽给出老大哥一个终极答案:“需要钱。”
几年之后,王赫泽与老大哥赵秀一同坐在北京某酒吧室外喝酒,他回忆起这一幕,十分庆幸自己当时的回答够简单、够真诚、够直接——“我想,这是给赵本山当团长的人,什么江湖没见过?你跟人家绕什么弯子?只有真实能打动他,如果不能打动,那就说明你这事儿分量还不够。”
坐在一旁的赵秀面露微笑,说自己那一刻的内心活动其实是——“这也太直接了吧!又一个鲁莽青年来了。”
说话漂亮的年轻人他之前见过不少,真正能成事儿的倒没几个。赵秀当时连剧本都没看到,听到王赫泽说“需要钱”时,他心想:“这个事儿啊,不一定能成。”
赵秀原以为眼前这个小伙子只是说说而已,便先应和着,心里其实没太当回事儿。没成想一年多之后,王赫泽又来到铁岭,还带着两份“成绩单”——过去一年多,他执导的短片《海岛》入围第53届金马奖,电影计划《二妖精》(后改名为《时来运未转》)入围2017年FIRST影展创投30强。
王赫泽直接向老大哥摊牌:“我这电影必须要拍了,整不整?”赵秀懵了:“你来真的?”王赫泽语气坚决:“当然来真的!我9月就要开机。”
赵秀知道对方这次是“动真格的”,那就往下落实吧——“东北人的性格,你只要应了这个事儿,就要尽全力把它做好,吃多少苦或者再怎么心酸,都得挺着。东北人不就这样吗,拉硬咱也拉到底。” (注:拉硬,东北方言,指“硬装”)

▲ 王赫泽手绘稿-小镇全景
2017年8月,王赫泽与铁岭民间艺术团正式签署了电影《时来运未转》的联合出品合同,所有落地开销都由铁岭民间艺术团负责。期间赵秀尝试过对外找一些资金支持,但资金一直没能落地,眼看电影就要开拍了,他心里急得冒火。
“其他问题都好解决,住咋办呢?这老些人住,那是真金白银呐。”最后实在没辙,他找到与妻子私交甚好的大姐帮忙。大姐原来是开宾馆的,后来准备转行,没精力再经营宾馆,于是暂停营业。得知赵秀团里要拍电影想借她的宾馆一用时,大姐二话不说——“弟弟,这楼都是你的,我一个客人都不接,你随便用!”
宾馆共七层楼,取暖费已经交完。一楼只有几个办公室仍在使用,《时来运未转》剧组所有人员入住四五六层,其余楼层全部空着。大姐对赵秀说:“弟弟,这楼就交给你了,你爱咋整就咋整,拆了我都不管!”
这是铁岭团第一次参与电影拍摄,赵秀不了解电影剧组的住宿条件是什么样,问王赫泽有什么要求?得到的回复是:24小时热水,24小时宽带,正常取暖。于是赵秀把剧组使用的40多个房间全部升级——安装宽带和热水器,床上用品和房门也全部换新。
剧本中开头和结尾的两场戏,地点是在一片被雪覆盖的森林,王赫泽原本计划等市区戏杀青后全组人转场去伊春拍摄,赵秀心里盘算:“100多人转到伊春,那费用得老大了!”他决定带王赫泽先去冰砬山看看。冰砬山位于铁岭西丰县境内,海拔870.2米,是铁岭最冷的地方,俩人9月份去时山顶仍有积雪。
赵秀问王赫泽:你看这儿符不符合?王赫泽看了一圈:“树矮一点儿,但是要坚持拍也能行。”赵秀又将自己的担忧告诉王赫泽:“在外地人生地不熟,不知道会有什么意外情况,但在铁岭这一亩三分地,起码所有问题我都好协调。”王赫泽理解了赵秀的考量,终于同意不转场了——“就在这儿拍。”
导演,太苛刻了!2017年11月15日,电影正式开机。

影片中有场戏是男女主请人吃饭,地点是一个餐饮大篷车。车刚拖回来时只是一个空壳,美术组重新刷漆、搭墙裙、挂霓虹灯、贴塑料布,里里外外装修了一遍,再一点一点做旧还原。当时为了做得真实,王赫泽还让人从贸易城一家烧烤店里买回来一个垃圾桶放在大篷车门口,里面都是别人吃过的肉串签子,插了一年半,垃圾桶花了二百块钱,买的时候店家懵了——买这玩意儿干啥?
餐饮大篷车的场景搭建完成后,有天赵秀接到交警打来的电话,说有人举报他们违规开店。对方是赵秀朋友,问他:“秀哥,是你们拍电影呢吧?”赵秀说:“对。”对方说:“我一寻思就是,你那车上写个‘串’,别人以为是真的店,举报违规,要不就真给你拖走了!”这次“举报事件”也印证了赵秀此前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但第一次拍电影,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尤其团队里有许多工作人员都是制作电视剧出身,没参与过电影拍摄,对此毫无经验。很多时候,王赫泽在现场不仅仅只是导演,同时还要兼顾摄影、道具、美术的指导工作。

▲ 《时来运未转》现场工作照
影片里有几场“黑传销”的戏,拍摄地点是在辽宁铁岭一间废弃厂房里,戏拍到十多天时,问题又出现了。那天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布置好现场等导演开机,王赫泽来到工厂门口,向里面看了一眼,立马察觉到“不对”——“谁把电线换了?”他指向大厅最里面墙角处挂着的一盏吊灯问道。
“没人换啊,导演。”一名工作人员回答。“我再问一遍:谁把那根儿电线换了?!”王赫泽语气中明显透着不满:“我确认它被换了,最好马上告诉我为什么换掉,我现在只问原因。”
工作人员一看导演要发火,终于坦白是前一晚移动组推轨道时不小心把灯线压折了,灯光组好心帮忙,找了根新的电线替换上。其实电线的长短、粗细、颜色与原来那根几乎一致,大家觉得看上去没什么差别。
但王赫泽从小学习美术,在视觉方面极其敏感。“新的线和用过的线,它的红是不一样的,我大老远一眼就能看见。况且原本那根电线是美术组做旧过的,上面挂着灰尘、胶布的痕迹,与新的线有很大差别。因为这涉及到接不接戏的问题,黑传销的戏已经拍了十来天了,道具如果出问题戏就接不上了。”但事已至此,他不想再深究下去,让美术组赶紧把电线做旧,开始新一天的拍摄。

▲ “黑传销”拍摄场地
吃饭过程中聊起这件事时,王赫泽指向面前摆满碗碟的饭桌,一一指出这张桌子上共有多少种色调,同一种色调之间的差异是什么。“因为我们那时候画画就跟体操运动员一样,基础训练特别重要,它几乎已经变成一种本能,我其实看一眼就知道。所以在片场,他们以为的‘看不出来’和我以为的‘看不出来’根本不是一个概念。”
王赫泽的好友,也是参与这部电影后期字幕制作的影评人汪金卫说:“做王赫泽的组员,美术糊弄不了他,摄影也糊弄不了他。”
赵秀描述王赫泽在片场的状态时会用“苛刻”、“强势”来形容——“比如说今天拍早上七点钟的阳光,第二天再拍时必须还得是这个点儿的阳光,分秒都不能差,差一点儿他就不拍了,明天继续拍七点钟的阳光。哎呀我天,太苛刻了!你道具放歪一点儿,他当时就急了,你可不知道他那脾气,进入电影状态的时候他人就不一样了,特别强势。”
在片场,赵秀常常充当王赫泽的“灭火器”——“团里这边的工作人员没经历过电影拍摄,他们不了解,冷不丁接触一个要求这么高的导演本来就害怕,结果你越说他越懵,越懵越干不好,越干不好王赫泽越急眼,他一发火我就得去灭火。”
一开始还有工作人员以为王赫泽是赵秀雇来干活的,看他在现场那么卖命,忍不住劝他:“导演,差不多得了,就一个活儿,咱别那么较真儿。”对方原本也是出于好意,把王赫泽当哥们儿想跟他“唠唠知心嗑”,没想到王赫泽直接火了——“你以为这是谁的事儿啊?我俩共同合作的项目,你让我差不多得了?”
有几次,赵秀为了缓和气氛,跟所有工作人员说“晚上戏不拍了,大家累了休息一下,导演请大家吃饭。”饭桌上,工作人员发现王赫泽在生活中与片场上简直判若两人,他个性随和,喜欢开玩笑,大家都说:“导演生活中其实是个挺好相处的人,怎么往那椅子上一坐就来神儿了,不一样了?”
经过一段时间相处后,这些人总算看明白了:导演对事儿不对人,他在工作中的那些苛刻、较真儿也只是想把电影拍好,没有针对谁。到后来在片场已经不用王赫泽再开口,每天各个组都有人自发号召大家:“咱都精神点儿,今天争取一条过,别费劲儿!”

▲ 《时来运未转》现场工作照
不能自己骗自己,不能自己劝自己“差不多得了”——这是王赫泽的做事底线。“我为啥在现场压力那么大?因为我知道投到电影里的钱是团里所有人每年一场一场演出挣来的,铁岭团跟着我投入了这么多财力、人力、物力和时间,如果连我都要求自己‘差不多得了’,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
“从公务来说,秀哥是我的联合出品人,从交情来说,这是我老大哥,在我人生第一个最难跨越的台阶上,他给了我一次不计后果的支持。所以我不能说这个事儿混日子就过去了,我必须给老大哥一个交代,哪怕片子最后没获奖,我自己在心里也要有一个完成标准。下了片场可以请大伙儿吃肉喝酒,上了片场谁也别跟我扯犊子,都得好好干活儿!”
赵秀想起一篇写鹰的文章,说鹰飞行到一定年头后会明显感觉力不从心,这时它会找到一处悬崖峭壁,用喙将自己的羽毛一根一根叨掉,然后重生。他觉得搞创作的人也是如此:“我们每一回创作都是在重生,都会迷茫、痛苦,就像‘扒皮’一样。所以我也非常理解赫泽的那种焦灼,他还不是单一地搞创作,摄像、道具、美术他都要管,为啥?大伙儿不懂啊。他如果在片场只是做个编剧、导演的话会轻松很多。”
采访过程中,王赫泽从手机相册里翻出一张自己手绘的场景设定图,背景是电影中小霞和馒头的家。这个家是在铁岭民间艺术团四楼排练厅搭建而成。

▲ 实景搭建图
王赫泽要求每个地方的尺寸必须做到绝对精确,道具的做旧程度也要尽可能达到他的标准。


▲ 搭景平面图与拍摄现场影棚图
他将后期拍摄图与前期手绘图进行对比——几乎完全还原他的想象。

这种不允许有任何差池的秩序感在王赫泽的生活中也随处可见——
聊天时,他每一次摆放手机的位置都要与桌子边沿形成90度直角;喝酒时,他的所有酒瓶横平竖直依次排列,酒标朝向必须一致,与桌子边沿组成一条平行线;停车时,但凡时间允许,他一定要找到最满意的车位再停,一旦发现更好的车位就要把车倒出去重新再停一次。赵秀无奈:“在他家,牙膏摆反了,他都特别难受。”
他有时候会劝王赫泽:“你拍戏怎么认真我都理解,但是在生活中放松一点儿,千万不要对自己那么苛刻。”
理想主义者的合作2018年1月26日,《时来运未转》正式杀青。
第一次拍片,王赫泽心里没底,一开始定的拍摄周期是75天,后来觉得时间太长,改为 45天。拍摄时他一直担心后期剪辑素材不够用,又在中途加了十几场戏。结果戏越拍越多,时间越来越紧,拍摄进行到第40天时,他跟赵秀说:“秀哥,咱还是按原计划执行吧,45天拍不完,还得75天。”赵秀同意了:“那就75天。”
采访时赵秀聊起这件事,说他当时心里早有准备:“创作的规律就是这样,说白了春种秋收,你提前一个月收它能成熟吗?我们也是搞创作的,虽然搞的是舞台创作,但我懂这个周期。”
赵秀曾经听人说过,有些人拍一部电影只用十几天。他心想:“十几天能拍出什么好电影?全都奔着打快拳去的。”而在王赫泽身上,他看到了那股想认真拍电影的劲儿。“赫泽最开始说的拍摄周期就是75天,如果他当初跟我说拍摄只要十几天的话,我就跟他谈别的了——那你给我多少钱?因为你是奔经济来的,我就奔经济给你唠了,你要是奔业务来的,咱就唠业务。”
他欣赏王赫泽的做事态度:“有些人对待一件事儿只是‘我完成了’就行,赫泽不是在‘完成’,他是在认真做事儿,这种认真也是触动我和他合作的原因,所以多难都得支持。”
王赫泽将他与赵秀的这次合作归结为一种缘分:“一个真正想做事儿的人碰上另一个真正想做事儿的人,所以我们可以一拍即合。”他把这次拍电影的过程比喻为“在战场上打仗”——自己在前方冲锋陷阵,老大哥在后方稳定军心。

▲ 王赫泽在拍戏现场
拍戏那段时间,如果结束得早,赵秀和王赫泽会请所有人下馆子。考虑到零点之后铁岭所有餐馆都已打烊,没法儿再点外卖,赵秀就让食堂师傅把香肠、卤蛋全都预备好,每天定时定点发放到每个人的房间。
电影杀青后,赵秀请剧组所有工作人员在铁岭最好的酒店吃饭,说来到铁岭的都是客——“抛开电影不谈,我一定用对待客人的角度去对待他们,业务是一方面,咱还得做人呐,东北人不就是这性格嘛——要脸儿。”
在王赫泽看来,没有几个剧组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哥俩合作,首先尊重专业,另外就是尊重人。”回到北京后,曾经被他在片场呵斥过的一名工作人员有天打来电话,跟他说:“赫泽哥,我想跟着你,你以后有什么戏就叫我。”
有一次,王赫泽和别人聊起自己的拍片计划,说接下来还会有项目继续与铁岭民间艺术团合作。对方听到后大吃一惊:“你超支一个月他们还能再跟你合作?”
王赫泽觉得自己很幸运,第一次拍电影就能遇到赵秀这样的合作者。“秀哥作为铁岭团团长,以他的年龄和资历完全可以生活得高枕无忧,但他没有,他一直在积极尝试往前走。而且他还能相信理想,这是让我特别敬佩的,你觉得这个时代有多少人还能真的相信理想?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我到他这个年纪,还能不能做到像他那么纯粹?很难想象如果我有名有号,会不会选择另外一种方式生活。”
但在赵秀心里,王赫泽才是那个真正纯粹的人——追求绝对完美。可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追求绝对完美只会遇到重重阻碍。“一个纯粹的人做不了电影”,赵秀说,“他需要旁边站着我这样一个‘不够纯粹’的人才能做成电影。”
当初被朋友一通电话叫到铁岭来“看一看”的王赫泽,没有想到最后真的在铁岭把自己第一部电影拍成了。几年后他回想起这一切,感慨——时也,运也,命也。

2022年7月29日,《时来运未转》在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首映。
放映当天,每位入场观众都会拿到一张“观众票选单”,放映结束后为影片打分。有人发现,影片中男主角馒头误入的黑传销组织叫“灯塔”,而票选单背面恰巧印着一个灯塔图案,那是FIRST官方数据支持机构的LOGO,名字也叫“灯塔”。
当电影放映结束,影院灯光再次亮起时,一个“魔幻时刻”诞生了:这个叫做“灯塔”的命运载体仿佛在这一刻从银幕落入观众手中,由虚幻走向现实。
8月4日晚,FIRST青年电影盛典在青海大剧院落下帷幕,王赫泽执导的长片处女作《时来运未转》获得“最佳编剧荣誉推介”。三天后,他发了一条微博:“一个学画画的,干了摄影,当了导演,拿了编剧奖,也许这就是生活。”回到北京后,他在一个午夜里和朋友们一起喝酒,回忆起过往种种,感慨人生不可预设。
酒过三旬,困意袭来,王赫泽与朋友们道别,一个人走在回家路上。他穿过马路,背影有些晃动。街角的灯依然亮着,那个青年导演此刻正摇摇晃晃地走向楼群深处,走进他的秩序王国。而前方,还有更多不确定的未来在等着他度过。



图源|文中配图均由被采访者提供。图片不为商用,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立即删除。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