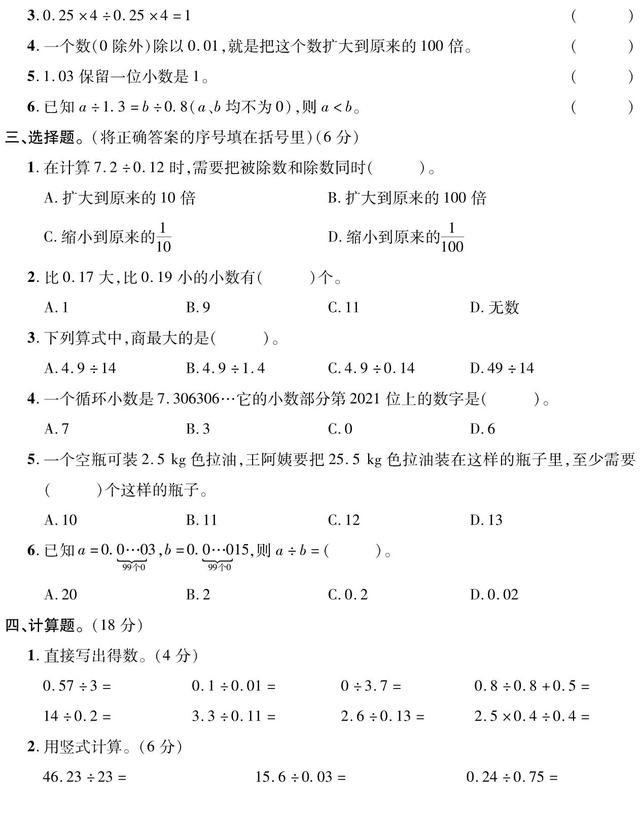那年那月在哪个海边(绛帐高中那年那月)
绛帐高中:那年·那月·那风
◎杨进云
在一些文字里提到过绛帐高中,一掠而过,不肯深究。那年、那月、那风,岁月深沉,神经元密布,那年、那月、那风,冷风清凉,十指微寒。

一九八九年秋天,我挎着一个颜色老旧,看不出本色的书包走进了绛帐高中。绛帐高中和我毕业的上宋初中大不相同,虽然,它们相距并不远,一东一西,都沿着物产丰饶的渭河平原排列。对上宋初中的印象,是一幢三层的红砖教学楼。操场在学校后面,每次上体育课,都要从学校的后门出去,在四周都是豆麦田地的操场上撒欢儿。紧挨操场的南边,一百多米远的地方,有一眼温泉,四季清水长流,汇成一个飘满浮萍的长方形水池,青蛙在水草里大声地唱着自编的歌曲。有时,因为人的惊扰,飞快地窜入水中,溅起一圈圈波纹。也许,每个人都有过落寞、孤独的日子吧!在上宋初中,我是一只孤独、倔强的山羊,常常夹着一本书,在这片水边徘徊、徘徊!对上宋初中的另一个记忆,是每天晚上都一个人睡在教室里。两张课桌,宽度吝啬,平躺,身体和灵魂都放好了,两只胳膊却悬空,无处搁置,更不能翻身。开始觉得有点难,久了,就习惯了,居然能夜夜安眠。教语文课的李文旭老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想不起他的名字,只记得他笑眯眯的一张脸。后来用了很长时间,在记忆里翻箱倒柜,有一天脑海里忽然就闪出了李文旭三个字来,有点兴奋。那年,临近毕业考试,因为觉得原来用的名字太小气,决定换个名字用,就找李文旭老师。他很热心地和我商量,给我另取了一个名字,进云。至此,这两个承载着李老师期望的汉字,就成了代表我的符号,一直和我如影随行,伴随着我越过长长岁月的阴冷,或者热烈。

二十多年后,当我有机会再经过上宋街道时,特意从那条窄窄的巷子走到学校门前去看。学校还在原来的位置蹲着,只是居中建了一幢磁砖贴面的暂新的大楼,楼的式样也时髦了很多,那幢熟悉的旧楼还在。想进去看看,但学校年轻帅气的保安很负责任,因为面孔陌生,就坚决不肯放行。只好绕到学校后面去,想看看那眼泉水。结果操场也早已用红砖墙围了起来。发了一支烟给田间锄草的村人,闲聊,打问那眼泉水的情况。村人淡淡地说,早枯竭了,不出水已很多年了。心里顿时有些失落,惋惜的情绪大约很明显地在脸上表现了出来,引得农人奇怪地盯着我的脸,看了一忽儿,说,就一眼泉水,没人在意的。他是在安慰我!一眼在我记忆里那么重要的喷泉,竟然就在我不知觉的时候,就这么消失了,连同那些落寂的,不可追的年少记忆。
绛帐高中的一草一木,一楼一阁,都有捉摸不透的深沉气息。站在校门前,我抬头,仰视这层层叠叠,有如宫殿一般的学校。从小长在骨子里的桀骜,让我能有敬畏之心的物事并不多,绛帐高中是个例外,至始至终,它在我的心目中一直都是一个庄严的存在。

简约的大门,绛帐高中几个闪着金黄色光芒的行书大字,被高高地举在大门的上空,和周遭的树叶相互辉映。学校的门前有河,河上有桥,桥头有树,树可合抱,枝繁叶茂,遮天蔽日。桥上有水泥和钢管加固的栏杆,生锈的栏杆因为手掌频繁的摸索,发出黑沉沉的亮光。课余,总有很多学生在桥上依着栏杆,看山,看水,看天上飘过的云朵。走进大门,对面是教师的办公楼,左边是教学楼。教学楼的出口处有一个自来水龙头,学生们常在这里洗手,或者直接扒在上面喝水。楼的拐角有一个报栏,定期更换《中国青年报》。记得传真机的普及和使用,就是我在《中国青年报》上看了一篇介绍的文章,才对它有了初始的印象的。后来在广东工作的十几年时间里,我一直用办公室里的一台黑色松下传真机,给客户发送或者接收资料,印象很深。
二楼的教室,挨窗的座位,可以看到白杨树的茂密的枝叶就在窗口,宽大油亮的叶子俯仰随机,伸手可触,有风掠过,树叶就会发出散乱的哗哗声。讲课的牛宗礼老师,头发花白,嗓音浑厚,知识渊博,史实典故,轶闻趣事,常常旁征博引,张口就来,那时,很乐意听他讲课。教代数的老师大约祖籍河南,一口流利的河南腔,听说数学功底非常深厚。但我常常听不懂他用河南腔读的三角函数符号,听课很出力,经常跟不上他讲授的思维,只好课下用功。他是一位很负责任的老师,每次上课必亲自抽查学生的课余作业,而且几乎每次都会查到我。

学校依着黄土塬,分为三级。第一级是操场,在学校门前的低低洼处。出校门,过桥,下台阶,一个很大的操场。操场的周围都是农田,依四季时令不同,长着小麦、玉米、或者长着开了花就会一片金黄的油菜。向南几百米远,陇海铁路东西横贯穿过,常有运货的长长的火车,鸣一声汽笛,然后伴随着车轮和铁轨轻吻的欢快的节奏声,从铁路上滑过。操场是同学们都喜欢的地方,每天早晨的晨操,中午的课间操,还有体育课都在这里活动。那时,我的爱好是武术,不在学校所授的体育课目内,所以经常在晚自习后,才和三五同好,一起来操场习练。

教学楼、教师的办公楼,还有一间平时并不开放的图书馆在第二个台阶,进校门即是。如果要去学生灶吃饭或者去学生宿舍,就要上一个长长的蓝砖砌成的台阶,才能到达,这是学校的第三个台阶,依着黄土崖,宽宽展展的一个面积很大的平台。那时每天都从那条长长的台阶蹦蹦跳跳上,蹦蹦跳跳下好几次。饭是大锅饭,用不着菜单。早餐和晚餐是稀糁子和馒头,菜是从家里用瓶子带来的盐渍的咸菜或者炒的辣角,馒头大多数同学都会从家里背来。但夏天天热,馒头不易存放,基本上星期三后中,就要买灶上现蒸的馍头。中午是面条,煮几片青绿的白菜叶子或者菠菜之类的绿叶菜。每到吃饭时间,房檐下,桐树下,就蹲满了一圈一圈的同学,一人手里捧一只蓝色的搪瓷碗,圈子的中间是红红绿绿的瓶瓶罐罐,红筷子、白筷子、黑筷子在其中穿梭,专挑自己喜欢的菜吃,但常吃不饱。现在回想起来,那些饥饥饱饱的日子,也充满了欢声笑语。

多年后,我曾郑重其事地回过一次绛帐高中。其时的绛帐高中,早已楼空人去,校园里所植的花木草树,因无人修剪,疯长成一团团凌乱的荆棘。水泥地面上水渍后的青苔,因为干涸而变成墨黑的颜色。楼舍依然保持着原先灰朴朴的模样,只是面额上平添了些许岁月累积的皱纹。站在楼前仰望,黄土崖的崖壁上开满了野菊。野菊,依然如当年精神抖擞的模样,染黄了黄土崖的沟沟坎坎。从教学楼落满灰尘的台阶拾阶而上,耳边,就条件反射般响起了《星星知我心》这首歌。那几年,每次午间放学吃过饭,我常常跟着学校广播的音乐,一边大声唱着这首歌,一边从这台阶走向教室。

其实,提起绛帐高中,习惯了文字蜻蜓点水式的不深入,感觉亦然复杂无绪,故此停笔,且用宋代柳永的两句词做结: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2021年7月3日于扶风
作者简介

杨进云,宝鸡市扶风县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陕西青年文学协会会员、宝鸡市作家协会会员,扶风县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数百篇(首) 散文、诗歌发表于《乡镇论坛》《延河》《长安报》《佛山文艺》《东莞文艺》《宝鸡日报》《陕西农村报》《陕西市政》《秦岭文学》《秦岭印象》《渭河文化》《海虹之声》《八九点钟》《扶风文化》《扶风文艺》等报刊杂志,有作品入选《2012年陕西青年文学选》《美丽陕西》《恭贺扶风》《宝鸡生态美》等文集,获省、市、县各类文学奖项十余次。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