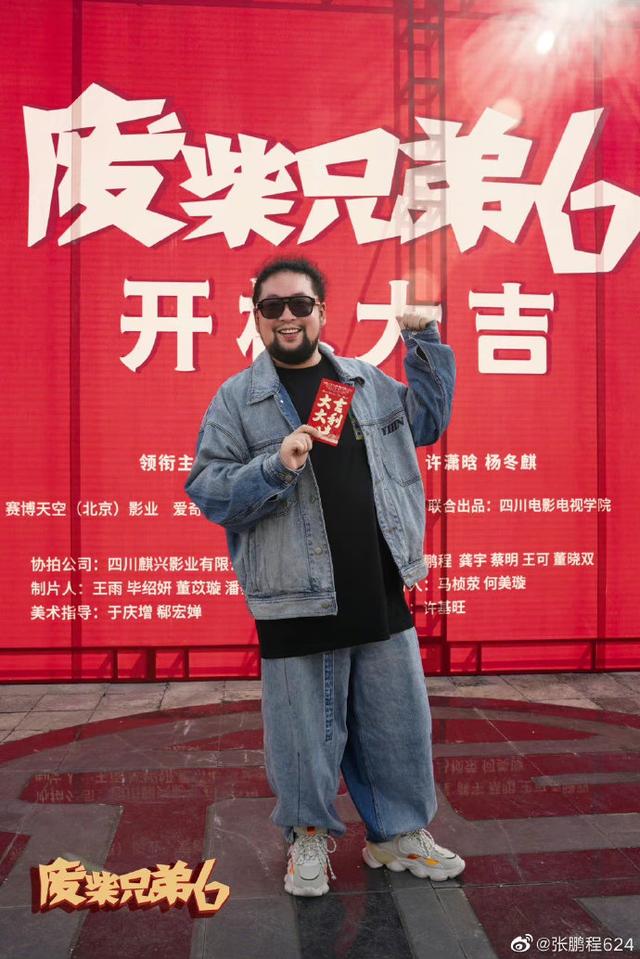我的父母名字(一我的父亲母亲)
目录
(一)我的父亲、母亲李兰颂:《江河之爱是大海——纪念我的父亲李又然》
李兰颂:《沪上》
刘华沙:《山——献给老爸》
刘华沙:《落叶——先父逝世周年祭》
(二)我的父亲、母亲李兰颂:《冰都雪野炉火烧——追悼我的母亲刘蕊华》
李兰颂:《在两个11号住到11岁的我》
李兰颂:《11月,晚秋早冬的生死念》
刘华沙:《母親節》
(三)我的父亲、母亲李兰颂:《我最终未能见到祖屋(2000年回慈溪拜谒记)》
李兰颂:《多想》
(四)我的父亲、母亲李兰颂:《我写〈金不换〉〈银发丝〉歌词(母亲理念的潜移默化)》
(五)我的父亲、母亲李兰颂:《李又然当时当地名家日记信札考》
/

李又然老年照/冯羽摄
李兰颂:《江河之爱是大海——纪念我的父亲李又然》1984年11月13日。这是一个即使在祖国东北边陲也算来得尚早的特大风雪天。我接到通讯员由机关追至工厂送达的一笺电文,惊闻父亲溘然长逝。组织上先已为我办好手续,立即送我从哈尔滨乘飞机直飞北京奔丧。这绝不是空中反应:我头疼、耳鸣、眼花⋯⋯一阵阵的沉闷和窒息。
“坐飞机来,快来!”
夜航中,我记起和父亲阔别多年终能得以相见的时候,父亲写给我的这一封信的全部文字。1979年以前的十三年,由于众所周知的缘故导致的骨肉分离,我思念父亲,父亲爱抚我,都只好企盼一封封频繁往来于地北天南的万金家书。父亲下放劳动,我失学又待业,我们父子所用的信纸、信封、邮票花费,更大大节缩了各自贫寒生活费用中有限比例的最低水准。重逢后的六年,我见父亲四次。每回探亲,每回惜别,我都不时地忧虑,我那大难之后初得安宁,却已年逾古稀、体弱多病的父亲,可能在医院里随时会停止呼吸。我常在睡梦里惊醒。
可是,这次,我来得再快也晚了!听在医院保健病房护理父亲足有三十一个月的姐姐达妮和弟弟华沙说:“爸毕竟是突然逝世的,呼吸系统衰竭,肺炎!”“爸直到最后时刻头脑也不糊涂,眼睛那样亮!”
姐弟商议后决定,向党组织建议为父亲从简治丧,不成立治丧委员会及治丧办公室,不搞向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不占八宝山革命公墓灵位,不保留骨灰,不让单位负担任何在父亲死后可能享受的高干与名人待遇。中国作家协会和商务印书馆就此联名发布了较长篇幅且较好印刷的讣闻,特别指出:“根据李又然同志的遗愿和亲属的意见⋯⋯骨灰撒在故乡和战斗过的地方。”
我终于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时间是1984年12月18日早晨。我双手颤栗地抱起父亲完全失去了体温的遗体,在堂兄李成甘、姐夫汪进军和遗体整容师的帮助下为父亲整容。父亲瘦削的脸庞,只有眉宇间保持近似生前的思索状,很是理智,充满感情。姐姐和弟弟献给父亲一大束鲜花。灵车,沉重而缓慢地从医院开到天安门广场。眼望人民英雄纪念碑,我流泪默诵父亲吟咏五星红旗的诗句:
李又然:《天安门广场上的五星红旗》你是无数烈士的鲜血所染成
你是对人民一片忠心的象征
你高高地在蓝天中飘扬着风
是烈士鲜血的波涛在汹涌
/
是的,是的,是的,父亲是以烈士的精神鼓舞我们子女三个从小长到大的,即使是在最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他也总是给我写信说:“爸心里总念着你,像你总念着爸一样。爸有可能见不到你了,感到伤心,希望你越来越坚强!爸对得起你的就只是,在遇到危险和困难的时候,心里总有烈士⋯⋯”
那是父亲站过的观礼台,那是父亲去过的大会堂,灵车绕过天安门广场,上了笔直宽阔的长安街,向八宝山革命公墓开去。很快,经过木樨地22号楼,这栋高层公寓内,居住着许多位父亲在上海、延安和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战友。李之琏叔叔,是中纪委常委,分管信访室以及教育室,曾为父亲转换医院一些问题,找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副部长黄树则叔叔作细致安排。丁玲阿姨和江丰叔叔,是父亲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那时在延安,父亲不愿意接续法国共产党的党龄,又由于在军人大会上批评了所在单位党组织的一个负责人,被长时间以有人道主义和晏起习惯为由,拒绝在党的大门之外。毛泽东同志知道后说:“他们不批准,由中央解决。”父亲才在接受陈云同志谈话以后,于1941年1月11日无候补期重新入党,竟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十几位由中央直接接收的党员之一。自己正患重病的丁玲阿姨,在父亲生前写了《李又然散文集》的序言,又来医院看望,多次打电话关照。《中国》大型文学双月刊创办,开招待会,她致词说:“我们追悼柯仲平、萧三、冯雪峰⋯⋯以及刚刚去世的李又然同志,他们已经不能和我们一起战斗了,但他们的功绩,我们是永远永远不能忘记的。”
尽管这是冬季里难得的阳光充足的好天,我却浑身发冷,感到灵车越开越远⋯⋯10:55,纵使我千呼万唤,也无法挽留住父亲,父亲真的、真的呀,离我们而去了⋯⋯走向永不复回的远方!
我和弟弟护送父亲骨灰到上海。1906年4月16日,父亲诞生在这个特大都市里。祖父李雅年,与人合伙在董家渡开办新长顺鸡鸭行。父亲在幼小的时候,家庭生活本还富裕,但是,他自少年时代起就不堪忍受金钱社会对人性的压抑,以至于越来越愤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五卅”惨案刺激,他终于,背叛祖父令其安身立命于银行金融界的意愿,远涉重洋旅欧留学。法兰西里昂、巴黎,比利时鲁汶,在瑞士弗里堡,父亲加入法国共产党,为《赤光》秘密撰稿,与罗曼·罗兰通信⋯⋯五年头,回上海,参加世界语者运动和反帝大同盟。就在此时,艾青叔叔把《大堰河——我的保姆》等一束诗稿,托人从看守所中带出交由父亲转而拿给《春光》发表的。也在此时,受被反动派拘押的江丰叔叔之托,父亲致函鲁迅,请求先生给在押的进步青年寄书的。更在此时,父亲为反战大同盟来华代表团的玛莱和古久里当翻译,冒着生命危险,抢救机密文件,保护纱厂女工⋯⋯
在父亲最初步入革命航程的上海港,交通艇冲向外滩水域,在两列处于舶位的万吨轮之间,破开一条浪花翻腾的水路。江风凛冽,汽笛高亢,午后微紫色的霞光映衬着与江水相连的天幕,整个世界都肃穆庄严起来。我和弟弟,还有表兄叶琪冠,我们的身体紧贴着船舷,悲痛地撒下了父亲的骨灰,颠簸中伫立甲板上脱帽致哀,再将鲜花向浪涛投去,零落的银柳、月季、石竹、文竹、康乃馨、腊梅黄、牡丹菊,随浪峰波谷起伏散尽⋯⋯我们,遥望远去的滔滔雪浪的黄浦江水,汇合长江,流向大海。
钱塘江大桥上,看江水异常平缓、宁静、宽阔、碧透⋯⋯我和弟弟,在这里撒下父亲的另一捧骨灰。父亲是在浙江老家度过的童年与少年。老家,老家,我和弟弟作为浙江人的后代,来到老家,缅怀父亲革命的一生。当年,国难当头,杭州湾和金山炮响,父亲就从老家出走,直奔抗敌前线;当年,经组织派遣,与何士德、麦新等六人,准备行军赶赴华东,又因时局变化,行军中途转赴东北;当年,父亲离延安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散文名作《吉普车》,就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浙江省中学生课外必读的范文⋯⋯
从万米高空鸟瞰,冰川,雪山,往东北,再往东北,开始出现的是一块块规矩平坦的赭石色沃土,继而那铺天盖地的大雪中显露出的一条翡翠色巨蟒,就是松花江!1946年2月,受党委派,父亲由延安来东北,接管学校,筹建文联,主编丛书和报刊,直到参与南下工作团政治部的领导工作,进关⋯⋯抗日战争在延安八年,解放战争在东北三年,父亲从延安到东北行军六个多月,我今天护送父亲骨灰到哈尔滨仅飞行了九十分钟,姐姐和弟弟在首都机场的话音还在萦绕于我的耳畔——“爸发表文字不多,在东北写的和写东北的却不少⋯⋯”的确,父亲生前出版过五本散文集,其中第一部《国际家书》就是在吉林出版的,距今四十余年,版本可谓珍贵。我知道有几位当年的青年人现在的老年人珍藏着这本书,想借来看一看,人家爱不释手,我得到的回答只一个:“绝版了。好书,真是好书。我珍藏多年,一定为你好好找找看⋯⋯”是啊,一个人的写作,能在读者中产生如此深重的影响,能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我以为,是最该满足的了⋯⋯冰雪世界最为严酷而又净洁,终于,终于啊,父亲的最后一捧忠骨、一颗纯粹的灵魂,陨落在松花江上相对太阳岛那破开冰冻层的清澈江水中了⋯⋯
黄浦江,钱塘江,松花江,不同流域,一个去向。江河之爱是大海。父亲以大海情怀写出大气魄的诗章,也把我无尽的哀思化作承接遗志的力量:
李又然:《致远方》远方朋友寄来相思子,
这红色珍珠象征爱;
我该最无限地爱谁呢?
党、祖国、人民和世界。
/
世界是我的家庭,
人民是我的父母,
祖国是我的光荣,
党呢?是我永久的生命!
相关链接:全文载《作家》文学月刊(1985年6月号);初收李兰颂散文集《兰颂特写》(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3月第一版)。

1979年翠微路2号院/唐欢摄
李兰颂:《沪上》我从外白渡桥
沿着观光台
一路走来
花坛的花儿
摇曳的姿态
把晨曦都弄香了
更有一朵儿又一朵儿散落的
野山菊
我就一捧又一捧地拾起
屏住呼吸
抛进波涛翻滚的
黄浦江里
/
晨雾推荐的东方明珠
很像是肩上披着薄纱的模特儿
这浦东独有的青春美少女
看都不看小伙子一样
来回奔忙的舰船
更毫不介意对面还有
海关大楼和众多银行的
老爷爷们
/
晨光洒满
曾经有过的一切
一切都不曾再有
冒险家的智商
总在欢乐边上
为严肃而死的人
死了也严肃
活着认真
死也认真地死
如此哲学
就叫脾气
/
金融风波再大
谁也无法把外滩
搬到华尔街去
商业气息再浓
最早抗战的延安人里
很多来自十里洋场
他们可以
乘邮船走好望角
学马赛曲到马赛港
更可以
住窑洞在窑洞里
唱响黄河大合唱
/
我从外白渡桥
沿着观光台
一路走来
约定没有代沟
诚信出于欣赏
就像永久的清明
有晚辈献花在沪上
资料链接:2003年清明,作于由上海回北京的飞机上,在外滩祭扫先父李又然骨灰撒布的陆家嘴附近,原载《中国红十字报》副刊。
刘华沙:《山——献给老爸》经过亿万年的地壳变动
和漫长的风雨侵蚀
山崩坍了
像烈日下的冰柱
一年比一年的小
一年比一年的矮
终于,一场狂风过后
山消失了
/
山消失了
却留下几块石头证明:
“从前,这儿有一座山!”
/
1985.1.29.拂晓北京安外
刘华沙:《落叶——先父逝世周年祭》秋天,树叶纷纷
告别了树干
像天上的流星
受大地的吸引
/
不再有绿色的喧闹
生命也已化为泥土
以自行消亡的方式
将完美还给了自然
/
1985年11月13日忌日
北京安外甘水桥
/
相关链接:《山》(1985.1.29)、《落叶》(1985.11.23)间隔近十个月写出,“拂晓北京安外”与“北京安外甘水桥”为同一地点。《山》连同李又然的遗作《泉》《夜是银色的世界》《萤火虫》一并在《诗刊》发表的——在《诗刊》(邹荻帆主编)1986年1月10日出版1月号总第200期。据胡昭日记与《山》有和诗。

叶琪冠、李兰颂、刘华沙在上海外滩陆家嘴附近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