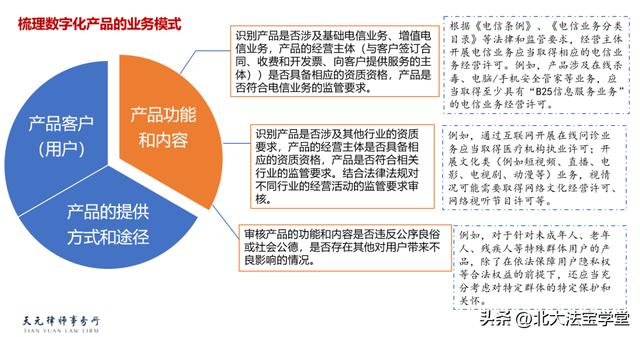《骷髅幻戏图》与永乐宫骷髅图什么关系(骷髅幻戏图与永乐宫骷髅图什么关系)
宗教视域下的南宋风俗画释读
——以传李嵩《骷髅幻戏图》为例
王一帆
“宋画力求要广泛地表现当时的士农工商、渔樵耕读各种人物的生活情景,以显示宋代是一个人人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因此宋画常带有风俗画的性质。”历史上的南宋,军事孱弱、偏安一隅,但其城市经济却发展迅速,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从北宋开始出现的旨在表现当时社会的不同侧面的风俗画,这时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了大幅的提高,并得到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的喜爱。社会需求量的增加又反向刺激了风俗画创作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南宋成为中国古代美术史上风俗画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这时期的风俗画题材多样、风格各异、名家辈出,其中画家李嵩就是较突出的一位。而其代表作之一的《骷髅幻戏图》尤以表现内容之奇诡为后世收藏家与研究者所关注。

目今存世的一幅传为李嵩作的《骷髅幻戏图》,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图为一幅27.1*26.1的扇面册页,绢本设色,画面左侧署有李嵩名款。画上钤有“会侯珍藏”、“信公珍赏”等几方收藏印。整幅画左侧绘一头戴黑纱幞头,身着透明对襟长衫的大骷髅。其左前方,斜横着一副担子,挑着一副箱笼,内盛箧奁、草席、雨伞、包裹等物,似乎要说明大骷髅为游方艺人。大骷髅右手操纵着一具提线傀儡,此傀儡为一小骷髅模样。其双臂前伸,悬腕沉肘,弓腰蹲步,整体姿态作蹲骑状,似在逗引其对面匍匐着的婴孩。
婴孩为傀儡戏所吸引,做向前扑爬状,右手五指乍开,够向小骷髅。傀儡与婴孩基本位于画面中央。婴孩身右,绘一身穿对襟旋袄的妇女,伸张双臂,做出欲探身阻止或抱起婴孩的姿态。大骷髅身后,亦有一妇人盘腿而坐,怀抱婴孩,坦开衣襟,做哺乳状;而她的目光则越过大骷髅,关注着画面中央的傀儡戏与婴孩。妇人背倚着一座砖砌方台,台上正中立一木牌,上有楷书“五里”字样。

▲骷髅幻戏图所附题词
此册页对幅为黄公望作、王玄真题写的小令《醉太平》:
没半点皮和肉,有一担苦和愁。傀儡儿还将丝线抽,弄一个小样子把冤家逗。识破个羞哪不羞?呆兀自五里已单堠。至正甲午春三月十日大痴道人作,弟子休休王玄真书,右寄《醉中天》。
这是现存关于该图所描绘内容的最早文字记载,在明人孙凤所编《孙氏书画钞》中亦有收录。另据明代书画鉴藏大家陈继儒《太平清话》记载,这幅图也曾被他收藏过:
余有李嵩《骷髅》团扇绢面,大骷髅提小骷髅,戏一妇人。妇人抱小儿乳之,下有货郎担,皆零星百物,可爱。又有一方绢,为休休道人、大痴题。金坛王肯堂见而爱之,遂以赠去。
但是,李嵩所作《骷髅幻戏图》可能不止此一幅。明代顾炳的《顾氏画谱》就收入一幅李嵩《骷髅图》木板画。其对幅则是明代吴来庭题《李嵩骷髅图跋》:
李嵩,钱唐人,精工人物,佛像尤绝,观其《骷髅图》,必有所悟,能发本来面目意耳。为李从训养子,颇得其遗妙,尤长界画,光宁理三朝画院待诏。——淮浦吴来庭
又清人吴其贞在其《书画记》中也有关于李嵩《骷髅图》的记载:
李嵩《骷髅图》,纸画一小幅,画在澄心堂纸上,气色尚新,画一墩子,上题三字曰“五里墩”,墩下坐一骷髅,手提一小骷髅,旁有妇乳婴儿于怀,又一婴儿指着手中小骷髅,不知是何意义。识二字曰李嵩。
这两幅《骷髅图》从质地上就与故宫藏本不同。由此可以推想,在元明清三代流传有多件被认为是李嵩所作的《骷髅图》,就像现存有四件题为李嵩的《货郎图》一样。这些作品可能是李嵩真迹,也可能是后世摹本或伪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自南宋至明末清初,李嵩一直被认为是擅绘《骷髅图》的代表画家,而《骷髅图》也往往以“李嵩作”(无论是否真是李嵩所作)的面目流传或被收藏。

较之于前代的骷髅母题图像,《骷髅幻戏图》不仅造型精准度大大提高,所描绘的内容亦十分奇特,明显是含有深层意蕴的。诚如吴来庭所言:“观其《骷髅图》,必有所悟,能发本来面目意耳。”而其“本来面目意”究竟为何,自古至今一直是众说纷纭。按南宋时期,是中国宗教向世俗化、平民化转型的重要时期。如刘浦江所言,此时“佛教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唐代义学宗派的衰落和新禅宗的崛起,以及佛教前所未有的社会影响。道教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神仙信仰的动摇、内丹术取代外丹术,以及南宋金元时期新道教的兴盛,道教从上层社会走向民间社会,民众道教成为主流。”将《骷髅幻戏图》的创作置于这样的宗教视域下,再结合相关传世文献的考察,笔者认为该图透露出南宋宗教普遍社会化的历史事实,即《骷髅幻戏图》是一幅富含宗教意蕴的风俗画。
一、《骷髅幻戏图》与道教生死观
道教在经历了由南北朝至唐代的贵族化发展后,至北宋开始了世俗化的转向,南宋新道派的出现则标志着平民化成为此时道教发展的主流。而道教对民间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其生死观的传播。《骷髅幻戏图》即很有可能蕴含有道教生死观,起码是可以在这种生死观的理路上进行解读。
上文提到黄公望作、王玄真题《醉太平》是今存最早的关于李嵩《骷髅幻戏图》的文字记载。考黄公望曾被诬入狱,出狱后遂亲近佛老,最终皈依元代盛极一时的全真教,与金篷头、莫月鼎、冷启敬、张三丰等高道过从甚密。王玄真是黄公望的弟子,也是全真教徒,并撰有《丹阳祭炼内旨》。从《醉太平》曲末题署可知,此小令写于元至正十四年春,正是黄公望去世的当年,此时这师徒二人已然入道多年。
作为道士的黄公望在解读这幅骷髅图时自然会渗入全真教的思想。曲子开首一句便是“没半点皮和肉,有一担苦和愁”。这显然是指操纵傀儡的大骷髅。画中的一担行李被黄公望比喻成愁苦。但这具体指什么样的愁苦?指谁的愁苦——骷髅还是妇孺?下面又有“识破个羞哪不羞”句。识破什么?这些黄公望都没有明说,仅是点到为止式的暗示。但是黄公望以全真道士身份评介《骷髅图》,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及其弟子谭处端等关于骷髅的诗画创作。
王重阳主张性命双修的修持方式,提出“凡人入道,必戒酒色财气、攀援爱念、疑愁思虑,此外更无良药矣。”为了让弟子能戒去色心,蠲除爱欲,王重阳曾多次画《骷髅图》并赋诗词以警示门人。如其作《警丹阳夫妇》诗劝导二人抛开爱欲,遁入道门:“堪叹人人忧裹愁,我今须画一骷髅。生前只会贪冤业,不到如斯不肯休。”现存《重阳全真集》、《重阳教化集》等诗文集中还收有其《自画骷髅》、《画骷髅警马钰》、《叹骷髅》,《骷髅歌》等一批与骷髅或《骷髅图》有关的诗作。
在今山西芮城全真教祖庭永乐宫的重阳殿内东、北、西三壁绘有《王重阳画传》,共五十组图。其中西壁上有一幅被命名为《叹骷髅》的图像。画面中央绘一年长男子面朝右方坐于松下石上,左手提一幅骷髅画立轴,右手指画,作解说状。此应为王重阳。下面右边立有一男一女,抱拳拱手,神态虔敬,在认真倾听年长者讲道。左边亦立有一男一女二人,女子手提瓦罐,可能是仆从。这即是全真教祖借《骷髅图》劝道说法的场景再现。

▲永乐宫重阳殿壁画叹骷髅(局部)
另全真七子中的谭处端在接引弟子时也曾如法炮制,自作骷髅诗画以启悟后学。如《骷髅歌》云:
骷髅骷髅颜貌丑,只为生前恋花酒。巧笑轻肥取意欢,血肉肌肤渐衰朽。渐衰朽,尚贪求,贪财漏罐不成收。爱欲无涯身有限,至令今日作骷髅。作骷髅,尔听取,七宝人身非易做。须明性命似悬丝,等闲莫逐人情去。故将模样画呈伊,看你今日悟不悟。
这首歌谣可能于警示世俗、劝度后学的宗教实践活动中演唱,据“故将模样画呈伊”一句推测,演唱时可能配套有骷髅图的展示,甚至有可能是边唱边画的宣教形式。范德裕曾形容谭作“骷髅落魄歌警悟世人,皆包藏妙用,敷畅真风,引人归善,甚有益于时也。”
全真教认为俗世之人无非是“白为骸骨红为肌,红白装成假合尸”。他们画骷髅图,作骷髅诗就是要警示教徒死生无常,想要羽化登仙,必须净心修炼:“欲要心不乱,般般都打断。子午卯酉时,须作骷髅观。”

▲叹骷髅(局部)
全真教这种视生死为自然的观念显然是源于老庄的。徐琰在《广宁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师道行碑》中讨论全真教与道家的关系时说:
道家者流,其源出于老庄……迨乎金季,重阳真君不阶师友,一悟绝人,殆若天授,起于终南,达于昆仑,招其同类而开导之,锻炼之,创立一家之教,曰全真。
《庄子·至乐》中所谓“叹骷髅”的寓言即反映了这种“齐生死”的观念:
庄子之楚,见空髑髅,髐然有形,撽以马捶,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故及此乎?”于是语卒,援髑髅,枕而卧。
夜半,髑髅见梦曰:“子之谈者似辩士。视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庄子曰:“然。”髑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髑髅深矉蹙頞,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劳乎!”
庄子在此设计了一个“左右互搏”的文字游戏。一方面,让“庄子”直接出场,扮出一副伤逝悼亡的脸孔,以生人之心悲死者之苦;另一方面,又借骷髅之口,托梦“庄子”,畅言离世之乐,在世之苦,断然谢绝“庄子”使之复生的好意。这是“庄周梦蝶”与“濠梁之辩”的复合:“枕髑而卧”的“庄子”与“梦蝶”时一样,穿梭于梦醒之间,不过这里的梦境与现实又和生死产生了究竟是人生如梦,抑或逝者如斯;生与死到底哪个才是人之本质存在方式?“叹骷髅”的“庄子”也与在“濠梁之上”的“庄子”一样,本想居高临下地劝教别人,不想反掉进了对方的逻辑陷阱。庄子让骷髅罗列在世的种种劳苦与牵绊,旨在说明生无需欣喜,死亦未必可恶,阐述了人之生死相通的道理。
《列子·天瑞》篇中,录有一条列子与弟子百丰关于骷髅的议论:
子列子适卫,食于道,从者见百岁髑髅,攓蓬而指,顾谓弟子百丰曰:“唯予与彼知而未尝生未尝死也。此过养乎?此过欢乎?种有几:若蛙为鹑,得水为藚,得水土之际,则为蛙蠙之衣……燕之为蛤也,田鼠之为鹑也,朽瓜之为鱼也,老韭之为苋也……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久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
这一故事套式显然借鉴于《庄子·至乐》,所要传达的“未尝生未尝死”的“齐生死”观,也源于庄子。不同的是,庄子是通过比较“生之累”与“死之乐”来论证生死无别,甚至“生不如死”;列子则敷衍“万物化生”的脉络,推导出近似于“生死轮回”的结论。
汉魏以降,玄老日盛。玄风熏染下,出现了一系列的骷髅母题的文学作品,表现了深邃的人生哲理思辨。东汉张衡撰《骷髅赋》,大致敷衍《庄子·至乐》而成篇。张衡索性以庄子充当骷髅,抒发“死为休息,生为劳役”的感叹;倡导“不行而至,不疾而速”的治世观。明代孙绪《无用闲谈》中评论道:“张衡《髑髅赋》,大率出于庄子马捶之问……如此类甚多,几于抄写《南华》全文矣。”三国魏曹植作《髑髅说》强调生前的努力奋斗,反对坠入冥冥空想而虚度平生。西晋的左思亦有《髑髅赋》。他们的思想大抵与庄子一致,都反映了不肯对现世妥协、无拘无束的逍遥心态。有所不同的是略晚于曹植的三国魏吕安的《髑髅赋》:
踌躇增愁,言游旧乡,惟遇髑髅,在彼路傍,余乃俯仰咤叹,告于昊苍,此独何人,命不永长,身销原野,顾曝大荒,余将殡子时服,与子严装,殡以棺,迁彼幽堂,于是髑髅蠢如,精灵感应,若在若无,斐然见形,温色素肤,昔以无良,行违皇干,来游此士,天夺我年,令我全肤消灭,白骨连翩,四支摧藏于草莽,孤魂悲悼乎黄泉,余乃感其苦酸,哂其所说,念尔荼毒,形神断绝,今宅子后土,以为永列,相与异路,于是便别。
这里的骷髅似乎还留恋尘世,未看破世间的各色欲望。
现在我们反观黄公望的那首小令,显然也是寄寓了类似的“齐生死”的观念的。所谓“苦和愁”可以是《至乐》篇中的“生人之累”、张衡所谓的“生为劳役”抑或曹植笔下的“劳我以形,苦我以生”;也可以是吕安感喟的“四支摧藏于草莽,孤魂悲悼乎黄泉”。不论生死,只要还存“我执”便有愁苦。所谓“识破”便是“把从来恩爱眷恋,图谋较计,前思后算,坑人陷人底心,一刀两段去。又把所著底酒色财气,是非人我,攀缘爱念,私心邪心,利心欲心,一一罢尽。外无所累,则身轻快,内无所染,则心轻快,久久纯熟,自无妄念……尘垢净尽,一物不留……自然显露自己本命元神,受用自在,便是个无上道人也。”也就是实现了庄子所谓“逍遥无待”的境界。
黄公望在小令里还描述了画面中“傀儡儿还将丝线抽,弄一个小样子把冤家逗”的情景。“傀儡”在宋代以前可以写作窟儡、窟磊、魁儡、魁垒等。陈志良曾提出“傀儡”发音不像汉语,可能“是外来的语言,不是我国原有的名称。”日本学者盐谷温也认为“傀儡”是译音。但常任侠很早就曾指出,作为后世门神之一的郁垒,与傀儡、畏累,发音相近。之后,邢公畹亦论证了“傀儡”是汉语中的一个双音节词,与“鬼”或“鬼魂”同源,不是外来语的音译。康保成则认为“傀儡”与“骷髅”应为一音之转,其共同的来源是“髑髅”,先秦时已普遍使用。所以“傀儡儿”即是指大骷髅。“小样子”当然是大骷髅手中的提线小骷髅。
大骷髅所逗的“冤家”则是画面中央匍匐的婴孩了。“婴孩图”是宋代风俗画中一个颇为流行的主题,后来发展为“百子图”,寓有“多子多福”之意,为民间所喜闻乐见。故亦有藏家和研究者将《骷髅幻戏图》归入“婴孩图”一类。但是从道教修炼的角度来看,“婴孩”(或称“婴儿”)则有着特殊的含义。
在道教外丹派中,“婴儿”是炼丹隐语,指炼丹用的铅;与其相对应的“姹女”是指炼丹用的汞。如五代崔希范《入药镜》彭好古注:“婴儿者,金也,水也,情也;姹女者,木也,火也,性也。”他们认为二者交合,乃结圣胎,服用后即能成仙,即所谓:“姹女妖娆性最灵,婴儿二八正青春,黄婆媒合为夫妇,产出明珠无价珍。”在内丹道教中,这两个词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婴儿”借指人之情,“姹女”指人之性。与之相关的还有“结胎脱体”,指“姹女”、“婴儿”交合后,精气神合炼,即结金丹,结圣胎,修炼成仙。南宋周无所《金丹直指》:“结胎脱体,譬超凡入圣之意。但能心不附物,神归气复,所谓换结圣胎;抱养月深,神金气化,所谓脱体也。”
全真教七子之首的马钰作有《示门人》诗解释得最为明白:“夫大道无形,气之祖也,神之母也。神气是性命,性命是龙虎。龙虎是铅汞,铅汞是水火,水火是婴姹,婴姹是阴阳,真阴真阳即是神气。种种异名,皆不用着,只是神气一字。”另外,在内丹派看来,精气神三者,先天本是一体,后天分而为三。生人是一生三,而成仙则必须从三返一。《悟真篇》云:“三家相见结婴儿,婴儿是一含真炁,十月胎圆入圣基。”刘一明解释说:“和合四象,攒簇五行,则精气神凝结,曰三家相见,名曰婴儿,又曰先天一炁,又曰圣胎,又曰金丹。”所以“婴儿”往往亦指“圣胎”,即由三返一的纯阳之体,也是老子所谓“复归于婴儿”的状态。这个意义的“婴儿”有时也被称为“童子”。陈抟即以童子来喻说太虚的境界:
浑浑沦沦,不知不识,童之体也;太虚无为,莫滞莫著者,童之用也;春风秋月,霭乎可亲者,童之品也;纯纯穆穆,毫垢胥捐者,童之量也……惟能保章之相,乃能辩理欲关头;惟其还此童之质,始得判仙凡界限。似在心,心失养便非童;理寓玄,玄不悟难云童。
《骷髅幻戏图》中将骷髅与婴孩并置,从道教的角度看或许也是其修炼理论的一种图示。在孙凤编《孙氏书画钞》中收录一篇《题李嵩画〈钱眼中坐骷髅〉》的画跋,撰人不详。原文作:
尘世冥途,鲜克有终;丹青其状,可以寤疑。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嗜物不衰。顾青草之委骨,知姓字之为谁?钱眼中坐,堪笑堪悲。笑则笑万般将不去,悲则悲有业相随。今观汝之遗丑,觉今是而昨非。
此跋虽未对画面内容做出具体交代,但指出李嵩此画的创作目的是寤疑辨惑,令观者睹画警醒,不可贪得无厌,自遗其丑。这也可从旁证明李嵩的骷髅画往往是含有劝解意蕴的。
二、《骷髅幻戏图》与佛教“白骨观”、“骷髅法”
前引吴来庭《李嵩骷髅图跋》先说李嵩擅长工笔人物画并特别强调“佛像尤绝”,接着声称“观其《骷髅图》,必有所悟”,原因是本图“能发本来面目意”。吴氏显然是在佛教语境下解读《骷髅幻戏图》的。这说明至迟在吴来庭所处的时代关于此图的接受中,已蕴含有佛教思想因素。至于佛教思想是否李嵩《骷髅图》的“本来意”,则是下文要论证的。
按佛教有所谓“白骨观”,为五门禅法之一。通常由不净观、白骨观、白骨生肌和白骨流光四部组成,主要目的是熄灭对色身的贪恋。“白骨观”是将人观想成一具白骨,如《禅秘要经法》记载佛陀教诫阿难:
(白骨观)当自观身作一白骨人,极使白净,令头倒下,入胯骨中。澄心一处,极使分明。此想成己,观身四面,周匝四方,皆有骨人……乃至见于无量无边诸白骨人,纷乱纵横,或大或小,或破或完……谛观是己,当自思惟,正有纵横,诸杂乱骨,何处有我,及与他身。尔时行者,思惟无我,身意泰然,安隐决乐。
在这种观想禅法的支持下,佛教常常利用骷髅或骷髅形像来说法、度人。如《增壹阿含经》卷二十描述释迦牟尼在世时,就曾反复“取死人髑髅授与梵志”,问其“此是何人髑髅?为是男耶?为是女乎?复由何病而取命终?”等问题,借用髑髅来演说“人死因缘”,劝教鹿头梵志勤修精进,以期实现“生死已尽,梵行已立”的至高境界。
佛教美术文献中也经常出现骷髅形象。据《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记载,佛祖曾嘱咐给孤独装饰施园时“于房内应画白骨髑髅”。在印度佛教和藏传佛教中,许多金刚、明王的造像佩戴有骷髅头串成的项链或头饰,或者手持嘎巴拉(Kapalas)。所谓“嘎巴拉”即梵文“骷髅杯”,用人头骨制成,为佛教仪式中的一种法器。如《佛说妙吉祥最胜根本大教经》中描述六面十二臂的焰鬘得迦大忿怒明王即是“左第一手执髑髅。”并且依照执行的仪式不同,嘎巴拉中盛放的内容亦不同:或“以髑髅满盛输尼帝”、或“用摩贺嚩舍安髑髅内”、或“以药丸安在髑髅内”、或“用自死童女头发,合发为索,于黑月八日安髑髅中”。甚至大忿怒明王像本身就有用人骷髅雕造的,据说有了这种造像,“持明者不须法事精熟,但一向供养能成就一切事”。
汉传佛教中,也存在许多骷髅图像。20世纪初德国探险家在新疆发现了大约为公元500年前后的绘有骷髅的绘画作品,其后斯坦因在吐鲁番地区的壁画中又发现了绘于公元6-8世纪的骷髅形象。这些大多出现于佛教石刻或壁画之中的骷髅,无疑是随着佛教艺术一同被传播到中国来的。在现存佛教壁画,如《众魔怖佛》、《明王像》、《尸林修行图》等作品中,所描绘的主要是骷髅的形象,具有明确的宗教象征意义。
由于同以骷髅主题来表达对生死苦乐的思考,佛教的“白骨观”渐与老庄的“齐生死”观产生了杂糅;甚至借助老庄传统下的“叹骷髅”文学母题来宣说释家的生死观。至迟到宋代,骷髅主题的佛教讲唱文学作品已在世俗中流行。刻于明万历二十九年的宋代宝卷《叹世无为宝卷》中附有《叹世警浮清音之同骷髅二十一首》,其中第一首以“叹骷髅”开头,篇幅比较长:
叹骷髅,七尺骷髅资易悭;贪财宝,出息难期入息。十方男女休怪我,谁知苦口是良药。这骷髅是死骷髅,睁眼喘气活骷髅……
其他各首均以“骷髅儿,叹你”开头,格式整齐:
骷髅儿,叹你,不知僧骷髅、俗骷髅,或是宰相共王侯。或是男骷髅、女骷髅,荣华富贵做骷髅,百年光景如捻指。骷髅儿,今朝一日无常到,骷髅儿,问你,真人真人在那里?
这宝卷明显是在宣扬佛教“白骨观”。“白骨观”在宋代文人中亦较有影响。如苏轼写有《惠州祭枯骨文》,其中言道:“尔等暴骨于野,莫知何年……但为藂冢,罕至全躯。幸杂居而无靡争,义同兄弟;或解脱而无恋,超升人天”。其诗《髑髅赞》云:“黄沙枯髑髅,本是桃李面。而今不忍看,当时恨不见。业风相鼓转,巧色美倩兮。无师无眼禅,看便成一片。”文与诗都是承《庄子·至乐》“叹骷髅”的题材而来,但内里的宗教思想却发生了变化。文中祈祷枯骨“超升人天”;诗中劝诫人们要警惕美色的诱惑,要具“无师无眼禅”。这些都是佛家思想的表现。以上材料均说明在宋代“叹骷髅”题材的文艺作品中已经渗入了佛教因素。
那么,在这样的宗教文化氛围中,《骷髅幻戏图》的绘制包含有佛家义理,甚至就是为弘法提供形象教材也是很有可能的:世人不过具有一副“臭皮囊”,终究要化成一具骷髅。或许画面中的妇人与大骷髅;婴孩与小骷髅恰构成相互对应的关系,用以警示观者人生无常,四大皆空。
另外,《骷髅幻戏图》的画面内容,主要是表现以骷髅做戏——让僵死的骸骨如生人一般活动起来。这一点与佛教中的所谓“骷髅法”十分相似。前文提及骷髅杯是用于佛教仪式中的法器;“骷髅法”亦是佛教,尤其是密宗的一种以骷髅为主要法器的宗教仪式。《千光眼观自在菩萨秘密法经》记“髑髅法”云:“若人欲使令一切鬼神者,当作髑髅法。其缚鬼观自在菩萨像,相好庄严如前所说。唯右手执髑髅杖,左拳安腰。画像已,其印相左拳安腰。右手屈臂举上作金刚拳,以印作召势。”《佛说妙吉祥最胜根本大教经》卷三所记更为详尽:
今说髑髅,须用左手执捉加持。持明者用木作一髑髅,广阔二十指。修事圆满,以香花饮食等如法供养,及随力作护摩已。然后以左手执于髑髅,以右手覆之,即诵大明,至髑髅出现光明。得上品成就为三界主。若出烟焰得隐身法,若髑髅暖热所求随意。若法不成,以此髑髅安木床上,用以帛盖覆已,观想种种,上味饮食,满彼髑髅,复诵大明八千遍已。日日以上妙饮食贮满髑髅,经宿加持已,取彼饮食,此名“甘露食”,若人食者,除诸病苦,获大安乐。若行人自食,身心适悦,永无病苦。
而《大佛顶广聚陀罗尼经》则分类说明了于尸陀林中对骷髅念诵经咒使其显灵复活的种种咒法。卷二云:“入尸陀林,取新死人未烂坏者”作法,“咒白芥子,散着尸陀林四方,其诸髑髅并皆作歌舞”。卷五记,用男子“髑髅七枚……清净洗前髑髅庄严,着眼鼻孔齿并须如法。次第着行坐,取前香烧供养。勿令人见,于深密处作之。欲驱使时,烧香咒二十一遍,即着髑髅,自行动转开门出去”,卷四则言咒师于尸陀林“烧林作舞,唱歌而走”,就能让“一切髑髅,自然相打”。甚至“于死尸骸骨边诵咒”可使“其骨化为人,起立作舞”。
按照常识,骷髅或者尸骸是不可能复活的。佛经当中这些关于“骷髅法”的记载,很可能是在做法时通过某种操控机关一类的办法使骷髅活动起来。这大概就是李嵩所绘骷髅戏的前身,而骷髅戏的表演在当时有可能和变文讲唱一样,是佛教于俗世弘法的一种“寓教于乐”的手段。因此,从画面内容的角度看,《骷髅幻戏图》亦与佛教世俗化的民间弘法实践有关。
三、“《骷髅幻戏图》寓意求子”质疑
清人陈撰《玉几山房画外录》记录《骷髅幻戏图》云:“《骷髅弄婴图》。骷髅而衣冠者众见,粉黛而哺乳者已见也,与儿弄摩侯罗亦骷髅者,日暮途远,憩五里堠者,道见也。与君披图复阿谁,见一切肉眼作如见观。”有学者认为陈氏所谓“摩侯罗”即是宋代的“磨喝乐”,寓有求子的期盼。进而推断李嵩的《骷髅幻戏图》描绘的是七夕乞巧的一个场面。笔者以为这种判断是值得商榷的。
“磨喝乐”是一种土偶,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对此有记载:
七月七夕,潘楼街东宋门外瓦子、州西梁门外瓦子、北门外、南朱雀门外街及马行街内,皆卖磨喝乐,乃小塑土偶耳……七夕前三五日……小儿须买新荷叶执之,盖效肇磨喝乐。儿童辈特地新妆,竞夸鲜丽。至初六日七日晚,贵家多结彩楼于庭,谓之“乞巧楼”。铺陈磨喝乐、花瓜、酒炙、笔砚、针线,或儿童裁诗,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谓之“乞巧”。妇女望月穿针。或以小蜘蛛安盒子内,次日看之,若网圆正,谓之“得巧”……又磨喝乐本佛经‘摩睺罗’,今通俗而书之。
这里有三点需要注意:
第一,磨喝乐是用来买卖的,其形制是由土塑的小偶形象。
第二,磨喝乐具有乞子功能。
七夕“乞巧”节有求子的风俗。古人意识到妇女怀孕需要“碰巧”,所谓“乞巧”本意是在求子。《开元天宝遗事》卷下载“蛛丝乞巧”条云:
帝与贵妃,每至七月七日在华清宫游宴。时宫女辈陈瓜花酒馔列于庭中,求恩于牵牛、织女星也。又各捉蜘蛛闭于小盒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
明嘉靖福建《建阳县志》载:
七夕乞巧,是夕儿女罗果酒于庭,拜祝牛女星。取小蟢子以盒盛之,平明启视,成茧者为得巧。
由这些仪式可见,七夕乞巧节是一种象征性的求子仪式。宋代话本《碾玉观音》中有一段文字:
郡王……实时叫将门下碾玉待诏道:“这块玉堪做甚么?”……又一个道:“这块玉上尖下圆,好做一个摩侯罗儿。”郡王道:“摩侯罗儿只是七月七日乞巧使得,寻常又无用处。
说明磨喝乐是专用于七夕乞巧节的。
第三,在宋代民间往往把“磨喝乐”与佛教“摩睺罗”混为一谈。这也是一些学者将二者等同的依据。实际上,二者是截然不同的。
所谓“摩侯罗”,梵文称Mahoraga,是印度神话中一个人身蛇首的蟒神。传入中土后,形象发生了一些改变。南宋画家郑思肖《心史》卷下《大义略序》记述了这尊神道的造像:
幽州建镇国寺,附穹庐,侧有佛母殿……后又塑一僧,青面裸形,右手擎一裸形小儿,赤双足踏一裸形妇女,颈擐小儿枯髅数枚,名曰摩睺罗佛。
这显然和土偶“磨喝乐”的形象大相径庭。此佛“颈擐小儿枯髅数枚”,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人们亦将小儿骷髅称为“摩睺罗”。
又董每戡先生提出:“由于‘摩睺罗’与‘罗睺罗’读音接近,不熟悉佛教的人们便将二者张冠李戴,以讹传讹,致使‘摩睺罗’冒名顶替了‘罗睺罗’。罗睺罗倒鲜为人知了。”
“罗睺罗”,梵语叫做Rahula,是悉达多之子,后亦随佛陀出家,道业极高,被尊为“密行第一”。据《酋阳杂俎续集》卷五载:“道政坊宝应寺……有王家旧铁石及齐公所丧一子,漆之如罗睺罗,每盆供日出之寺中。”“盆供日”就是指盂兰盆会,即农历七月十五的中元节。如果董先生的推论正确的话,《骷髅幻戏图》倒有可能是一幅中元节剪影。又中元节与七夕节日期邻近,“罗睺罗”、“摩睺罗”、“磨喝乐”读音相似,久而久之,民间便将它们混用了。但是陈撰这里“摩侯罗亦骷髅”的解释,还是用的“摩睺罗”的佛语原意,可见他还是将这幅图解读为含有佛教意蕴的作品的。这种小骷髅的造型在佛教中或有特别含义,但绝不是民间乞巧节用来乞子的道具。
要之,李嵩《骷髅幻戏图》的创作及传播与接受背景,既有道教视生死如自然的生命观的影响,亦有佛教白骨观的因素,可以说是南宋以降,宗教世俗化,甚至释老出现合流的宗教现象在美术史上的一个缩影。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