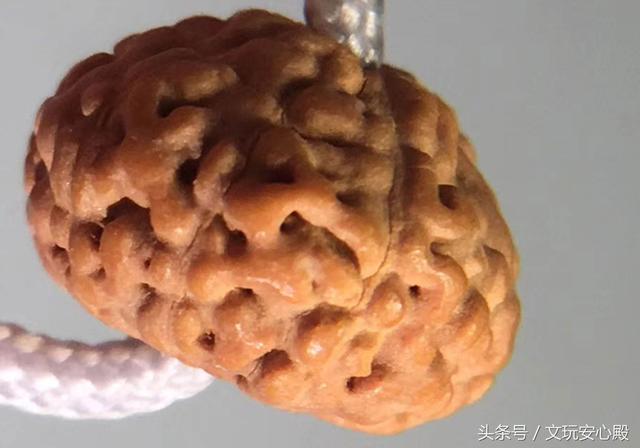知青时代的地主(泪流之后是刚强)
泪流之后是刚强
胡光
南开中学1968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8月16日从天津赴黑龙江省德都县(现五大连池市)永丰农场(现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五大连池监狱)生活了五年。之后调入黑龙江省黑河地区农场管理局工作队,进驻长水河农场,最终留在长水河农场工作,前后又是一个五年。十年的北大荒生活,是我人生的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

2004年九月中旬,我三十余年前下乡所在的黑龙江省长水河农场党委书记、场长和部分职工代表千里迢迢来到天津,看望天津知青,与我们欢聚,纪念天津知青下乡三十五周年。其间,我写下一首诗,在二百余人的联谊会上,献给了北大荒农场领导和乡亲们:
《思 念》
思念于羞涩的青春
已成为矜持的中年
从沉静朴实的黑土地
走到喧嚣浮躁的都市
或许这不是世界上
最长最长的思念
但它的确很纯很真
纯真的如塞北冬日飘下的
第一片晶莹剔透的雪花...
思念是浓浓的又苦又香的咖啡
思念是对苦难中真情的摄影
思念是我的不醒的梦境
思念是对昨天的永久收藏
三十八年过去了,农场生活的许许多多的情景我始终未有忘却,我在此节选了下乡十年间我五次流泪的经历,作一记叙。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我的这五次流泪的背后,都是一件件真实的故事……
第一次流泪
1969年8月18日,我和南开中学一百二十多名同学来到永丰农场十二连(南阳良种站),我时任十二连副连长。起初,我们连队吃饭是“包伙”,即每人每月从三十二元工资扣除十二元作为伙食费,男同志每人每月配给口粮32斤,女同志每人每月30斤,饭菜不限量,吃饱为止。由于每日劳动强度大,我们这些人又正值十六岁至二十岁之间能吃的年龄,因此没过几个月,食堂收支出现严重逆差,亏损很大。而农场当年受洪涝灾害影响,粮食产量大幅下降,需要吃国家调拨的“返销粮”,不能给予我们补贴,因此这种吃饭形式不得不终止。当时,在每人每月定量的口粮中有一部分是稗子(草籽),一部分是用发了芽的麦子磨出的面,很难吃。冬天来了,最冷的温度在摄氏零下四十几度,高寒和极大的劳作强度配伍,严重消耗着每个人的热能,于是饥饿凶神恶煞一般地扑向了我们……“胆大”的同志从打谷场院“偷”些玉米,黄豆,从菜窖“偷”来土豆充饥,“胆小”的同志干熬着……我时任副连长,劳动、工作要处处带头,虽然饿得很,但必须自律。我身高一米八四,体重只有一百二十斤,瘦瘦的,常常饿得夜里睡不着觉……有一天,我去牛号(牛棚),无意间发现草料槽子下面稀稀拉拉散落着一些豆饼渣儿,有的和地面冻在了一起。这些豆饼渣儿极大地诱惑着我,我弯下身来用手抠,用手划拉,最终手里有了一捧豆饼渣儿。我把它放在旁边屋里的铁炉盖上烤,待到有了七八分熟的时候,把它放进嘴里,艰难地咀嚼着,而后又艰难地徐徐咽下,但又觉得很香很香……第二天,由于不消化,我胃口疼,去了卫生所,不得不向医生说了实情……赵大夫(当地职工、南阳良种站党支部书记、后调苏家店农场任场长的唐子坤夫人),这位四十多岁的阿姨,马上回家给我捧来几个熟土豆,我推辞不过,土豆热在手里,暖在心上,望着赵姨那慈祥善良的面孔,我忍不住眼泪滚了下来……不久,连队的女同志们纷纷捐出一些粮票,支援男同志。我本人先后曾经得到张琴、张敏、周敏、刘虹锦、刘秀莲、穆瑞兰、张荣珍、张荣华等同志的热心帮助。患难之中见真情,我一辈子不会忘记这些老大姐。后来,随着农场粮食生产的不断发展,随着每人粮食定量的增长,以及连队想方设法改善伙食,饥饿现象逐步改善……
第二次流泪
1972年冬,是北大荒最寒冷的一季。有一天,我和一些同志上夜班,进行脱谷劳动。我们先把从地里收获的豆秸均匀的铺在场院上,然后用履带式拖拉机将铺得满满的近一米高的大豆秸压来压去,我们随后用木叉将豆秸挑去,将地面留下的豆粒堆在一起。凌晨两时许,拖拉机突然停止了轰鸣,一检查,原来温度太低了(零下四十多度),把高标号的耐冻的柴油都凝固住了。尽管我们用力干活儿时不觉什么,甚至身上出汗,但停下手来没多久,手、脚就没有什么知觉,冻僵了。我看到拖拉机无法再启动,就让大家收拾一下场院,提前下工回到宿舍。从冰天雪地里进到暖暖的宿舍,一身寒气逐渐退去。但没过多久,忽然我的手脚有一种回暖异样的刺痒,那刺痒又渐渐转为疼痛进而恶心……我站立不安,静卧不成,又不好意思呻吟喊叫,陡然眼泪禁不住流下来……由于在1969年底和1970年初,我曾暂短调场部武装民兵基干连,在一次军事演习之夜,脱下自己的棉鞋为跑步丢掉鞋子的上海知青洪东升穿上,脚有冻伤,加上这次夜里干活冻伤,多少年后,我的一只脚终于留下后遗症:无论冬夏春秋,两只脚总是一热一凉,好像记录显示着那些身遇高寒的经历……
第三次流泪
1969年8月,我下乡时还只有十七岁。承蒙组织的信任培养,我担任副连长。连长、指导员、副指导员都是我们学校高中一年级的大哥大姐。在那年月,我们都能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劳动、工作、学习走在前。很快,指导员和连长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三位同志于1972年选调回天津,分别上大学和中专。1974年初,党组织准备发展我入党,支部党员大会上,全体党员表决一致同意我的入党申请。但万万没想到,农场党委认为我的出身有问题,没有批准。党支部领导很关心我,细致地做了我的思想工作,鼓励我经受考验。虽然我内心有些想法,但我还是没闹情绪,更加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工作劳动。1974年10月,党组织把我送到黑河地区农场管理局培训,后又随局工作队进驻长水河农场。这期间,我因出色的工作成绩和表现被任命为分队小队长、办公室主任、副分队长,并评为工作队优秀干部。我的事迹被农场管理局以简报形式发放给各农场进行表彰宣传(1986年,冯骥才先生搜集“文革”资料,我将此简报和一些书信、在南开中学时的红卫兵袖章一同送给了冯先生)。1975年2月,工作队党组织又讨论了我的入党申请,又是全体党员一致同意我入党。当长水河农场党委和局工作队党委研究我的入党申请时,又以我的出身问题查不清而未能通过。当组织转达党委意见时,我内心十分痛苦。想一想,我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废寝忘食拼命地工作,想一想和我一块下乡的同学许多人早已入了党,并且回城上学,我心中充满委屈、不平……我的入党介绍人江家骅(北安农场革委会副主任、工作队分队长、党总支书记、上海知青)和黄作存(北安农场老干部、分队党总支委员)给了我许多真诚的温暖鼓励、帮助和引导。这些领导十分同情我、理解我,又很无奈。最后,决定送我回城上大学。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面对组织对我的关怀,思绪逐渐平静下来,考虑很久,谢绝了回城上学的机会:
这是因为:一、我的大妹和我一起下乡在永丰农场,1975年夏她同南阳部分知青调往新开垦的建边农场,条件非常艰苦。我不能丢下大妹,让她孤苦伶仃地留在北大荒。二、我和一些知青干部在组织和广大知青面前发出了“扎根边疆一辈子”的誓言,不能失信。三、我虽然暂时不能加入党组织,但不能丢掉自己的信仰。我下决心继续经受党的考验,坚信我的人生志愿终会有一天实现。针对上述想法,在现实年代,可能有不少人感到不可思议!但是这些想法,的确是我当年在那个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真实反映,也是某种程度的身不由己……
我的出身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据我父亲讲,我的祖父系国民党政府在云南一偏远小镇盐务所的普通职员,因稽查武装走私盐贩,和盐贩形成尖锐矛盾。有一天,走私盐贩们得知盐务所长要出门去省城,就在半路埋伏,欲射杀所长。不凑巧,我祖父与所长相貌相似,当祖父送所长上路时,走私盐贩们误以为祖父是所长,开枪击中了祖父的大腿动脉,流血不止,祖父不治身亡。党委讨论此事时,有“是不是走私盐贩?或许还是共产党游击队呢?单凭亲属说不能为证。”的意见,所以还是以问题不清,没有通过我的入党申请。其实,祖父去世时,我父亲才15岁,底下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在旧社会,他们拾破烂儿,捡煤核儿,当饭馆跑堂的,什么苦都受过。退一步讲,祖父即便有问题,与我这个未曾谋面的孙子又有何关联?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时代,因“出身不好”在政治上受株连的绝不止我一人矣。
1975年9月,局工作队撤离之前,长水河农场党委和工作队党委再次开会讨论我的入党问题。长水河农场党委书记王文章同志(后任北安农场管理局常务副局长)在会上表态:“如果不让胡大个子这样的好青年入党,我们的政策哪里去了?也没法和他交代,他的出身问题一辈子查不清,他就一辈子入不了党了么?”这一掷地有声的话在尚处文革时期,实难能可贵。几经周折,党委终于批准了我的入党申请。当我得知喜讯时,我跑到野外,面对空旷茫茫的天地,一个人痛痛快快的大哭了一场……
第四次流泪
1977年春节,我和长水河农场北岗的几十名未返城探亲的知青坚守在工作岗位上。这其中的一位天津女知青张秀玲(因家中姐妹排行第四,朋友们都称她“四玲子”)感冒发烧,卫生所医生开了“合霉素”让她服用,但高烧几天不退。我安排人陪她到场部医院就诊,医生让赶快转北安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医院,随即她被诊断为“再生障碍性贫血”。病情危急!消息传来,我带着两名女知青和两名男知青去医院守护。此病需输血,我是O型血,便毫不犹豫地和另外一名男同志各输了200cc血。我把医院给我的四十元输血补贴费交给同志们,为四玲子买了营养品。晚上,我让两名女同志在女病房守护,让另外两名男同志在医院附近的旅店休息,而我则选择在病房走廊守候。走廊没有椅子,我就背靠墙壁蹲在地上。深冬寒夜,献血后的虚弱使我困乏不堪。第二天早上,病房护士对我们连队的同志说:“你们这个病人的男朋友真够意思,他昨天刚刚输了血,夜里在走廊里又冻了一宿,一直没有离开。”同志们说:“他不是她男朋友,是我们的指导员”护士听了十分感动,请示了领导,专门为我安排了一张空闲的病床,让我休息了一下。因一师医院治疗条件有限,我们又抬着担架护送四玲子坐火车到八百里外哈尔滨市医大附属医院继续救治。但四玲子的病情急转直下,生命垂危。根据规定,医院不允许我们守候重症病房内。四玲子两只眼睁得大大的,脸色蜡黄,用手紧紧攥着我的手,不让我离开病房。医生见此情,破例让我一个人坐在她床前守候。四玲子用十分微弱的语音自言自语地说:“我太年轻了……”又对我说:“指导员你多保重!”稍后她的呼吸突然急促起来,我连忙喊来医生,对她进行抢救。在医生为她做人工心脏按摩时,由于钢丝床太软,按摩效果不好。医生让我钻到床下,用后背使劲儿往上顶。大约半小时后,医生见四玲子已无法救治,便停止了按摩。我从床下钻出来时,四铃子已经完全没有了呼吸……四玲子遗体火化时,我们一直守候在火化间门外。当工作人员捧来一个白色盘子,将骨灰送到我手中时,骨灰尚微微烫手。患难之中朝夕相处的知青战友四玲子带着对生命的渴望,带着知青战友间兄弟姐妹般的感情离我们而去……我们把青春留给了北大荒,而四玲子把生命留在了北大荒……我端着盘子的手颤抖着,望着灰白色的四玲子的骨灰,我泪水不停地淌下来……
第五次流泪
1979年1月,农场近万名来自上海、天津、哈尔滨、黑龙江省内地的知青绝大部分相继返城了。我所在的分场,有一名青年和当地女子结了婚,无法回津,另一位男青年还在办理返津手续。我当时的思想充满彷徨,困惑。在家中母亲焦急地接连二三的书信催促下,我也随波逐流选择了“病退”返城。当我拎着那绿色的军挎包要告别北大荒,告别父老乡亲们的时候,我的心境异常复杂,鼻子酸酸的……分场老书记张占奎和一些乡亲们送我老远老远,望着他们那善良黝黑的面庞,我胸中涌动着艰苦环境中结成的深深的割舍不断的感情,终于按捺不住哇的一声哭出来,有的乡亲们也哭了……我再也不敢多看他们一眼,头也不回地走了,带着对北大荒十年生活难以释怀的酸甜苦辣和父老乡亲们的深情眷恋……
泪流之后是刚强
我下乡十年,总共流过五回泪,每一次流泪都是一次本色感情的释怀;都是一次对人生的咀嚼品味;都是一次生活的积淀;一次精神的升华;一次意志品质的锤炼;泪流之后是不断的成熟和刚强。
我和我的千千万万的知青战友们,把青春埋在了黑土地,那是一段在特定条件下的难以忘怀的人生经历,我们的命运和共和国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经历是人生的财富,苦难是成熟的摇篮。在那难忘的岁月中,我们失去的和得到的同样珍贵……

胡光
作者:胡光,北大荒长水河农场天津知青,网名衔泥斋主人,退休于天津市公安局,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
来源:知青50年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