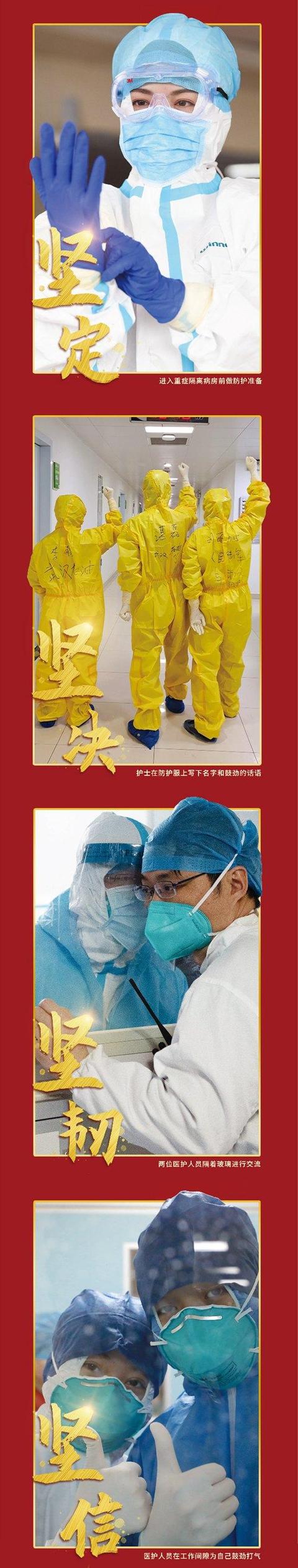现在大凉山贫困彝族人现状(为什么凉山接受了那么多捐助依然贫困)
本文只讨论依然贫穷需要帮扶的那部分彝族,脱贫攻坚的对象已经下山并受到良好教育,成功融入现代社会的那部分彝族不在讨论范围本文篇幅较长约12000字,从起源、变迁、社会结构、地理单元、风俗习惯、扶贫救助、教育、解决方案和展望等多个角度尽量给读者展现一个完整的大凉山彝族社会,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现在大凉山贫困彝族人现状?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现在大凉山贫困彝族人现状
本文只讨论依然贫穷需要帮扶的那部分彝族,脱贫攻坚的对象。已经下山并受到良好教育,成功融入现代社会的那部分彝族不在讨论范围。本文篇幅较长约12000字,从起源、变迁、社会结构、地理单元、风俗习惯、扶贫救助、教育、解决方案和展望等多个角度尽量给读者展现一个完整的大凉山彝族社会。
前言大凉山是非常典型的二元结构,也是全国地区结构的一个缩影。安宁河谷片区的几个县市与四川内地区县的差别不大,州府西昌的城建、商贸、消费、旅游跟成都郊县也差不多,年年也能进入全国经济百强名单,还有那恼人的四川第二高房价也仿佛不像一个边远地区。然而,离开州府西昌几十公里范围以外的大凉山彝区和更远一点的木里藏区,底子薄、基础差、经济社会不发达又是不争的事实,仿佛不是身处同一片天空。好在这几年国家扶贫力度非常大,从交通、住房、水电网络等基础设施硬件建设,到产业发展、技能培训、就业输出、教育医疗保障、再到禁毒防艾、治安整治、移风易俗这些软环境的打造和提升,国家、省和我们自己,都是做了非常多的事的,改变也在一天天地发生。
印象大凉山18年中旬在大凉山深处待了大概1个来月,对于彝族人有一些了解。我去的地方古天乐的学校已经建好了,自来水也有了,通了电,政府也给他们建了房子。
那村民一般做什么呢!出太阳的时候一群人在太阳下晒太阳打牌。下雨的时候在屋檐下聊家常。把一个穷人扎堆体会的淋漓尽致。和酒店老板开玩笑说他们日子过得怎么怎么安逸,老板说在那里你稍微勤快的种点土豆养头牛你就是村长。
还有彝族本身存在的思想问题,别人从来没想过怎么出人头地,混的好不好全靠拳头大不大。晚上基本上我连酒店大门都不敢出去,喝酒闹事打架的太多了。没有什么诚信道德可言,我们找了好久找了一个老爷爷过来做我们模特画画说了100一天,十一点说饿了,给他买了饭,一吃完说上厕所人就跑了。去到一个村部说给我们地址可以给他们寄衣服。村干部告诉我要寄你就寄新的。寄旧的村民会不高兴的。我脑海里瞬间就出现了一副几个村民骂骂咧咧在那里伟着一堆衣服说又是些旧衣服的场景。最后说一下其实彝族人织锦真的很好看。
“著名”的艾滋病之乡,这边的男士其实不是很多,各种原因吧。导致关系很混乱,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会往自己身体里注射艾滋,因为国家对于艾滋病人补助足够他们生活费。只是可怜了孩子,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
很干净也很不堪的地方,那边也有很比较好一点的。从来不洗澡,孩子大一点就会学汉语了。孩子去上学书包里就背一个碗,没有老师了老师跑了(也是看村来的),所以我这毕业多年的人,还站在讲台给她们上了俩节课。吃饭就土豆块米饭煮的像稀饭一样(样子参考我们90年代小时候喂猪的那种)东西不贵买了点零食给她们,他们父母居然给我送了一块比我脸还大的牛肉干。我们外面孩子都吃腻了的糖果巧克力是他们从来没有尝试过的宝贝。
和他们打交道多了,走的前一天问我们同行的一个女孩,姐姐你有妈妈嘛?姐姐你家里在哪里?女孩细细的告诉他们,我有妈妈,妈妈就在大山外面的家里,好好读书以后考上大学了就能去姐姐的家里那边看一看了。走的时候一直看着我们的车,内心真的无比的复杂。
离开后,我结合自己的所见,以及查询了一些资料,终于理出了一些头绪。为什么在物资如此丰富的时代,这里依然存在着广泛的贫穷?这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即不能简单的归结为一个懒字!
其实我想说句公道的话,有些人只站在他的那个角度来批评彝族人,根本不知道彝族人的真实状况,一个彝族人会流畅的说普通话交流最起码要6到8年,父辈些百分之八十没读过书,根本不知道怎么教育后代,教育落后导致观念落后,观念落后导致贫穷,一环扣一环。还有就是彝族社会一下子从奴隶社会到社会主义,这步子迈的太大,不是几年就能改变过来的,汉族从奴隶社会到社会主义中间还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直接跳过了封建社会,来到现代社会主义,中间差了很多东文化思想,得慢慢来。有些人看了凉山那边的情况,只知道骂,说彝族人不思进取,懒惰成鬼,嗜酒如命,确实也有很多人这样,但是也不全是这样,凉山彝族人需要批评,需要改变,但我一直觉得凉山彝族人更需要教育,唯有教育,才能改变思想,改变人生。
彝族的起源彝族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唯有史书上对彝族的源流问题没有系统的阐述,彝族的来源众说纷纭,主要有北来说、南来说、东来说和云南土著说等,因而,一百多年来,彝族的族源问题,就成为中外学者聚讼不休的问题。《彝族简史》一书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数所说:
第一,东来说 ;有人认为彝族先民原是楚国人,居住在洞庭湖流域。《左传·恒公十三年》载称:“楚屈瑕伐罗。”罗与卢两部联合起来大败楚军。后罗、卢两部随楚将庄蹻入滇,然后播迁西南各地,历史演变,即成为今日的彝族。新中国成立前彝族被称为“罗罗”,即“罗卢”的对音。
第二,西来说 ;有人认为彝族来自西藏,或来自西藏与缅甸交界的地区,语言和体质特点的相似,是彝族与藏族关系密切的明证。
第三,南来说 ;认为彝族祖先是古越人或古僚人。持此说者把《北史·僚传》所载僚人习俗归纳为18项,认为有许多项跟彝族的习俗有相同或相似的特点。持此说者有的甚至还认为彝族最初来自南方,属于马来人种。
第四,北来说 ;认为彝族祖先在远古时期原住在“旄牛徼外”,后迁到“邛之卤”,然后播迁金沙江南北各地。根据彝族的历史传说,其祖先在远古时代居住在“邛之卤”,后来才南下到“诺以”、“曲以”两水沿岸(即金沙江和安宁河流域)。古羌人便是彝族的祖先。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北来说。据汉文和彝文历史资料记载,彝族先民与分布于西部的古羌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彝族主要源自古羌人。
第五,濮人说; 认为彝族先民是古代的濮人,“今称倮倮”。
第六,云南土著说 ;认为云南自古便是彝族的发祥地。今川、黔、桂各地的彝族皆发源于滇。云南土著说的一个佐证就是,云南有元谋人的发现。
第七,卢人说 ;认为“周武王牧野之誓有卢人,滇之倮即卢之专音”。
第八,卢戎说 ;认为彝族先民“卢鹿部”,可能与春秋时的“卢戎”有关。
第九,主要源自早期蜀人与又一源古东夷族融合说; 易谋远《彝族史要》认为彝族起源的主源是以黄帝为始祖的早期蜀人,在彝族多元起源中的有一源是彝族以母族昆夷而始祖古东夷族;并且提出彝族的族称统称为“尼”,“尼”是古“夷”字即古东夷族的“夷”,同“彝”今译。
但是以上学说我个人认为不完整,因为彝族DNA到底还是揭露了其族群中很多是中古之后,从印度迁徙进四川的印度达罗毗荼族群,只是语言被周围其他人群转化成藏缅语族的语言。
彝族有40%左右的父系就是达罗毗荼语族的主体父系,彝族的南亚成分比例比周围所有民族都高的多。
还有一个佐证就是解放前彝族的社会结构和印度的社会结构及其相似:
统治阶级:
婆罗门————兹目,大约占总人口1%;
刹帝利————诺合,大约占总人口7%;
被统治阶级:
吠舍 —————曲诺,大约占总人口50%;
首陀罗————阿加,大约占总人口33%;
达利特————呷西,大约占总人口10%。
语言方面:
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同属彝语支的语言还有我国的哈尼语、拉祜语、僳僳语、纳西语、白语、基诺语、桑孔语、怒族怒苏语、怒族柔若语,以及泰国的阿卡语、姆比僳语、姆比语,老挝的普诺伊语、西拉语,越南的彬语等。
四川彝族有印度基因,云贵那附近到印度东北都没印度土著基因。还有一种解释就是吐蕃强盛时,从印度引进的奴隶军。类似的有蒙古人从中亚引进的花剌子模奴隶军。和英国殖民缅甸从孟加拉引进的罗兴亚人。 人种性格也像,懒,躺平,种姓。
因此综合来看,本人更倾向于彝族的起源是,印度达罗毗荼族群从南亚北迁(包含从印度引进的奴隶军这一说法)和四面八方迁徙而来各族群的一次大融合,在大凉山,小凉山,乌蒙山等封闭地理单元下形成的独特民族,而在最开始的族群战争中达罗毗荼人占据上风,成为统治阶级,就是黑彝,而社会结构也沿袭了印度种姓制度,其他战败族群成为了被统治阶级,即白彝。由于条件限制,加上生存需求(1、食物等物质需求,2、外敌入侵,他们的战力不如华夏文明),被破进入大凉山腹地,即金沙江河谷和安宁河谷等相对平整的地区。经过长时间的融合形成了彝族。而这一封闭就是上千年。
彝族的发展变迁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初期,彝族先民活动的中心大约在滇池、邛都(今四川西昌东南)两个区域。在这些地区居住着称为“邛都”、“昆明”、“劳浸”“靡莫”和“滇”等从事农业或游牧的部落。根据彝族的历史传说,其祖先在远古时代居住在“邛之卤”,后来才南下到“诺以”、“曲以”两水沿岸(即金沙江和安宁河流域)。
大约在公元3世纪以后,彝族的先民已经从安宁河流域、金沙江两岸、云南滇池、哀牢山等地逐渐扩展到滇东北、滇南、黔西北及广西西北部。由于彝族先民定居西南后,曾不断与其他民族融合,如古代南方的濮人后裔就有许多成为了今天的彝族。贵州古彝文典籍《西南彝志》中就有许多关于“濮变彝”的记载。同时,古代彝族居住的地区,又分布着彝语支的其他许多部落。因此,彝族在历史上的名称十分复杂。
大约在2000多年前,彝族先民已经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据彝文典籍记载,彝族的祖先“仲牟由”有6个儿子,这6个儿子就是彝族尊称的“六祖”。“六祖”为武、乍、布、默、糯、恒六个支系的祖先。根据贵州彝族水西土司安氏世传的父子连名谱系,自仲牟由至清康熙三年(1664年)的水西土司安坤,历传85代,由此上溯,“仲牟由”约为战国初期人。六祖分支标志着彝族先民由氏族、部落走向部落联盟阶段。
大约在公元前二、三世纪,居住在云南滇池周围的彝族先民已开始进入阶级社会。汉初,在滇池地区(原“滇国”领域)设益州郡,彝族先民为“滇王”所统治。公元8世纪,在云南哀牢山北部和洱海地区出现了六个地方政权,史称“六诏”(六王)。其中“蒙舍诏”的首领皮罗阁在783年统一“六诏”,建立了以彝族为主体,包括白、纳西等族在内的“南诏”奴隶制政权,并由唐朝册封为“云南王”。同一时期,在贵州彝族地区也出现了“罗甸”等政权,总称为“罗氏鬼主”。
公元937年,封建制的“大理政权”取代了由于奴隶和农民起义而崩溃的“南诏”,从此,云南彝区开始走向封建制。13世纪后,“大理”、“罗甸”相继被元朝征服,并在这些地区设置路、府、州、县和宣慰司。元末,云南许多彝族地区封建地主经济迅速发展,但在一些地区领主经济和奴隶制残余仍然不同程度的存在。
明代,在彝族地区兼设流官、土流兼治和土官三种官职,对彝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起了十分显著的促进作用。明代改土归流之后,兹莫阶层衰落,诺合纷纷独立,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变成了诺合。兹莫的后代失去了政治经济的实力,但身份地位仍然最高的。
清代加强了对彝族地区的直接统治,从而使大多数彝族地区的领主经济解体,封建地主经济进一步发展。
落后的制度可以说凉山彝族从从奴隶社会一步跨千年来到社会主义社会,步子迈大了,一只脚跨进来了,另一只脚还在后面。他们是直接从奴隶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所以这个转变注定充满坎坷和崎岖。去看本地的历史博物馆,你会被黑白照片里瘦到脱型,表情麻木的奴隶震惊到,很难想象那已经是民国后期和建国之前。那些奴隶主用铁链子,麻绳牵着奴隶,就像牵着一只羊,或者一只猪。
人类族群在跨越社会制度都必须经历剧痛。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人类在从奴隶制度跨越到封建制度,再从封建到资本,都必须经历过巨大的社会变动甚至流血牺牲。而我国还有多一道社会主义的跨越,付出了多大的艰辛和牺牲,大家心里都有数。
而大凉山彝族,这算是一步从奴隶制跨越到社会主义,可以说,一步走了中国3000年的进程。这期间还有中国几十年走完西方几百年进程的浓缩在里面。
1956年凉山解放之后才废除奴隶制。以土司为首的黑彝阶层为奴隶主,占有所有生产资料和白彝,白彝为奴隶。40年代50年代出生的彝族,相当一部分还活着,包括他们的儿女这一辈,他们是见过奴隶社会的,其中的黑彝家支失去了权力,但依然想保有曾经的地位,所以家支观念也就是宗族观念依然存在,他们依然抱团发展,想要守住曾经的尊严,这样的旧贵族阶层,要一步从奴隶社会来到社会主义是很难的。比起黑彝,白彝汉化得比较快,被解放的奴隶当然迅速投身社会主义的怀抱。所以那些依然强调家支强调出身的往往是黑彝,白彝往往羞于提起自己的出身。
纺锤形的社会结构彝族的社会结构和印度种姓制度如出一辙,是一种纺锤形社会结构。
解放前,彝族分5个等级:兹目,诺合,曲诺,阿加,呷西。兹目是汉人封的土司,诺合是黑骨彝,就是黑彝,又叫黑骨头,地位仅次于兹目,两者是统治阶级。黑彝如果听话,得到汉人的赏识后,就能上升为兹目。
兹莫是最高统治者,大概占总人口的1%。下面有数个诺合,这部分人虽然只有7%,但是拥有70%的土地,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家支。以上两类人是统治阶级,因为彝族以黑为贵,他们也就是常说的黑彝。这里要说一下
与黑彝对应的就是白彝,是属于被统治阶级,即奴隶,也就是娃子。
娃子又分为三个阶层:
曲诺——百姓娃子,这部分人占到了近50%,不过大部分在云南,曲诺是白色的意思,也就是清白人,所以也叫白彝。理论上的奴隶阶级,归诺合所有,不能随意离开家支的土地。曲诺有自己的土地和财产,有一定的经济独立性,其中一些还能有自己的奴隶。曲诺阶层人口最多,抱团起来实力较强,诺合也不能随意欺压。
阿加——安家娃子,占到彝族人口的大概33%,主子家里家外的人。实际上的奴隶,不能离开主子左右,主子可以卖掉或者转让阿加。阿加也没有婚育权,婚配是主人指定,孩子直接被带走做奴隶。但还有极少部分阿加能混得不错,甚至拥有下一级的阿加或者呷西。
呷西——锅庄娃子,火塘边的人,最底层的奴隶,占总人口的10%。来源有破产的曲诺、阿加,家支争斗的俘虏,阿加(男)和呷西(女)的孩子,被掳走的汉、白、苗、土家等外族人。
封闭的地理单元“没有爬过支尔莫乡阿土列尔村的藤梯,就等于没有去过古里拉达峡谷。”
这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人用来相互调侃的一句话。因为道路不通,村民要想进出村庄,最近的路就是顺着悬崖、攀爬17条岌岌可危的藤梯。因此,阿土列尔村也被称为“悬崖上的村庄”。
彝族聚居地大致可以分为三块,大凉山、小凉山和云南。大凉山简单说就是四川的凉山州;小凉山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凉山彝族自治州东部,它是大雪山的东南分支。西北方为大、小相岭,东南方隔金沙江与五连峰相望,东北方没入四川盆地。海拔2000~4500米,为金沙江、马边河的分水岭,以黄茅埂为界,东为小凉山;云南是指楚雄和红河这两个州。地理因素导致了三块地方的人口构成不太一样。
俗话说,大凉山山小,小凉山山大,大凉山虽然总体海拔较高,但是地势相对平缓,有比较多的山间平地、河谷之类适合生存的地方,是彝族传统的地盘(这里采信彝族是源自古羌人的北来说),也是家支文化势力最强的地方。而小凉山正好相反,平均海拔低但是山势陡峭,生活艰苦,当地人口除了本来就在小凉山安家的诺合,还有很多是不堪大凉山诺合压迫,历经苦难逃出来的阿加和呷西。云南彝族则是源自和汉人接触较多的白彝,他们学到了更多的知识,慢慢开化,和汉人通婚,有了向外走的愿望,再加上黑彝对他们的控制力较弱,于是走出大凉山,向东方和南方的平地越走越远,红河的彝族都已经到国境边上了。
新中国成立后消灭奴隶制和封建制,确实也解放了很多人,至少名义上已经没有奴隶了。云南彝族本来就开化得早,前任省主席龙云都是彝族人,下野后还回老家宣讲民主,这方面就没什么问题,顺便说一下,龙云出身的纳吉家族其实是川滇交界处相对开化的黑彝,按照家族谱系,龙云彝语名字应该是纳吉乌梯,而且他的母亲是汉族;小凉山的阿加和呷西翻身做主得解放,对新中国感恩戴德,社会改造相对积极。
大凉山则是完全另外一回事,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6年大凉山还在打仗,国民党退的时候选择当地头人封了很多官,给了很多枪械,留下许多承诺。凉山这种意识形态,导致没有办法“革旧迎新”,每个朝代更新都不会影响吐司的地位,上面说的剿匪,打掉一批后他们剩下的一些“拨乱反正”,仍担任一方要员。包括现在黑彝贵族仍然在各级政治机构中稳占一席之地。因为彝海结盟,上层的黑彝帮助过红军,作为回报,新政府在政策上有所优待,加上地处偏远,各种社会改造没有彻底深入完成。大凉山成为了家支制度最后的堡垒,以前的黑彝,现在是村长,以前家支抱团,现在还是抱团,以前有纠纷了找德古,现在还是找德古……奴隶制度的形没了,但魂还没散。
根深蒂固的观念观念的形成是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累计的结果,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仍有许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遗留:
1、有多余的食物,一定要拿出来分享,否则大家都会饿死。收到别人的物品也不用内疚,因为当你有有结余时,也会无偿拿出来分享。
举两个例子,正面的例子是,不少的家族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就是如果哪一个孩子成材后定居县城或者市里,家里的兄弟姐妹的孩子就会送到他家,这家人会好好照顾自己的侄儿侄女在城里读书,给他们创造教育机会。负面例子,他们会包庇自己犯罪违法的族人,比如高赞里面提到的帮助本族的小偷,并以此为荣,会用人海战术解决本来应该走法律程序的事件。
2、外出时一定要团结,否则容易被别人伤害或动物吃掉。
3、每年必须要祭祀,否则天神会降罪。
4、家里有多余的物品,一定要及时和亲人享用了,明年的生活怎么办,到时候再看。
5、宝哥哥要娶林妹妹,表哥娶表妹现象很多。
6、生病了不去正规医院,找来神婆跳一下祛除灾祸。
7、“下等人”不能和“上等人”结婚,社会中,有些人生下来,就比另外一些人“高贵”。
8、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早晚是别人家的人。
9、家里祭祀,无论多远都要回来,表示对祖宗的尊敬。
10、宗族里发生了矛盾,需要找双方信得过的人来协助处理,有些时候,可能已经是法律该管的东西,都私下私了了。
11、毕摩权力很大,有时对一些事情具有决定权,但有时这种决定并不科学。
毕摩是彝语音译,"毕"为"念经"之意,"摩"为"有知识的长者"。是一种专门替人礼赞、祈祷、祭祀的祭师。毕摩神通广大,学识渊博,主要职能有作毕、司祭、行医、占卜等活动;其文化职能是整理、规范、传授彝族文字,撰写和传抄包括宗教、哲学、伦理、历史、天文、医药、农药、工艺、礼俗、文字等典籍。毕摩在彝族人的生育、婚丧、疾病、节日、出猎、播种等生活中起主要作用,毕摩既掌管神权,又把握文化,既司通神鬼,又指导着人事。在彝族人民的心目中,毕摩是整个彝族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是彝族文化的维护者和传播者。(来源:百度百科:毕摩)
12、娃娃亲。
曾经有布拖的一位同学家里接受毕摩建议,从湖边搬迁到山上“风水好的地方”,家里所有牲畜、家禽、物品都拿来祭祀治病,最后人病死,家里一夜致贫,现在住在快倒塌的房屋边。因为是外来搬过来的,没有人帮助,家里异常艰难。同时她也被家长定了娃娃亲。有两个同学,大学上着上着就回家结婚,因为“娃娃亲”时间到了,不结婚要陪很多钱。
13、没有什么事情是关系搞不定的,只要关系到了,就都能解决,什么法律之类的,都靠边。
14、多子多福,婚丧嫁娶。
第一随礼,随什么呢,牛,羊,一家人死个人,可以收几十头牛,现在一头牛的价格已经被牛贩子炒到了一万多了,本身经济就不富裕的家庭,一年辛辛苦苦存的钱,只需要随两个礼就又回到了解放前,本身就穷的人更不用说了,借钱都得把这个面子撑过去,可能有人说,那自己家如果有什么事,不就可以大赚一笔,错,收的礼,要不了多久,就会干干净净的回给别人。第二,讲究兄弟义气,杀牛,杀羊招待客人。第三,娶媳妇,娶个媳妇的彩礼按照文化程度来分,文化越高,彩礼给的越多,一个高中文凭可以给到20万,没钱,借钱给,有人说那养女儿不就赚了,错,这些钱是要分给女方的叔叔伯伯之类的亲戚,女方父母根本分不了多少。
这些我们听着都比较熟悉,我们封建社会都有的现象吧,在凉山彝族自治州里都有,而且很强,可能出乎你的想象。学生间打架了,伤到了对方,两个家长底下私了了,居然被打的那方要质疑学校为什么要处理打人的一方?
整个彝族人口接近900万,凉山州境内约占彝族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的人是没有问题的,即使是同为四川省的攀枝花这样的移民城市也有10万彝族人。凉山的地理环境影响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进一步拖累了凉山的经济发展,封闭的地域环境与落后的教育使人文环境进一步恶化。
整个凉山彝族的现代问题远了说是清末鸦片贸易开始,近了说是凉山解放之后的民改没能完全解决问题。而问题的爆发就是从1978年州府从昭觉移到西昌,支援凉山的知识青年大批返城开始的。安宁河谷地区和大凉山之间本来就不平衡,新的政策又几乎是放逐了老凉山。对于当时的凉山彝族,老的社会秩序已经被破坏,新的秩序又还没来得及建立足够的影响就更替了(这个不能多说,理解就好)。青年无事可做,看不到希望,大量外出,又不懂汉语没有技能,只能沦为社会边缘的违法犯罪人员,彻底失败。到了90年代,毒品和艾滋问题就通过这样一批一批出去又回来的青年肆虐了整个大凉山。
凉山山高路陡,自然条件恶劣,走过之后很难再有什么人定胜天的想法,剩下的只是对大自然的敬畏和无力感。
幸好国家和社会没有完全遗忘大凉山。脱贫攻坚以来,国家投入了很多,路网电网水网基站建设,一村一幼等等教育投入,让凉山彝族离现代社会越来越近了。感谢网络,让没有电视的家庭也能用手机接触外界,让他们对很多东西有了概念,有了概念才能萌生与之相关的梦想。感谢教育,用几代人的时间,慢慢改变彝族传统落后的观念,让他们知道读书改变命运,让他们与汉文化实现相互理解融会贯通。
凉山扶贫有什么问题?1. 民间力量缺席
这也许是所有西部地区扶贫存在的问题。在扶贫过程中几乎所有参与者都是“公家”,无论是当地政府,东部发达地区帮扶政府,还是高校点对点帮扶,国企以购代捐;当然扶贫的主力自然是这些单位,但在此之外资本和个人的主观能动几乎没有发挥作用,很可能也是因为民间对于凉山的看法较为负面,对于待发展的民族地区接触意愿不高。凉山的私企几乎都是本地人创办的,或者就是大企业,中小企业中特别鲜见外地资本。
2. 社会转型较慢
凉山的政府仍然是传统的管理型政府,可能因为当地没有较强的企业,也可能是因为时间的问题。传统政府存在的问题包括官僚作风、贪腐和大吃大喝,这些在凉山仍然是较为普遍的现象。2019年凉山纪委立案了53名县处级干部,以及坠亡事件都反映了政府的一些问题。
另外,老生常谈的问题,凉山的社会体制在解放后直接从农耕奴隶社会跳跃到社会主义社会,一些传统的陋习和社会风貌仍然残存。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在建立彝家新寨之后,彝族老乡不会使用蹲便器冲水,不习惯使用卫生纸,使用后用石头盖住就完事儿……另外由于基础教育的缺失,其他答主提到的打工之后不存钱,喜欢坑蒙拐骗,大摆宴席,抱团闹事这些问题确实存在。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很多人没有一个认知,就是你现在习以为常的一切不是生来有之,是极具优势和生命力的汉文化几十代人祖祖辈辈积淀的结果。包括“勤劳致富”这种概念,是农耕文明小农经济发达的汉族才有的观念,因为努力种地就会有收获,而彝族居住的高山耕种跟你努不努力没啥关系,基本就是土豆荞麦青稞;汉族从科举制开始用上千年时间树立了“读书改变命运“的概念,而对彝族来说考试都是一个新词。更别说曾经的奴隶主和奴隶脑子里没有努力这个概念了,奴隶主不用努力,奴隶不想努力。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穷,是,别人想致富,但是没有钱去致富,想改善生活而没有经济能力,于是你给点钱,人家就会用这些钱去置办种苗,养殖种植,然后卖钱来改变生活。
这就是通常的替代思维,用自己的视角去看别人的问题,用自己的想法去解决别人的困难,我们觉得自己帮了别人,别人就有动力去改变一切。
然而现实却是,很多时候你的帮助只能暂时改善他的生活,而不能让他改变生活。
他们不是不想变的有钱,但是也仅仅是想变得有钱,而你的捐助恰恰就让他变得有钱,于是,他就暂时满足了,还想得到更多。
所以第一线扶贫的工作者,都需要花费大半的时间和精力跟那些彝族人同吃同住,和他们交朋友,说知心话,穷人的道德感很低,但自尊心是很高的,他们可以为了生存做各种撒泼打诨的事情,但是若你喊一句:“嗟!来吃!”他们又断然不肯过来吃,所以你怎么办?当初共产党建立根据地是怎么办的,你就得怎么办!
而有些所谓的扶贫工作者,有些所谓的一线记者,撇着大嘴踩着高跟鞋,抹着红嘴巴梳着满头的油,光鲜亮丽的晃荡两下,送几袋面,拍几张照,送几袋米,扯几条横幅,报纸上一登,电视一上,拿到了政绩,拿到了素材拍拍屁股就走了。
很多时候不是他们好吃懒作,而是在很长时间内,他们并没有持续的财富来源,导致很长时间他们都徘徊在温饱线,于是他们迫切的渴望是脱离温饱,但是也害怕回到温饱线之后,所以有些改变生活是需要投入,他们就不敢。因为没有后退的余地。至于说从质上去改变生活,这往往就被观念所限制了。举个例子,就是政府救济的粮食种子都不能给早了,给早了就给吃掉了。
因此单纯的捐助根本改变不了梁山的现状,扶贫的人送吃的送喝的,好时代,来临了!混吃等死那就彻底的不用担心了,时不时抱团了闹一闹,还有人给钱,多好。旧有的社会结构把贫穷的彝族人禁锢在家支里,压在社会底层无法翻身,让他们认为自己无法通过努力改变人生;另一方面扶贫让他们的生活得到了温饱,让他们达到了底层生活的满足,而从未走出家支的眼界根本就不知道更高层次的生活是怎样的。懒惰的两方面原因在他们身上达成了完美的统一,扶贫变成了越扶越贫。
在意识形态不匹配社会发展模式的前提下,贫困者是无法通过“超越一点点适当经济补助范围”的帮助 走向富裕的。
改变这种情况,必须要改变观念,当然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就像云南地区的彝族,接触汉族较早,就比较开化,更容易融入现代社会告别贫穷落后的生活状态。
解决方案,两个办法:一个是扶贫教育,彝族几千年来的基础教育都太薄弱了。他并不能像汉族同胞一样,能迅速的适应工业文明以及现代社会。知识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给他们灌输希望。教育有个功能叫社会化功能,就是通过教育,让人学会普通话,学会写字,学会算数,学会坐板凳(凉山前几年有个行动叫“板凳工程”,就是教彝族要学会和习惯坐板凳,之前都是席地而坐席地而睡),学会红灯停绿灯行(高山上的彝族下山来第一件事就是学会这个,不然死得硬硬的),学会别盗窃抢劫否则就要蹲监狱,学会基本社会规则,能够正常融入社会并找到工作。彝族十分需要教育,否则难以融入现代社会,所以会有控辍保学。所以会有一村一幼,所以会有村村通,会有移动通信基站(大众传媒也有教育功能,起码能学普通话,很多彝族四川汉话说得不伦不类,普通话却说得很标准,因为是跟着播音员学的)。可是学校教育代替不了父母,所以彝族的改变需要小学毕业的父母养出中学毕业的孩子再养出大学毕业的孩子,需要代际更迭,需要时间。
另外一个,现在实行的易地搬迁扶贫也是个不错的办法,一来脱离了山上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前因为争夺土地彝族才被迫上山,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大家都到平地上来是最好的;二来,走出大山的彝族人更容易接触到外界的信息,睁开眼睛看过世界就会发现原来的寨子那片天地是多么的渺小和局限;三来,易地搬迁优先搬迁贫困户,而且是多个乡镇的迁出人口集中安置于同一个安置点,这样也是在慢慢打破原有的社会结构。人走出来,眼睛望出去,这是脱贫的第一步,好好走下去吧。
最近反映宁夏西海固地区扶贫的电视剧《山海情》火了,其实本回答也是非常赞同异地搬迁扶贫的方式。搬迁都知道难,但宁夏就是埋着头苦干,即便暂时看不到希望,即便被人误会,宁夏人也没怎么宣传,一句话,“干就完了”。历史证明宁夏的扶贫方式是正确的,是值得推广的。
大凉山既然交通不便,那就让他们出来。虽然四川多山地少平原,但是一点一点来,慢慢的来,建好村落,到各个村子去宣传,愿意去新地方的,给地,给工作机会,给生产补助。不愿意去新地方的,没关系,不去就不去,但是原本的扶贫力度要慢慢减弱,直至没有。而后去新村子的,给的利益也要比先去的少。一个村子里能有一两户过不下去的,愿意脱离这个环境的就行,新的住宅区来的人都是来自不同村落的更好,就是要打破宗族,让他们认识到日子过得好,主要靠自己经营,靠国家扶持,这样才能让他们思想上不再依赖宗族势力,心里不再有家没国。
结语:展望未来其实我有一些感悟,说出来大家可以探讨一下。贫困区的人最需要的是改变,最重要的是思维的改变。而人思维的改变不是需要强制的思想教育来达成,而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春风化雨式的影响。
首先,需要先让接触到现代化社会,通过哪种方式呢?最简单的就是通过电视,无论老还是幼,先让他们接触到丰富的外接社会,每户都赠送电视机,让他们无聊就看电视。每天必看电视,对外接有所认识,细风化雨的改变世界认识然后顺其自然的意识到更丰富的物质生活,就会有渴望,有想法。就像80/90年看香港节目,对香港无限的渴望,无数人做梦都渴望偷渡去香港是一样的道理,基本的人性嘛。有想法了就要组织起来,诱导去外接体验,有个最简单的解释:外出打工。至于怎样安排落实诱导外出,我就不贻笑大方了,基层干部大把的经验。
最后还得一步步的从底层教育抓起,不过一旦接触了外部社会,自然的就会懂得要赚钱就要有基础的文化知识,那就保障了儿童的基本教育。至于高等教育的需求,只能慢慢来,思想的转变没办法一步到位,可能需要两三代人的努力。不知道说得怎样,感觉最重要的是诱导,顺应人性的诱导。
讨论凉山扶贫时,很多人自我代入的是扶贫者的角色,所以在看到花钱不讨好的时候会觉得这钱花的不值得,看到少数民族的负面信息是会觉得愤懑。这其实是傲慢的,一旦人将自己代入到鄙夷链里去考虑问题,那总有站得更高的人认为你也一样不努力,一样愚蠢。这其实是和盖茨比里讲的那句“每当你觉得想要批评什么人的时候,你切要记着,这个世界上的人并非都具备你禀有的条件。”有着相同的内涵:我们必须承认人人生来不够平等,能力之外的资本在和平时期可能比能力本身更重要,但不代表我们支持血统论和那些继承来的资源带来优越感。
希望各位能够理解少数民族地区扶贫的必要性,能够理解扶贫基层工作的难度和意义,能够接纳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过程中带来的问题。如果能够在扶贫和西部建设的过程中能够发现机会,将自身的价值实现和社会发展的动向结合,那就更好了。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对大凉山,对整个彝族的未来充满信心,乃至对全中国所有少数民族的兄弟姐妹充满信心。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