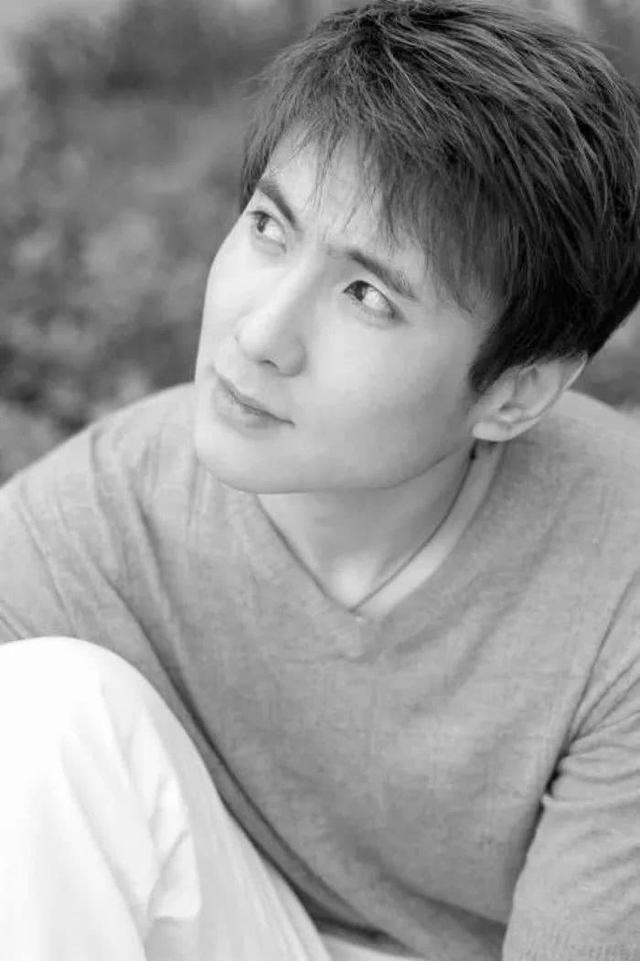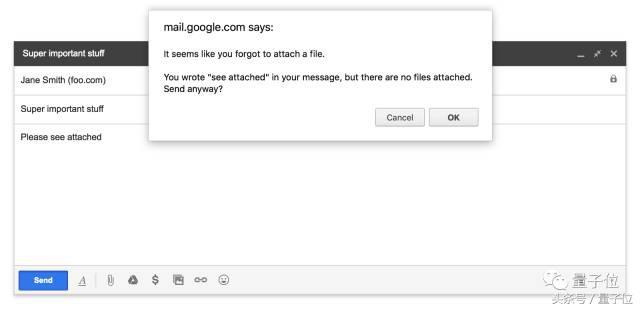基因诊断及治疗的伦理案例(本土基因重塑的样板个案)
新一季《爸爸去哪儿》已于7月10日如期开播,这档引领风气之先的明星亲子秀、中国电视荧屏上最具有话题性的文本之一,不知不觉间,已经走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三个年头 ,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基因诊断及治疗的伦理案例?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基因诊断及治疗的伦理案例
新一季《爸爸去哪儿》已于7月10日如期开播,这档引领风气之先的明星亲子秀、中国电视荧屏上最具有话题性的文本之一,不知不觉间,已经走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三个年头。
一个节目是不是 “最好看”、“最精彩”、“最有创意”都属于主观判断,涉及每个人的态度、口味、立场和喜好,难免见仁见智、众口难调。唯独“最具有话题性”这个表述,是一种客观现象和已经发生的状态——无论这个社会有没有因为它而变得更好,至少因为它而变得更加热闹:它的自黑与自曝、积极与消极、引导与误导、正常与非正常、底线与无底线,无一例外地储备和提供了大量的争议空间和讨论余地,骚动着这个迫切需要谈资的时代,除了作为一个惯性选择而持续霸占周五晚间的遥控器、作为一个网络热词而刷爆微博微信朋友圈,它更具有了一种文化学、伦理学、大众心理学层面的样板个案价值,透过它,我们似乎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电视的成与败、媒介的得与失、观众的爱与恨,乃至当下中国大众文化的需要、希冀和无助。
户外真人秀在东方伦理的改写和纠偏下,完成的一次重新自我塑型,在多个方位上都呈现出更贴近中国人思维模式和精神气质的状貌
作为一种来自西方的节目模式,户外真人秀 (比如盛名远播的 《阁楼》、《幸存者》、《荒野生存》等)素来以野外竞技和生存权的角逐作为核心内容:封闭的空间、严苛的赛制、残酷到不近人情的淘汰机制,选手在规定情境下与队友竞争、与自然搏斗,不断探求体能和意志的极限。很显然,这种把“谁将被谁排挤出局”作为主悬念、让饥饿疲惫创伤和钩心斗角伴随始终的重口味取向,并不适用于中国观众所习惯和渴求的那种温情、和谐、积极、健康、正能量的审美,也不吻合中国观众对于电视的休闲、娱乐、精神疗愈的定位——我们对腹黑与厚黑的围观欲求,已经由宫斗、家斗、职场、商战等电视剧类型所承载释放,在“真人”这个层面,我们还是愿意相信人性本善。
所以回溯中国电视发展史不难发现,在《爸爸去哪儿》出现之前,户外真人秀在内地的收视业绩几乎是一地鸡毛——大约湖南卫视已经坚持到第八季的 《变形计》是个例外,但它更偏向于苦情化宣教和治愈,不适合承担黄金档的综艺要求。
相比之下,《爸爸去哪儿》的原产地是同归东亚文化圈的韩国,可说是户外真人秀在东方伦理的改写和纠偏下,完成的一次重新自我塑型,在多个方位上都呈现出更贴近中国人思维模式和精神气质的状貌:第一,参与者从个体变为父子,参与内容从生存比拼变为组团旅行,情感交流取代了封闭空间内的人性实验,体现出儒家文明对“天伦”的绝对重视;第二,保留一部分虚拟设定和竞争关系,但无关乎你死我活、谁走谁留,也不进行成绩统计,每一场游戏的输赢充其量只决定当晚烹饪食材的优劣、居住房屋的大小,这种无伤大雅的喜感贯穿始终,吻合亚洲观众的轻口味愉悦;第三,参与主体从普通人变为明星,剔除歌唱走秀演戏竞赛的核心技能后,这些带着光环的个体在洗衣做饭中暴露的失措和无奈,又在心理上拉平了观看与被观看双方在社会阶层上的隔膜,符合国人最偏爱的“公子落难”、“丝逆袭”、“草根的大腕化和大腕的草根化”等关于身份错置的快感;第四,在东方社会的父系权威传统里,“爸爸”是威严与决断的象征,母亲则总是与子女日常起居绑定更多的一方,当二者在节目中完成任务逆转——母亲缺位而父亲回归家庭,这种为东方观众所不习惯的反差感,足以转换成节目的新意与创意。
不止于此,当《爸爸去哪儿》从韩国进入中国之后,某些更细致、更贴合、更接地气的改造仍在继续将其拉近中国观众的心理需要:其一,从一个父亲带两三个孩子变为一个父亲带一个孩子,匹配中国特有的独生子女现象;其二,相较于原版较为缓慢的剧情设置和强烈的综艺形式感 (三天两夜一次任务,分两期播完),湖南卫视版明显更注重节目编排和节奏的紧凑性 (两天一夜一次任务,分三期播完),叙事重点也转移到搞笑、哭闹、撒娇、安抚这些直观冲突上(韩版的儿童都比较大,最小的也已经六岁,所以自控力更强),这种简单明快、对情绪的直接撩动,显然与本土观众群体年龄跨度大、女性居多、知识水平相对偏低的特质有关;其三,中国幅员辽阔的地域也给了拍摄得天独厚的环境便利性——农村、沙漠、苗寨、海岛、古镇、雪原,视觉上的奇观效应乃至 “饱览祖国大好河山”的自豪感,也无疑很对国人的胃口。
用孩子身上天籁般的善意、博爱和赤子之心作为价值旨归的时候,一个巨大的空白被填补了
必须提及的还有《爸爸去哪儿》登陆中国荧屏的时间点:歌唱类选秀扎堆混战的夏天刚刚过去,综艺竞技造成的审美疲劳和内耗透支了观众的热情,整个电视业仿佛置身于群雄逐鹿后百废待兴的迷茫中,急需一种更清新、更鲜活的血液补充进来,挖掘一个新的潜在热点。而2010年之后,80后初为父母、二胎政策引发关注、第四波生育高峰如期而至、“小儿难养”成为无数家庭最集中的困惑与焦虑——孩子正在不可逆转地重新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心。与之相比,由于长期以来的偏见和盲视,也由于低龄参与者在电视拍摄制作中存在着太多不确定性,中国电视荧屏上的儿童形象始终是缺位的、偏狭的、符号化的,至少是被动的、机械的和没有存在感的,孩子们或者在少儿节目中担任被教育、被规训的对象,或者在家庭剧中扮演婆婆媳妇争吵角力的触因。是以,当《爸爸去哪儿》将这个群体第一次作为情感寄托中心、故事推进中心和精神传导中心,放在前所未有的突显位置上,试图用孩子身上天籁般的善意、博爱和赤子之心作为价值旨归的时候,一个巨大的空白被填补了。一个新的、低龄的、天真烂漫的兴奋点,再次拯救了中国电视。
当然,作为孩子们的监护者,明星父亲们才是这档节目实际上的决策领袖,近年来以《艺术人生》、《鲁豫有约》为代表的名人访谈节目的社会影响力正在急剧萎缩,尤其是大量曾经在这类节目中谈过道德操守的明星们出了道德问题、秀过夫妻恩爱的大腕出了婚姻问题之后,观众对于这种端坐演播室里声泪俱下的抚今追昔越来越失去兴趣和信任,明星们也发现,在这个推重真性情的时代里,自我形象营销和商业价值提升的最佳模式,已经不再是谈话节目里干巴巴地讲述“我很厉害”,而是去户外真人秀节目的田间地头表演一幕幕 “我很能干”,再不济,也是“我很可爱”甚至“我很呆萌”。
我们需要无微不至的暖男,于是我们找到了张亮(这是中国第一个没有通过任何具体专业才艺展示,而在综艺真人秀里用性格和家务红起来的明星)和黄磊;我们需要不会老去的帅爸,于是我们找到了林志颖和陆毅;我们觉得女孩子应该美丽善解人意如天使,于是我们找到了森碟和多多,现在又有了夏天;我们觉得男孩子应该坚毅甚至粗糙,于是我们找到了石头和费曼,现在又有了康康。
当所有随时升起的愿景,都能在这个标靶式的节目里找到落点和对应,你只能说,它确实搔到了这个社会和这个文化的痒处,让人愉快而且舒畅。于是,当户外真人秀以“先韩国再中国”的逐步趋近完成了战略调整和本土改造,辅之以恰当的时代背景和公众焦虑,瞅准了节目开播时机,呼应了明星曝光需要,这一切条件都聚合在《爸爸去哪儿》身上时,它已经变成了一枚精准的针灸,不偏不倚地扎在了那个最准确的穴位和神经元上,立即释放和激活了整个躯体的内循环。
□邵 杨(作者系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广电系博士、讲师)
《爸爸去哪儿》海报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