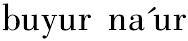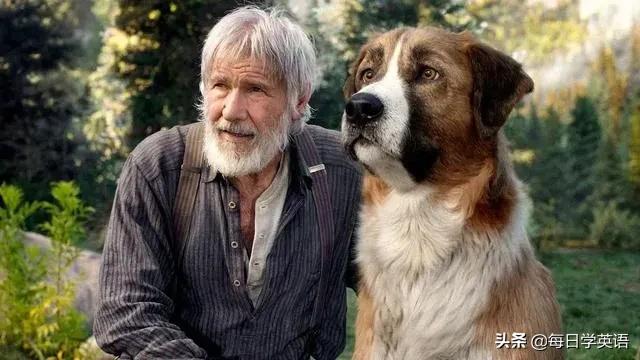汉代外族地名(西域地名考录蒙古地名考误)

《西域地名考录》一书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系统、完整而且全面地考释西域历史地名的工具书。此书收录地名共6500余条(其中有重复的条目)、90余万言,全部词条、字数均比冯承钧先生1930年编著的《西域地名》710条(陆峻岭增订本增加到920条)多出六倍以上。此书无论从所收地名词条的数量还是涉及的地理范围方面,远远超出了前者,而且大量增加了蒙元史及清代蒙古史上著名的一些蒙古地名条目。不过,仔细拜读之余,发现此书编著者对这些蒙古地名的考录,存在若干错讹瑕疵,笔者不揣浅陋,举出一些例子,作些探讨,还望方家不吝赐教,批评指正。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能探讨此书所收录的所有蒙古地名,下面按照《元朝秘史》地名、《元史》地名及清代蒙古地名等三个不同时期地名,分别选取十二个蒙古地名考释中存在的问题逐一讨论。
一、《元朝秘史》地名
1.第150页,捕鱼儿海子Bouyour(Bouirnor) 湖名。又称达里诺尔、达里泊。位于内蒙古东南部,周围凡140公里,湖中有岛屿,鱼族水禽最夥。按:捕鱼儿海子即贝尔湖,《元朝秘史》音写形式作“(第176节)/捕鱼児纳浯児(第53节)”,其蒙古文原文正确拉丁文转写应作
。buyur,蒙古语,意为公水獭。但贝尔湖不称达里诺尔、达里泊。而俱轮泊(呼伦湖)才称达赉诺尔或达赉湖。此书第487页俱伦条解释为:一是河名,即俱沦水;二是湖名,俱轮泊即呼伦湖;三是山名,即俱伦山。这条解释虽然指出了俱轮泊即呼伦湖,但遗漏了呼伦湖又称达赉诺尔或达赉湖的事实。反而张冠李戴,把呼伦湖的别称达赉诺尔或达赉湖误置到贝尔湖。另外,贝尔湖并不位于内蒙古东南部,而是位于内蒙古的东北部,也就是说在呼伦贝尔高原的西南部边缘,是中蒙两国共有湖泊,而且贝尔湖的大部分面积在蒙古国境内,仅西北部很小面积为我国所有。至于达里诺尔、达里泊(意为肩胛湖)是指内蒙古赤峰市(原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境内的达里泊,与贝尔湖、呼伦湖无关。
2.第231页,的的克撤合勒 Dedckechehele 地片名。《蒙古秘史》云:“王罕桑(鲜)昆父子二人,罄身走至的的克撤合勒地面涅坤水处(《亲征录》作涅坤乌柳河),王罕行得渴了,将入去饮水,被乃蛮哨望的人豁里速别赤拿住。自说我是王罕。哨望的人不信,将他杀了。”位于蒙古国鄂尔昆河(流——漏掉此字,系引者所加)域。
按:的的克撤合勒,误。此地《元朝秘史》音写形式作“合仑涅坤兀速纳(第188节)”,总译作“的的克撒合勒地面”。应该说,《元朝秘史》这段原文有误,关于“的的克撒合勒”是地名还是人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学术界还有争论。
主张“的的克撒合勒”为地名的代表性学者有以下几位:蒙古国X·普尔赖说:“的的克撒合仑涅坤兀速TИДИК САКАЛ-УН HЭКYH УСУH §188。在《马可波罗游记》里经常提及,作TAHДУКTAЛ,乃系王汗之城池,按TAHДУК一地应在王汗山地区。”
阿尔达扎布译注《新译集注〈蒙古秘史〉》注释说:“合仑(Didik-saqal-un)地名。didik或дiдik纤维,一绺(见《试用突厥语方言词典》,第1771页);saqal乌拉草(见《御制五体清文鉴》草类)。按:Didik-saqal之地,必盛产一绺一绺的乌拉草。didik被单,床单;遮布,罩布;面罩,阵面纱(见《古突厥语辞典》第160页)。titig即titik глина粘土,缪泥。земля地球,地;陆地;土,土壤;地,地面。гpязь泥,泥泞,稀泥;垢,泥垢;泥地,沼地;боль疼痛,剧痛,刺痛;痛苦,苦楚,苦恼(见《古突厥语辞典》第564页)。Saqal боpода须,胡子。的的克撒合仑涅坤·兀速TИДИК САКАЛ-УН HЭКYH УСУH,在《马可波罗游记》里经常提及,作TAHДУК TAЛ,乃系王汗之城池,按TAHДУК一地应在王汗山地区。见《〈蒙古秘史〉地名考》第28页。”
村上正二译注《蒙古秘史2——成吉思汗的故事》一书的“的的克·撒合仑·涅坤兀速纳”Didiγ Saqal-un Nekün Usun-a条说:“《亲征录》作捏坤乌柳河。的的克·撒合勒恐怕是克烈王国与乃蛮王国之间国境附近的地方,Didiγ<turc.titiq意为泥或粘土,既然‘的的克撒合勒’是叫做‘泥髯’的草名,那么,是指‘野草丛生的潮湿地’吗?其次,叫做涅坤兀速Nekün Usun的涅坤,一般来说,信从伯希和所认为的相当于意为满语的‘女奴隶’的Nehu的说法之学者多,那么在这个场合怎么样呢?还有,谢再善认为将这个位置往王罕根据地的黑林方面寻求有些奇怪,与其这样,倒不如往乃蛮方面寻求。”
前引村上书又说:“豁里·速别赤Qori Sübecči,Ra.Qōri
豁里·速别赤、火里·速八赤(《亲征录》)。好像是在乃蛮国境方面的将军。此人名字与豁里·不花Qori Buqa、豁里·失列门Qori Silemün等名字一样,冠于豁里族出身命名的见于《秘史》的非常多,那么此人是其中的一个人吗?速别赤Sübeči的意思不明,按照出自蒙古语的一个词衍生的意思解释的话,是指‘针眼’,‘敌军侵入之际,务必要通过的狭窄的通道’,还有‘成为军事要冲的狭窄的通道’(莱辛p741b∕科瓦列夫斯基p1424b∕《鄂尔多斯辞典》p599 b)。因此,速别赤Sübeči为蒙古语,意为‘坚守军事要冲隘路的人’,正好符合在这个场面登场的人物之名。所以,不能认为此人可能由编者有意杜撰的人物,特别是《秘史》只有仅此一个人。然而,见于《亲征录》的则说:‘为乃蛮部主太阳可汗之将火里速八赤、帖廸沙二人所杀。’出现了除此人之外所属不明的叫做帖廸沙的一个人。拉施特也与此相同,只是将这位帖廸沙的名字写作Tätik shāl?可是,这位帖廸沙之名的写法无论如何好像与《秘史》中作为地名出现的‘的的克撒合勒’同一发音。那么,把这个视为人名还是视为地名成为问题,从前后的文脉来看,当作地名的《秘史》方面,不管怎么说符合情理的。还
有如果寻求‘的的克撒合勒’这个地方,此地大概在出自乃蛮国大官的豁里·速别赤所领地盘中去找吧?”
余大钧先生认为“的的克·撒合勒的捏坤河——‘的的克·撒合勒’,意为‘野草丛生的潮湿地’,其地当在乃蛮国东部边境附近。捏坤河,《亲征录》作‘捏坤乌孙河’。”
笔者认为“合仑”不是地名,而是人名。据拉施特《史集》记载:“的的克撒合勒”是擒获王罕的乃蛮两个将领之一的叫做帖迪克—沙勒(或写作“丁—沙勒”)的人。这两位将领分别是豁里—速别出(又写作“豁鲁—速别出”)和帖迪克—沙勒(又写作“丁—沙勒”)二人。最早指出这一点的是,法国著名东方学家伯希和。雷纳·格鲁塞《蒙古帝国史》说:“《秘史》第188节说是的的克撒合勒的涅坤水。伯希和校正,《秘史》的‘的的克撒合勒’就是《拉施特书》(别列津译,第145页)所说的乃蛮将领‘德的克察勒’(写错为Tong-chal)。参看伯希和的讨论,《亚洲学报》,1920年,I,176—177。”伯希和此说甚是。
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1分册说:“当王汗在最后一次与成吉思汗作战时,他被击溃后逃走;在涅坤—兀孙地方,[王汗]被太阳汗的两个异密:豁鲁—速别出和丁—沙勒擒获;因为他们[对他]有夙怨,便杀掉了他,将头颅带给了太阳汗。”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2分册说:“战败逃出来后,一路上他们来到了乃蛮地区……地方。乃蛮王的两个异密,一个名叫豁里-速别出,另一个名叫帖迪克-沙勒,在那里巡哨,便将他抓起来杀死了。他们将他的头送到了自己的君主太阳汗处。”
笔者坚持认为“的的克撒合勒”不是地名,而是人名的另一个直接证据就是《圣武亲征录》也说:“汪可汗仅以子及数骑脱走,顾其左右,谓其子亦剌合曰:‘我父子相亲,其可绝而绝之乎?今由此缓颊儿绝矣。’至揑(辟)[群]乌柳河,为乃蛮部主太阳可汗之将火里·速八赤、帖廸沙二人所杀。”显然,《秘史》把帖廸沙这个人名误为“的的克撒合勒”的地名。
3.第376页,合剌合勒只惕额列惕 Kalakaldzhin Elet 地片名。乌珠穆沁右翼旗有胡卢古尔河潴于阿达克诺尔。胡卢古尔为合剌合勒的异写。此河水色黑,故曰合剌合勒。其流急,故有只惕之称。所经之地皆小沙陀,故有额列惕之名。
按:众所周知,铁木真创业史上最险恶的一战,即合剌合勒只惕之战,是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各部的过程中发生的一次著名的战役。这个地名,《元朝秘史》音 写形式作“”,拉丁文转写Qala
Eled/Qara eled之地地望,至今蒙古史学界颇为关注。而钟先生在这里简单援引抄录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二《成吉思可汗本纪二》的原文时,并没有引用全部原文,所引不全,还漏掉了“牧地”“呼鲁合尔”等几个重要的词汇。当然,屠寄所谓“胡卢古尔为合剌合勒的异写”一说难以成立。
札奇斯钦译注《蒙古黄金史译注》已经检出,然后说:“(卷六一七〇)合剌—合勒只惕—额列惕(
)(沙漠名),一二九页四行作Khalkhachineled作(原文误植为alat)。”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二《成吉思可汗本纪二》,完整的原文是这样说的:“合剌合勒只惕·额列惕地名。见蒙文《秘史》,义谓黑色水之急流于沙陀者。《亲征录》作合兰只之野。旧史本纪作哈兰真沙咜(陀字的误写——引者)。辣施特(拉施特——引者)书作哈兰真额列特,且云地近乞台界。盖近临潢边堡也。《蒙古游牧记》云:‘克什克腾旗东北三百十里有阿达尔图河,源出兴安山,西北流入乌珠穆沁界,北流会呼鲁合尔河。又曰:乌珠穆沁右翼旗牧地有胡卢古尔河,瀦于阿达克诺尔。’呼鲁合尔、胡卢古尔,皆合剌合勒之异文。□图作呼鲁呼儿河,此河水色黑,故曰合剌合勒,其性流急,故纳惕之称。所经之地,皆小沙陀,故有额列惕之名。李侍郎以流入贝尔池之哈勒哈河当之,误甚。”
这里屠寄把“”这个地名比定为流经乌珠穆沁右翼旗的呼鲁合尔、胡卢古尔或呼鲁呼儿河,即呼鲁谷尔河(秃河),此说错误很明显,所以不可取。不过,屠寄同时指出李文田《元朝秘史注》所断定的“”为合泐合(哈拉哈)河之讹谬。其实,屠寄、李文田二人均把“”这片沙地误为河流之名,前者误认为呼鲁谷尔河,而后者误认为哈拉哈河。
笔者赞同“”今地地望大致范围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北境或该旗东北部的说法。当然,这个范围不包括蒙古国东方省南境。更具体一点说,笔者赞同布和哈达先生所提出的东乌珠穆沁旗北部的合剌真戈壁一带,包括合剌真戈壁南部及北部,即著名古代战场“”之地地望所在地的说法。
4.第376页,合剌温只惕 Kavaun-Dzidun 温泉名。位于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北部达巴(坂)梁东麓道旁里许,有汤山之名。《蒙古秘史》写作合剌温只惕,《北征录》作哈剌温只敦,《史集》作合剌温赤敦,《蒙古游牧记》云:“克什克腾旗北百八十里有噶尔达哈尔泊,百九十里有温泉。”
按:合剌温只惕,误。据《元朝秘史》音写形式作“”或“”,蒙古文原文拉丁文转写,应作
,此地应该是合剌温只敦山,而不是温泉名。《元朝秘史》第183节写作“”,第206节写作“”,总译均作“合剌温山”;《圣武亲征录》写作“哈剌浑只敦山”;《元史》写作“哈剌浑山”;拉施特《史集》写作“Qrāūūn Jīdūn”,余大钧先生译作哈剌温只敦。
李文田认为它是肯特山的一个支脉,策·达木丁苏隆与札奇斯钦两位先生沿用了李文田的观点;那珂通世认为它是大兴安岭,王国维援引《元史》、洪钧翻译的《史集》等资料(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对那珂通世的观点作了补充;最近澳大利亚学者罗依果提出“合剌温只敦”意为“黑色的山脊”,其地在大兴安岭索约勒诗(济)山的西麓。目前国内外蒙古史学界一般认为哈剌温山,亦作合剌浑山、哈剌温只都山、哈剌温只敦山,指今大兴安岭。
值得注意的是,《元朝秘史》第150、177节的合剌温合卜察勒qaraγun qabčal(qabčil),总译分别作“哈剌温山”“合剌温山的狭处”。可见,此合剌温合卜察勒qaraγun qabčal(qabčil),也指的是今大兴安岭。
5.第400页,横相乙儿 Qum-Sengir 地片名。《史集》第2卷记述贵由汗本人在距别失八里有一星期途程的地方(误为撒马尔干境内)去世。波伊勒英译本第121页,注95:此地名为“横相乙儿”(Qum-sengir,突厥语“沙岬”)。横相乙儿位于乌伦古河上游某处,大概在该河自北南流急转向西流之处,位于新疆青河县阿尔曼特山东北麓。据《元史·定宗纪》,贵由死于戊申年春三月,即公元1248年3月27日至4月24日之间。
第421页,胡木升吉儿 Qum-sangir 地片名。《蒙古秘史》胡木升吉儿。位于新疆青河县南部。互见“横相乙儿”条。
第416页,忽木升吉儿 Qum-Sengir 地片名。位于新疆青河县青格里河流域。南宋庆元五年(1199)成吉思汗与汪汗伐乃蛮,自忽木升吉儿之地,顺兀泷古水追之,进至乞湿泐巴失之野。
按:钟先生书第421页说:“《蒙古秘史》胡木升吉儿”,误。《元朝秘史》音写形式第158节作“
”,转写Qumšinggir-un ürünggü,总译作“忽木升吉儿地面兀泷古河”。《元史》作“横相乙儿”。横相乙儿、胡木升吉儿、忽木升吉儿,三者均为突厥语Qum-Sengir和蒙古语Qumšinggir的同名异译。在古代蒙古史上,此地因蒙古帝国第三位大汗贵由汗去世之地而闻名遐迩。钟先生书第421页作互见“横相乙儿”条,还差强人意,但第416页,忽木升吉儿条就遗漏了作互见。因此,以上三个条目有重复收录之嫌,而且未能全部做到互见。这是全书统稿时,因编著者粗疏而失检出现的瑕疵。
前引蒙古国X·普尔赖《〈蒙古秘史〉地名考》一文指出:“忽木升吉仑·兀泷古кумшигир-ун урунгу经度90°,纬度46°。该河同发源于阿尔泰山的布勒干、青格勒二河相连,汇成兀泷古河。”
另外,钟先生所说“贵由死于……1248年3月27日至4月24日之间”一句,来自于伯希和《蒙古与教廷》一书。
6.第542页,客勒帖该·合答 Qltaki-qda 地片名。《史集》第1卷第2册云:“成吉思汗从合剌阿勒只惕·额列惕之战回来后,在客勒帖该·合答斡儿·沐涟河地方聚集并清点了军队。”客勒帖该·合答《蒙古秘史》作合勒合河斡儿讷兀地的客勒帖该答地,合勒合河即流入贝加尔湖的哈拉哈河;《亲征录》作斡儿弩兀遣忒哥山或斡儿弩兀·遣忒哥山冈。
按:客勒帖该·合答的地理位置正确。《元朝秘史》音写形式作“
合打(第175节)/
(第191、192节)”,蒙古文原文拉丁文转写,应作keltegei qada。这里所谓“合勒合河即流入贝加尔湖的哈拉哈河”,误甚。很遗憾,本来应该说贝尔湖就变成了贝加尔湖。这里还有一个可能是因校对不精细或印刷错误所致。必须指出的是,哈拉哈河流入贝尔湖(《元朝秘史》的捕鱼儿海子),而并非流入俄罗斯的贝加尔湖Bayiγal naγur。《元朝秘史》第176节总译说:“合勒合河流入捕鱼儿海子处有帖儿格等翁吉剌。”一字之差,竟然把地理空间上的距离拉开至几乎遥不可及的贝加尔湖。钟先生的书作为历史地名方面的大型考论著作,因粗心大意,校对不认真而出现了不应有的错误。贝尔湖和贝加尔湖之间的距离非常遥远。俄罗斯的贝加尔湖距离蒙古国边界大约111公里。当然,离位于中蒙两国边境上的贝尔湖也是距离非常遥远的。因此,这两个湖名不能混淆。
7.第760页,撒阿里客额儿合里勒秃纳兀儿 Haliutu 地片名。即成吉思汗萨里川哈老徒行宫所在地。撒阿里客额儿,为“黄野甸”之义。合里勒秃纳兀儿,即噶老徒(哈柳图)。其地有噶老台岭、噶老台河、噶老台泊。成吉思汗行宫在噶老台泊之边岸,位于客鲁伦河与土拉河源之间的肯特山南岭。殷化行《北征纪略》云:“五月初四日雨雪,暮抵土拉河,御营所期与大将军会兵地也。十三日戊辰晓发,食时已哨得贼,满汉兵骑严阵以待,久之贼不至,大将军遂令整阵而行。可二十里,过淖,至昭莫多。其北大山千仞,矗立如屏,不见所尽处。大山之下,平川广数里,林木森立,有河流其间,曲折环绕,其南出差多于北,渐坦而下,有小山似马鞍横焉,战地也。”屠寄《蒙兀儿史记》案,化行所见之大山,即肯特山之南岭,小山似马鞍者,即噶老台岭,大山下之平川,即撒阿里客额儿,所过之淖尔,即噶老台泊,亦即合里勒秃纳兀儿,其间之河,即噶老台土拉河之别源。
按:钟先生所说有关撒阿里客额儿的方位大致不误,但个别地方还不十分准确。撒阿里客额儿,《元朝秘史》音写形式作“
(第128节)/
里
(第161、177、193、197、250节)”。合里勒秃纳兀儿,《元朝秘史》音写形式作“
(第136节)”。“/ 里 ,蒙古文原文拉丁文转写,应作saari keer-e Hariltu naγur。陈得芝先生指出:“萨里川即《秘史》之撒阿里客额儿(Saghari-keger),意为马臀[形]原野。明初金幼孜扈从朱棣北征经过其地,称之为双泉海,他记载说:‘双泉海即撒里怯儿,元太祖发迹之所。旧尝有宫殿及郊坛,每岁于此度夏。山川环绕,中阔数十里,前有二海子,一咸一淡……西北山有三关口(地名康哈里孩),通饮马河、土剌河。’根据其前后文记载,撒里怯儿位于饮马河(明人给克鲁伦河起的汉名)和土剌河两河上游之间。罗洪先《广舆图》‘朔漠图’所标位置亦同。这个地方确有两个较大的湖泊,据清代地图(康熙《皇舆全览图》,乾隆《内府舆图》),北面一个名噶老台泊,南面的名衮泊。两湖四周是一片很好的草原,即元代之萨里川无疑。其西北之山名杭盖达巴汉,今尚为克鲁伦、土拉两河上游间的通路所经,显然就是金幼孜所说的三关口(康哈里孩),亦即《秘史》第193节记载的康合儿合。还是那珂通世最早指出此噶老台泊就是元哈老徒行宫所在地,这当然是不易之说;而衮泊即《元史·宪宗本纪》所载之军脑儿(《佛祖历代通载》作君脑儿),也是毫无疑问的。”
来源:《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3期
作者:希都日古
选稿:耿曈
编辑:徐萍
校对:檀金玲
审定:王茜
责任编辑:吴雪菲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欢迎来稿!欢迎交流!
转载请注明来源:“江西地名研究”微信公众号
,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