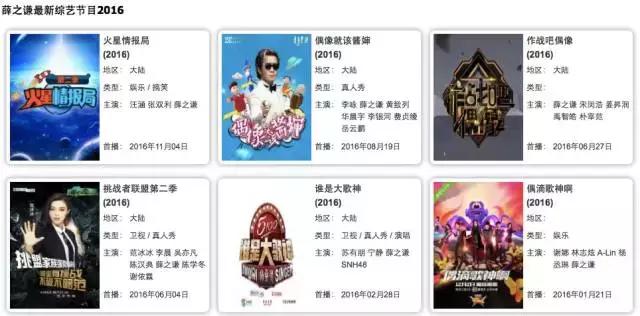真实的冤家路窄的故事(痞子与文人)

就内容而言,《晚熟的人》大致围绕着三个方向展开:《左镰》《口哨与火把》《地主的眼神》这些经典性篇章,反思了历史和文化的若干深层问题;《晚熟的人》《等待摩西》等是对主体性的生成、苦难的化解等问题做的形而上的思索;《斗士》《红唇绿嘴》《贼指花》《表弟宁赛叶》《诗人金希普》等讽刺性作品,则集中塑造了“痞子”和“文人”两类人物形象。前两个方向的内容姑存而不论,此文主要讨论这两个人物形象系列。
何谓痞子?所谓痞子,就是“利欲、私欲百分之百占据了身心,道义、正义从身心中百分之百消亡了的人。他们为了获取‘生存状态优越’或体现这种‘优越’,常常无德、无节、无耻、无行”[1]。他们的行为毫无原则,毫无理想,乏责任感,醉心暴力,欺软怕硬,见风使舵,具有反文化、反价值的特性。《斗士》中的武功、方明德,《红唇绿嘴》中的覃桂英、谷文雨,都是这类人物。
有些痞子生于社会底层,常乏财产,少权力,本属于弱势群体。他们几乎没有资源可资掌控,要争得权力只有依靠人类最为古老的资本——肉体及其衍生出的暴力。在原始社会,只有肉体强壮者在生存竞争中才能占得优势,赢得权力。武功(《斗士》)就是依靠肉体和暴力“出人头地”的。武功出身地主家庭,光棍一条,体质瘦弱,外貌丑陋。在讲究阶级斗争的年代,他这样的条件自然属于弱势群体。但是,他却在“命贱”的根基上,不断同他人打架,依靠肉体与暴力强行为自己拓展出一块权力空间。
有些痞子摆脱了社会底层,生活在不同的职业领域。他们往往非常懂得“借势”,让自己的痞性和职业赋予的权力相结合,更充分地满足私欲。于是,不同领域生出了不同的痞子:官痞、文痞、地痞、法痞、网痞,等等。《斗士》中的方明德就是一个官痞。他1948年入党,参加了抗美援朝,三等残废军人,具有牢固的红色资本,家族势力也十分强大。如果他利用这些资源为人民服务,一定会造福一方;可惜他喜欢做土皇帝,把满足私欲视为人生信仰。他看上了武功的那副祖传的象牙象棋,就变相索取;村里的女人都是他的囊中之物,随便就生一个私生子。他手段狠毒,为打击别人不惜设局构陷,罗织罪名。方明德是基层干部,但对他来说权力带来的不是神圣感和责任心,而是释放“痞性”、满足欲望的手段。
痞子缺乏的是道德感,但往往并不缺乏智商。依靠智商施展破坏力的痞子虽然不回避暴力,但手段更丰富,破坏力就更大,更难以对付。章太炎先生曾提出“俱分进化论”,认为善的力量进化了,恶的力量也在进化。确实如此,社会文明程度提升了,痞子就会利用自由和法治赋予的空间发展壮大自己。平日里痞子多是单打独斗或三两个组成小集团,在犯罪的边缘不断骚动,真正感到切身疼痛的是身处弱势的下层民众。他们往往是小错不断,又难以绳之以法,即便惩处了也很难长久羁押,这就给了他们一定的生存空间。
在《十三步》《丰乳肥臀》《十三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金鲤》《模式与原型》等以往的作品中,莫言塑造了一些知识分子形象,他们大都以受难者的形象出现。在《晚熟的人》中,莫言则主要是聚焦于文坛弊病,讽刺“文人无文”和“文人无行”的怪现状,带有《儒林外史》的风范。这些所谓“文人”,儒雅的面具下掩饰的不过是骗子、小偷、自恋狂的真实身份。
《诗人金希普》中的金希普就是这样的“文人”。春节前县里官员到北京宴请家乡在京名流,金希普挤进来把自己吹嘘成享誉世界的诗人,引起大人物们的赞叹。他又以这次宴会上的合影为“物证”,把自己装扮成手眼通天的人,到处行骗。春节期间他留居姑父家,把他家吃了个底朝天;继之以为表弟安排工作为诱饵,骗走2万元。虚拟的著名诗人的头衔,成了金希普攀附权贵的敲门砖;而同权贵交往的经历又成了他欺骗他人的凭证——经过这样一个传递过程,“文化资本”就转化成了“经济收入”。
金希普是带着文人面具的骗子,武英杰(《贼指花》)则是带着文人面具的小偷。他写过一首意蕴悠长的《贼指花》,算得上诗人;他以斗酒的方式征服彪悍的开船人,算得上男人;他以潇洒的英姿闪亮整个舞场,算得上是女士心中的骑士;他曾是反扒英雄,还曾以贼人的一根手指为女记者复仇,算得上侠士;但是,他在笔会的游艇上偷过钱包,在下榻的客栈里偷过商人的巨款,又确实是货真价实的小偷。鲁迅曾对“无文”“无行”的文人颇为失望,说过一句很“毒”的话:“他们不过是在‘文人’这一面旗子的掩护之下,建立着害人肥己的事业的一群‘商人与贼’的混血儿而已。”[2]鲁迅说的“贼”只是象征意义上的;莫言更“毒”,他用一篇《贼指花》告诉你,这个“贼”字有时会落到实处。
提起自恋,人们就会想起古希腊神话纳喀索斯的故事。《表弟宁赛叶》中的表弟宁赛叶(秋生)就是一个当代的那喀索斯。文学青年宁赛叶盲目地欣赏自己的创作才华,一篇题为《黑白驴》的小说尽管不曾发表,但被他视为惊世之作,声称“一旦我的《黑白驴》面世,你们(指莫言等)这一茬作家,通通都要退下舞台”。
自恋和自私往往是一体两面。“自恋主义文化是这样一个观点的弥散:将自我实现作为生活的主要价值,并且似乎很少承认外部道德要求和对他人的严肃承诺。”[3]固然表面上宁赛叶是文学的信徒,但他既没有献身文学的追求,也没有常年累月的创作实践。在某种意义上文学不过是他证明自己高雅品味和与众不同的幌子,是他试图敲开荣誉和利益之门的砖头。骨子里,他“自我实现”的标准是原始欲望的满足。在锻压设备厂工作,他借恋爱之名玩弄了两位姑娘;入伍从军,他又勾引地方女青年;办野鸡报纸,他炮制负面新闻敲诈地方政府;开办实业,他拿借来的钱挥霍显摆。其实,他并无高蹈的精神追求,恋爱、新闻、实业甚至文学,都构不成他为之奋斗的人生基石,情欲、钱欲、虚荣才是他趋之若鹜的目标。至于自己欲望的实现是否对他人造成危害,是否合乎道德,他丝毫不去顾忌。
自恋者永远走在证明自己正确的路上,任何失败都要做“外部归因”。他们一味沉溺于自我欣赏,在精神内部搞循环,不能正常认知世界,也缺少自我反思能力。“经验表明,生活里的自恋主义者大多是一些自怜自艾的人,生命力在他们身上不仅没有强化反而被大大削弱了;缺乏自立精神导致他们也缺乏真正的自尊品格。”[4]
《晚熟的人》思想丰富,既有反思历史、直面人生的严肃之作,亦有这种亦庄亦谐的讽刺性妙文。我们平时一说到传统社会,就立刻联想到儒、释、道文化。其实,一种被称为“痞性”的反向力量始终暗流涌动——它来自人类原始、粗鄙的动物性,蔑视道德,践踏人性,随时都会释放出瓦解社会秩序的黑暗力量。文坛也总是令人向往,这里有作家、精英龙盘虎踞,可是实际状态是鱼龙混杂,也有带着文人面具的骗子、小偷和轻薄的自恋者游弋其间。莫言“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看到了天下太平背后的污泥浊水,不免讽刺与批判起来,希望社会的肌体恢复健康。
注释:
[1]毛志成:《“痞子”公论》,《文学自由谈》1996年第2期。
[2]鲁迅:《辩“文人无行”》,王得后编:《鲁迅杂文全编》(下),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64-1165页。
[3][加]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程炼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页。
[4]徐岱:《自恋主义与美学问题》,《中国美学》2004年第1期。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