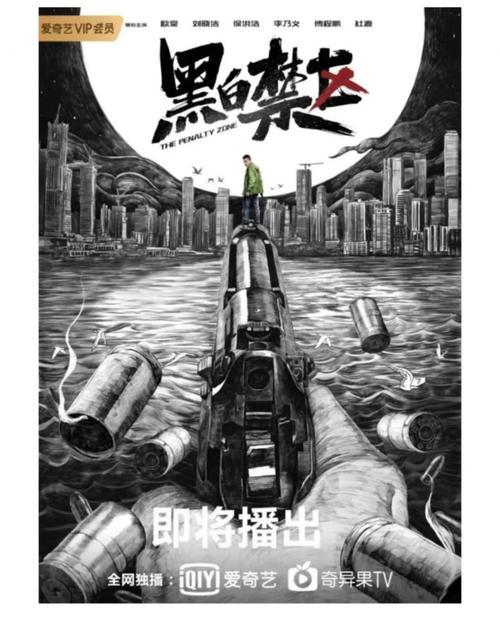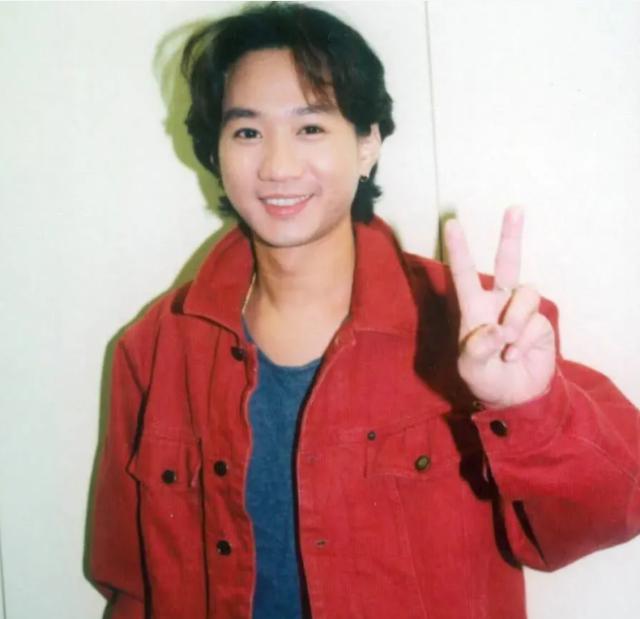曾为马绳子怒摔杯(曾为马绳子怒摔杯)
东方网记者包永婷10月12日报道:“电影对于吴贻弓导演来说不是一部,而是一生。”距离吴贻弓导演去世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上海电影博物馆今天下午举办“电影家宴”特别活动:“月随人归——吴贻弓导演特别纪念活动暨电影回顾展”,邀请吴贻弓的亲人、曾经的合作伙伴,回顾他的光影人生。活动一开始,影迷们纷纷上台献花,表达对这位电影人的哀思。

“在我的电影生涯中,能跟着吴导拍了三部戏,给他当助手,这是我人生最大的幸运。”导演江海洋说。1982年,江海洋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去了正在拍摄中的《城南旧事》剧组,结束后又跟着吴贻弓拍了《姐姐》《流亡大学》。他说:“我导演生涯的场记、副导演、助理导演的全部过程,都是在吴导的教诲下完成。今天我能做一个合格的导演,全是跟着他学的。”
江海洋回忆恩师跟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2018年《流年未肯付东流(吴贻弓)/海上谈艺录》在上海文联签售,吴导对他说:“我们老早在一起的时光老开心。”江海洋想到:“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就是拍电影的时光,电影对于吴贻弓导演来说不是一部,而是一生。”
“想到吴贻弓导演,想说的很多,他是我认识的、在片场从不发火的导演。导演发火很正常,因为压力大、时间紧。我跟了(吴导)三部戏,只看到发了一次脾气,而且脾气发得极大。”当时《城南旧事》剧组在圆明园拍摄最后两辆马车相向而去,小英子看着自己的一位长者离自己越来越远。吴贻弓摔了手中喝水的玻璃杯说:“我说了多少遍,马缰绳要考究的,结果拿来的是麻绳。”随后有人安排去换缰绳,他说自己刚才失态了。“海洋,怠慢我没关系,不能怠慢电影!”江海洋表示,这件事他记一生,吴导是为电影而发火,而不是为哪个人,从此以后再没见他发脾气。“我拍戏也从来不发脾气,不去骂合作的人,这是跟我老师学的。”

吴贻弓的儿子吴天戈也是一位导演。“从小耳濡目染,继承衣钵是挺自然的事。”他表示,其实父母并不希望自己从事这个行业,不过俩人都比较开明。父亲与他的谈话并不多,刚刚踏入工作的时候有过一次。“父亲严肃地问:‘你以后想怎样?’我说:‘我以后也不想怎样。’他说:‘非常好,健康快乐地生活。’”活动现场,大屏幕显示的两张照片,一张是吴贻弓与家人的合影,一张是吴贻弓的单人照,正是由吴天戈提供。“他很幸运,得了癌症会活了11年,快乐地活着。”吴天戈说。
演员向梅参演过吴贻弓执导的电影《月随人归》《流亡大学》。她记得,上海电影制片厂有个习惯,电影开拍前都有导演阐述环节,讨论剧本。“吴导的阐述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场景)。他不拿本,从头到尾,这段戏是近景还是远景,哪个地方什么音响效果,他都能表现出来,音乐是什么就唱出来。我们听了就傻了,从没听过这样的阐述,仿佛在眼前放了一部电影,每个人听完脸上都放着光彩。”

“我的童年里离不开《城南旧事》。”小英子的扮演者沈洁说:“导演就像亲人一样,为了让我跟宋妈(郑振瑶)有亲近感,请郑老师把我带回北京的家住了一段日子,因为故事里的英子可是和宋妈无话不说。没几天,我就和郑老师亲啦,直接就喊起了‘宋妈’,演的时候没有压力。”她也常被记者问导演拍的时候是怎么教你演的?会逗你吗?会故意凶你吗?诸如此类的问题,“我都无法回答,吴导演从不发火,说话声音里有种让人放心的感觉。”
从国外赶回来的张闽有点哽咽地说:“非常幸运跟吴导拍了三部戏,《巴山夜雨》是我的第一部戏,改变了我的一生。他是个非常从容、温和的人,现场给演员讲戏,简洁明了。”她还带来了一份珍贵的书信,来自《城南旧事》作者林海音的4个子女。信中写道:“先慈林海音生前一直喜爱这部电影,《城南旧事》带她回到了童年,带回她对北京的记忆,我们家人也因此片感到光荣和快乐。首先感谢贻弓先生拍摄了如此温馨动人、令人怀念的《城南旧事》。我们没有人能回答死亡是什么颜色,我们一直认为死亡是蓝色的,像天空一样的蔚蓝,因为蓝色带给我们许多想象,贻弓先生,你不会寂寞,因为有许多人会怀念您、感激您,与您隔着无尽的天空和大海对话。”
据悉,10月12日和13日,吴贻弓9部影片《月随人归》《巴山夜雨》《城南旧事》《阙里人家》《少爷的磨难》《流亡大学》《姐姐》《海之魂》《我们的小花猫》将在上海电影博物馆放映,并且全部是胶片版本。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