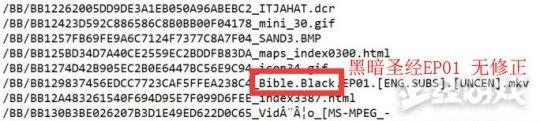满族的历史变化(从DNA层面小议满族历史上的汉化过程)

鄙人基因检测
1,解答满族的蒙古·通古斯成分较低问题。23魔方北方汉族(占比约80%)的解释:
原始社会末期,黄河两岸崛起的北方部落等经过长期的征战、分化与融合,渐渐形成了部落联盟也就是北方汉族的先民。商周及以后又逐渐与北狄、西戎、诸胡、蛮等融合,逐步形成了现今的北方汉族。汉代开始,周边民族以“汉人”代替“秦人”称呼中原居民,汉族渐渐成了民族称谓。到了现代,根据不同遗传标记的研究表明中国南北方汉族大致以北纬30度为界,浙江北部整体上接近北方型而四川盆地整体上接近南方型。由于长期的融合,北方汉族代表的不仅仅是现在的“汉族”人,还包括汉化许久的北方少数民族(例如部分满族人、蒙古族人等)。
南方汉族(占比约3.6%)的解释:
商周以来不断南迁的中国北方居民与南方本地的百越、蛮等逐渐融合,形成了现在的南方汉族,其中北方汉族南迁有三次较为集中的时段,分别是西晋末年、唐中后期和五代、两宋之际,其余的时代亦有规模较大的迁移事件。到了现代,根据不同遗传标记的研究表明中国南北方汉族大致以北纬30度为界,浙江北部整体上接近北方型而四川盆地整体上接近南方型。
蒙古·通古斯(占比约7.6%)的解释:
蒙古·通古斯包括蒙古和通古斯。蒙古部先民居住在额尔古纳河流域,公元8世纪后迁至鄂嫩河上游并繁衍出多个血亲关系的尼仑蒙古和迭儿列斤蒙古两大支系。13世纪铁木真统一蒙古诸部,建立大蒙古国,并融合了蒙古高原中部大漠南北的汉、满、达斡尔等民族,形成了现在的蒙古族。通古斯族群包括锡伯族、鄂伦春族、赫哲族等。从生产生活方式、语言习俗看,鄂伦春族可能与商周时期的肃慎、南北朝时期的钵室韦人有较大关系。赫哲族祖先出自黑龙江流域,可能与古代的肃慎、挹娄、勿吉、女真等有密切的族源关系,在发展过程中融合了鄂伦春、鄂温克、满、蒙、汉等民族。对于锡伯族,有学者认为其祖先为古代居住在嫩江、松花江、淖儿河一带的鲜卑人。
鄙人父方那边黑龙江满族,祖籍辽宁,已知两代母系皆为汉族(辽宁汉族、安徽汉族)。即使鄙人是这个水平,也比已知在各家基因检测机构的绝大部分满族用户蒙古·通古斯比例高,比如23魔方此前有个统计文章《中国满族群体父系单倍群及民族血统构成情况简介》一文:
当代满族群体的民族血统中以北方汉(80%)、南方汉(6.57%)、蒙古-通古斯(3%)、日韩(5%)等成分为主,整体上与北方汉族的情况较为相似。
23魔方为何测不出“满族血统”、或满族用户的通古斯血统比例为何极低,23魔方的解释: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无论经过怎样测试、提纯,满族样本几乎全部落在北方汉族的参考集里。

图源:23魔方为何检测不出满族血统?
2,造成这种现象的第一个因素是通婚。满族是以清代满洲八旗(前身为明代女真)为核心,结合汉军八旗、蒙古八旗等旗人为主体的,有一定历史基础的政治建构人群,自清代以来满洲八旗就与入旗汉人长期通婚且普遍存在(参考滕绍箴、定宜庄、邱唐等文)。自新中国建立后,满族与民人成为了新的婚姻模式。
根据学者在《中国蒙古族、满族与汉族的族际通婚状况》一文对现代满蒙婚姻研究,在多民族聚居地区婚姻模式中,虽然满蒙族内婚姻占据半数,但主要原因是汉族的人口规模和汉族极高的族内婚比例冲淡了满蒙族际通婚强度,因此一些文章说满族多族内婚是存在统计学上的偏差的。在此种情况下满汉婚依然能占比约39%。

不同民族通婚通婚组合的比例
在婚姻模式中,满族族际通婚以“娶的多、嫁的少”为特点,通婚对象以选择汉族为主。

满蒙族际婚主要通婚民族
根据调查,满蒙族际婚姻通婚比例存在地域性特点。以身份为单位,满族族际通婚以北京最多、内蒙古与天津次之,东三省以吉林最高、辽宁最低,出人意外河北是满族族际通婚比例最低的身份,作者认为河北与辽宁通婚比例偏低与两省设置满族自治县导致满族人口高度集中有关。

不同身份满蒙族际婚姻比例
以地级市为单位,满族民族通婚主要分布于人口较多、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这与东北地区人口高度城市化有关。

三类族际通婚主要城市比例气泡图
由于满族长期与汉族通婚与汉化,造成满族血统中占有较高比例的汉族的旁系来源。在23魔方等基因检测机构兴起前,一些大学机构亦曾对满族进行线粒体DNA采样测试,证实了满族在基因层面的汉化现状,如:《满族汉化的DNA证据》。

满族人口经历过曲折性增长的过程。满族人口在清入关前约有60万人,清末增加到约500万,日伪时期1940年普查东北满族人口约268万人,新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全国满族人口242万,1982年满族人口增加到430万,到1990年满族人口猛增到980万。在1982到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8年间,满族人口猛增482万,这些新增人口占据1990年近半数满族总人口,其中因为更改民族成分占比为满族自然增长人口的4倍,这与几年间在辽宁、河北等地设置民族自治县、当地政府推行的民族政策密切相关。因此,设置自治县、造成大量东北、河北自治县区域汉族改报满族,亦是造成满族血统中通古斯成分偏低的原因之一。
4,向汉文化靠拢——满族历史上的汉化过程。如果说清代以来的民族通婚、新中国以来的民族政策是造成满族血统层面汉化的近现代因素,那么,满族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古代样本所显示的血统成分变化则是肃慎族系向汉文化靠拢的古代因素。
2021年,Genomic insights into the formation of human populations in East Asia作者团队根据对东亚新石器以来的50余个遗址、166个古人基因组捕获的测序一文中,有4个(或2个)肃慎族系遗址样本引人注目。

文章选取古代样本地图
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大彼得湾的Boisman遗址是为三层文化遗址,下层博伊斯曼文化层为新石器前期,上层扬科夫斯基文化层属早期铁器时代,根据数据,其遗址两个文化层父系分别为前者C2a-M48、C2a-M504,后者N1a*,血统成分以东北亚人群为主体。一些学者根据器物特点认为此遗址属于先周时期广义上肃慎文化遗存之一。此遗址是否为肃慎文化遗存尚存争议,但至少反应肃慎或比其较早的附近人群遗传水平。
另两个人群为渤海靺鞨与11~13世纪的黑水靺鞨,分别来自Roshino-4、Chernyatino-5墓地,样本信息显示,首例渤海人与黑水靺鞨人古代样本父系皆为O2,黑水靺鞨古人的Y染色体更是细分到M133。可惜的是,渤海古人样本由于俄罗斯考古人员的肢体接触,致使其出现大量西欧亚血统成分,导致样本无效。黑水靺鞨个体的说明显示,这例样本有约43±15%的源自阿穆尔河流域血统(28~58%),剩余的42~72%的成分则来自一位假如历史时期有南方移民的汉族祖先,而这在其附近地区的Boisman遗址两个文化层古人中,汉族的血统成分是极低的。我们认为,至少在靺鞨(或者勿吉)时代,肃慎族系就已经与汉人进行了接触与融合,至少有相当比例的汉人融入进了肃慎族系的部落社会中,这是否与高句丽崛起吞并了辽东汉人有关,有待高句丽时代古代相关人群样本的测序予以证明。

关于黑水靺鞨样本的说明
近期,吉林大学通过对明代野人女真(即兀狄哈)的研究,黑龙江流域绥滨东胜明代墓地古代人群基因组学研究一文显示,该遗址所对应的明代兀狄哈村落人群父系分型为C2a-F1756、N1a-TAT、O2a-F1391以及Q1a-MF1647,前三者为当时村落中的一般部民,即在“纯粹”的野人女真;C2a-F1756与N1a-TAT为东北亚土著,样本A026的父系O2a主要集中于南方以及黑吉地区,很早即融入进了肃慎族系,至墓地所在的时代已经成为了彻底的野人女真。样本编号A109(父系Q1a-MF1647)与北方汉族遗传结构相似,为汉人融入进当地社会通婚产生的第一代后裔。

14个明代野人女真(兀狄哈)的单倍群分型

兀狄哈与古今人群的对比
因此,在野人女真(兀狄哈人)的产生与其遗传结构形成中,亦受到明显的来自汉人的影响。就如李朝实录中“一梁之室,其制与唐人居室相似,此则兀狄哈,昔时抢掳开原卫之人,男婚女嫁,累代而居,故其居室之制如此”、“兀狄哈则室大净洁,又作大柜盛米,家家有双砧,田地沃饶,犬豕鸡鸭亦多畜矣”所展示的都骨兀狄哈村落农业生产生活现象那样,明代中原王朝的农业文明与黑龙江流域的明代野人女真存在持续且广泛的交流。满族历史上的汉化,是文化上向汉文化靠拢、以及与汉族通婚融合相互并轨的。
参考文献[1]旗民不婚?——清代族群通婚的法律规范、实践与意识[J]. 邱唐. 清华法学. 2016(01)
[2]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M].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定宜庄著, 1999:352
[3]清代的满汉通婚及有关政策[J]. 滕绍箴. 民族研究. 1991(01)
[4]程梦瑶.中国蒙古族、满族与汉族的族际通婚状况[J].人口研究,2022,46(02):48-60.
[5]翟鹤书. 满族汉化的DNA证据[D].吉林师范大学,2014.
[6]刘庆相,王元清.满族人口的发展及其构成特征[J].人口与经济,1991(03):47-49 35.
[7]刘庆相.略谈满族人口的历史演进及其特征[J].人口学刊,1995(05):34-38.
[8]Wang, CC., Yeh, HY., Popov, A.N.et al.Genomic insights into the formation of human populations in East Asia.Nature, 591, 413–419 (2021).
[9]杨海鹏,姚玉成.关于肃慎的考古学文化[J].满族研究,2011(01):40-45.
[10]郭孟秀,胡秀杰.商周时期肃慎考古学文化考论[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31(02):125-135 215.
[11]李建. 黑龙江流域绥滨东胜明代墓地古代人群基因组学研究[D].吉林大学,2022.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