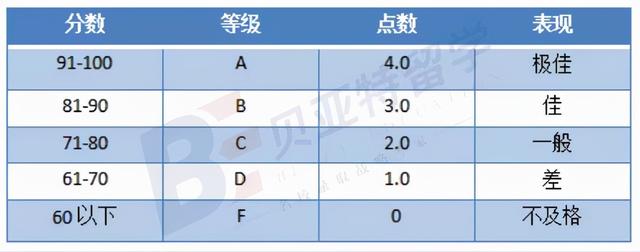植物园序言(植物园里的人世间)
1960年2月16日,农历正月二十,穿一身洗得发灰、套着棉衣的藏蓝中山装、戴酒瓶底儿眼镜的爱新觉罗·溥仪拎着大网兜,外带一个绑着被褥的背包,拿着北京市民政局的介绍信,在北京西郊四王府公共汽车站下了车。
四王府是汽车终点站,在站上等候他的人将他接到了四站地外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园。他网兜里那些暖水瓶、洗脸盆、铝饭盒、刷牙缸、毛巾,包括被褥,都是从抚顺战犯管理所带来的——1959年12月4日,溥仪被特赦后,需要先参加一年劳动以培养对普通劳动人民的感情,再安排正式工作,根据他的意愿与兴趣,周恩来特地为他选定这里。

1957年的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园 (孟慧忠供图/图)
菩提树
当年2月19日,溥仪开始“工作”:浇水和搞卫生。第二个月转到扦插繁殖温室,学会了播种、移栽幼苗、上盆、换盆和松土,三个月后又被分配到观察温室和繁殖温室,学会给一品红、一品白、一品粉、倒挂金钟剪枝,为盘子花、金边万年青、仙客来换盆……劳动之余他还收集各色植物标本、阅读植物学书籍、写了几十页心得。
住在灰砖房职工宿舍第二排东头第一间的“皇帝”,生活自然是不能自理的:衣服扣子系错位、经常迷路、枕巾夹在棉裤和衬裤间的糗事数不胜数。上级安排他半天劳动、半天休息,周日可以回城——特赦回京后,他暂住西城区前井胡同6号胞妹“五格格”金韫馨家中。
休息时间,他也很忙碌:来植物园一个月,俨然已成为这里最著名的“标本”——前来参观末代皇帝新生活的国际友人、外宾络绎不绝;除了参加植物园的民兵组织、副业生产,他还常去香山饭店改他的“前半生”——为了修改后的《我的前半生》能够尽快付梓,群众出版社的李文达在饭店蹲点,帮他改写。

溥仪在植物园温室工作。 (孟慧忠供图/图)
在工友们和“溥仪先生”工作的年代,中科院植物研究所还在西郊公园(今北京动物园)内,但这香山脚下的植物园,从那时起直至今日被划入国家植物园,一直都是植物研究试验区。1928年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与尚志学会在北平石驸马大街成立静生生物调查所;1929年,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成立后,曾在西郊公园建立植物园,然而囿于经费有限和战乱影响,均收效甚微。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后,将两所合并,成立中科院植物分类研究所,后重新选址香山脚下香颐路(今香山路)南侧建立园区。
如今,这里已是我国北方生物多样性和种质资源迁地保护及可持续利用研究的重要基地,树木掩映各种实验室,路边更有图片展览,介绍研究所的重大成果,诸如“相分离驱动叶绿体内蛋白分选的新机制”云云,让人不明觉厉。
摄影发烧友的长枪短炮,自然不会对准科研建筑与叶绿体——园区收集保存植物七千余种,建有丁香园、宿根花卉园、环保植物区、壳斗科植物区、水生与藤本植物区等十余个专类植物展区和一个热带亚热带植物展览温室,汇集两千多种植物:多肉、棕榈树、阴生植物、食虫植物……还有一株“友谊之树”——1954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带来从菩提伽耶佛祖坐禅的大树上取枝条扦插培育而成的菩提幼苗,赠送中国,以示中印人民的友谊——那棵大树,就是阿育王的女儿僧伽蜜多折枝带到斯里兰卡,成树后又折枝带回菩提伽耶重新栽种的。
植物如同文化般生生不息。当年装在紫砂盆里只有五片叶子的15厘米菩提幼苗,如今在展览温室中,已经“亭亭如盖”了。
可以确定的是,菩提树的养护和溥仪并不相关,植物园的“学霸气氛”也和他格格不入,但并不妨碍他在这里拿到选民证,并将这里视作“第二个家”:1960年5月26日,蒙哥马利元帅访华期间,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招待宴会上,周恩来向蒙哥马利介绍溥仪:“这是过去的宣统、‘康德’皇帝,现在我们都在一起了。”蒙哥马利问起他的工作情况,溥仪说:“在植物园,很有兴趣。”

早期的植物园(南园)温室 (孟慧忠供图/图)
白皮松
彼时,同样在寿安山南麓、香山脚下、与溥仪的“单位”一街之隔的路北,北京植物园亦刚建成不久。
1954年,中科院植物学研究所的青年学人王文中、董保华、胡叔良、孙可群、吴应祥等上书中央,提出“首都今后一定要有一座像苏联莫斯科总植物园一样规模宏大、设备完善的北京植物园”。1956年,由中科院与北京市联合上报国务院的“筹建北京植物园建议书”,很快得到批复,并拨付560万元经费用于第一期建园工作。
1957年,中科院植物学研究所和北京市园林局共同组成了专家规划设计委员会,以莫斯科总植物园为蓝本,对北京植物园进行了总体规划设计:香颐路以南为试验区(即“南园”),以北是开放游览区(即“北园”),自然形成两个独立单位。上世纪90年代,中科院植物学研究所从动物园迁至南园内,南北两园各自发展演变。
“北京只有一个植物园,即北京植物园,不能分。分开后南园缺少土地,北园缺少科技。”1984年,病危中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俞德浚教授还在语重心长地建议。他的夙愿,直到2022年4月18日才得以实现:人们乘坐西郊线来到“植物园”站,下车看到的不再是“北京植物园”,大门前景观石上取而代之的是“一统”的“国家植物园”。
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合作共建的国家植物园,已收集各类植物1.5万种、濒危植物近千种;拥有亚洲最大植物标本馆、6个国家花卉种质资源库和国际海棠品种登录权。

今日国家植物园 (视觉中国/图)
两园相对,各具特色——如果说南园的风格是“以科学为遵循,追求植物之真”的话,那么北园的氛围则是“以美学为引领,追求植物之美”。从北园东南门沿中轴路向北行进,月季园、桃花园、芍药园、丁香园、宿根花卉园与银杏松柏区、槭树蔷薇区、椴树杨柳区、木兰小檗区、悬铃木麻栎区交错映衬,就连路西侧貌似有些突兀的热带温室,都是20世纪90年代北京十大建筑之一,外观以“绿叶对根的回忆”为主题,设计出根茎交织的倾斜玻璃顶棚,其下“囊括”了热带雨林、四季花园、沙漠植物、专类植物四个展区。
各园亦各具风情。木兰园颇富西方园林风景趣味,二乔木兰尤为难得,每逢早春,玉树琼花,清香四溢,搭配青桐、雪松、紫薇、洒金柏、白皮松、大叶黄杨,以及秋天才显露艳色的红枫,韵味十足。而卧佛寺附近的集秀园,则在方寸之地,运用中国传统园林置景手法,采用大片竹林衬托空间,又点缀少量花木,使整园“庭院深深”,精炼别致。春季粉白西府海棠、朱红碧桃相映生辉,夏季有粉嫩合欢争奇斗艳,入秋银杏和槭树黄红相间,隆冬季节,成片白皮松蔚为大观,特别是金银木,红果累累,有若朝阳。一处“角落”,却在人们竹下花憩之时,产生“万竹引清风”“秋风动枫枝”之感。
植物园以展示中国东北、华北、西北地区植物资源为主,兼顾部分华中、华南观赏植物,当然也有“外来物种”: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赠送的美洲红杉、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赠送的樱花树、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赠送的金蝶兰……有“名人植物”,亦有名人之墓。植物园内及周边安葬了许多近现代名人:民国时期的烈士高仁山、民国总理张绍增、军阀孙传芳、“洋灰大王”王锡彤、学者冒鹤亭……出植物园西门步行约10分钟,亦有梨园墓,梅兰芳和马连良的墓地均在彼处。

梁启超墓 (视觉中国/图)
园内最著名的墓地当属园东北的梁启超家族墓。梁公逝世后,与其妻李蕙仙合葬于银杏松柏林中,三面环山、林木茵秀,墓园由白色砌筑石墙包围,阳光透过松柏树梢细碎地洒下,十分幽寂肃穆。
步入墓园,1931年由长子梁思成设计的墓地,正中平台上的墓碑、墓顶和供台衬墙均为土黄色花岗岩雕成,前后浑然一体,坐北朝南的墓碑正面刻“先考任公府君暨先妣李太夫人墓”,却无碑文,亦无其他记录生平之文字,这是梁启超的遗愿——不用浮词。
墓旁还有一个小墓碑,葬梁之继妻王桂荃,她为梁启超生育六子女,将九个儿女抚养成才,家族后人在碑后种下一株白皮松,命名为“母亲树”。主墓西南还有三座小墓,安葬梁的三个子女梁思礼、梁思庄、梁思忠。
砖砌甬道两侧低矮冬青外,各伫立一座康熙年间的高大石碑——这个是梁家从没落皇族墓地买来的废碑,准备磨掉文字重新刻字,后因财力枯竭而弃置于墓园内。墓园西侧又有八角亭一座,通体石构,四面辟门,亭顶覆以琉璃瓦,亦出自梁思成之手。亭内空空如也——最初设想在亭中立梁启超铜雕像,后也因经费问题而作罢。而今,在宁静的黄昏,立于亭中,是植物园远眺观景的绝佳时刻——百多年前梁公经历的澎湃风云和鼎沸人声,都已经化作秋蝉之鸣与风动松涛的声籁。

静听风动松涛的声籁,山上为乾隆年间留下的碉楼。 (孟慧忠/图)
水杉林
植物园内的清代遗物并不仅存在于梁墓内——墓园南方不远,即有清代碉楼。乾隆十二年(1747年),因在平叛四川金川土司叛乱的金川战役中损失惨重,乾隆帝下令在香山一带旗营间仿金川建筑修建碉房碉楼,让士卒训练攀爬云梯,并于1749年设健锐营,在此“依山为碉”,日常演练。据记载,香山地区曾建有68座碉楼,如今仅存6座半,其中保存完整的两座,就位于园内澄明湖东西两侧。
游人从园东侧健步道信步而行,能找到的通常是上世纪90年代复建的三层碉楼。碉楼旁又有清初修建八旗军营房所挖的正白旗古井,亦有碑林,立从香山地区搜集的古碑14座。
敦敏在游碉楼后所写《西郊同人游眺,兼有所吊》诗中写:“秋色召人上古墩,西风瑟瑟敞平原。遥山千叠白云径,清磬一声黄叶村。”碉楼、古井、碑林,以及它们之南的曹雪芹纪念馆,都是“雪芹小道”的一部分。1971年4月,此处正白旗村39号院住户舒成勋在粉刷墙壁时,发现内壁上有8首题壁诗,其中一首落款的“拙笔”与据说为曹公遗物的黄木书箱上的“拙笔”暗合,又有“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少;疏亲慢友,因财而散世间多”的对联,与传说中曹公送给友人卾比的对联大致吻合,不过多了句尾“真不错”三字——经多方考证研究,认定此处为曹公晚年著书处,“呼应”敦诚诗作《寄怀曹雪芹霑》中所写“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一时掀起红学、曹学讨论与口水齐飞。
1984年,以正白旗村39号为基础建立的中国首家曹雪芹纪念馆在此开馆,因无定论,故谨慎地并未以“故居”定名。如今馆外门前古槐让人步入“门前古槐歪脖树,小桥溪水野芹麻”的情境;沿台阶进入带女儿墙的护院,矮篱环护,石径蜿蜒,院中修竹,别具风韵,形成古朴清雅的文化氛围,再现曹雪芹绳床瓦灶著书黄叶村的生活场景。村内辟菜园、药圃、瓜棚,设石碾、石磨、辘轳,追摹曹公时代的河墙烟柳;又有芹溪茶舍,售卖“仿制”的“王夫人舍不得喝、宝玉挨打才有的喝”的玫瑰清露——第二杯半价。

黄叶村曹雪芹纪念馆 (视觉中国/图)
曹雪芹纪念馆亦是雪芹小道的起点,据说当年曹公居此,常到山后访友,诊治病人,往来山中,走出一条从黄叶村向西北,经关帝庙、卧佛寺、樱桃沟,到达寿安山后白家疃的小道。10公里小道沿途颇多自然美景与文化景观点缀,古槐、翠竹、水杉与碉楼、碑林、名寺彼此辉映——曹雪芹这个“关键词”,串联了植物园内中部至西北部的重要文化空间。
出曹雪芹纪念馆向西,沿中轴线直向北,至路尽头山坡,著名的十方普觉寺——卧佛寺,就近在眼前了。寺庙始建于唐代贞观年间,初名“兜率寺”,寺内古树参天,花木扶疏。穿过琉璃牌坊、山门殿、天王殿、三世佛殿,当得知卧佛殿门额悬“性月恒明”匾为慈禧太后所题之时,几乎所有人都会举起相机或手机——殿内供奉身长5.3米、重54吨的元至治元年(1321年)铜铸释迦牟尼卧佛,以及环立十二圆觉塑像,是禁止拍照的。
据《北京植物园志》载,园内“有古树名木1197株,300年以上的一级古树名木121株,二级古树名木1076株”。卧佛寺三世佛殿山墙东西两侧,就各有一株高大银杏,据说为建寺时所栽,每至深秋,明黄扇叶在蓝天红墙的衬托下,格外明丽璀璨。天王殿前还有一株古蜡梅,是外层黄色、内层淡紫的“九英梅”,有“京城蜡梅之冠”的美誉。此梅曾一度枯萎,而后又发出新芽。曹公写怡红院中海棠枯萎,忽又于次年重新开花,据传就取自卧佛寺“二度梅”的素材——此说并非空穴来风,他居西山时,友人说他常“寻诗人去留僧舍”的。

卧佛寺 (孟慧忠/图)
而樱桃沟内“赐予”曹雪芹灵感的风物似乎更多——香山地区有民谣,“退谷石上松,人称木石缘。巨石嶙峋宝,甘泉溢水甜”——水源头、元宝石、石上柏,是这里的“三绝”。
“水源头”在樱桃沟尽头,这里曾是一处泉眼,现在的水流则是从山上流下来的。紧挨“水源头”即是体量巨大的“元宝石”——它就是大荒山青埂峰下的顽石。“元宝石”南侧的山坡上耸立一块高十余米的巨石,一株侧柏在巨石顶端破石而出,因民间松柏混称,“石上松”或“石上柏”之称便传开了。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前朝进士孙承泽隐居樱桃沟,之后廿载光阴用来研究北京史地,写下《春明梦余录》和《天府广记》。他在《春明梦余录》中记述石上柏:“独岩口古桧一株,根出两石相夹处,盘旋横绕,倒挂于外,大可数百围。色赤如丹砂,夫人不能拊虬龙而谤视之,使得谛视,当如此桧矣。是又岩中之奇者也。”据说曹雪芹受此景启发,写出“木石前盟”的故事。
隐居于此的孙承泽自号“退翁”,将樱桃沟称作“退谷”;后清末举人、古物陈列所第四任所长周肇祥居此,民间又将这里称作“周家花园”,别墅门额上的“鹿岩精舍”,即为周肇祥所题。如今这里仍以富于野趣而著称,沟内溪流清澈,鸟鸣声声,游人可以一边观赏玉玲花、青檀、红松等珍稀植物,一边行走在曲曲折折的木栈道上——它盘桓在遮天蔽日的水杉林中,徜徉其中,宛若回归原始森林。
蔚然成林的水杉,是上世纪70年代从湖北神农架引进的,今日已形成中国北方地区面积最大的水杉林;作为孑遗物种,水杉一度被认为已经灭绝,上世纪40年代末,植物学家胡先骕和郑万钧联名发表论文,颠覆了“水杉属植物早已灭绝”的观点,震动世界。
水杉林和樱桃沟,可以看作植物园的一个缩影——在叠合多重空间中的缩影,一个充满生机的植物空间,让多种文化与记忆在此呈现和交融。相比每每人满为患的香山公园,植物园少了几分喧嚣,多了一丝宁静,山水相衔,别有一番景致,而诸多人文历史遗迹,又为草木增添几缕文秀之气——它总是内秀深藏,爱之者独爱之,就如安放在湖边、日本艺术家空充秋创作的雕塑《茁·生》,植物园中的花草石与人,都“向上延伸”,记录了生命的萌动与成长。

樱桃沟 (视觉中国/图)
溥仪自是“爱之者”之一。“我是一个渺小的人,我的分量不过如同花园中的一粒花种,但我却是六亿五千万中的一个”,1961年3月6日,在植物园劳动锻炼了383天的他,离开植物园,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整理、编写和审议清末、北洋政府相关文史资料。自此之后,他每每以园丁身份为荣,侍弄花草亦成为他晚年的爱好,还多次回园看望工友们——只是仍然会坐错车和迷路。
1964年3月,第三稿《我的前半生》始得出版,在全世界引起轰动——这自然是可以想见的,毕竟,“皇帝”比水杉更能吸引眼球。
张亚萌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