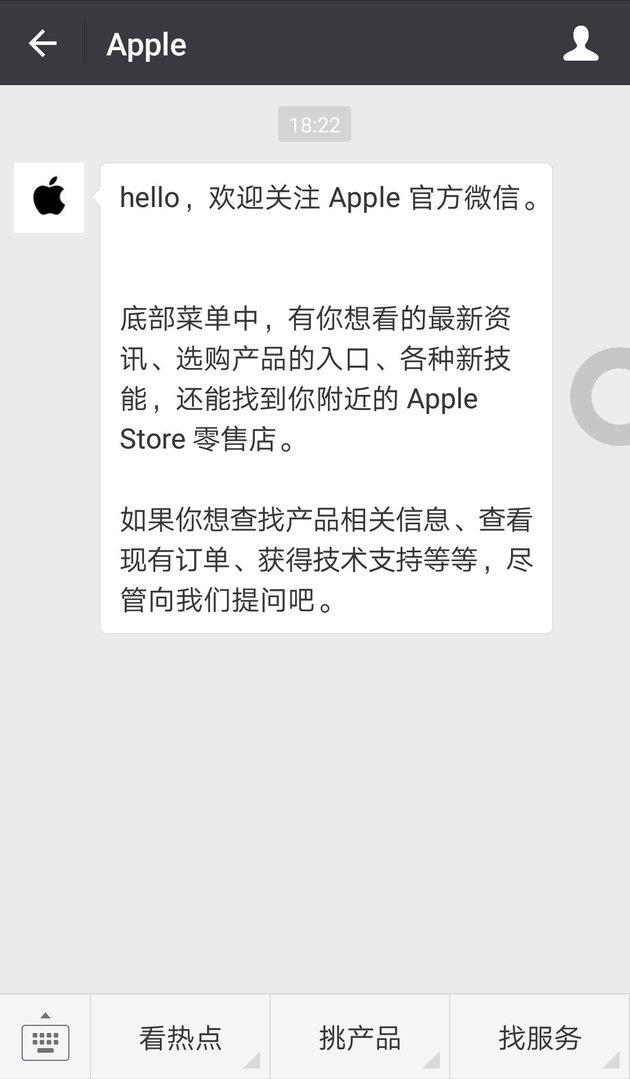周王朝历史人物(周荣从非溺于释氏)
感谢刘缙老师提供宝贵信息
原文载姜锡东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30辑
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
从“非溺于释氏”到“曾亲佛座”
——宋代史籍对宋太宗与佛教关系的书写与塑造
文丨周荣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西安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研究所副研究员
内容提要:当前学界一般都认为宋太宗是一位崇佛的君主。考察宋代史籍、佛教文献,不难发现有宋太宗与佛教相关事迹的大量记载。但在不同的史料记述中,宋太宗与佛教的关系又呈现出差异,甚至是截然不同的面貌。《宋太宗实录》称宋太宗“非溺于释氏”,呈现的是其理性对待佛教发展的形象。《宋史·太宗本纪》塑造的是太宗更重道教的形象。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宋太宗似乎是一位“崇尚释教”的崇佛皇帝。而在释道法:《佛祖统纪》记载里,宋太宗则是一位“曾亲佛座”的佛教转世弟子形象。实际上史料中呈现出“清静无为”、“非溺于释氏”、“崇尚释教”抑或是“曾亲佛座”这些截然不同的形象,是著史者出于不同目的对宋太宗在不同时期与佛教关系进行放大的结果。通过对比分析这几部重要文献中太宗与佛教关系史料,既有助于厘清宋太宗与佛教的真实关系,也可以了解宋太宗对待佛教态度的变化及其背后动因。
关键词:宋太宗;崇佛;形象;书写

宋太宗是宋太祖的胞弟,也是宋朝的第二位皇帝。历史上宋太宗被认为是“得乎丘民而为天子”[1]的贤君。除了帝王功业外,宋太宗还非常留心释道两教。翰林学士宋白在为拟定宋太宗谥号的奏议中提到“(太宗)释老之教,崇奉为先,名山大川,灵踪圣境,神祠仙宇,经之营之”[2]。对释道两教的尊崇被大臣写入拟定谥号的奏议,说明当时的北宋官方认为崇奉释道是宋太宗的统治功绩之一。目前,诸多学者综合不同史料的记载,围绕宋太宗与佛教关系、宋太宗的佛教见解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3]还有学者对史料中宋太宗崇佛记载的传说进行辨伪。[4]虽然对于宋太宗崇佛问题已经形成大量研究成果,但对不同史料中宋太宗与佛教关系差异关注较少。记载宋太宗与佛教关系较为集中的文献里,除了《宋太宗皇帝实录》(以下简称《宋太宗皇帝实录》)《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等由儒家文人撰写的基本文献外,还有由僧人撰写的《佛祖统纪》等佛教史书。受到政治立场、现实需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各书呈现出的宋太宗与佛教关系并不一致的。因此,本文拟从以上史书所塑造的宋太宗与佛教关系出发,探讨宋太宗崇佛形象的变化,力求把握在这一变化背后隐含的历史真相。

宋太宗 画像
一、官修文献中的宋太宗与佛教关系
《宋太宗皇帝实录》《宋史·太宗本纪》是对宋太宗与佛教关系记载较多的官修史书。此外,《续资治通鉴长编》也保存了大量宋太宗和佛教关系的记载。虽然《续资治通鉴长编》是私家所修史籍,但与一般的野史不同,李焘曾分四次将《续资治通鉴长编》上呈朝廷。宋孝宗“诏藏秘阁”,还称赞“其书无愧司马迁”。除了高度评价《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孝宗还“许焘大书《续资治通鉴长编》七字,且用神宗赐司马光故事,为序冠篇,不谓其止此”[5]。这充分说明了《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的权威性和真实性得到了南宋政府的认可。因此,因此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官修史书。
《宋太宗皇帝实录》《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虽同为官修史书,但其中所呈现出的宋太宗与佛教关系却各不相同。
(一)《宋太宗皇帝实录》对宋太宗与佛教关系的书写
现存《宋太宗皇帝实录》所记载的宋太宗与佛教关系史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佛教徒的管理。如宋太宗下诏加强对于僧人度牒的管理,“先是,祠部给僧、尼牒,并传送诸处,州长吏亲给,如闻吏为奸,募人以缗钱市取,赍以至外郡卖焉,得善价,即付与之,自今所在,宜奉行前诏,违者重致其罪”[6]。二是对修建寺院的记载。《宋太宗皇帝实录》中宋太宗所修建的寺庙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新建寺庙,如将自己出生之地修建为启圣禅院,“六年而工毕,所费巨数千万,计殿宇凡九百余间,皆以琉璃瓦覆之”[7]。另外一种则是应地方官员和百姓请求由宋太宗批准修建的寺庙。三是前往寺院祭拜。每逢中元节,宋太宗都会前往寺观进行参拜。如太平兴国九年(984年)三月宋太宗就专程“驾幸兴国寺”[8]。
检视《宋太宗皇帝实录》中的这些记载,能够发现《宋太宗皇帝实录》在记录相关史料时进行了文本处理,从而展现出宋太宗“非溺于释氏”的形象。从以下几则史料可见一斑:
《宋太宗皇帝实录》记载,雍熙二年(985年)正月宋太宗下诏“应天下佛寺、道宫,自来累有诏书约束,除旧有名籍者存之,所在不得上请建置”。仅从诏书内容来看,似乎对佛道两教都进行了限制。但史官在诏令之后对出台背景进行了解释,“初,有僧乞于近城之地积薪自焚,上以其惑众,令配流远恶处,仍毁其所居院舍”。宋太宗还就僧人要求增建寺院对宰相进一步解释“近日多奏请建置僧院,有十余间屋宇,便求院额,甚无谓也。多是诳惑闾阎,藏隐奸弊,宜申明禁止之”。《宋太宗皇帝实录》希望通过这一记录来说明宋太宗限制释道的诏书主要是针对寺院,尤其是对希望通过新建寺院以扩大影响力的僧人给予严格管控。[9]
《宋太宗皇帝实录》在处理宋太宗前往寺观祈福的记载时仍不忘平衡释道关系。如太平兴国九年(984年)的中元节,宋太宗就分别前往建隆观和太平兴国寺。宋太宗在建隆观还专门对宰相说“道门以冲澹为本,夫道者,天地万物之祖,而其教终微,岂主之者非其人乎?”从史官的记录来看,宋太宗对于道的定位是“天地万物之祖”。
《宋太宗皇帝实录》还有意将宋太宗亲近佛教与亲近道教行为放在一处。而且明显表现出在两教中太宗对于道教的支持规格略高。如宋太宗“御制《莲花心轮回文偈颂》十部,共二百五十卷,回文图十轴,以示宰相、近臣”[10]。其后文记录了“城南太一宫成,命枢密直学士张齐贤、司天春官正楚芝兰祠五福太一”。张齐贤请求用“祀天之礼”“杀其半,又小损之”,宋太宗在此基础上增加教坊灵官百人“如汉祀之制”。相较于将御制偈颂和图给宰相、近臣阅看的私人行为,宋太宗用“祀天之礼”祭拜太一神,展现出宋太宗对待道教要更加重视。再如至道二年(996年),内侍裴愈按照宋太宗旨意探访到了王羲之兰亭旧迹。上奏“僧子谦状预建佛庙殿阁,以藏所赐御札,望赐名额”,宋太宗遂赐名天章寺。紧跟着裴愈又上言称“茅山道馆凡九处,有水田三百顷,并免租税,令金坛、句容两县籍入之,岁量供给外,余蓄藏以备修葺及三元斋醮”,宋太宗也准奏了[11]。一边是允许新建佛寺并赐名,另一边又为茅山道馆的三百顷水田免租税,《宋太宗皇帝实录》希冀通过文本平衡释道的意图非常明显。
除了平衡释道之外,《宋太宗皇帝实录》还有意消解宋太宗的崇佛行为。以泗州僧伽塔为例,《宋太宗皇帝实录》里仅有泗州向皇帝报告“僧伽塔白昼有光,民燃顶及焚指、断臂者数千人,吏不能禁”。[12]这条记载呈现出官吏没有能够有效地制止民众“燃顶及焚指、断臂”等狂热的崇佛行为,刻意规避了僧伽塔乃是由宋太宗授意修建的背景。
除了在史料编排上进行文本处理之外,《宋太宗皇帝实录》还通过删减、篡改宋太宗话语淡化宋太宗的崇佛行为。宋太宗在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和雍熙二年(985年)分别向大臣解释了自己翻译佛经和建内道场的目的。宋太宗的这两段言论在《宋太宗皇帝实录》《续资治通鉴长编》与《佛祖统纪》均有记载。不过三种史料却通过文本处理让太宗言论意思截然不同,具体记载详见下表:
表1:太平兴国八年宋太宗翻译佛经记载对比表
|
实录 |
长编 |
佛祖统纪 |
|
浮屠氏之教,有禆政治,而梁武舍身为寺家奴,布发于地,令桑门践之,此真大惑,朕甚不取也。先是,胡僧自西域赍贝多叶经至,朕因令以华语译之,殆百馀卷。虽小道,亦有可观,卿等试之。盖存其教耳,非溺于释氏者也。[13] |
浮屠氏之教有禆政治,达者自悟渊微,愚者妄生诽谤,朕于此道,微究宗旨。凡为君治人,即是修行之地,行一好事,天下获利,即释氏所谓利他者也。庶人无位,从或修行自苦,不过独善一身。如梁武舍身为寺家奴,百官率钱收赎,又布发于地,令桑门践之,此真大惑,乃小乘偏见之甚,为后代笑。为君者抚育万类,皆如赤子,无偏无党,各得其所,岂非修行之道乎?虽方外之说,亦有可观者,卿等试读之,盖存其教,非溺于释氏也。[14] |
佛氏之教有裨政理,普利群生,达者自悟渊源,愚者妄生诬谤。朕于此道,微识其宗,凡为君而正心无私,即自利行也;凡行一善以安天下,即利他行也。如梁武舍身为奴,此小乘偏见,非后代所宜法也。[15] |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对宋太宗在太平兴国八年言论以《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最为详实和准确。这从南宋曹彦约《经幄管见》中可以得到佐证:“此番僧新献贝叶,今以华言译之,无所增减。朕于此教深悟宗旨,凡为君治人,却以修行之地,行一好事,天下获利,即释氏所谓利他者也。凡庶人无权无位,纵或修行自苦,不过独善一身。如梁武帝舍身为寺家奴,此真大惑。书之史册,为后代小。为君抚育万类,皆如赤子,无党无偏,各得其所,岂非修行之道乎?方外之说,亦有可观者。盖行其教,非溺于释氏也”。[16]对照《续资治通鉴长编》和《经幄管见》的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到史官在修《宋太宗皇帝实录》时有意对宋太宗言论进行了处理。一方面将宋太宗对于大小乘佛教自利、利他理论的理解全部予以删除;另一方面将“虽方外之说”修改为“虽小道”。《宋太宗皇帝实录》的编撰者通过对宋太宗言论进行修改的方式,希望营造出宋太宗虽然翻译佛经,但认为此举实为“小道”的印象。以此消解因翻译佛经而形成的宋太宗崇佛的形象。
《宋太宗皇帝实录》通过选择史料和文本处理等方式,希望营造出一个致力于平衡释道,“非溺于释氏”的宋太宗形象。
(二)《宋史·太宗本纪》对宋太宗与佛教关系的书写
《宋史》虽是官修史书,就记载宋太宗与佛教关系史料的丰富程度而言,较《宋太宗皇帝实录》《续资治通鉴长编》相去甚远。《宋史·太宗本纪》对于宋太宗与佛教关系记录较少,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宋太宗修建寺庙,如修建平晋寺、启圣院等。二是前往佛寺祈雨雪。三是置译经院。四是对僧人的管理,如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九月,令给西京诸道给沙弥度牒。[17]
这些内容虽然并不丰富,但在《宋史·太宗本纪》中仍能看到史官有意营造太宗更重道教形象的意图。比如,《宋史·太宗本纪》记载有六处宋太宗下令修建道观的记载,分别是“诏作北帝宫于终南山”[18]“诏作苏州太一宫成”[19]“诏作太一宫于都城南”[20]“诏作上清宫成”[21]“以宣祖旧第作洞真宫成”[22]和“诏作寿宁观成”[23]。可以看到史官在记录宋太宗修建道观时,除了以宣祖第为洞真宫外其余均使用了“诏作”二字。文字上传达出这些道观是以皇帝诏令的形式进行修建,说明宋太宗对于修建道观的重视和对道教的崇敬。而对宋太宗修建佛教建筑的记载就是另外一种处理方式。如“丁酉,以行宫为平晋寺,帝做平晋记刻寺中”[24],“丙子,置译经院”[25],“诏以帝所生官舍作启圣院”[26],“诏作开宝寺舍利塔成”[27]。两者对比能够看到,相比修建道观的六处记载,修建佛教建筑的只有四处,而这四处记载中只有两处为“诏作”。除了措辞上的差别,以上所有新建寺观,只有道教的太一宫多次在《宋史·太宗本纪》中出现。如“甘露降太一宫庭”[28],“八月丁酉,亲祀太一宫”[29]。这些记录都营造出宋太宗与道教的关系远比和佛教的更为密切。
除了以上这些区别之外,《宋史·太宗本纪》对于记载宋太宗与释道人物交往上也有很强的倾向性。《宋史·太宗本纪》记载三则宋太宗与道士丁少微往来: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宋太宗“召华山道士丁少微”[30]。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的九月,“华山道士丁少微诣阙献金丹及巨胜、南芝、玄芝”。同年“十一月庚辰,放道士丁少微归华山”[31]。而《宋史·太宗本纪》中与僧人有关的记载仅有“以天竺僧天息灾、施护、法天并为朝请大夫、试鸿胪少卿”一则[32]。两相对比能够明显看到,《宋史·太宗本纪》中呈现出宋太宗与道教人物来往更加密切,迎来送往间关系非常亲近。而与僧人交往则仅记事,没有提及封赏是因译经而起。
虽然《宋史·太宗本纪》里对于宋太宗处理释道事务的记录不多。但从有限的记载中依然能够发现史官保持了《宋太宗皇帝实录》大体一致的编撰方向,即塑造一个平衡释道关系,更重道教的皇帝形象。
(三)《续资治通鉴长编》对宋太宗与佛教关系的书写
相较于《宋太宗皇帝实录》和《宋史·太宗本纪》,《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对太宗从事佛教活动的记载更加丰富和全面。其中尤以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到雍熙三年(985年)这七年间最为频繁。这段时间也是太宗大规模译经的时期。因此,通过译经活动可以管窥《续资治通鉴长编》对于宋太宗崇佛行为的记载。
第一阶段译经启动。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北天竺迦湿弥罗国僧天息灾、乌天曩国僧施护相继来到汴梁。听到天息灾到来的消息,受到过太祖赐紫方袍的中天竺摩伽陁国和尚法天也随即返回京师。众多域外高僧是自发聚集还是宋太宗有意邀约已不可考,但是外僧齐聚京城使得译经成为可能。于是宋太宗下诏在“太平兴国寺建译经院”准备翻译佛经[33]。宋太宗对此事非常重视,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译经院建成不久后便专程前往。宋太宗还把禁中所收藏的“梵夹”也都给了天息灾,让他们“视藏录所未载者翻译之”。为了进一步壮大译经的声势,宋太宗于同年九月下诏“系籍童行长发,并特许剃度”。在诏书中宋太宗特意提到“朕方隆教法,用福邦家”,凸显出自己潜心向佛的形象[34]。三月后宋太宗第二次前往译经院。[35]除此之外,宋太宗还“遣使取杭州释迦佛舍利塔置阙下”,修建“巨丽精巧”的开宝寺佛塔。[36]修建舍利佛塔、两次前往译经院、大规模度僧,这些记述描绘出太宗尊崇佛教的形象。
第二阶段译经。在佛经翻译过程中,宋太宗依旧保持着对这项活动的热情。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宋太宗赐译经院额“传法”。同意了天息灾增加翻译学生的请求,“令两街选童子五十人,就院习梵学、梵字”[37]。当年十月,宋太宗以新译经五卷示宰相。[38]十一月“上撰莲华心轮回文偈颂十部二百五十卷、回文图十轴,示近臣”[39]。值得注意的是《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录与《宋太宗皇帝实录》不同,并没有把太一宫成与此事记录在一起。但有一处与《宋太宗皇帝实录》相同,《续资治通鉴长编》也记录了宋太宗在这两次活动时发表的评论。通过前文的对比分析能够清楚地看出,《续资治通鉴长编》并未对这段文字有所加工。宋太宗希望通过宰相向官员们传达佛教对王朝统治有积极的作用,另外也表明自己并不是要崇佛,即佛教“有俾政治”、“有可观者”,自己也“非溺於释氏”。而赵普的回答“陛下以尧、舜之道治世,以如来之行修心”也从侧面点明了宋太宗此番言论的目的。十一月,宋太宗又对宰相宋琪解释自己崇佛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天下,“朕夙夜孜孜,固不为己,每焚香,惟愿民庶安輯,不近理之事,断不为也”[40]。除了不断向宰相表明心迹外,宋太宗在十二月“令诸州禁还俗僧道赴举”。禁止僧道还俗参加科举以保证儒家士人的核心利益不被侵害。宋太宗在这道诏书颁布前对宰相解释了诏令出台的目的“进士先须通经,遵周、孔之教,或止习浮浅文章,殊非务本之道,当下诏切戒之”[41]。宋太宗的这道诏令为儒释道三教划分了明确的界线,将释道两教弟子隔离在官僚体系之外。
第三阶段翻译完成。为了扩大译经的影响,宋太宗先于雍熙二年(984年)按照唐制恢复内道场,并向宰相解释此举“未必便能获佑”,稳定文官集团的情绪。雍熙三年(985年),译经成果已成规模,宋太宗撰写了“御制新译圣教序赐宰相李昉等”[42]。为了庆祝这一盛事,宋太宗第二次度僧,“诏祠部,凡僧尼籍有名者,悉牒度之”。在这次度僧后不久,宋太宗随即提高僧人系籍的标准,要求“须经业精熟,阅试及三百者乃许系籍”[43]。端拱二年(989年),开宝寺塔竣工。该塔“造浮图十一级以藏之,上下三百六十尺,所费亿万计,前后踰八年”,且“巨丽精巧,近代所无”[44]。考虑到开宝寺塔修建开始于太平兴国七年,端拱二年的这次活动也可以被看做是译经活动的余韵。
除了译经活动,《续资治通鉴长编》对宋太宗与佛教相关的记载少且分散,主要集中在以下内容:一是宋太宗不断规范僧籍管理和提高僧人系籍要求。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应工部郎中侯陟上奏之请,宋太宗要求“岁令诸州上僧尼之籍于祠部,下其牒,俾长吏亲给之”[45]。宋太宗的这次诏令进一步规范了僧人度牒的管理,将自唐代开始各地方“三年一造”僧籍上报中央的管理制度调整为“三年一供,每一供全帐,三供刺帐”的“全帐”、“刺帐”管理制度[46]。二是修建寺院。比如修建平晋寺,“号平晋,上自记之,刻石寺中”[47]。三是僧人干政的记载。淳化五年(994年),有僧人向宋太宗进言称赴成都的赵昌言“鼻折山根,此反相也,不宜委以蜀事”。此事记载版本较多,李焘也对此进行了考释,认为此事“未可信也”[48]。
通过以上对于宋太宗度僧、译经,修佛塔等活动的记载,《续资治通鉴长编》呈现出“素崇尚释教”的宋太宗形象。而且相比于《宋太宗皇帝实录》《宋史·太宗本纪》为了消解宋太宗崇佛而表现出的强烈政治性,《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更加全面和详细。
二、僧史对宋太宗与佛教关系的书写
对于宋太宗与佛教关系的记载,《佛祖统纪》《历朝释氏资鉴》《广清凉传》《指月录》等佛教史书和典籍中也有所涉及。宋代由于天台宗与禅宗对于佛教正统之争旷日持久,两派为此撰写了大量著作。其中志磬撰写的《佛祖统纪》是天台宗史学著述的集大成者。《佛祖统纪》参考和延续《史记》《资治通鉴》和天台宗史学著作《宗源录》《师门正统》等著作的编写体例撰写而成,“依放(仿)史法,用成一家之书”。《佛祖统纪》中的《法运通塞志》对自周昭王至宋理宗各朝帝王与佛教相关的历史记载进行了收集和整理,其目的在于“列三教之迹,究一理之归,系以编年,用观通塞之相”[49]。《佛祖统纪》对宋代皇帝与佛教关系的记载尤为详细,志磬选取国史、笔记等相关资料,按时间顺序记录宋代诸帝与佛教相关的言行,使该书成为研究宋代统治者与佛教关系重要的参考资料。有学者甚至认为“此二书(《佛祖统纪》、《历朝释氏通鉴》)都注重材料的可靠性,尤其《佛祖统纪》选用资料有根据,这一点史家亦承认”[50],“该书采择史料面广, 资料翔实, 编选精当,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很高的史料和思想价值”[51]。《佛祖统纪》中呈现出与《宋太宗皇帝实录》《续资治通鉴长编》完全不同的宋太宗与佛教关系形象。
《佛祖统纪》中记载的宋太宗与佛教相关活动与《宋太宗皇帝实录》《续资治通鉴长编》各有异同。比如在度僧、修建佛寺、翻译佛经等方面,《佛祖统纪》与《宋太宗皇帝实录》《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录基本一致。但对于宋太宗所说不利于佛教的言论,《佛祖统纪》则会通过文本书写予以消解。如上文提到的宋太宗在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言论,《宋太宗皇帝实录》希望通过文本处理消解宋太宗崇佛形象。而《佛祖统纪》则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对文本处理以营造宋太宗尊崇佛教的印象。《佛祖统纪》对宋太宗的话语进行了以下修改:一是添加了“普利群生”这样赞美佛教的语句。二是将宋太宗原本谈到的帝王如何“利他”,按照佛教义理修改为兼谈“自利行”和“利他行”,从而彰显宋太宗对于佛教义理理解之深。三是将“梁武舍身为寺家奴”删改为“梁武舍身为奴”,还将百官“率钱收赎”和“布发于地”“令桑门践之”等言语予以删除,从而将宋太宗对于梁武帝佞佛的批评完全隐匿。最后,《佛祖统纪》将宋太宗这段话里最核心的“盖存其教,非溺于释氏也”予以删除。志磬通过文本处理,将这段原本宋太宗对自己并非崇佛的辩解处理成对佛教“有裨政理,普利群生”的推崇,营造出宋太宗认为佛教有助治国的崇佛形象。
再如,《佛祖统纪》还对宋太宗恢复内道场的记载进行了改写。《宋太宗皇帝实录》《续资治通鉴长编》《佛祖统纪》对于宋太宗恢复内道场记载详见下表:
表2:雍熙二年宋太宗设内道场言论对比表
|
实录 |
长编 |
佛祖统纪 |
|
己卯,诏两街供奉僧于内殿建道场,上谓宰相曰:“今夏麦丰登。比闻岁稔则民多疾疫,朕恐百姓有灾患,今建此为民祈福,未必便能获祐,且表朕请祷之意。”[52] |
六月己卯,诏两街供奉僧于内殿建道场。上谓宰相曰:“今兹夏麦丰稔。比闻岁熟则民多疾疫,朕恐百姓或有灾患,故令设此,未必便能获佑,且表朕勤祷之意云。”[53] |
诏两街供奉僧于内殿建道场,为民祈福,岁以为常。[54] |
这段宋太宗向宰执解释自己恢复内道场并非因为崇佛,而是“为民祈福”的言论,《宋太宗皇帝实录》与《续资治通鉴长编》基本一致。《佛祖统纪》仅保留建内道场的记载用以说明宋太宗与佛教的紧密关系,将宋太宗“未必便能获佑”的言论予以删去。
除了官修史书,宋人笔记也是《佛祖统纪》取材的重要来源。出于相同的目的,《佛祖统记》根据需要也对部分内容进行了删改。以宋太宗在开宝寺塔安放舍利时的言行记录为例。端拱二年,开宝寺塔建成,宋太宗参加了安放舍利的仪式,《佛祖统纪》的记载如下:
安舍利日,上肩舆微行,自手奉藏。有白光起小塔一角,大塔放光洞照天地,士庶焚香献供者盈路,内侍数十人求出家扫塔。上谓近臣:“我宿世曾亲佛座,但未通宿命耳。”诏直学士院朱昂撰塔铭,谓曰:“儒人多薄佛,向中竺僧法遇乞为本国佛金刚座立碑,学士苏易简为之,指佛为夷人。朕恶其不逊,遂别命制之。卿宜体此意。”[55]
这段记载中宋太宗亲口说出“宿世曾亲佛座”,呈现出宋太宗是佛教转世弟子的形象。除此之外,宋太宗还认为“儒人多薄佛”。因“学士苏易简为之,指佛为夷人”,“朕恶其不逊”。厌恶苏易简这样不尊敬佛教的人,更说明宋太宗对于佛教的虔诚态度。这样的记载对于树立宋太宗崇佛形象尤具说服力。考察这段记载的来源,分别来自杨亿《谈苑》和释文莹《玉壶清话》。
《谈苑》对于此事的记载如下:
葬日,上肩舁微行,自安置之,有白光由塔一角而出。上雨涕,其外都人万众皆洒泣,燃指焚香于臂掌者无数。内侍数十人,愿出家扫洒塔下,悉度为僧。上谓近臣:“我曩世尝亲佛座,但未通宿命,不能了了见之耳。”[56]
《玉壶清话》的记载如下:
开宝塔成,欲撰记,宋太宗谓近臣:“儒人多薄佛典,向西域僧法遇自摩竭陀国来,表述本国有金刚座,乃释迦成道时所踞之座,求立碑坐侧。朕令苏易简撰文赐之,中有鄙佛为夷人之语,朕甚不喜,词臣中独不见朱昂有讥佛之迹。”因诏公撰之。[57]
对照《谈苑》和《玉壶清话》,可以看到志磬将两则材料进行了文本加工。对《谈苑》的修改主要在于将“有白光由塔一角而出”修改为“有白光起小塔一角,大塔放光洞照天地”。修改后的舍利佛光更加璀璨夺目,也更能表现佛法普照天地。此外,志磬将“上雨涕,其外都人万众皆洒泣,燃指焚香于臂掌者无数”修改为“士庶焚香献供者盈路”。志磬可能是觉得“上雨涕”的记载不符合宋太宗的身份,而将此删去。另一处是将“燃指焚香于臂掌”修改为“焚香献供”。虽然宋太宗时期伤害肢体礼佛的行为被官方禁止,但依然普遍流行。上文提到的《宋太宗皇帝实录》对僧伽塔建成的记载中也提到有数千人燃顶、焚指。而且杨亿也不认为此举有何不妥之处,所以才会特意写明。而《佛祖统纪》将这一记载进行改写,与徽宗时的禁止毁伤肢体礼佛的诏令有关。宋徽宗在大观五年(1111年)下诏“毁伤肢体,有害风教。况夷人之法,中华岂可效之?累有处分,终未能革。可徧行下,违者以大不恭论”[58]。大不恭是“十恶”的第六条[59],宋政府将燃指等毁伤身体礼佛的行为作为重罪进行惩处。所以,南宋人志磬在修编史书时特意避免宋太宗安放舍利时出现“大不恭”的行为,删除了原文中“燃指”的记载。
对于《玉壶清话》的文本处理主要有两处,一处是将“上谓近臣”修改为“诏直学士院朱昂撰塔铭,谓曰”。《佛祖统纪》通过文本处理将原记载中一段宋太宗与近臣的私下话语改造成皇帝诏书的文字。而改造后文本无论从意义和权威性上都更能证明宋太宗尊崇佛教。另外一处是将宋太宗的“朕甚不喜”修改为“朕恶其不逊”。从“不喜”变成“恶其不逊”,经过志磬的改写,文本中展现出的宋太宗对于大臣们不尊佛的反对态度更加激烈。
从这两段史料来看,《谈苑》的记载是唯一一个记载宋太宗说出“我宿世曾亲佛座”的材料[60]。《玉壶清话》中对于宋太宗厌恶苏易简对佛不逊的记载也存在问题。仅从《佛祖统纪》中摘编其他有关苏易简材料中就能看到与此的抵牾之处。《佛祖统纪》在此事之后的淳化元年条记载“诏参政苏易简撰三教圣贤录”[61]。假设《玉壶清话》记载属实,苏易简因为“指佛为夷人”被宋太宗“不喜”,宋太宗又怎么可能在此事发生后的第二年让其领衔撰三教圣贤录?另外《佛祖统纪》在淳化二年(991年)载“杭州西湖昭庆寺沙门省常刺血书华严净行品,结社修西方净业,宰相王旦为之首,参政苏易简百三十二人,一时大夫皆称净行社弟子”[62]。对于此事有苏易简撰写的《施华严经净行品序》传世。苏易简在序中说:“彼上人者果能立见解,成是功德,予当布发以承其足,剜身以请其法,犹无嗔恨,何况陋文浅学,而有吝惜哉!即时预千人之受持,同诸佛之赞叹”[63]。除此之外,《宋史》苏易简本传中也记载他“旁通释典”[64]。一个“旁通释典”,愿意为僧人“布发以承其足,剜身以请其法”的人又怎么可能说出“鄙佛为夷人”的话语?
这段对苏易简“指佛为夷”的记载存在明显错误,志磬在编辑材料时怎么会没有发现?那么是否存在志磬看到的是已经被修改过的《玉壶清话》,而志磬只是疏于考校而误引其文?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同书的五十二卷的《圣君护法》条,再次出现了苏易简“指佛为夷”的记载。“宋太宗谓近臣曰:‘儒人多薄佛,向为中竺佛金刚座令苏易简作碑,指佛为夷,遂别命为之’”[65]。此处“指佛为夷”又记载为“宋太宗谓近臣”。由此可见,志磬所用的《玉壶清话》与今天能够看到的版本并无二致。而《佛祖统纪》前文提到的几处修改就是出自志磬之手。将这段明显不可信的史料选入书中,志磬有其特殊目的。因为在这段文字之后,志磬特意进行了总结:
人无通识,不足以知佛,故韩愈夷其佛,欧阳修亦夷其佛。宋太宗以苏易简指佛为夷而恶之,自古人君莫如宋太宗之有通识也。佛圣人也,五天中土也,此方即五天之东境也,今称中国者,此方自称尊也,称四夷者,且约此方四境之外论之也。儒家乏通识,即目睫以言之,故多失言。[66]
志磬这段话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儒家所谓的“中国”是以自身所在地作为大地中心,将所处之地外称为四夷。而在更为宏大的“五天中土”来看,中国不过是五天中土的东境而已。儒家由于没有这样的“通识”所以才会认为佛是夷人。二是宋太宗是所有人君中最有“通识”的,因此他才会“以苏易简指佛为夷而恶之”。志磬修改史料的目的在于反驳了儒家所谓“夷其佛”看法的同时,将宋太宗作为支持自己理论的强大后盾,让人不敢轻易反驳。由此可见,志磬选取这段存在明显抵牾之处的材料还进行二次加工,就是为了后面的这段论述。宋代随着“崇文抑武”国策的不断加强,“儒家思想文化广为传播,对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67]。在这样的背景下,文人士大夫对于佛教的攻击也持续不断。“本朝之欧阳公,以及闽洛诸公,皆阐明正道以排释氏”[68]。在此过程中,“指佛为夷人”是其中的重要观点。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在《本轮中》就提出“佛为夷狄,去中国最远”[69]。南宋大儒朱熹也说“佛祖是西方夷狄人”[70]。如果说文人所论不过是各家观点的话,那么宋徽宗在禁绝自残礼佛的诏书中提到的“况夷人之法,中华岂可效之”给佛教带来的负面影响则更为巨大。作为“自古人君莫如宋太宗之有通识”,既表扬了宋太宗,又不点名的批评了如徽宗一样缺少通识的皇帝。另外,志磬制造的宋太宗诏书中提出“指佛为夷人,朕恶其不逊”。这对于将尊崇祖宗家法作为政治生活重要原则的宋朝人而言,借宋太宗的诏书去批评徽宗“指佛为夷人”的诏令则无疑更具合理性。
三、不同史料书写下的宋太宗与佛教形象分析
《宋太宗皇帝实录》《宋史·太宗本纪》《续资治通鉴长编》和《佛祖统纪》分别塑造了平衡释道、以道为重、崇尚释教和佛教转世弟子这四种不同的宋太宗形象。之所以会有差异化的宋太宗形象,既与宋太宗统治时期对待佛教态度的变化有关,也离不开史家因自身立场和政治需要对宋太宗形象的改造。
首先,宋太宗与佛教关系展现出的不同形象与其统治策略改变紧密相关。继位之初,宋太宗迫切希望掩盖篡位得权的不光彩经历,因此将唐太宗作为自己执政的样板。宋太宗希望通过学习和借鉴唐太宗的成功经验,让自己能够成为彪炳史册的明君。比如在文治方面,宋太宗学习唐太宗的统治策略,扩大科举录取人才;编写大型类书;练习飞白书。在武功方面,太平兴国三年南方的陈洪进和钱俶先后纳土归降,宋太宗兵不血刃就平定了南方割据势力。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御驾亲征消灭北汉。虽然此后的高粱河之战让宋太宗大败而归,但宋太宗业已实现了政权统一。
消灭北汉的成功让宋太宗对自己能够成为一代英主充满信心。他希望通过译经、度僧的行为,使自己成为宗教领袖,进而能够如唐太宗那样抚远万方。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宋太宗开始修建译经院。此后,他修建佛寺、大规模度僧、在开宝寺修建佛塔、多次前往译经院。在这背后都有唐太宗当年作为的影子。宋太宗甚至还问过大臣们“朕何如唐太宗”这样的话[71]。可见此时的宋太宗一直都将唐太宗作为自己比较、学习的对象。大臣也非常清楚宋太宗的想法,主动配合加强这一联系。比如赞宁在《进高僧传表》中就将宋太宗安排翻译佛经并作序一事与唐太宗进行了类比,认为宋太宗“翻译成经,制甚深之御序”的举动“属此雍熙之运,申其贞观之风”[72]。赞宁作为与宋太宗关系紧密的僧人,他的这一举动也从侧面证明宋太宗有学习唐太宗的想法。就连宋白在为宋太宗拟定谥号的议文中还多次将宋太宗与唐太宗进行类比,如“天下英雄,落吾彀中”、“著治化之书,贞观之风也”等语句都与唐太宗紧密相关[73]。可见当时的官方都将宋太宗比作唐太宗。
对于这一时期宋太宗大张旗鼓的崇佛行为,虽然史料没有记载士大夫的反对声音。但是考虑到宋太宗反复对赵普、宋琪不断解释自己崇佛行为“不近理之事,断不为”、“非溺於释氏也”,还有佛教系“小道”,崇佛“未必便能获佑”等等。这些言论作为塑造宋太宗崇佛与否的关键性证据被《宋太宗皇帝实录》《佛祖统纪》分别进行了修改。但是抛开著史者如何裁剪史料不谈,宋太宗此时不断向宰执解释自己并非“非溺於释氏也”,也能从侧面说明当时有不少士大夫对于宋太宗崇佛是持反对意见的。这时的赵普方因积极配合宋太宗贬斥秦王廷美而重获信任。而宋琪是宋太宗的潜邸之臣,是“周知人情,尤通吏术”之人[74]。宋太宗根本不必向他们多次解释自己的行为。而史料上所记载诸多辩解之语,应当是宋太宗通过宰相向文官集团解释自己并非沉溺佛教,以平息文人士大夫们对此事的反对。当然,对于此时的宋太宗而言,崇佛是实现自己伟业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能够在即将开始的北伐中取得胜利,那么所有的反对之声将会消失不见。
事与愿违,随着雍熙三年(987年)北伐失败,宋太宗已经失去成为天下雄主的可能。当局势稳定后,宋太宗便开始调整执政策略。端拱二年(989年)年初,宋太宗“诏文武群臣各陈备边御戎之策”[75]。王禹偁就在上奏中直接指出“望陛下少度僧尼,少崇寺观,劝风俗,务田农,则人力彊,而边用实也”[76]。这是目前能够看到的第一篇反对宋太宗崇佛的奏疏。《续资治通鉴长编》还记载王禹偁上奏的效果,“上览奏,深加叹赏。宰相赵普尤器之”[77]。宋太宗和赵普都非常赞赏王禹偁的批评,这反映了宋太宗开始反思调整执政策略。同年八月,当开宝寺塔建成的时候,田锡上奏反对此事,田文中有“众以为金碧荧煌,臣以为涂膏釁血”这样严厉的反对声音[78]。到了年末,宋太宗将尊号由太平兴国六年(981年)雄心勃勃时确定的“应运统天睿文英武大圣至明广孝”[79]修改为“法天崇道”[80]。这说明宋太宗开始以“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作为自己的执政理念。“清净致远,黄、老之深旨也。夫万务自有为以至于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81]。将“无为”作为自己的统治策略之后,之前心心念念想要模仿的唐太宗就成了反面典型。宋太宗先是批评唐太宗征辽,“炀帝昏暗,诚不足语。唐太宗尤如此,何失策之甚也。且治国在乎修德尔,四夷当置之度外”[82]。此后,宋太宗更是直接指责唐太宗“好虚名”,“大凡帝王举动,贵其自然。朕览唐史,见宋太宗所为,盖好虚名者也。每为一事,必豫张声势,然后行之,贵传简册,此岂自然乎”[83]。伴随着将执政策略转为清净,宋太宗也随即调整了对待佛教的态度。自雍熙三年(987年)以后,除了端拱二年(989年)外宋太宗基本再没有举办大规模崇佛活动。
除了因宋太宗调整执政策略而使他与佛教的关系不断改变之外,著史者的立场是形成宋太宗与佛教形象多样化的根本原因。
真宗刚一继位就安排钱若水主持修撰《宋太宗皇帝实录》[84]。九个月后“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钱若水等上宋太宗实录八十卷”[85]。虽然现在的《宋太宗皇帝实录》只保存了八十卷中的二十卷,但是透过这二十卷依旧能够看出史官希望营造宋太宗“非溺于释氏”的形象。
《宋史》虽于元末修成,但实际是对宋代史馆记注进行加工而成[86]。真宗景德四年(1107年)“诏修太祖、宋太宗正史”[87]。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监修国史王旦等上两朝国史一百二十卷”[88]。《国史》中有“帝纪六(太祖太宗各三)”记载太祖、太宗史事[89]。《宋史·太宗本纪》就是以《国史·太宗本纪》三卷为基础删减为两卷。相对真宗初年修撰的《宋太宗皇帝实录》所呈现出的是平衡释道关系的宋太宗形象,成书于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时的《宋史·太宗本纪》呈现出一位更重道教的宋太宗形象。这背后的变化无疑是为了配合真宗“圣人以神道设教”[90],大搞封禅、天书的政治需要。《宋太宗皇帝实录》与《宋史·太宗本纪》塑造的宋太宗与佛教形象的不同,体现了真宗朝“天书降”、“圣祖临”前后官方对于释道两教态度的变化。
修撰于南宋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成书虽距宋太宗朝已150余年。但李焘坚持司马光“宁失于繁,无失于略”的撰史思想,内容相比《宋太宗皇帝实录》《宋史·太宗本纪》更加丰富和详实[91]。而且《续资治通鉴长编》无需如《宋太宗皇帝实录》和《国史》一样考虑宋真宗的政治需要。因此《续资治通鉴长编》反映出的宋太宗与佛教关系和《宋太宗皇帝实录》《宋史》相比出现了巨大的改变。李焘通过考察各种史料,得出了“上素崇尚释教”的判断[92]。
《佛祖统纪》对宋太宗与佛教关系的记载,通过有目的选取特定资料、改写、剪裁文本,塑造出宋太宗“曾亲佛座”的崇佛形象。再借助宋太宗之口反驳徽宗诏书和儒家“指佛为夷人”观点。虽然志磬在《佛祖统纪》中批评欧阳修撰写《新唐书》《五代史》删除有关释道记载时说“夫唐书,唐家之正史,非欧阳之私书也,借使不足法,论之可也,岂当以己所不好而悉删之邪”[93]。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反击“指佛为夷”,志磬放弃了对于所谓“信史”的理解和坚持。他不但特意选取存有抵牾的记载,还按照自己的需要对史料进行了剪裁和修改。这种肆意篡改史料的行为远要比他所批评的“以己所不好而悉删之”更加悖离“信史”的要求。
结 语
宋太宗与佛教形象的变化与其统治策略改变紧密相关。当他将“削平天下”作为目标时,佛教成为实现理想的重要工具。度僧、译经等崇佛行为能够帮助他建立“现在佛”的形象笼络四夷。而当他以“清净”作为统治目标时,更能够被士大夫接受的道家思想成为他的选择,与佛教的互动也随之趋于正常。正因为宋太宗与佛教关系亲疏变化,为史书撰写者能够塑造截然不同的宋太宗形象提供了素材。历史记录者从价值取向和现实需求出发,将太宗与佛教关系书写成自己需要的样子。
作为奠定宋代执政策略的关键性人物,宋太宗与佛教关系的形象由书写者以史实为基础构建而成的。所谓“清静无为”、“非溺于释氏”、“崇尚释教”抑或是“曾亲佛座”,都是宋太宗在不同时期与佛教关系的写照。因此,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需要跳出将同一人物从不同文献记载中剥离出来进行研究的方法。而应充分认识到人的复杂和多变,发现不同历史文献记载中的差异及形成原因,以求能够更加真实的反映历史人物。
注 释
[1]《宋史》卷5 《太宗本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1页。
[2] (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礼二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323页。
[3] 竺沙雅章先生认为宋太宗“崇佛”是为了“服从于政治需要”而非“溺佛”(竺沙雅章著,张其凡译:《宋初政治与宗教》,《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第3集),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5页)。李裕民先生认为宋太宗虽然与太祖一样“都信崇佛教”,但佛教在太宗心中处于儒释道三教的末位(李裕民:《论宋初的佛教政策》,《宋史新探》,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7页)。黄启江先生认为虽然宋太宗“奠定了北宋皇室崇佛的‘祖宗之制’”,其目的是建立其“现在佛与转轮王”形象,是为实现他“使大宋帝国重振汉、唐雄风”政治抱负服务(黄启江:《宋太宗与佛教》,《北宋佛教史论》,台北: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1页,第57页)。汪圣铎先生认为宋太宗崇佛是“利用佛教为巩固自己统治服务”(汪圣铎:《宋代政教关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8页)。闫孟祥认为虽然宋太宗对佛教“有所管制”,但都是为了佛教更好的发展。而且“宋太宗崇佛影响及于家人出家、归佛,说明他的崇佛比较太祖已经大大进一步了,不仅仅是一般的‘利用’”(闫孟祥:《宋代佛教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8页)。
[4] 闫孟祥、李清章:《宋太宗“受佛记”传说考》,《河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5]《宋史》卷388《李焘传》,第11919页。
[6](宋)钱若水修,范学辉校注:《宋太宗皇帝实录校注》(以下简称《宋太宗皇帝实录》)卷26,太平兴国八年六月壬子条,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43页。
[7](宋)钱若水修,范学辉校注:《宋太宗皇帝实录》卷33,雍熙二年四月己卯条,第318页。
[8](宋)钱若水修,范学辉校注:《宋太宗皇帝实录》卷29,太平兴国九年三月丁巳条,第136页。
[9](宋)钱若水修,范学辉校注:《宋太宗皇帝实录》卷31,雍熙二年正月丙申条,第278页。
[10](宋)钱若水修,范学辉校注:《宋太宗皇帝实录》卷27,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己未条,第74页。
[11] (宋)钱若水修,范学辉校注:《宋太宗皇帝实录》卷76,至道二年二月壬辰条,第671页。
[12](宋)钱若水修,范学辉校注:《宋太宗皇帝实录》卷27,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癸丑条,第65页。
[13] (宋)钱若水修,范学辉校注:《宋太宗皇帝实录》卷26,太平兴国八年十月甲申条,第56页。
[14]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冬十月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54页。
[15] (宋)志磬撰,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卷44《法运通塞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33页。
[16] (宋)曹彦约:《经幄管见》卷4,,《丛书集成续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影印本,第276册,第475页。
[17] 《宋史》卷4,《太宗本纪一》,第69页。
[18] 《宋史》卷4,《太宗本纪一》,第56页。
[19] 《宋史》卷4,《太宗本纪一》,第67页。
[20] 《宋史》卷4,《太宗本纪一》,第70页。
[21] 《宋史》卷5,《太宗本纪二》,第96页。
[22] 《宋史》卷5,《太宗本纪二》,第97页。
[23] 《宋史》卷5,《太宗本纪二》, 第99页。
[24] 《宋史》卷4,《太宗本纪一》,第62页。
[25] 《宋史》卷4,《太宗本纪一》,第68页。
[26] 《宋史》卷5,《太宗本纪二》,第75页。
[27] 《宋史》卷5,《太宗本纪二》, 第84页。
[28] 《宋史》卷4,《太宗本纪一》, 第72页。
[29] 《宋史》卷4,《太宗本纪一》,第72页。
[30] 《宋史》卷4,《太宗本纪一》,第58页。
[31] 《宋史》卷4,《太宗本纪一》,第63页。
[32] 《宋史》卷5,《太宗本纪二》,第76页。
[3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太平兴国七年六月条,第522页。
[3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太平兴国七年九月己丑条,第527页。
[3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太平兴国七年十月壬申条,第528页。
[36]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端拱二年八月条,第686页。
[3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十二月条,第567页。
[3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十月甲申条,第555页。
[3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条,第577页。
[4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十月甲申条,第556页。
[4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十二月癸卯条,第561页。
[4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雍熙三年十月戊午条,第625页。
[4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雍熙三年十月条,第624页。
[4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端拱二年八月条,第687页。
[4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三月癸亥条,第401页。
[46](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4,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26页。《宋会要》在释道门开篇也记录了“凡僧道童行每三年一造帐,上祠部,以五月三十日至京师”的僧籍管理制度。除了三年一造帐,《庆元条法事类》中还规定“诸僧道及童行帐三年一供,每一供全帐,三供刺帐,周而复始”,这里的刺帐制度应当就是来源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的这次诏令。
[4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太平兴国四年五月庚子条,第454页。
[4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淳化五年九月条,第797页。
[49](宋)志磬撰,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卷35,第766页。
[50]闫孟祥 李清章:《宋太宗“受佛记”传说考》,《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16页。
[51]韩毅:《<佛祖统纪>与中国宋代僧人的史学思想》,《河北学刊》,2003年第5期,第167页。
[52](宋)钱若水修,范学辉校注:《宋太宗皇帝实录》,卷33,雍熙二年六月己卯条,第339页。
[5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六月己卯条,第597页。
[54](宋)志磬撰,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卷44,《法运通塞志》,第1036页。
[55](宋)志磬撰,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卷44,第1038页。
[56](宋)杨亿:《杨文公谈苑》,卷6《喻浩造塔》,《全宋笔记》第8编第9册,河南:大象出版社,2017年,第107页。
[57](宋)文莹撰,郑世刚、杨立扬点校:《玉壶清话》卷2,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3页。
[58](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刑法二禁约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318页。
[59]窦仪:《宋刑统》卷一《名例律》,北京:中华书局, 1984年,第 9-11 页 。
[60]闫孟祥、李清章先生在《宋太宗“受佛记”传说考》一文对宋太宗曾亲佛座传说进行了详细梳理和分析。此文中列举了宋代各个时期对于宋太宗“受佛记”的记载,但除了杨亿一文外,再无其他资料有宋太宗承认“曾亲佛座”的文字。因此,杨亿和志磬记录的宋太宗自称“曾亲佛座”说法难以令人信服。
[61](宋)志磬撰,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卷44,第1038页。
[62](宋)志磬撰,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卷44,第1039页。
[63](宋)苏易简:《施华严经净行品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168,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313页
[64]《宋史》《苏易简传》,第9173页。
[65](宋)志磬撰,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卷52,第1219页。
[66](宋)志磬撰,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卷44,第1038页。
[67]陈峰:《文治之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56页。
[68](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126《释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3009页。
[69](宋)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居士集》卷17《本论中》,《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88页。
[70](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26《释氏》,3007页。
[71](宋)王称撰,孙言诚、崔国光点校:《东都事略》,山东:齐鲁书社,2000年,第258页。
[72](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页。
[73](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礼29“历代大行丧礼”,第1323页。
[74]《宋史》卷264《宋琪传》,第9131页。
[7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端拱二年正月癸巳条,第667页。
[7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端拱二年正月条,第675页。
[7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端拱二年正月条,第676页。
[7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端拱二年八月条,第687页。
[7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太平兴国六年十月癸酉条,第504页。
[8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端拱二年十二月庚申条,第693页。
[8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淳化四年十一月条,第759页。
[8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淳化四年十一月条,第759页。
[8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淳化五年四月丁酉条,第780页。
[8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2,至道三年十一月己巳条,第890页。
[8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咸平元年八月乙巳条,第916页。
[86](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23,“宋辽金三史”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94页。
[8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6,景德四年八月丁巳条,第1486页。
[8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6,大中祥符九年二月丁亥条,第1973页。
[89](宋)王应麟撰:《玉海》卷46,江苏:广陵书社,2016年,第908页。
[9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7,景德四年十一月庚辰条,第1507页。
[9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进续资治通鉴长编表》,第7页。
[9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太平兴国七年六月条,第522页。
[93](宋)志磬撰,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卷40,910页。
一宋史研究资讯一
邮箱:txq1627@126.com
编辑:潘梦斯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