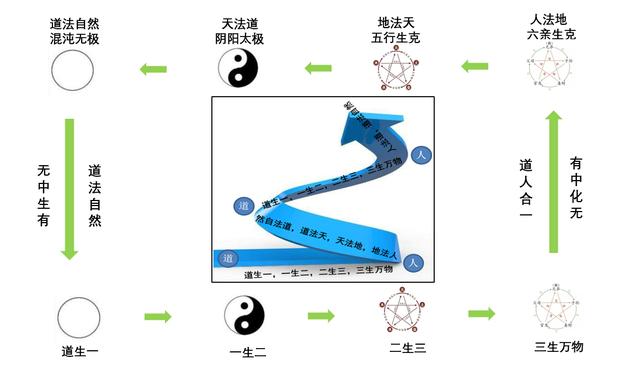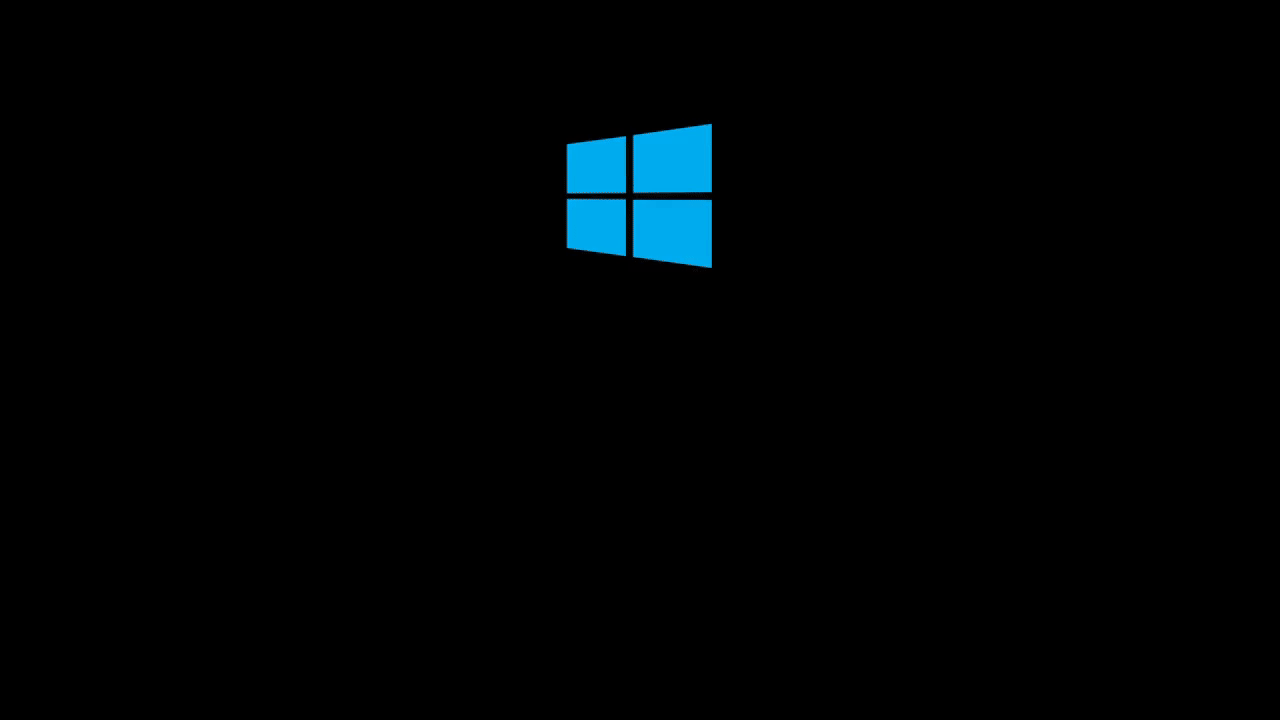八十年代的糖瓜故事(亮晶晶的番薯馃)

偶回老家,妻子年近九十的奶奶给了我一袋别人送她的番薯丝,不多,五六斤左右。拿回店里,我和妻子商量怎么烧好吃,儿时番薯丝粥、番薯饭吃太多,至今还有阴影,妻子说,还是做番薯馃好吃,顿时咽了一下口水,眼前浮现出儿时吃番薯馃的场景。
穿着蓝色土布大襟,围着黑色粗布围裙,瘦瘦小小的奶奶,从热气腾腾的灶台,端出一屉小蒸笼,我们兄妹几个马上犹如小猪上槽般伸长了脖子围了过去,迫不及待的伸手去争抢那乌黑发亮,冒着袅袅热气,散发着薯香味的番薯馃。把热烫烫的番薯馃在两手间来回颠儿下,“呼呼呼”地吹上几口“仙气”,美滋滋地咬上一口,有番薯淡淡的轻甜,柔柔软软,粘粘韧韧的,又有点嚼劲。那感觉,套用一句现在的广告词,“这酸爽,不敢相信!”。
在那物质匮乏年代,番薯和番薯丝是除米面之外的主食,为了填饱肚子,不太舍得精加工成粉,所以番薯丝粉也是珍贵之物,奶奶只能偶尔做几次番薯馃,给我们解解馋。

夫妻二人一番回忆后,恨不得马上把番薯丝碾成粉,重做番薯馃尝尝。
只是把番薯丝碾成粉却是个问题,在横店这影视名城,不知上哪儿找碾米厂,找了多天也没找到。后来求问房东,房东也不知,还说这一点儿东西,加工费也不合算。无奈之下,妻子说只能煮番薯丝粥了,梅雨天放着怕受潮,烂了可惜。
没想到第二天,房东拿了一个小小的粉碎机来,说是他女儿用过的,看能不能用。我们甚是欣喜,擦拭干净后试了试,还能正常运转。只是小了点,一次只能碾上手抓四五把,俩人盯着机器,四五分钟后,听着轰轰声渐渐平稳,打开盖子,红薯丝已经碾成细细的粉,呈现出一种温暖的淡黄色,用手一摸,还真是温热的。碾了几罐后,觉得薯干有点受潮了不太好碾,于是,乘着梅雨天难得的阳光,因地制宜的用一块菜板和吃饭的小方桌翻晒,下午,妻子一小罐一小罐的碾,直到晚上才全部碾完。碾这一点番薯粉竟如此大费周折。其实从种番薯,掘番薯,再到晒成丝,又有哪样不付出艰辛劳作呢。
第二起了个大早,我把番薯丝粉搅拌揉成面团,妻子扯上一小坨,围着筷子轻轻捏好,用手盈盈一握,抽出筷子,留下一个中空的通气管,一个手掌般长,比拇指粗上一圈,有着四指压痕的番薯馃就做好了。放入蒸锅,待大气直上,薯香四溢,出得锅来,看着热腾腾,亮晶晶的番薯馃,我忍不住连吃了几个,妻子笑说要被我一个人吃光了,儿女们都没得吃了,我才不舍的住了手。

女儿却只吃了一个,就不肯吃了。00后的女儿自小生活在自家开的超市里,触手可及是满货架的零食,在她嘴里,原汁原味的土货番薯馃,自是没有她喜爱的精加工薯片美味。同一锅番薯馃,我甘之如饴,她却味同嚼腊。家乡的传统小吃,对她已经没有吸引力,她吃不出轻甜的番薯馃里揉着奶奶的宠爱,清香的清明艾馃中藏着对亲人的思念,她不知道圆圆的糍粑是一堂屋后生抡着大锤轮流打出来的,方方的冻米糖是在满厨房姑嫂婆媳的欢声笑语家长里短中切出来的,她的眼晴不曾掉进熬了一天的糖油里,她的口水不曾随一层一层的千层糕一口一口的咽满肚子,她又怎能吃出美味,吃出欢喜来!
儿女们从小跟着我们在外开超市,很少回家。十多岁时儿子随我回老家时,见我一路与熟人招呼,歪着头,奇怪的问:“他们怎么都认识你,我怎么一个都不认识?”
在异乡出生长大的儿女,已全然不知故乡事,不识故乡人,只是从小教会的家乡话还不曾忘记。在异乡,儿女是借读的外地人,回家乡,儿女又成了家乡陌生的“客人”。也许,在他们眼中,家乡,那只是父母的老家,没有经历,没有故事的山水,成不了心中的“故乡”。
“试问乡关何处是,水云浩荡迷南北。”,以后,他们该去哪里寻“故乡”呢?
我是该常带他们回家看看的。
吃罢早餐,翻看朋友圈,老友国华发上圈的早餐,竟也是亮晶晶,充满煽情与回忆的番薯馃,评论区里,满是老同学的馋相,和70后的回忆杀。


作者简介:聂钦,金华市作协会员,近年已在各地报刊,网络平台发表散文多篇。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