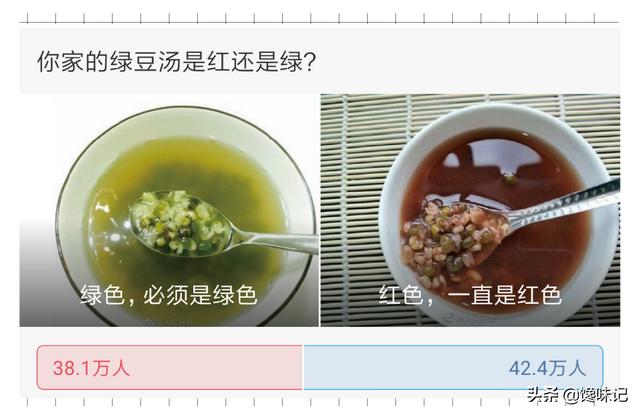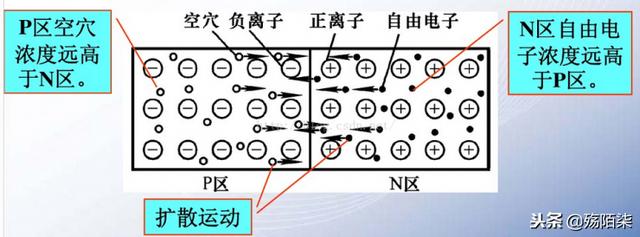罗检是什么样子的(同光文治的内弱外强及其后果)
摘要:同光之际,清廷一度收回了督抚们掌控的大部分军政权力,却始终缺乏对文治主导权的自觉。同光朝廷对于重建庙堂儒学和经学消极迷茫,而理学廷臣恪守程、朱教条,无所作为,与地方理学家因时变通、经世致用的取向反差鲜明。晚清内弱外强的文治格局一直没有得到清廷的重视和扭转,学术文化主导权的地方化遂不可逆转,从而加剧了清朝的崩溃之势。
清朝同光年间,社会秩序逐渐恢复,经济和文化进入重建轨道,一些人称为“同治中兴”或“同光中兴”。多年来,学界对这次短暂“中兴”的败因有所探讨,有的指陈清廷腐败、保守,有的归咎儒学本身。笔者认为,儒学虽有保守性,但仍有其内在活力和调适性。质言之,晚清“中兴”的主要败因潜藏于制度和权力结构之中。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后,曾国藩裁撤湘军,朝廷收回了督抚的大部分军政权力。直到义和团运动兴起,清廷的权威再次跌落下去。学界对晚清央地的军事、财政和行政关系多所论述,但对晚清的文治状况鲜有注意。“同光中兴”时,清廷一如既往地加强军事、财政和行政的中央集权制,这些方面与地方主义的博弈中占据主导。但晚清文治举措的提出和施行,大体均发源于地方官绅。清廷对于文治举措毫无主导性可言,影响所及,清廷的治国理论左支右绌,文化权力的下移始终未得到扭转,从而加速了“中兴”局面的瓦解,清朝无可挽回地走向崩溃。
一、内外参差的儒学教化
中国古代文治的重心是在儒学引导下,通过科举考试、研读儒经和刊刻典籍等举措对四民进行人伦教化,塑造价值观念和社会风尚。然而,在太平天国冲击下,作为人文渊薮的江南惨遭战乱戕害,大量学宫、庙宇、书院被毁,许多士人被迫逃亡,甚至像曾国藩的经学朋友邵懿辰那样死于战争。因之,重建儒学教化成为“中兴”的文治主题,但它是由地方官绅主导、实行的。
曾国藩被困祁门时,曾经自留遗书以备死。一日,想起皖中多经师学者,“遭乱颠沛,存忘殆不可知,遂遣人四出存问。存者遗书约相见戎幕,亡者恤其细弱,索其遗文。如桐城方宗诚存之、戴均衡存庄,歙俞正燮理初,黟程鸿诏伯敷诸家,皆借以得脱于险。”由此可见曾氏在危难之际的殷殷惦念。理学家方宗诚亦记云:“曾公既克复金陵,立书院以养寒士,立难民局以招流亡,立忠义局以居德行文学之士,立书局校刊《四书》《十三经》《五史》,以聘雅博之士。故江浙被难者,无不得所依归。”同治三年十一月,两江总督曾国藩恢复中断了十二年之久的江南乡试。同时,湖北、贵州、广东等省都恢复了因战争而中断的科举,标志着儒学的制度保障机制得以重建。
耐人寻味的是,有的地方官绅已流露出对科举会试的不满。道光进士冯桂芬于同治初年入李鸿章幕,主持修复了吴县等处学宫。他提出乡试后一月,“即于省闱借地会试,定为若而人取一人,一切如乡试法。中式者始令进京殿试,是亦恤士之一道也”。他或许是为士子节省费用考虑,而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进而主张:会试“然既归省,则非会试矣。不如径废会试,不愈邪?”这种“目无朝廷”的主张隐含着朝廷与地方文教作用的消长。同治四年,曾国藩、李鸿章会奏朝廷,请劝捐修复江宁、常州两府学宫。曾国藩指出:修复学宫,讲明孟子兴礼兴学之旨,“上以佐圣朝匡直之教,下以辟异端而迪吉士。盖廪廪乎企向圣贤之域,岂仅人文彬蔚,鸣盛东南已哉!”他们恢复儒学教化的愿望不仅践履于自身施政,而且影响各省大吏。
修建书院是“同光中兴”的地方要政之一。湘军克复安庆后,曾国藩捐廉修葺了安庆敬敷书院,招集士人入读。左宗棠声言:“今督两江,与有兴教劝学之责,愿承学之士,以程、朱为准的,由其途辙而日跻焉。升堂入室,庶不迷于所向矣夫。”举人涂宗瀛道光末年在京从吴廷栋、倭仁问学,后入曾国藩幕府,同治年间任江宁知府,其间将寺庙田产划归钟山、尊经、惜阴、凤池四书院,聘请学者名儒授徒。至“光绪中,梁鼎芬、缪荃孙长钟山,黄体芳、张謇长文正”。光绪二十九、三十年,“各书院遂尽改为学堂焉”。又如苏州的绝大多数书院、祠宇都毁于咸丰十年的战火,却在同治中期以后重建。同治二年,江苏巡抚李鸿章“复建紫阳书院,课四书文试帖如旧制。”次年又购新址,重建正谊书院,“参用湖南岳麓、城南等书院之式”。兼通中西学的冯桂芬“殚力经世之学,亦以肄业生为两院院长,士林尤为推重”。类似情形在江浙地区不胜列举。
咸同之际,湖南成为兴学重教的中心地区,湘军将领于此也不遗余力:胡林翼于咸丰十年建箴言书院;罗泽南修复石鼓书院,置湾洲义学;彭玉麟将积蓄充作书院开办经费;李元度建爽溪书院。同光年间,复书院、建义学的风气遍及南方,波及北方诸省。陕西贺瑞麟主讲学古书院、鲁斋书院多年,曾为兴建义学撰序云:“教养,在上者之责也,而在下亦与有力焉……此举也,较崇信异端、布施佛寺者,其功之大小得失为何如哉?识者当自知之。”他还上书学政吴大澂,指出“古者大儒所至,无不以兴学校为急务”。而关中士子于关学之祖张载“率不能举其名字,况知其学乎?若以之提倡,则承学之士庶识途辙之正,于以会归程、朱而不惑于他歧,尤麟之私愿也”。战火之后,重建儒学教化大体是从朝廷到地方官绅的共识。
清廷虽然涉及文治问题,却既无统揽全局的思想蓝图,又无切实举措。道光年间,太常寺卿唐鉴是京师理学的中心人物,“专以义理之学相勖”,曾国藩“遂以朱子之书为日课,始肆力于宋学矣”。唐鉴作《国朝学案小识》,以“守道救时”为己任,贯通内圣和外王。其所守之道基于宋学,尊程、朱而排陆、王。唐鉴以理学享誉士林,有“德望为京城第一”之誉,曾国藩、窦垿、吴廷栋、何桂珍、倭仁等人从之讲道问业。道光二十六年,唐鉴致仕归里,与罗泽南在省城一见如故。时处草野的左宗棠则谓“镜翁所学之正之邃,吾楚二百年来所仅有者”。京师理学人物遂与在野理学家罗泽南、方东树、路德、贺瑞麟、朱琦等人学术上遥相呼应。
然而,咸丰帝长期不信任理学人物。吴廷栋曾在咸丰二年觐见,自称读程、朱之书,咸丰则问“何以学程、朱者多迂拘?”又询问曾国藩、倭仁的学行。吴氏认为,程、朱以“明德为体,新民为用”,“迂拘”是不善学程、朱之故。曾国藩是咸丰帝欣赏的明代杨大洪一流节义之士,倭仁“是笃守程、朱之学者”,“其守道近似迂而能知大体”。吴廷栋的对答有为同道辩解之嫌,同时注意到曾、倭二人的学行差异。曾国藩创办湘勇以后数年,并未得到清廷真正的信任。他最初保举吴嘉宾、李鸿章等人为地方官的奏疏均遭部议驳回。到咸丰十年四月,咸丰帝同意明代理学家曹端从祀孔庙,谕令从祀“应以阐明圣学、传授道统为断。嗣后除著书立说、羽翼经传、真能实践躬行者,准奏请从祀文庙外,其余忠义激烈者入祀昭忠祠,言行端方者入祀乡贤祠”。实则朝廷对理学家从祀文庙进行了严格限制。但在咸同变局中,理学经世派成为清朝的中流砥柱,理学的实用价值迅速彰显。
应顺天府尹蒋琦龄的疏请,清廷于同治元年三月发谕:重申崇儒重道,各省科举“悉以程、朱讲义为宗,尤应将性理诸书随时阐扬,使躬列胶庠者,咸知探濂、洛、关、闽之渊源,以格致诚正为本务,身体力行,务求实践,不徒以空语灵明,流为伪学”。可见,清廷依重程、朱理学的倾向有所增强。同治二年十二月,清廷责成地方官吏教化民众。除优选学官之外,“着各省学臣督饬教官,实力宣讲圣谕,考其勤惰”。对教授书院、义学者,“务各延请耆硕,以副敦崇实学至意”。朝廷以“宣讲圣谕”为教官的首要职责,不能不使教化的儒学内涵大打折扣。
同治帝继位后,朝中理学官僚梦想再现魏裔介、熊赐履等人启沃康熙的故事,致书手握重兵的曾国藩,请其力保倭仁为帝师:“现在根本之计,孰有师傅所系之重;新政首务,亦有孰急于此者……乞特上一疏,专保艮峰以固根本,万不可放过此关。”倭仁随后身膺帝师,并于同治元年重掌翰林院,李棠阶、李鸿藻、吴廷栋等人在同治朝也逐渐显赫。颇具象征意义的是,同治八年正月十六日,清帝在乾清宫赐宴,倭仁领满大学士、尚书西向坐,曾国藩领汉大学士、尚书东向坐。于是,理学在晚清的重要性臻于高峰,却隐含了满、汉和央地权力的分野。
同光朝廷的儒学教化偏重宣讲太后、皇帝诏谕,学术色彩远逊于清前期。同治五年四月,署理广东巡抚郭嵩焘鉴于康熙朝“耆儒宿学,聚集京师,用以成一代人文之盛”,而同治朝“儒臣之在列者,学行远逊于前代”,特上疏保举人才,提出广东“经术湛深”的陈澧宜任职国子监,“专精数学”的邹伯奇和浙江李善兰“宜置之同文馆”。湖南精研儒学的朱宗程、丁叙忠、罗汝怀、吴敏树,江苏顾广誉、刘毓崧当由“皇上特召简用”或“置之八旗官学”授课。但这类奏疏都如泥牛入海。光绪二年,郭嵩焘以王夫之“笃守程、朱,任道甚勇”,“学行精粹”,“足以光盛典而式士林”,奏请将其从祀文庙。此疏表达了许多湘军儒将的愿望,却被礼部以王氏著述纯驳互见、不足当道统之传驳回。直至光绪三十四年,清廷摇摇欲坠时才准许将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从祀先师孔子庙廷”。
晚清最高统治者既无心培植庙堂儒学,而知识水平又停留在古代。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时,咸丰帝频繁地拜神、拈香,清帝轻教化而佞鬼神的信仰偏向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与许多远鬼神的“中兴”儒臣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形成鲜明对照。朝廷和地方对于儒学教化的自觉性既然相去天壤,其文治实效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语。
二、央地经学的消长
从康熙到乾嘉,经筵御论的学术倾向不无变化,而形式上重视经学。咸丰朝延续了经筵形式,而实效甚微。康熙朝日讲成为惯例,增进了君臣间的儒学交流,助益清初庙堂儒学的建立。咸丰即位后,礼部侍郎曾国藩奏陈日讲事宜,而廷臣认为“日讲一节,于听言之道、取人之法,两无裨益……该侍郎所陈,应请毋庸置议”,咸丰帝“从之”。程、朱经注仍见诸咸丰殿试,春秋经筵也大体保留下来,所讲内容重复以往,涉及《四书》及《五经》,而较强调道德礼义,或“节用而爱人”等主题。不过,这些仅仅是经学形式。
更有甚者,在长期没有皇帝亲政的同光时期,经筵形式已不复存在。那么,如何培育小皇帝的儒学基础?同治元年二月,两宫太后为同治帝选定祁寯藻、翁心存、倭仁、李鸿藻为师傅,令“其各朝夕纳诲,同心启沃。帝王之学,不在章句训诂。惟冀首端蒙养,懋厥身修。务于一言一动,以及天下民物之赜,古今治乱之原,均各讲明切究,悉归笃实”。因此,倭仁启沃清帝的文本是辑录古代帝王事迹及名臣奏议的《启心金鉴》。勤勉的李鸿藻在同治元年即参与编写《治平宝鉴》,又青睐于讲授宋英宗时期太后临朝的故事。同治三年五月,清廷令倭仁、贾桢选派翰林十数员,“将《四书》《五经》择其切要之言,衍为讲义,敷陈推阐,不必拘泥排偶旧习,总期言简意赅,仿照《大学衍义》体例,与史鉴互相发明”。然而,帝师们所授囿于帝王之学,同治帝较之康雍乾幼年的经学熏陶已经难望项背。
光绪年间也无经筵,此时殿试策问已注意到汉、宋学论题,如谓:“经学导源于汉”。《易经》本为十二篇,“何人始以彖、象、文言杂入卦中?《尚书》伏生所传者二十八篇,孔安国传、晋梅赜始奏于朝,果可信欤?”“《春秋》三家之义孰长?”“《三礼》之学,不讲久矣,能言其所心得欤?”这可谓经学再受关注的表征,一定程度上汲取了清代汉学家的见解。然而,光绪帝缺少研习儒经的愿望和精力,经学熏陶流于表层。
晚清朝廷经学形式残缺的同时,刻书也变得有名无实。康雍乾时期,内府武英殿是全国最重要的官书局,集全国之财力、物力,编刻人员近千人,精选底本,校刻、印刷精美,刊刻钦定经、史、子、集图书,旁及各种典籍,刊成《通志堂经解》《三礼义疏》《四库全书》等。但至咸同时期,武英殿急剧衰落,所刻书籍仅寥寥数种,光绪朝所刻也仅有24种。时人记载:《四库全书》于雍乾学者著述,或因“时代太近,或其人生存,格于定例,不及著录。嘉道以后,更无论矣。光绪中叶,论者多主续修《四库》,朝旨允于《会典》告成举行。未几即有日本之败,《会典》成后,新说繁兴,百政待举,无暇及之矣”。这种状况虽有客观条件所限,而主要根源在于最高统治者的学术造诣和认识。
然而,其时督抚刻书方兴未艾,接续了经学脉络。江南官私藏书多毁于战火,收藏《四库全书》的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无一存者。“宁波天一阁,亦孑然无余,可谓千古文字之厄”。有的藏书家“所存仅十之三,亦散落人间矣!”于是,晚清地方官书局接踵兴起。咸丰九年,湖北巡抚胡林翼建立武昌书局,刊刻《读史兵略》《弟子箴言》。同治二年,曾国藩及其弟曾国荃在安庆建立书局,着手刊刻《船山遗书》。次年攻克江宁,旋即成立金陵书局。当时士子欲求《四书》而不可得,金陵书局先刻《四书》《十三经》,继刻《史记》《汉书》,后又与浙江、湖北等省分刻《二十四史》。此外,曾国藩在安庆、金陵还刊刻了《皇朝中外一统舆图》及莫友芝的《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笺异》、邵懿辰的《尔雅正义》等。各地书局的刻书重点均为《四书》《十三经》《二十四史》,有的也涉及先秦诸子及近代西学。刘声木说:“同治年间,曾文正公国藩踵前代南监本、北监本之例,创立官书局。一时如江南、江苏、淮南、浙江、江西、湖北、湖南七处,均设立官书局,刻印四部中要籍,流传甚广。”同光年间,督抚设立的官书局总计达30余家,成为重建学术文化的重要工程。地方书局得到清廷认可,却不是清廷诏谕的产物,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理学经世派的文化自觉。
督抚们学术上多兼容汉、宋,重视程、朱理学。以金陵书局为例,校刊者多长于汉学,而主事者多是理学人物。涂宗瀛官江宁后,除短期主持金陵书局之外,晚年还以求我斋、六安斋等号刻印书籍300余种,绝大多数为程、朱和晚清理学家倭仁、何桂珍等人著述。道光举人洪汝奎早年在京师从倭仁、曾国藩、吴廷栋讲求性理之学,主持金陵书局达12年之久。在他们主持下,金陵书局刊刻的儒家典籍兼容汉、宋,而理学书籍占据主流。同治四年左宗棠在福建设立正谊堂书局,重刻清初理学官僚张伯行编纂的《正谊堂全书》,收有程、朱学派的著述55种,凸显了复兴理学的主旨。官刻之外,有的民间学者也热心刻书。贺瑞麟在咸同之际坚辞地方官举为“孝廉方正”,而强调孔孟及宋儒之书“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离。学者不欲求道则已,如欲求道,亦安可舍圣人之书而他务哉!”他自咸丰初年主持编刻理学著述,至光绪十九年卒时已刻印100多种,后人编为《清麓丛书》。
晚清兴建的一些书院成为重兴经学的中心。光绪十年,江苏学政黄体芳得两江总督左宗棠支持,在江阴创办南菁书院,“专课经学古学,以补救时艺之偏”。次年,王先谦继任学政,在院中设立书局。两年后刊成《皇清经解续编》,收书207种,凡1430卷(光绪十四年南菁书院刊本),篇幅超过阮元编纂的《皇清经解》。这与朝廷“无暇”续修《四库全书》形成了鲜明对照。光绪五年,郭嵩焘与湖南学政重建湘水校经堂,并记云:自阮元于嘉道年间建诂经精舍、学海堂后,“自顷十余年,各直省亦稍建书院,以治经为名,下及郡县亦相率为之。而湖南校经堂课实开偏隅风气之先。意者经学将遂昌明,承学之士有所凭藉以资讨论,庶几一挽末世之颓风邪?”这些举措未必能挽“末世之颓风”,却表明了经学的区域性增长。郑观应指出:“中兴将帅,每克复一省一郡,汲汲然设书局,复书院,建书楼。官价无多,尽人可购,故海内之士多有枕经葄史,堪为世用者。”稍后,四川的尊经书院也成为培育经师的摇篮,发展为西南地区传衍经学的重镇。很大程度上因地方官绅的倡导,经学虽受晚清战火和西学的冲击,却在同光时期有所恢复。原来偏重理学或经学薄弱地区,如湖南、广东、贵州、四川等省,汉学还有相对发展。湖南的魏源、邹汉勋、王先谦、皮锡瑞、叶德辉,岭南的林伯桐、陈澧、侯康、康有为,福建的陈寿祺、陈乔枞父子、林春溥、林昌彝,贵州的郑珍、莫友芝,四川的廖平、胡从简等学者转治或专心汉学,成就引人注目。
三、保守或经世的理学分流
康熙朝庙堂儒学汲取了在野理学,而咸同朝廷对地方理学缺少注意,遑论吸取民间学术。同治及光绪初年的朝中理学官僚在清议导向上不无意义,朝廷与地方理学家的学术基础亦大体相同,但二者思想倾向反差明显,也表明其文治关怀的高下之分。
首先,朝中理学官僚多视程、朱理学为万能的治平理论,固守“诚意”“居敬”信条而不能在学理上因时变通。倭仁对窦垿重释理气、格物不以为然,认为程、朱所论“至精且备”,“何必另立新说,滋后人之惑耶?讲学最忌一‘我’字,自辟一解,以为独得之奇,而旁征博引,以证其是,此是己见为害。”吴廷栋称:“某生平笃信朱子,不敢师心自用妄发一语,故所立说处尚不致为识者所摒”。此处所谓“识者”即是京师倭仁为首的理学圈子。与倭仁、吴廷栋齐名的李棠阶学术上不排斥陆、王,但仍然“以治心克己为至要,居敬穷理,一守程、朱之法”。与倭仁交往密切的李鸿藻笃守程、朱,晚辈帝师翁同龢在同光之际的治学诗云:“当时帘前被慈命,蒙养工夫重心性。进讲惟闻谟训辞,退朝还主程朱敬。”他们只是恪守程、朱信条,“返本”而不“开新”。
地方理学人物在究心程、朱之学时,注意因应时势,重释理学,最终将重心转向“开新”方向。曾国藩尊程、朱而不完全排斥陆、王,又兼采汉、宋学之长,其日记云:“今人讲理学者,动好评贬汉、唐诸儒而等差之;讲汉学者,又好评贬宋儒而等差之,皆狂妄不知自量之习。”其《圣哲画像记》既有先秦文、周、孔、孟等宗师,又包括汉代大儒许慎、郑玄及清代经学家顾炎武、秦蕙田、王念孙等人,较之唐鉴、倭仁等人的儒学系谱更具有包容性。他贯通为道与为学,兼重道器,敏锐地回应晚清的内外危机。罗泽南不满记诵词章之学,而重视讲求身心性命之学以明道,提出士人治学居处当为醇儒,“出则以道济天下而为王佐”。他们穷理明道,大体将礼治作为践履途径,形成内理外礼的儒学结构。
郭嵩焘认为:“《礼》者征实之书,天下万世人事之所从出也,得其意而万事可以理,不得其意则恐展转自牾者多也。”曾国藩认为,“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他尊崇江永的《礼书纲目》、秦蕙田的《五礼通考》,也重视唐《开元礼》,在军营中研读不辍。清末徐珂认为:“其在江南大营平乱也,治官书,上封事,指陈属官一切,有所施行,率多取诸《五礼通考》,而于后生小子,亦兢兢以是书为言。”刘蓉“少承庭训,独好礼书”,中年戎马倥偬,而于礼学书“未尝一日或释”。他休致之后,又建绎礼堂,每日研究历代礼制及清代秦蕙田、江永等人的礼学著述。故有论者云:他们是用礼教来武装湘军,“用儒学来指挥作战”,“要用礼来统治国家”。这些居处草野或身任督抚的理学人物学术上多是阐释程、朱旧题,却将内圣功夫推衍于以礼治国,将理学导向了更新、发展的轨道。
其次,朝中理学官僚号称“正人立朝”,却流于空谈性理,很少涉及社会实际。吴廷栋、方宗诚地位不同,而都认为同治初年朝政有中兴之象,而“盈廷积习已深,变化匪易,非得一二见微知著、通达治体者以为赞助,则中外之气不能流通”。如何“通达治体”?吴廷栋与倭仁的救本之策是“平居讲学要当以绝利一源为先。务必由浅而深,由粗而精,充类至尽,始为究竟”。标榜治本而不切实务的偏向在其仕途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咸丰二年,倭仁正外任新疆叶尔羌副都统,上《敬陈治本疏》泛论治道,却不及边陲情形,又劝君主“立志为尧、舜”。倭仁因此被咸丰帝斥为“忽近图远”,疏忽职守,告诫其当“留心边务,实力讲求”,“毋得徒托空言,致负委任”。李棠阶对考据、词章不以为然,而强调“古之学术,道在明伦,功在慎独,无他务也”。他在同治初年提出朝廷振纪纲,明赏罚,而君主“刻苦奋励之实,不徒在于用人行政,而在于治心;治心之要不徒在于言语动作,而尤在于克己”。他们侈谈内圣修身,而置“用人行政”的实务于不顾,没有改变“忽近图远”的习气。
当然,晚清也有精明的廷臣。恭亲王奕好理学,常谈“以道制欲”。他像湘军儒将一样认为:“礼也者,理也。古之王者懋德建中,以之正一己之心莫如礼,以之治天下人之心亦莫如礼。”但是,恭亲王的礼学重心是重塑君主权威,强调“辨上下而定民志者,礼也。上下之分既明,则威福之权皆出自上。君君臣臣,国本固矣。春秋之时,君弱臣强,上失其政,下执其柄,国势日替。盖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这与郭嵩焘等人因时变礼的主旨显然有别,却包含强化君权的现实针对性。循奕的策略,朝廷和君主的权威无疑会得到加强,但太后垂帘听政也不合礼制,故他以“君君臣臣”为主旨的礼制仍然不能落实。
在西太后的控制下,理学廷臣不可能有所作为,至多成为掣肘洋务运动的清流派。同治四年二月,翰林院编修蔡寿祺参劾恭亲王奕和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正中西太后兔死狗烹的策略。在西太后与奕的争斗中,倭仁成为西太后的干将。郭嵩焘的日记写道:“天下乃有此狂悖善噬之人,于时为妖矣。”倭仁、万青藜参劾刘蓉时,郭嵩焘更感叹:“朝政之乱,尤可知也”。随后,奕逐渐丧失权位,“中兴”将领不得不解甲归田或缩减权力,西太后则日益走上独裁专制之路。虽然李鸿藻、翁同龢、徐桐等人也曾合奏劝阻西太后重修圆明园,提出整顿八旗官学及某些维护国家权益的主张,但读其书札、日记可知,他们沉溺于官场应酬,罔顾下情,不思作为。光绪十三年,陕甘总督谭钟麟致信军机大臣翁同龢,提出增设官车局以代替征用民车,减轻百姓负担。翁氏回信云:“弟于此等事从未措意,坐啸画诺,几同偶人。”57这种情形大体是“中兴”廷臣的常态。
与之对照,地方理学官僚早年既讲求程朱理学,又蕴含经世关怀,左宗棠为家庙所撰“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的联语,恰好表达其思想主张。他们本程朱之学而发为事功,在奏疏中一再指陈社会积弊。罗泽南早年假馆四方,曾执教于湘籍官员贺长龄、贺修龄兄弟家,自道光十六年“因取《性理》一书读之,遂究心洛、闽之学”59,宗朱子而辟阳明,著《人极衍义》《姚江学辨》等书。欧阳兆熊指出:罗氏“凡天文、舆地、律历、兵法,及盐、河、漕诸务,无不探其原委,真可以坐言起行,为有用之学者。而至性亦复过人,可谓笃行君子矣”。罗氏于咸丰二年倡办团练,加入湘军作战,四年后战死。尽管如此,“湘中书生多拯大难、立勋名,大率公弟子也”。故论者谓罗氏“大讲理学于湘中,后湘军遂以治理学者为干城”。
在道光年间的唐鉴看来,“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受其影响的曾国藩彼时也认为:“盖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至咸丰元年,曾国藩则在三者之外增加“经济之学”,认为“此四者缺一不可”。他主张“义理”与“经济”本不可分,而后者所读之书包括《会典》《皇朝经世文编》。他在日记中提出“经济之学”的具体内容:“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前世所袭务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 其中涵盖了嘉道年间经世实学的主题及礼制关切,并且凸显了兵制、刑律及更新创制的重要性。
其三,朝中理学官僚既然拘守崇道抑器、重义轻利的教条,那么贬低、排斥西学也就不足为怪了。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廷不得已采取了一些应时之策,却始终没有自觉地走上变革轨道。
晚清一些人以西学沟通理学的“格物致知”,在“格致学”名义下容纳西学。湘、淮将领也积极实践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他们在奏疏、言论中竞谈西学、洋务。左宗棠认识到西方由器以进于道的富强之策:“泰西弃虚崇实,艺重于道,官、师均由艺进……盖得儒之数而萃其聪明才智以致之者,其艺事独擅,乃显于其教矣。”在他们影响下,清廷于同治元年设立了京师同文馆。其后,李鸿章设立了上海同文馆,郭嵩焘也在广东巡抚任上设立广州同文馆。这些机构旨在培养语言人才,研习算学及科技。附设于江南制造总局的上海机器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及医学堂亦有成效。自同治十年,曾国藩奏请挑选幼童赴美留学,至光绪元年已选送四批共120名学童。光绪初年,李鸿章主张朝廷对留洋学生“破格从优给奖,以昭激劝”。这些留学幼童所习专业仍囿于水师、制造、科技、医学等领域。当洋务派官僚主要从中道西器的视野认知中西文化优长时,郭嵩焘进一步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他已触及西方富强的根本,成为出类拔萃的洋务派思想家。
然而,许多廷臣仍然排斥西学。倭仁热衷于从宋儒经注重建理学权威,认为宋儒“格物”,“即格修齐治平之理,文义本极明显”。他割断了程、朱理学与晚清“格致学”的思想关联,无异于为理学作茧自缚。为了突破同文馆的困境,同治六年恭亲王奕主持的总理衙门疏请同文馆从正途科甲人员(包括进士、举人)中招考天文、算学生。御史张盛藻等人强烈反对,倭仁随后疏请停罢此举。在他看来,“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他也反对聘用西人教习天文、算学,坚信中国士人“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西太后最初认可在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馆。但在倭仁等影响下,同文馆招收正途科甲人员的计划无果而终。到光绪二年,郭嵩焘仍感慨:“京师士大夫不下万人……但以诟毁洋人为快,一切不复求知,此洋祸所以日深,士大夫之心思智虑所以日趋于浮嚣,而终归于无用也。”
太平军的战火余烬尚存,英法联军入侵也才过去几年,曾国藩记录在京情形:“二十一、二、三、四各处公请听戏四天。二十五、六皆有事趋朝。京中向系虚文应酬,全无真意流露,近日似更甚矣。”曾氏这等大员至京,仍难免官场消沉之感。京官们忙于应酬,却无心探究时艰,更没有痛定思痛。同治年间郭嵩焘曾致信友人:感叹面对“西夷之祸”,朝中“无能一发其愦愦”者。非但如此,朝中并且不能容忍郭氏耿直上书。赵烈文评论倭仁等廷臣与地方官的分歧:“按今朝政以洋务为至急,倭身任宰辅,岂得自处清流,置身事外。坐言起行,事无二致,既以总理衙门为办理不善,一奉朝命,即当不避艰难嫌怨,力图振耻,方为大臣视国家主忧臣辱之道。乃在人则议之甚严,在己则去之若浼,君子耻躬之不逮,是在闾阎犹不可,而况秉国者哉?”他们对倭仁秉政的不满,折射出央地儒臣的思想分野。洋务实践激发了一些地方官绅重释治平之学。冯桂芬于咸丰十一年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稍后,郑观应提出“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这些言论被后人视为“中体西用”论的滥觞。它基于儒学而又融合西学,成为最初嫁接中西文化的基本模式,有裨于弥补庙堂儒学的理论缺陷。然而,“中体西用”论长期没有得到廷臣的重视。朝中重臣既在学理上固步自封,又疏离经世关怀,自然不能提出像样的文治主张,清朝的文治弱化、衰微遂成必然之势。
结语
清廷在太平天国战争后一度收回了大部分军事、财政大权,却缺少对文治主导权的自觉。清代有的君主(如康熙、嘉庆)治下,尚能注意朝野士人的学术风尚,而晚清朝廷文治大体乏善可陈。晚清最高统治者西太后擅弄权术,却没有儒学造诣,也缺少政治见识,于文治策略茫然无知。湘、淮儒将直面民生现实和社会积弊,对清朝危机有着强烈的切肤之痛,故注意讲求实务,尊崇程、朱理学而因时变通。因之,同光年间的文治举措均出自地方官绅。有的经过地方官反复疏请,渐获朝廷认可;有的则始终被清廷束之高阁。
同光文治的内弱外强格局冲击了清廷的文化霸权。李鸿章曾论其师曾国藩总督两江:是时曾氏“威振方夏,名闻外国”,“中外大事皆就决之。公所谋议,思虑深远”。战后曾国藩裁撤湘军,交回了军权,但清廷并未取得文治的主导权。章太炎有云:“盖孔子所以为中国斗杓者,在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而已。”也可以说,“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正是建立文化“斗杓”的根本。朝廷于此无所作为,文化权力的斗转星移或者说地方化趋势就不可避免。赵烈文在同治六年对其幕主曾国藩说:“今师一胜而天下靡然从之,恐非数百年不能改此局面。一统既久,剖分之象盖已滥觞,虽人事,亦天意而已。” 曾国藩从清代“世俗文法”中破茧而出,却不能扭转清帝国的“剖分之象”。满族统治者一直敏感地集军事、政治之权于朝廷,却没有自觉地扭转文治的剖分、衰退之势。于是,晚清的新思想、新学术静水深流,直到汇集为民初文化新潮。
作者简介:罗检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来源:《安徽史学》2022年第6期。
,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