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问题(卢梭社会契约论)
英国人伯特兰·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用一个专门的章节来介绍卢梭,他把卢梭称为“浪漫主义之父”,认为卢梭是“伪民主独裁政治哲学的发明人”,是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精神导师,而罗斯福和丘吉尔则代表了洛克的自由主义光荣传统。在谈到《社会契约论》时,罗素几乎是把卢梭的主权学说与霍布斯的理论混为一谈了。霍布斯在《利维坦》里把“主权者”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所有人都必须服从于“主权者”,“主权者”永远也不会犯错,“主权者”的权力来自于所有人的转让,臣民们对“主权者”的任何反抗都是不正义的。显然,霍布斯的“主权者”具有专制君主的影子。但是,卢梭虽然把霍布斯所建好的这座庙搬了过来,却已经换掉了里面所供奉的神灵——卢梭认为“人民”才是真正的主权者,也就是说主权在民。这使整个主权理论发生了质的变化。
或许是因为罗伯斯比尔曾拜访过卢梭,或许是卢梭的主权理论与集体主义有几分相似,罗素就肤浅的认为卢梭主张由社会、国家来统治所有人。这种理解水平,就好比说冰和玻璃都是透明的,所以它们是同一类物质一样,十分愚蠢。卢梭确实说过“公共意志总是正确的并且有公共益处”,确实说过“主权权力是绝对的、神圣的和不可侵犯的”,但这跟暴民政治理论完全是两回事。卢梭的核心概念是“公共”,暴民却狂热地崇拜“多数”。

公共意志并不是多数意志
社会契约是公意的体现在物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合力”,它是指几个力共同作用所产生的效果。合力的方向不一定是最大的那个力的方向,而是由所有力共同决定的,即使是微弱的力也会对合力的方向起到影响。在政治学领域中,“公意”就是一个类似于“合力”的概念,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区分了“公意”与“众意”,认为社会契约是公意的体现,而非众意的结果,其中民意就是一种众意,它是集体的意志,而非普遍的意志。
集体与普遍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集体利益不一定是普遍利益。在一个国家中,生命权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普遍的利益;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国家需要牺牲某些人的生命来维护集体的利益,例如在弹尽粮绝的守城战中,主将臧洪、张巡等人就曾牺牲掉老弱病残的利益,把他们杀死并且分食,以此来坚守城池,维护集体利益。集体利益代表的只是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普遍利益则必然是所有人都一致拥有的利益。
类似的,集体意志只是大多数人的意志,而公共意志却是所有人所共有的意志。例如通过表决来发布某项政令或推举某人担任某个职位,大多都得通过集体表决,根据少数服从多数来的原则来作出决定。只要多数意志在数量上获得了胜利,那么少数意志就可以忽略不计,这时多数意见就代表了众意、民意;公共意志却并非如此,它必然是所有人所共有的、共同承认的意志,例如要保护人身财产安全、不得损害他人利益、买东西要付款、欠债要还钱等等,这些规定是所有人都一致承认的,因为它们维护了所有人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存在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
集体意志是由各种不同意志组成的,它选择遵从人数最多的那个意志,直接忽略掉其他各种呼声不高的意志;而公共意志则是由各种不同意志相互作用形成的,各种意志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合力”,这个“合力”代表的就是各种意志之中所共同拥有的部分、代表了它们的共性,名为“公意”。
人们把人数最多的意志称为民意,但民意并非公意。对于人类的利益,人们可以有各种理解,产生出各种意志,有时候大多数人认为财产公有、平均分配符合全人类的利益,有时候则认为财产私有、阶级差别更符合人类利益。民意随着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环境而动荡起伏。但是,无论哪个时代、哪种社会环境,人们都一致承认保护人身财产安全,对全人类都有利——这就是一个不变的公意。
社会契约就是公意的产物,人们普遍认为签订社会契约、参与社会生活,能够保障人身与财产安全,约定互不侵犯、遵守规则、服从法律。毫无疑问,公意始终能够认识到人们的公共利益;而民意却不能如此,正如卢梭所说:“人民永不会被腐蚀,但是它常会受到蒙蔽。”人民永远也不会把“奴役他人”上升为一个普遍认可的公意,但人民有时候会被蒙蔽,认为受人奴役可以混口饭吃,符合自身的利益。
因此,卢梭认为公意永远也不会犯错,但民意经常动荡起伏、受人摆布,常常出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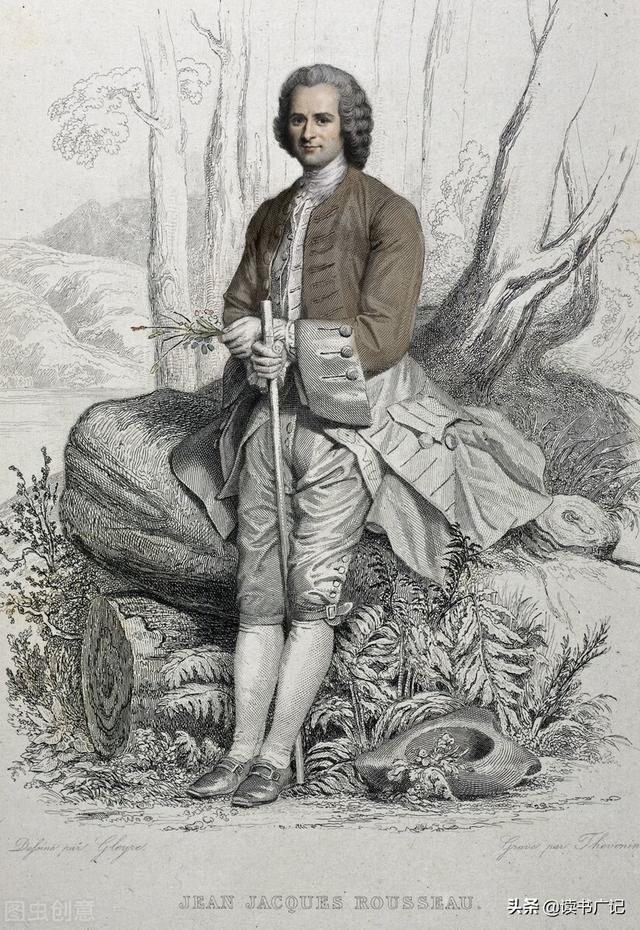
公意永远不会犯错,民意却常常被蒙蔽
公意永远存在,不会被任何民意所取代正如合力的方向不一定是最大的哪个力一样,公意也不一定由人数最多的群体来决定。民意在很多时候都仅仅是众意而非公意,它浮躁易变、容易被舆论所左右,为此才需要不断地进行民意调查。
很多时候,统治者只要控制媒体,钳制舆论,主导教育,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塑造民意。但无论他怎么做,都始终无法改变公意,在他的权力影响减弱或者消失之后,公意就会逐渐体现出来,狂热让位给理性,人数让位给真理,虚构让位给事实——因为人民永远也不会承认“奴役他人或被他人奴役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从来就没有哪个统治者敢宣称他有权奴役所有人,他们只能通过谎言与话术,让人民相信君权神授等虚假理论。统治者只能操作民意、蒙蔽民意,但不敢对抗公意,不敢公然违背人们所普遍认可的东西。
《乌合之众》里说人们都曾狂热地崇拜过拿破仑,把他当做神一样的存在,可是自从拿破仑战败从而丧失一切权力之后,这种狂热的民意也就消失不见了。再也没有人把拿破仑当做神,人们承认他是一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但他只是一个人,并非神灵。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拿破仑当权的时候,他的政敌与反对者都因权势的压迫而缄口不言,任由他的崇拜者将他吹奉上了天,着时多数意志起到了压倒性的优势。但是,当这种权势压迫解除之后,不同方向的力就会逐渐产生,不断修正原先的合力方向,把拿破仑从神降低为人。
法国大革命就是一部民意不断脱离公意又不断回归于公意的历史,当时人们都普遍认为应当破除旧制度、迎来新时代。但究竟怎么改变旧制度,不同阶层的人有不同的想法。在最初的时候君主立宪制成为了民意,但是在国王出走、并且涉嫌勾结反法共盟之后,共和制立即就成为了最广泛的民意;而当国王被处死,法军却接连战败,祖国在危急中时,由爱国热情所点燃的暴民情绪忽然喷发,人们四处捉拿“卖国贼”,到处滥杀贵族与无辜,演变成了雅各宾派的大恐怖统治。人们起初反对暴君,结果却弄成了人人皆是暴君。当民意脱离公意的轨道之后,它再次迎来了修正,并且从督政府转化成拿破仑的帝制。法国人仿佛又回到了原点,他们推翻了一个帝国,却又建立了另一个帝国。但是拿破仑帝国已经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帝国,而非旧的封建帝国了。

公意的存在,使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日趋客观
公共意志必然会维护公共利益卢梭认为人民就是主权者,所谓的人民就是那些拥有公共意志,为了公共利益而签订社会契约,组成共同体的人。
在这种共同体中,政权所要维护的并不是集体利益,也不是特殊利益,而是普遍利益。维护集体利意味着可能会牺牲少部分个体的利益,维护特殊利益意味着要牺牲其他人的普遍利益。例如,在斯巴达,为了城邦的集体利益,要实行优胜劣汰,那些体格不健康的婴儿可能会被秘密处理掉,以免拖累集体;又如在古雅典,为了维护自由民的特殊利益,就需要认可奴隶制的存在,让一部分人像家畜那样供人驱使和管理。只有在卢梭所设定的国家中,公共利益才成为共同体所追求的目标,要维护所有人都有的人身、财产、平等、自由、名誉等多项基本权利。而且公意始终都承认这些权利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是社会应当加以保障的。
公意始终都面向公共利益,它着眼于全人类、包括每个人都普遍拥有的利益,着眼于人们的基本权益。所以当卢梭说“公共意志总是正确的并且有公共益处”时,他是指人民永远也不会堕落,永远也不会认识不到自己的权利,只要把遮在他们眼前的黑皮扯去,只要能够对他们进行启蒙,他们很快就会明白什么是公共利益。人民就是主权者,公意就是人民的意志,人民的权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民的公意永远是正确的。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