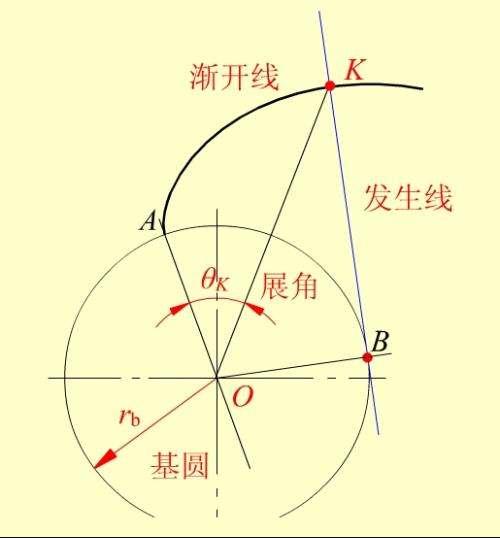树正气立公心(林官明引风导气)
2004年,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的一部名为《国家使命》的电视剧风靡全国。该剧改编自长篇小说《风洞》,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一批专门研究空气动力学的军人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去征服风洞王国中那一座座科技高峰的故事。通过此剧,很多普通百姓知道了“风洞”一词。
风洞最早应用于航空业,被称为航空风洞。20世纪30年代,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开始利用航空风洞研究风对建筑和结构的影响,其后,西方国家陆续建设了一些风洞专门进行大气污染扩散与质量迁移的研究,这些风洞叫作环境风洞或气象风洞。
1984年,我国第一座完全自主研发的环境风洞——北京大学2号环境风洞建成并投入运行。运行至今,该风洞在科研、教学以及国家建设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取得了多项荣誉。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高工林官明是北京大学2号环境风洞实验室的第5任负责人,自2001年担任主任以来,他带领着实验室完成了大量有关环境空气动力学方面的研究课题和测量任务,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应有贡献。

林官明
风洞研究助推环境科学发展北京大学2号环境风洞实验室位于北京大学力学大院西北侧,物理学院北侧,占地约870平方米,高度8米,风洞总长50米,实验段长32米、宽3米,能够高精度地进行大气扩散、大气湍流机理、近地表起降尘、近地表防风效应、建筑物风荷载与风振动等研究。它是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开展中国的环境科学研究,由北京大学叶文虎教授率领其课题组创建的,已成为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领域重要的组成部分。
“环境风洞是用来产生人造气流的管道,其功能在于模拟大气边界层流动,因而,涉及大气边界层流动的一些科学和工程问题都可以用环境风洞进行模拟,做相关的测量和研究。”1999年,林官明放下手头的核电站应急事故模拟研究,前往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进行访问,师从Joubert教授学习风洞模拟研究。之后,他回到北京大学一边从事研究工作,一边攻读博士学位,导师为北京大学2号环境风洞实验室创建人叶文虎教授。博士毕业后,他留在北京大学2号环境风洞实验室工作至今。
20多年来,林官明在环境风工程,尤其是大气污染扩散研究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前沿、创新工作,主持过多项有关大气环境污染的国家攻关项目以及国内外横向课题,其测试基础数据用于许多重大工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参观科普展览
目前,我国在很多领域对环境风洞研究都有着重大需求。尤其是在环境科学的教研中,环境风洞是目前国内外都无法替代的重要手段之一,是理解大气扩散现象的基本工具。
林官明介绍说:“直接对大气中的污染物进行测量,耗资巨大,费时费力,而且获得的往往是特定情况下的测量结果,当外界条件如风速、建筑物形状或地形改变时,现场实验就很难预测污染物的迁移扩散规律。风洞实验方法测量方便、准确、安全,气流参数如速度、压力、密度、温度等易于控制和改变,可满足各种试验要求,一般不受天气变化的影响,可以连续进行试验,利用率高,实验费用比较低廉。”
至今,2号环境风洞实验室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已经承接了包括国家大剧院、国家体育场、北京市金融街、北京电视台、北京商务中心CBD在内的70余项重要建筑风荷载试验;在安全能源领域,承接了包括山东邹县超大型冷却塔、华能电厂煤棚、聊城电厂冷却塔等10余项风荷载试验;在环境领域,实验室承接了大亚湾核电站大气扩散试验、澳门街区汽车尾气污染扩散试验在内的20余项重大项目试验,为环境控制与发展等国家级课题提供了第一手试验数据。
“在风洞实验室做实验研究,很多工作都富有挑战性。没有现成的教科书可以参考,也没有人告诉你该怎么做,好多试验完全靠自己去琢磨。”说完,林官明又有些愉快地说道,“但是,在风洞里面做试验也很好玩,因为我们要模拟现场,用到的模型都要我们自己设计并制作出来。比如,街区汽车尾气污染扩散试验,我们就做了移动的汽车模型,煤堆起降尘研究中则设计制作了堆起料机的模型,当然这个堆起料机模型得按要求一定时间内运送一定量的煤粉。”
在所有的科研教学项目的背后,风洞的正常运行是顺利完成科研教学任务的前提。多年来,在实验室工作人员的精心维护下,北京大学2号环境风洞实验室的设备和仪器都工作正常,满足了风洞实验所需。
开展干沉降的前沿研究在干燥天气期间,尤其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干沉降是大气颗粒物的主要去除方式,它对区域辐射平衡、地表沉积、深海沉积和全球气候变化都有巨大的影响,因而正成为大气环境科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气溶胶颗粒向地球表面的干沉降规律在大气环境科学中属于基本研究内容之一。湍流边界层的速度分布和下垫面空间结构的不规则性导致气溶胶干沉降具有很强的随机性,而颗粒物粒径和密度的不同以及微气象条件的多变使得干沉降过程更加复杂。目前国内外对干沉降速度的物理意义仍缺乏深入研究,相应的基础数据也比较少。
早在2000年,林官明攻读博士学位时就已经对大气颗粒物的运动规律进行了初步探索,并且与导师叶文虎教授多次讨论边界层湍流的影响。在北京大学2号风洞从事实验工作后,林官明继续对“壁面猝发湍流对颗粒物起尘机理”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研究,相关成果已发表在2008年的《中国环境科学》期刊。
2017年5月到2018年12月,在武威的腾格里沙漠,林官明作为现场实验人员参与了“长江生态遥感分析和沙尘重污染起尘机理研究”项目,协助任阵海院士探索风沙起尘的机理,在大气颗粒物实验研究方面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为后期的实验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他还与任阵海院士共同研究了室内颗粒物的稳态置换流的净化机制,引起了国外同行的高度重视。
2018年,在大气气溶胶干沉降方面,林官明团队还开展了自由探索课题“典型下垫面比表面积与干沉降速度的关系”,已初步建立了一个干沉降速度模型。在研究过程中林官明团队发现,国内外几乎没有研究涉及干沉降速度与颗粒物物理运动速度以及参考高度之间的关系,并且缺乏同时测量多种下垫面的系统资料,颗粒物干沉降的数值模拟与实测结果相差甚远。
因此,基于前期在干沉降方面所做的工作,林官明开展了“大气湍流作用下气溶胶干沉降特征”的实验研究,项目将以现场测量为主,辅以数值实验和理论分析,对干沉降速度与颗粒物物理运动速度之间的内在联系,剪切应力和湍流强度的垂直分布规律及其对干沉降过程的影响进行较为细致的研究,进而提出新的干沉降参数化方案,以完善气溶胶干沉降的研究理论,促进大气环境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该项目研究在国内外属于比较前沿的研究。其创新之处在于:揭示干沉降速度的物理意义,提出干沉降参数化方案。
科研站在好奇的背后亚里士多德说,“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学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林官明对这句话有着深切的认同。在他看来,好奇是科学的源动力,因为好奇,哲学家才会思索人生的真谛,科学家才会探索宇宙的奥秘。
了解林官明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喜欢“玩儿”的人。他的很多决定都是基于“好玩儿”的初衷。他从小就爱问为什么,对各种自然现象充满好奇,看着父亲做木工,他也喜欢动手做一些小物件,还带着两个妹妹用土法熬硝做火药。中学时,他曾将高中物理的所有实验全部做完,期间,物理老师周良襄干脆把学校物理实验室的钥匙交给了他。这些经历造就了他超强的动手能力。
1987年,林官明以优秀的成绩考进北京大学力学系。“当时选专业是有些盲目的。高考前,我在中学的图书馆看了一本《八大科技领域巡礼》的书,当时觉得力学挺好玩儿,就选择了这个专业。”大学毕业后,林官明因偶然的机会进入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中心工作。由此,研究方向转向环境空气动力学方面。
谈及转向环境科学研究的原因,林官明先讲到了他中学时的见闻:“我读的中学是临汾一中,学校临近汾河,周末时我总是去河边玩。20世纪80年代的汾河污染已经很严重了,捧一捧水放在沙滩上,水干以后,都能揭下一层皮。”对此,林官明还专门写了几篇有关环境污染的作文。上大学后,他选修了“环境科学概论”课,让他对环境科学有了更多的认识,也对环境科学产生了很大兴趣。
林官明坦言道:“做研究需要有兴趣做基础,因为科研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探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时候都是沮丧和挫败的。如果没有兴趣作为基石,很难持久地坚持下去。”尤其是做实验研究,极其需要耐心与恒心,接触的东西也十分复杂,“如果你觉得好玩儿,那你就不觉得苦,结果出来的那一刻,真的会很开心。”
当然,这种开心的背后,是对“创新”和“自力更生”这两种本领的掌握。在实验过程中,对软硬件的掌握全靠自己,很多时候,还要根据理论的指导和实验的需求,自己动手做出所需要的装置和模型。近期,林官明正在做的一个完全自动采样的装置就是“无中生有”。他说:“创新不能墨守成规,尤其要鼓励‘不听话’的孩子,跳出框架和束缚,才能更好地实现创新。”
近几年,林官明在做风洞试验的过程中由堆料后的沙纹联想到沙漠里的沙纹、天上的云街、鸣沙,规律性的空间分布背后一定有其必然性,兴趣促使他思索。“这是不由自主的思考,我喜欢思考。沙纹很有规律,沙丘也很有规律,我就觉得好玩儿啊,就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呢?沙鸣又是怎样产生的呢?然后,我就去研究了。”

在腾格里沙漠中进行与沙纹研究有关的表面波测量
很多人对他的钻研行为不理解,问他:“你研究这个有什么用吗?”面对这些疑问,林官明也表现出了不理解,他说:“我不喜欢别人问我你研究的这个东西有什么用,为什么一定要有什么用呢?我看见一个现象,然后搞清楚为什么,这就很有意义,很好玩,不是吗?”
觉得好奇就去研究,觉得好玩儿就去研究,对林官明来说,很多时候,研究就是如此单纯,仅仅是他想知道原因,然后他就投入精力去探索,去找寻。
揭开鸣沙的神秘面纱鸣沙现象最早见诸文献《三秦记》:“河西有沙角山,峰崿危峻,逾于石山,其沙粒粗,色黄,有如干躇。又,山之阳有一泉,云是沙井,绵历今古,沙不填之。人欲登峰,必步下入穴,即有鼓角之音,震动人足。”《敦煌录》载:“鸣沙山去州十里,其山东西八十里,南北四十里,高处五百尺,悉纯沙聚起。此山神异,锋如削成。其间有井,沙不能蔽。盛夏自鸣,人马践之,声振数十里。风俗端午日,城中士子女皆跻高峰,一齐蹙下,其沙声吼如雷。”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也记载了在沙漠中听到的神奇的声音。20世纪前后,Nature也对鸣沙有连续的报道。鸣沙现象曾一度蒙着一层面纱,人们不知道声音从何而来。
从对沙鸣现象产生兴趣到文章写出来,林官明花了2年多的时间。他结合理论与计算,建立沙坡表面沙粒运动模型,对鸣沙的发声机理进行了研究。林官明发现沙粒的协同进行是鸣沙现象形成的根本机理。

沙漠沙纹
将沙堆的沙流分层,最外表面可自由运动的一层称为自由层,而较自由层低的一层称为参考层。假设自由层中,相邻的两颗沙粒受到扰动,开始沿沙坡向下运动,如果它们步调一致,两者不会相撞;如果后者速度快,追上了前者,那么二者碰撞,后者把动量传递给前者,前者加速,后者减速,以此类推,位于沙流锋线的沙粒总能够较快地达到稳定的运动;如果后者速度小,那么对前者不会产生影响。这样,沙坡上的沙粒最终按锋线沙粒的移动速度下行,达到频率自锁。“沙粒同步下滑是一个快速适应的过程,从计算过程看,历经5次碰撞或5个沙粒粒径即可协同。”即便沙粒粒径不十分均匀,只要运动时,从一个沙粒正上方到下一个沙粒正上方所需的时间比较接近,沙粒仍会自行协同进行速度,从而整体上达到同步,形成共鸣。
进一步,若自由层沙粒基本匀速同步进行,则它们对参考层沙的作用基本均匀,因而诱发参考层沙的运动必然也是均匀的,以此类推,得到近似线性的沙流速度剖面。自由层沙与参考层沙的相对移动过程看上去更像是两层砂布的摩擦,颗粒之间相对位置不变,形成了较大的轰鸣声。
目前,林官明对沙纹的研究还在持续,他认为沙纹、云街的产生是表面波的体现,“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还需要理论和实验验证”。
为环境伦理学投入一份力量林官明称自己是一个“不安分者”,这不但体现在他在本职工作内的创新能力,还体现在其他方面的工作上。林官明曾在国家图书馆看到英文版《环境伦理学》一书,觉得很有意思,就将书的内容讲给别人,这使得他与环境伦理推广结下不解之缘。后来他将这本书慢慢翻译成中文,以便宣传环境伦理。再后来,北京大学出版社得知此书有中文译稿,就联系他出版了此书当时的最新版,之后,应北京大学邀请他开讲了这门课至今。
林官明曾和《环境伦理学》的原作者有过沟通与交流,他认为这本书的内容多为西方环境伦理思想,欠缺中国内容,所以后来在编写教材过程中他加入了东方的环境哲学理念。“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进行环境科学研究多年,我觉得很多环境问题的解决是不能单单靠科学技术完成的,它也应该从人的环境意识上去努力,环境伦理正是从道德的方面来进行研究的。”
环境问题是一个需要集各方之力,全民行动起来解决的问题。林官明说:“我并没有打算做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我只是一个‘喇叭车’,将我知道的东西传播出去,普及开去。”
近期,北京大学正在昌平地区新建一个环境风洞实验室,林官明希望自己能早日将实验室建设好,尽快投入科研运行。在这个新的环境风洞中,他们还打算进行气与水的界面的污染物交换研究。他坦言:“攻克这一新方向其实并不容易,有太多的理论与技术问题需要解决,但是我还是有信心的,希望可以在这方面做出新的成果。”
来源:《科学中国人》2019年08月(下)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