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的才下眉头又上心头(不如向帘儿底下)

挣脱开对东坡词的缱绻,我又把目光投向了北宋与南宋词史上的最后一人和第一人,以词名声振文坛的女词人一一李清照。
李清照....写到她的时候,我的笔触不禁有点涩滞。她,实在是一个不容易形容的女子。前半生的美满与后半生的颠沛流离,让她的人生形成红与黑的鲜明对比,丈夫的死、北宋的消亡构成一个巨大的断层,造就了她生命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她身不由己地跌落,生活忽然如江河直下,一泻千里,她被卷入“魔鬼洞急流”中不能自拔。

她与赵明诚的感情,实在是太过美好。想来清照文名早著,明诚对她应该是几分敬慕,几分怜爱的。从她的词里可以看出,她的生活疏懒而自由。去划船就“轻解罗裳”,去赏景就“沉醉不知归路”,想心事或愁思得倦了,就“浓睡不消残酒”,思念丈夫,就“东篱把酒黄昏后”,懒得梳妆就“起来慵自梳头”.如果没有明诚带着怜爱的纵容,清照恐怕会如朱淑真一样,词中少几分疏慵,而多几分凄厉,并同样抱恨而终吧。
明诚怜爱和敬慕她,是有根据的。据说一次清照思念在外的丈夫,写了一首词给明诚。明诚见后,爱不释手,又不服气,于是闭门三日,独思独想,写了五十多阕词,把清照那首掺在里面,让好友陆德夫评价。德夫审慎再三,拈出一首,说有三句最佳,乃为:“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明诚大乐,说清照才气真是胜我十倍。

这便是那首有名的《醉花阴》了: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好词,好句,还要有好人来怜来爱,这才是圆满的人生。如果没有明诚的大度,清照感情无从寄托,恐怕写不出来如此多情而清丽的词句。清照遇明诚,是清照之幸。
如果,圆满真的需要残缺和流离来补齐的时候,不知清照会做如何选择?是选择廿余年不离不弃的相濡以沫,然后宁愿在人世形单影只地漂泊流离,最后于默默中撒手尘寰,还是另有选择?
可惜,结局已经写好,在命运的字典里,永远没有如果。
她十八岁嫁给明诚,共同生活二十六年后,北宋灭亡,明诚病逝,这是她漂泊的开始。

赵构南渡后,建南宋,年号建炎。建炎三年,明诚去世,时年清照四十四岁。看过她三十一岁时的画像,在宋朝以丰润为美的年代,她不算是个美人,尖尖的下颏,瘦弱的身材,唯前额饱满而光滑,宽阔得几乎有些夸张,向后梳起的发髻使得这额头更加明显。
她见证了北宋的灭亡和南宋的孱弱,流离中多少炎凉和世事的粗糙,年华的老去,并没磨损她那颗诗意的心。在一个元宵节,她谢绝了一些好友的邀请,独自待在家中。或许见惯了种种繁华,知道繁华背后的虚幻;或许只想自己静静地沉思一下,回首一下往事。

只是这一回首呵,忍不住了思绪纷抛,“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百感交集之下,她饱蘸浓墨,挥毫填下了这首《永遇乐》: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熔金 一作:镕金)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撚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一作:捻)
诗情里埋藏着的沧桑,在易安笔下呈现出怎样的疏落?
她看到,那落日的光辉,像熔化的金子,辉映着天边变幻的彩霞;而空中的云朵,则如洁白的浪花围拱着玉璧一般的明月。然而人飘离至今,又身在何处?哪里都不是故乡,哪里都不再有那包容的胸膛来呵护,那么,在何处都是一样的吧。
她看到,在浓重的烟幕下,初春的稚柳颜色似乎深了一些,草木感知到春的召唤,已经浓墨重彩起来,而自己的春天将不能再回;在笛子吹出的幽怨的《梅花落》曲调声中,春意又浓了几许呢?
她感思,元宵佳节,如此美好的天气里,谁知道会不会包含着不可预料的风雨?惊怕了风雨的人呵,这一生便没有了晴天。
因而,一些诗酒朋友来召唤同去参加盛会,宝马香车满路,她一一婉言谢绝。

只是因为心情不复当初呵。回忆起从前汴京之时,那么多闲暇的时间都未曾空掷空抛。每到元宵节的时候,戴上插着翠羽的帽子,和金线捻丝所制的雪柳,打扮得整整齐齐,暗争服饰风尚,那是何等洒脱宽怀,乐景无限。
当乐景转为悲景时,便是如今模样。孤身独影,失却爱侣呵护的人,年已半老,憔悴不堪,两鬓斑白,发髻散乱,却是最怕夜间出去了。热闹的景象更衬托出孑然孤影,凄怆难掩一-还不如躲在帘子背后,暗自听听街上游人的欢声笑语啊。
这是怎样一种深刻的悲哀,是不流泪的哭泣。当踏遍红尘之时,见惯世间种种,心是会产生抗体的。理性将逐渐抬头,一直高仰至麻木的顶端;而感性,由丰沛而干枯,泪水就被尘世的沙漠吸干。
她,不是因为老去而不愿卷人笑语人声里;她只是心情不再。回想当初的盛景,衣冠楚楚,呼朋引伴,那些热切的人们,看她这个有着花般眼神的女子,曾填下那么多广为传唱的词。她出身名门,意气风发;如今,意气消磨,她仅是一个困窘的老妪,守着爱人留下的金石著作聊以度日而已。对人间再无期盼,再无希望,生命便如白水,直至熬干也不会有任何滋味的了。
因而,“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这是何等的寥落,“灯火阑珊处”尚有“那人”的等候;而她,避开热闹,独留于一份清寂之中——听人笑语。那百感交集的时刻,便如辣水呛喉般哽咽难言,更搅得情绪在波峰浪谷间出没。

那欢声笑语,此刻都成了溅向她的水点,把她淹没在欢乐的海洋里。她似被欢乐吞没的孤岛,固执地守着那份坚硬,沉人海水平面下。
帘子后面伫立着的那个苍老瘦弱的身影呵,从此粘人这词里,再也扯脱不开。摧毁她心情的究竟是什么?
不仅是岁月,还有沧桑。

怪不得南宋末年著名爱国词人刘辰翁在所填的《永遇乐》词序中说:“余自乙亥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
读了清照这首“落日熔金”之后,他忍不住落泪。三年之间,每次听到这首词,都禁受不住。于是取清照这词之韵,他也填了一首《永遇乐》,以写清照身世,用来抒发自己的感情。
“璧月初晴,黛云远淡,春事谁主?禁苑娇寒,湖堤倦暖,前度遽如许!香尘暗陌,华灯明昼,长是懒携手去。谁知道,断烟禁夜,满城似愁风雨!
宜和旧日,临安南渡,芳景犹自如故。缃帙流离,风鬟三五,能赋词最苦。江南无路,鄜州今夜,此苦又谁知否?空相对,残缸无寐,满村社鼓。”

说实话这首词我不喜欢。太过直白,缺少含蓄之美。苦则苦矣,留给人回味的东西不多,而且过于纷乱,一时写清照,一时又写自身,总感觉缠夹不清。字句方面也没什么突出之处,但因承载了清照的遗风,还是把它录了进来,权且作为《永遇乐》的补充吧。
写至此,终于完结了《永遇乐》这个词牌。《永遇乐》,以一则传说而起,渴望永遇的欢乐,可惜希望终如眼前飘飞的肥皂泡般轻易破灭,留下一缕诗魂缠绕于词牌之中,将这词牌没渍得辛辣悲壮,总有股抑郁不平之气似要挣脱世情羁绊脱飞而出,因此,稼轩的感,有东坡的梦,有易安的悲。
千载之后,谁与评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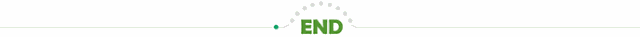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关注遥山书雁,和您一起品读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