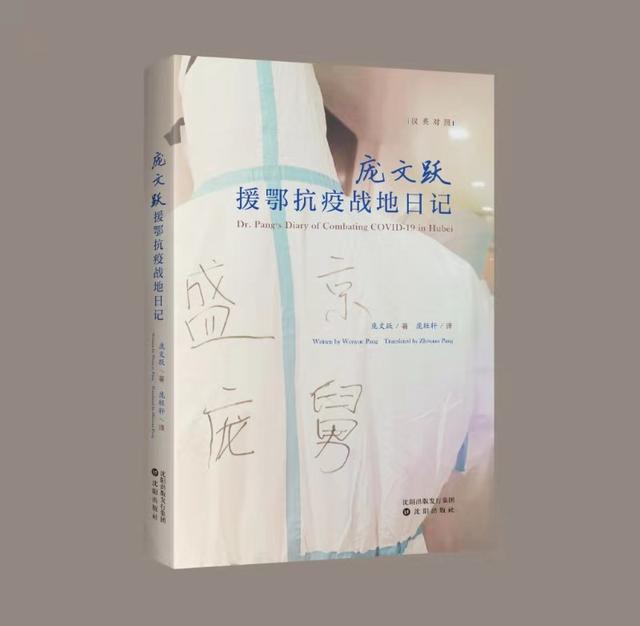良师和益友称之为忘年之交(不期而遇的辅仁同学)
作者 | 王培良
郑板桥写的“难得糊涂”四个字被制成拓片或各种礼品曾经风靡一时,人们却对“难得糊涂”的理解莫衷一是,由此可见每个人的心理需求、思维定势和价值取向都有所不同。
自己也认识这几个字,而且“糊里糊涂”地过了许多时日,眼看就古稀之年了,或许也是“难得”的境遇。
我在常德道67号旧宅从1949年一直居住至1995年,由孩提到知天命可谓前半生甚至大半生了,这46年里按我一位朋友的说法:“在那里我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及最混乱的时期……”

常德道67号(原静安别墅8号)
说得太详细就成了自传,不妨把我的喜怒哀乐、或把我的所见所闻挑一些片段写出来,写出来做什么?不过是自娱自乐而已。
受到耀华65微信群里同学们的启迪,看了黄邦洁妙笔生花的美文、吴保裕真实感人的回忆、郑宝发有感而发的杂记……不由得手痒,写了“五大道的西餐馆”后,不仅得到了麦汉威、黄邦洁、吴保裕等诸同学的鼓励,而且勾起了盛安利、董佑儒等同好的馋虫,哈哈,真是有趣的交流。
我不称邻里为“街坊”,那显得过于亲昵,怕惹恼了达官贵人们的后裔亲朋,有不屑与我等草民为伍的,耻笑我趋炎附势;我讲左邻右舍,则与他人无碍,毕竟豪宅毗邻的夹缝间还住了不少寻常百姓。
说实在的,好多人搞不清五大道的住户都是什么底细,有前朝的遗老遗少、退隐的王公大臣、过气的军阀大鳄、家财巨万的买办富商、医生律师高级白领,解放后,又增加了些进城干部……
住户间的往来有点像单元房的邻里关系,倒不是不相识,只是各忙各的,没事从不凑在一起聊闲篇,遇到了就客气地点点头,最多是寒暄两句,只有亲戚朋友才互相串门。
文革前,居民们和谐相处,看不出有什么贫富尊卑,哪怕是政府的官员也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隔壁的几户人家往来多些,原因太多了,远亲不如近邻么。

现在的常德道63号(原73号)老住户都搬走了,新搬来了一家敬德书院。
张家镇伯伯一家住在常德道63号二楼,他是二十一中的老师、张伯母是十九中的美术老师,同是老师的父亲和他们夫妇自然能聊到一起。
他家四个孩子,三个儿子张丰声、观声、民声和我们家三兄弟比肩,妹妹张琴声,他们兄妹也都在四友小学(常德道小学)上学。
老大张丰声比我小一岁,以前四友小学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又都住在附近,所以好多学弟学妹也都认识,比如冯骧才(冯骥才的弟弟)、吴季麟(五原知青,音乐学院毕业后在天津儿童艺术剧院做业务主任)、张家宣、冯学珉等。
张丰声个子不高却爱打篮球,绰号大眼儿,他有好多球友,张豹(标枪打破过亚洲纪录)、关弘等。我在耀华中学时的俄语老师是毛若昭老师,她的儿子赵明也是其中一位。
赵明在部队和地方都打过篮、排球专业队,后来在天津大学教体育,成了教授,他比我小三岁我俩却很投缘,至今还有联系。
说起赵明的姐姐赵雪琪大家可能都知道,她是我耀华同学赵雪慧的姐姐,天津女排的前任教练(在王宝泉教练之前),为咱天津女排日后在联赛多次夺冠打下了相当坚实的基础,功不可没!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正值文革,张家镇伯伯大儿子张丰声和女儿张琴声上山下乡去了山西,家里只剩下他们老两口和张观声、张民声两个儿子。学校里学生们不上课了,倒落得清闲,他喜欢摄影,有时拍些风景照片自娱自乐。
那时候我父母带着三弟“疏散”去南郊了,二弟上山下乡去了内蒙,家里只剩下我自己,下班后常去张家串门。
张伯伯喜欢抽烟,尤其喜欢抽从上海买来色泽金黄的烟丝,满屋子浓郁的香味。我在工厂里是个逍遥派,工作之余帮张伯伯做了几个造型别致的烟斗,他真的好喜欢。

我为张家镇伯伯治的闲文印,他盖在自己的摄影作品上很高兴。
张家镇伯伯的父亲张子谦(1899-1991)是我国著名的广陵派古琴大师(详见附录),浦东三杰之一,他善弹《梅花三弄》、《平沙落雁》等曲;尤以《龙翔操》为突出,故得此称号。
张爷爷是上海民族乐团古琴演奏家, 1988年被天津音乐学院聘为名誉教授,为古琴音乐的理论研究、打谱和教学作出贡献。自此和儿孙们住在一起,尽享天伦之乐。
1991年张爷爷病逝,当时上海、天津民族音乐界来吊唁的花圈摆满了常德道63号门口。

古琴大师张子谦老先生
常德道63号一楼的孙桂年伯伯和我父亲也很熟,他在天津储运公司工作,和我三堂兄王培福同事,孙伯母在天大精仪系工作。
他家一儿一女,儿子孙维坚是耀华老初一的学弟,女儿孙悦若自小习国画,一手好工笔,后到加拿大定居。
我父亲在辅仁大学同届学友李世瑜伯伯(我父亲是西语系,李伯伯是社会学系)常来家里串门聊天,他和孙伯伯也相识,每次来我家注定去孙家挂角一将。
李伯伯嗓门大、谈吐风趣,满口纯正的天津地方话,在院子里就能听见他洪亮的男中音和爽朗的笑声。

李世瑜(1922—2010)
说起李世瑜伯伯,还真得啰嗦几句。
他是咱天津有名的文化人,上百度搜搜有不少介绍他的文章。他当年提出的“天津方言岛理论”和“天津话母方言来自淮北平原”的两个论断,都是正确的,得到了广泛认同。
但他也有过曲折的经历,早年间他老先生居然隐匿目的,冒充信徒打入了秘密宗教的内部,得到了第一手资料,探得真相,从而写出《现代华北秘密宗教》的著述,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没料到由此惹上了不少麻烦,有人却误认为他信奉秘密宗教,成了问题。
文革中“疏散人口”,我父亲带着我三弟去了南郊赵连庄公社刘塘庄大队落户,背着筐拾粪时,大喇叭里播放着交响乐沙家浜,老爹是乐观派,很会苦中作乐,告诉我那不就和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一样么,山清水秀就是诗情画意……
没想到他和李世瑜伯伯不期而遇,他也被“疏散”到那里去了。李伯伯更潇洒,农闲时在村里牵着一条大狗溜来溜去,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俩老头窘境里遇故交,真有点喜出望外。
常德道65号(原75号)与我家一墙之隔,文革前的老住户我最熟的是何家姐弟。
大姐何振英比我大一岁,1964年高中毕业去了新疆;二姐何振琪比我小,一直在天津总医院工作,想必朱理玮、翟鵘琨、许瀛海等总医院的大夫同学都认识;三弟何振黎是走南闯北的摄影师,自称“一只眼睛看世界”,他拍摄的纪录片多次获奖;幼弟何振钰憨厚敦实,海军复员后就职于汽车配件公司保卫科。
他们的祖父是北洋水师的将领之一,何伯父因为做外贸工作,经常出差,所以见面较少。
至于常德道65号其他住户频繁更换,所以知之甚少。只依稀记得“情系五大道”微信群里的王新民小妹妹一家、一位羽毛球教练和另外姓李的一家。

文革初期,门口的小伙伴们有时爱到房顶上去玩。上图前排左起:张民声、王培刚、孙维坚。后排左起:王培德、马洪勳、何振黎、何振钰。
其实邻里、亲朋、故旧、相知,没法择清,所以扯得远了些。几十年的老邻居,故事虽然平淡,却积存了一肚子,太多的话反而不知从何说起。
就说说这几家如何过周末节假日吧。
张家镇伯伯酷爱打桥牌,逢节假日在家中邀上几位牌友打上大半天,有时甚至在家随意便餐后接着大战。受他的影响,我上小学时就开始和同学们学习打桥牌,虽没上瘾,却也喜欢,一直打到七十年代中期,我迷上了围棋,桥牌就很少摸了。
后来几个棋友打桥牌也打出了成绩,耀华二班的刘学文等经常参加全国和市里的比赛,拿了不少冠军呢。张伯伯的旧牌友中有几位我认识,有南开大学的李宗伯,还有汤耿良和他的夫人佟若珊等。
李宗伯家旧宅在我家西侧仅一墙之隔,是一座深宅大院的三层别墅,邻近的孩子们一直把他家的门洞称为李家大门。解放初期李家搬走了,这座宅邸卖给某机关做了办公用房。
李宗伯比我大十几岁,他弟弟李宗鄂与我年龄相仿,所以我常充小大人称他为大哥。李宗伯为人憨厚,牌品极佳,如偶遇则点点头,露出招牌式的笑脸,绝没有臭架子,总是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
汤耿良伯伯的祖父是民国时期热河省长、军阀汤玉麟,他们夫妇在桥牌界小有名气,曾著有《桥牌打法》、《桥牌入门》等普及读物,他们住在常德道昆明路口附近的平和里,和歌唱演员刘欢家住同一个里弄。

现在的常德道平和里。
文革前我耀华的初中同学刘毅也曾住在这里,那时胡同口东边的那幢是体育馆卫生院。他们院一楼的孙伯母喜爱京剧,常邀票房里的友人们到他家,票友们司鼓操琴清唱聚会。
孙伯母本人唱谭派老生,声音高亢入云,一字一板,中规中矩,听起来真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意味。
受家里影响我也喜欢京剧,所以一俟孙宅唱戏,就跑过去伫立门边,即便我连西皮二黄都分不清楚,也听得如醉如痴。
说到京剧,家里几代人都喜欢,不仅爱听爱看,甚至都会唱两口。
我堂兄王培基是家里的长子孙,他长我十三岁,记得他结婚那天喜筵之后,叔叔大爷姑姑们不方便去闹洞房,高兴之余,自己架弦,唱起京剧来了,个个都能闹两口。
那天我才知道,我父亲的兄弟姐妹个个多才多艺,只不过家教太严,没人敢去吃文艺这碗饭罢了。
耀华同班徐开生的母亲和我父亲是辅仁大学的同学,前俩月徐开生和我微信视频,还提到我父亲当年在大学时扮黑人跳踢踏舞受到热捧的旧闻。
我父亲兴趣广泛,业余爱好很多,滑冰、游泳、唱歌、跳舞、打网球……所以周末节假日我家的活动多姿多彩,大多是全家去干部俱乐部。
吃过饭大人去二楼舞厅跳舞,孩子们就去室内游泳池游泳、地下室打保龄球、小剧场看文艺演出……一旦有露天电影时,天没黑下来我们小孩子就早早占了好位置等着开演了。

天津干部俱乐部舞厅
耀华同学王爱玲现住在美国硅谷,她母亲林惠枝(民国海军总长刘冠雄的外孙女)和我母亲是圣功女子中学的同学,我们的父母是几十年的好朋友,当年常定好了一起去干部俱乐部休闲,两家孩子小时候在俱乐部玩时一起照的照片文革时全毁了,日前我和王爱玲通电话时还提及往事,已恍若隔世了。
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聊了半天,没啥正格的,还是那句话,自娱自乐!或许能博耀华65微信群兄弟姐妹们一笑。
2015.5.14.
2018.8.修改
未完待续
作者王培良在五大道生活了近五十年,对五大道怀有深厚的感情,退休后利用业余时间致力于五大道纪实回忆录的撰写工作。
采稿 校对 编辑 | 紫石
关于我们
本号汇集了五大道人讲述的老故事及五大道人的文学、摄影作品等,旨在重温五大道老时光、探寻五大道人的生命轨迹、弘扬五大道的人文精神。欢迎新老五大道人踊跃投稿,文字、口述均可(有意者请在私信留言,我们会尽快回复)。本号刊登的文章(不代表本号立场)均为原创,不经许可请勿转载,违者将追究法律责任。
,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