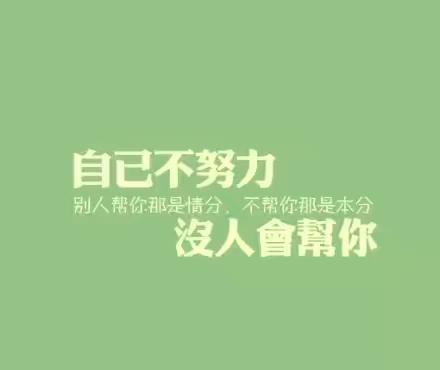伊朗圣裔(为什么在洛杉矶有很多伊朗裔)
除了伊朗,世界上伊朗人最多的地方是哪里?
时至今日,美国是伊朗本国以外居住着最多伊朗人的国家。
01.
伊朗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
根据2005年至2007年美国社区调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的数据,37%的伊朗裔美国人居住在加州,其中最大的聚居地在洛杉矶(Los Angelos)。洛杉矶的伊朗移民社区因此被称为「德黑-杉矶」(Tehrangeles)或「小波斯」(Little Persia)。
而据美国人口统计局2017年数据,伊朗裔美国人有47万;非营利组织伊朗裔美国人公共事务联盟(PAAIA)则估计,当前其人口在50万至100万之间。这些数据还没有算上由于身份认同差异和各种原因造成的主动隐瞒,各类统计数据差异比较显著。
居住在美国的伊朗裔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认同呢?
伊朗裔美国人的自我定位有不同程度的分化,身份认同多种多样:包括伊朗裔美国人 (Iranian American),波斯人(Persian),波斯裔美国人(Persian American),伊朗人(Iranian),或者美国人(American)。此外,还有一些伊朗裔美国人表示,他们更倾向于以宗教身份来做自我定位。
▲1979年,被伊朗激进分子扣押的部分美国人。拍摄:Bettmann/Corbis
「伊朗革命」后到2001年的「9·11」事件,伊朗人移民美国进入第二阶段,伊朗人开始大批离开故土,被称为「伊朗人大流散」(Iranian diaspora)。
随着新政权与美国交恶,第二阶段前往美国的伊朗人群与第一阶段有显著不同:前往美国的伊朗人有较多难民、政治避难者(包括前政府官员)和少数族群(例如各类非伊斯兰教教徒)等。
随着「伊朗革命」和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1980—1988)所造成的政局动荡,大批中高收入阶层也陆续移民国外。
与此同时,虽然伊朗并未参与「9·11」恐怖袭击,但是美国总统小布什(George W. Bush)在2002年国情咨文中将伊朗和伊拉克等国形容为支持恐怖主义的「邪恶轴心国」(axis of evil),继而签署了相关法案,限制相关国移民。进入美国的伊朗移民和难民数量在随后几年显著减少,直到2005年前后才恢复。
03.
在「他乡」的困境与挣扎
「伊朗人质危机」破坏了伊朗人在美国人眼中的印象。这给伊朗裔美国人在当地的生活带来了诸多困扰。
根据《休斯顿邮报》当时的报道,人质危机期间,成百上千的美国人在示威游行中焚烧伊朗国旗,他们高举各种各样的标语牌:「回家去,傻瓜伊朗人」「感恩节快乐——抓个伊朗人质」「要么释放美国人,要么杀掉伊朗人」「十个伊朗人等于一条寄生虫」以及「1万伊朗人换60个美国人」等等。
除了游行示威,反伊情绪也遍及餐馆、商店等公共场所,乃至波及大学校园。很多中东人为了避免被误认为是伊朗人,甚至在衣服上印了国族名称。
在休斯顿大学城区分校副教授穆赫辛·穆巴舍尔(Mohsen Mobasher)看来,「美国人把对人质危机所有的愤慨、怒火和失望转化为对伊朗以及在美伊朗移民发动的一场经济和政治的『小型战争』」。

▲「伊朗人质危机」后,在华盛顿特区抗议伊朗的示威游行人群中,一个人举着牌子写道:「驱逐所有伊朗人:滚出我的国家」。拍摄:Trikosko, Marion S.
针对伊朗人的歧视事件在校园里频频发生,这对新一代伊朗裔美国人的成长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一名伊朗裔美国少年说:
「虽然周围人从未公然仇视我,但他们会取笑我是一个伊朗人。他们开这些玩笑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不觉得这是冒犯。我有个朋友,他知道伊朗人和『9·11』无关,但他还是叫我『恐怖分子』,因为觉得好玩儿。我只能尽量理解他。」
伊朗裔记者塔拉·巴冉普尔(Tara Bahrampour)则生动地记述了在「伊朗人质危机」余波下的童年:
「我好奇班里同学知不知道我来自伊朗。班里没有别的伊朗人……我恨电视里的人戴着黄丝带喊着要伊朗人骑骆驼回沙漠去……我恨那个把海滩男孩乐队『芭芭拉·安』的歌词改成『炸伊朗』的乐队……你不能跟人说你是伊朗人,他们会打你的。」
「伊朗人质危机」期间,《时代》和《新闻周刊》两份主流美国杂志上先后出现题为「殉道的信仰」「伊朗的殉道者情结」的文章,将伊朗人形容为「非理性」「渴望殉道」和「不愿妥协」。
为了避免「伊朗」(Iran)一词在美国社会中的负面印象,一些伊朗裔美国人为了将自己与当前伊朗的伊斯兰政府区分开来,开始自称「波斯人」(Persian)。他们常年在美国尤其加州南部的电视台,面向伊朗侨民宣传着非伊斯兰化的波斯民族认同。这些在美国的伊朗人电视台节目,大都由反霍梅尼的君主立宪支持者所主导。
04.
刻板印象下的冲突
1987年,在美国普渡大学的一项调研显示,该校本科学生对男性伊朗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有:敌对、有侵略性、永不妥协、脏、傲慢和自大;对女性伊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则是:家庭中心、顺从、保守和骄傲。
无独有偶,到2013年,针对南加州大学本科生的另一项调研显示,该校本科学生对中东男人的刻板印象是反西方、可疑、好讨价还价;对中东女性的刻板印象则是安静、内敛、压抑、家庭中心、多子女、性保守和做家庭主妇。
另外,由于伊朗移民在美国的收入水平在总体上处于较高水平,在媒体、影视和书籍等的渲染下,部分美国民众对伊朗移民一度有负面印象:戴着金项链、开着豪车,在象征着财富和名利的加州洛杉矶罗迪欧大道(Rodeo Drive)上购物。
这些刻板印象显然是夸张和片面的。在哥伦比亚大学文学教授爱德华德·塞德(Edward Said)看来,美国人对革命后的伊朗缺乏了解,将伊斯兰与战争、谋杀和冲突相关联,并且将穆斯林描述成反美的和尚未开化的(uncivilized)。
这种趋势至今依然存在。据PAAIA在2018年的数据,将近一半的伊裔美国人表示,他们因为民族身份或来源国家遭遇过歧视。2017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禁穆令」,伊朗首当其冲。不必说,大部分伊朗裔美国人都对「禁穆令」表示反对。
在融入主流社会的同时,伊朗人在美国继续建立和塑造着他们的社群,试图保持自身文化。例如,在洛杉矶和贝弗利山(Beverly Hills)等地,他们聚集而居,很大程度上保留着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
面对美国的主流社会,他们保持某种距离;面对当前的伊朗,他们又难以回归。多种原因造成了他们处在文化认同的夹缝之中(in-between)。
当前在美国生活的很多伊朗人并没有回国定居的打算。对此,一名生于伊朗、长于美国的34岁伊朗裔美国人在2008年的一项匿名调查中这样写道:
「如果有机会,我想回伊朗看看。重返故土对我意义重大,那里生活着我的先辈,也是我人生开始的地方。那里是我所知甚多又所知甚少的地方。但是,我不会移民回去,因为现在我找到了可以自由说话、思考、做事……的地方,我找到了我可以充分利用自己聪明才智自力更生的土地。要离开这样一个地方太难了。」
05.
「且认他乡作故乡」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曾在《我们是谁?》一书中总结全球化时代人们身份与特性的双重特点。

▲《我们是谁?》作者:塞缪尔·亨廷顿 译者:程克雄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出
一方面,人们的身份认同趋于具体和窄化:
「现代化、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全球化使得人们重新思考自己的特性/身份,从较狭隘、较亲近、较社群的角度重新界定身份和特性。国民层次以下的文化身份和地区身份比广泛的国民身份更受关注。人们认同于那些最像他们自己的人,那些被认为有着共同的民族属性、宗教信仰和传统以及传说的共同祖先和共同历史的人。」
另一方面,人们的身份认同则超越国家界限,趋于泛化:
「在出现这种身份/特性狭窄化的同时,又出现身份/特性广泛化的现象,这是因为文化和文明背景很不相同的人们如今日益增多其相互交往,而现代通信联络手段又让那些虽然相距遥远但却有类似语言、宗教或文化背景的人得以彼此认同……超国家身份/特性的出现……同时又加剧着身份/特性的狭窄化。」
最终的结果,则是「各种社群既互相杂居而又各自抱团,既彼此交往又彼此分隔。」
对伊朗裔美国人来说,他们已经丢失了「故乡」,并试图在「他乡」寻找和建立「故乡」。
问题在于,美国真的能成为伊朗裔美国人的「故乡」吗?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