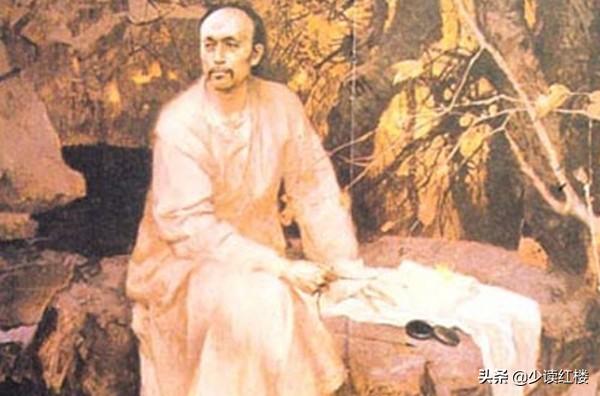喜欢自然风景的原因(今人同风景离得这样近)
马力/文 雁子/编辑
编者的话:
2016年国庆,德阳举办“三星堆戏剧季中国散文名家进德阳”大型采风活动。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旅游报》原副刊部主任、主任编辑马力受邀为德阳的文学爱好者做了一场名为“山水旅行与文学想象”的大型讲座,讲座盛况空前。雁子作为此次笔会的组织者,特将此次讲座录音整理并分享给广大的文学爱好者。
各位老师还有作者及文学爱好者,大家下午好!
今天是国庆节,按照我们这个近年来的过节这个状态来看,我们一百多号人是来讨论文学。此时此刻,有许多甚至数以亿记的游客,正在祖国的山山水水行走,有的甚至出境游,在国外去旅游——我们闭目都可想像这么一种出游的景像。中国的读书人走名水大山,回来必定写一篇远足记,才觉得功德圆满,远足记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游记。随着中国出境旅游人数的递增,那么游记写作也是蔚然大观,在中国旅游报做编辑写了许多的名山名水,记游作品的产生,有许多的电子稿。邮箱满了,也反应我们国家这种旅游形式的兴旺的一种局面。

游记是散文的一种。中国是散文大国,也算游记大国。
游记是最常用的叫法,也可以叫旅行散文、山水散文。总之是把旅行生活和山水风光拿来当成抒写对象。
游记是一种很古老的文体,通常把东汉马第伯的《封禅仪记》当做最早的游记作品。封是祭天,禅是祭地。作者马第伯是汉光武帝的侍从,曾经跟着皇帝封禅泰山,留下这篇记。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三十多万字,写了一千多条河,写了河两边的城镇、物产、风俗、传说、历史,是记载中国水系的重要著作。郦道元的文笔好,这书又被看成文学作品。
明代的徐霞客写的《徐霞客游记》,是一部个人的行走记录,日记体,文学性强,水文、地质、植物、民俗都写到了,所以说,它的地理色彩也不淡。
中国古代游记的一个明显的文体特征,就是文学和地理学相合得很紧,按照我们现在对狭义散文的理解,不算纯粹的文学。

中国古代游记的创作高峰,在唐宋时代。这两个时期也是中国散文的发达时期。唐宋八大家中的领军人物柳宗元,他的《小石潭记》是名篇,结尾几句: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看似写景,实乃寄情。柳宗元在安史之乱后,协助翰林学士王叔文进行改革。这场“永贞革新”只进行一百多天,就失败了。柳宗元当然受到牵连,下放到永州当司马。永州,在今天的湖南南边,我去过。九嶷山、潇水全在那里,风光很美。蛇也多,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开头一句“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大家都记得。千年之前,一定很荒僻。一看这几句,就能领受那种被贬永州之野的落寞心绪。柳宗元一辈子写了那么多诗文,这篇《小石潭记》最为人们记诵。
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也是名篇。是在参与范仲淹推行一年多的“庆历新政”失败后,被贬到滁州当太守时写的。文调比起柳宗元,好像明朗一些: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柳宗元、欧阳修被贬,还是官,但他们更是文人。做了官员的文人写文章,和不是文人的官员写文章,品格、神韵是不同的。
唐宋时期,游记基本有了成熟的文体形式,跟近现代游记样式很接近。对于现代文学时期的游记创作,它的价值在哪里呢?应该说是很直接的。
我们读古代散文,或者读古诗,一个好的方法就是一遍一遍地朗读,以至背诵。这个方法的好处是,读多了,自会琢磨、体会出长长短短的文句里的滋味。《三国志》里有一句话:“读书百遍而义自见。”意思是,读书上百遍,书中之义自能领会。
有一次听许嘉璐先生的课,他专门说过,要学会涵咏。古人吟诗,哼哼唧唧,自我陶醉,入了境。现代人好像不大费这个劲儿了。但是,古文读多了,你自会感到一种文言的韵味,简练、传神,能够体味出注释之外的韵味。上面说到的柳宗元、欧阳修的散文,那种内心的忧伤,那种超脱的怡然,来回读几遍,多多少少能体会到。

五四作家多半有过古文训练,他们在创作中,就会带上这种痕迹。文言和白话杂糅,半文半白,读起来别有一种味道,和我们今天的语感不大一样。有人适应,有人不习惯。这是汉语书写的时代特征。
鲁迅写的游记很少,有一篇《辛亥游录》,日记体,文言味很重,那时他的岁数却很年轻。三味书屋教出来的,就是这个味儿。这篇游记发在1912年2月他的家乡绍兴办的《越社丛刊》第一辑。
1911年,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教书,课余,去郊野采集植物标本,他把这个过程记了下来。你读那个句子:“掇其近者,皆一叶一华,叶碧而华紫,世称一叶兰。”今人较少这样写文章。再往后,特别是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白话的势力加大,读起来更接近今天的文味。

我一直以为,现代游记写作中,出了两位大家,一个是沈从文,一个是郁达夫。两个人又都是写过小说的。景象的描写、细节的刻绘是他们的长处,又都保留着文言文简洁、传神的优长,读着特有味道。
沈从文的《湘西》和《湘行散记》是名篇,他不是侧重写地理,而是专情写荒蛮之地原始、朴素、真实的风俗、世态、人情,笔墨很细,有些和中篇小说《边城》的调子接近。凌宇是研究沈从文的专家,他有一本著作,叫《从边城走向世界——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研究》,他在书里说:
《湘行散记》、《湘西》在文体上不拘一格,具有抒情散文、游记、小说、通讯等各种文体因素,但又突破了其中任何一种文体的固有格局。它是散文中的‘四不像’。
然而,正是这‘四不像’,表现出沈从文在散文文体上的大胆创造……游记、散文、小说是三个具有不同特征的文学种类。揉合三者而为一,即吸取这三种文学体裁的长处,融铸成一种新的散文样式。游记以写景、状物为主,散文适于即景即事而抒情,小说重在人物和情节的完整。

在《湘行散记》《湘西》中,作者对地理物产、山光水色、历史遗迹的介绍,采用游记的写法,尤其是景物的描写十分出色。景物描写贯串《湘行散记》始终,《湘西》更通篇皆是,虽多达数十处,却富于变化,毫不雷同。他能以敏锐的艺术感觉,捕捉各地景物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传递出各自特有的神韵。
神韵,是通过语言传达出来的,我们可以把《湘西》和《湘行散记》找来读读,品品它们的滋味。那种带点生涩的、有时会产生阅读阻力的语句、句群、段落,读惯了,再看一般文章,你会觉得没味道。听听这一段:
水面人语声,以及橹桨激水声,与橹桨本身被扳动时咿咿呀呀声。河岸吊脚楼上妇人在晓气迷蒙中锐声的喊人,正如同音乐中的笙管一样,超越众声而上。河面杂声的综合,交织了庄严与流动,一切真是一个圣境。

有声音,有画面,糅合得又是那么谐调。这是用文字画出来的梦世界,这是那种课堂文化程度不高,却对生活语言具有天赋的作家写出的具有艺术灵性的语言,而且是不可模仿的。
郁达夫的游记名篇,经常说到的是《雁荡山的秋月》《超山的梅花》《浙东景物纪略》《钓台的春昼》等篇,也是现代散文史上的经典之作。他在《钓台的春昼》里这样写:
我当十几年前,在放浪的游程里,曾向瓜州京口一带,消磨过不少的时日,那时觉得果然名不虚传的,确是甘露寺外的江山,而现在到了桐庐,昏夜上这桐君山来一看,又觉得这江山的秀而且静,风景的整而不散,却非那天下第一江山的北固山所可与比拟的了。
旧式才子的风雅情调,在郁达夫的记游文章里特别地表现得圆满。
这样的文字,在今天的创作中,不大容易欣赏到了。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我们也不好硬做比较。只是觉得,作为欣赏者,每人有每人的尺度,说好说差,内心自有高下。

中国现代游记散文,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形成了一个创作高峰。它直接继承了古代和近代的游记文学经验,加以创造,出现了高质量的作品,出现了游记作家群。这里面,有散文家,小说家、诗人、报告文学作家,他们创作了艺术风貌各异的作品。从大量的创作中,可以看到时代的、社会的、历史的面貌。这些文学财富,又开启了当代游记散文的创作。我在一本书里说过:
作为中国文学现象的现代风景散文创作,已经成为文学史的永久性部分。充满人文情怀的作家群体,以前卫性的创造姿态进行构式探索和内涵开掘,完成了中国当代风景散文的历史性奠基。
旅游是空间的移动。现代游记创作能够发达,还要感谢交通工具的发达,它给出行提供了古人享受不到的便利。郭沫若、郁达夫、郑振铎、冰心的作品,经常有火车的影子。现代交通工具使个人的活动范围扩大,视野更广远,心境也更辽阔,直接影响着创作活动。

1922年10月26日,冰心在《晨报副镌》发表散文《到青龙桥去》。临着车窗看风景,眼前是一幅流动的画:眼前“只是无际的苍黄色的平野,和连接不断的天末的远山。——愈往北走,山愈深了。壁立的岩石,屏风般从车前飞过”。年轻的心,随着风景动。
1934年7月7日晨,在燕京大学当教授的郑振铎,受平绥铁路局局长沈昌之邀,跟冰心、吴文藻、雷洁琼等八人从北京清华园车站出发,开始沿平绥线的社会调查性质的旅行。经过居庸关、宣化、张家口、大同、呼和浩特、包头等地。沿线风景、古迹、风俗、宗教、经济、物产等都看到了。
他用书信形式把塞外见闻讲给夫人,一共十来篇。10月,发表在文学月刊《水星》上。后来编为《西行书简》,作为“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第二种”出版。
郑振铎的《云冈》是《西行书简》里的一篇重要作品,写得很细。

游记作家描摹的风景,按照大致的划分有两类:一是自然景观,二是人文景观。
自然景观最能激荡胸襟。峰、岭、峦、嶂、岩、峡,具有雄、奇、险、秀、幽、奥、旷、野的美感;江、河、湖、泊、海、泉、瀑,具有狂、柔、平、软、清、浊、急、缓的美感;还有绚丽艳美的花地、辽远壮阔的草原、苍翠蓊郁的林木等,愉悦着我们的感官和心神。
对这些自然景观做文学化的表现,比较难。有一年,我和汪曾祺先生去桂林开笔会,汪先生回到北京后,在《北京文学》封二上发表一篇随笔,叫《从桂林山水说到电视连续剧〈红楼梦〉》,说自己想用文字捉住对于漓江之游的一点印象,枯坐多时,毫无办法。“待寄所思无一字,桂林宜画不宜诗。”由此感叹:“状难状之景如在目前”其实是不易办到的。这里借的是宋人梅尧臣的话。

如实呈现风景之美,文学是赶不上摄影和美术的。也就是说,文字和景物之间不一定存在完全对应的关系。
奥古斯特·罗丹把照相和翻模所表现的精确称为“低级的精确”,这种精确“既然不是出于自己的心灵,也就不会真实”,而文学的使命正是要创造心灵的真实。
当然,同样作为艺术创作样式的摄影与美术,和文学有共同点,不好用排斥的眼光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我要表达的意思是,成功的游记,应该近风景之真、心灵之真,尽量使文字和景物的关系实现一种平衡。
过去,郁达夫给写景文章提了一个标准:“细、真、清”。这话放在今天也是适用的。只因现今的游记创作中常有“粗、假、浊”的东西入我们的眼睛。
粗,便不能细;假,便不能真;浊,便不能清,作品的失败也常在这地方。虽然是一样的写景文字,高下可要差得多。

人文景观最能引发追怀。人类在社会演进中创造的习尚、风俗、心理、情感、智慧,体现了社会主体——人的核心价值,它们蕴涵着各自的审美特征,在艺术心境中产生不同的美学感悟。
饱含人的创造性劳动的景观,组构成一个有机的意义系统,作用于欣赏主体的审美感觉、审美知觉、审美想象。
进入文学视野,创作者更凝眸其所承载的历史的欢欣与苦痛。他们流连于宫殿、寺观、石窟、摩崖、陵墓、古城、民居、书院、园林前,会回溯昔年的盛况,会浮想过往的人物,会听见遥远的声响,会感受工匠的余温。
建筑其实是不好写的,得有营造学、社会学、宗教学、美学等方面的知识储备,要不然,下不了笔。拿古典园林来说,厅、堂、楼、阁、馆、斋、榭、轩、舫、亭、廊、桥、墙,都要略懂一二。楹联、匾额也得能看明白,这涉及造园艺术、建筑文化方面的学问。十几年前,上海老人郑逸梅来信,要在《中国旅游报》副刊上开设《名人与园林》栏目,我编发了四十篇稿子。手稿我留着,一直想把它编成书,可是出版社不会接这个活儿,因为不赚钱。

两类景观,我们在游览中常能碰上。感受、领悟之后,便可化成文学材料,融入创作过程。我过去在一篇文章里说:
游记的面其实可以很宽泛,除去写风景,还能记人事,叙掌故,绘草木,花鸟虫鱼、岁时风物、瓜果饮食、祭典礼仪、歌舞乐调,凡文化者,皆可入篇。人家读起来,才感到不单薄,有文化厚度。
有一天在汪曾祺先生家里,聊起游记创作,汪先生说写游记要“跳出风景去写”,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一篇作品,只是记录一些你在旅途中见过的东西,陷在里面,读者不会获得阅读的满足。你得写出景物深处的东西,往大了讲是文化。
所以,不要把风景看得太浅。心里要有历史背景、哲学背景,在大背景的挤压下产生游记。从表面看,你写的是景物,其实你写的是文化积累。你得给读者不知道的东西,新鲜的东西,要有你自己的发现。这种发现,一是从景物中来,一是从长期的修养中来。

眼前之景人人能见,心中之景就未必了。要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如果你的修养深,连节气、物候都会引发文思。
我近日读到一则小品文,说日本的湿气,磨练出一种“湿气智慧”,以至影响了国民性格。日本文化崇尚“寂”,就是从湿气中产生的美的意识。风雨、雾霭、云霞、雪光笼罩下,岛国的树木上、石头上长满了潮湿的苔藓,抬眼一扫,不是庭院内的水池,就是纸窗前的灯笼,这种生活环境中,心能不安静吗?不懂这个,就写不出来那种境。
为什么有的人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爱找来地方志看,就是要了解当地风情。假设一下,一起结伴去黄山,回来每人写篇游览记,肯定不一样。老人和青年的感受不一样,学生和职员的体验不一样,有文化方面的,也有心理方面的、气质方面的。

我以为,游记是一个文体框架,负载的东西多了去啦!散文写到最后,就是拼修养——文化积累、思想见识、人生阅历和艺术表现。
当然,动笔时,还得记住“剪裁”和“节制”,千万不能一味铺张扬厉,以显博学。苏东坡有话:“取之至宽而用之至狭。”老作家孙犁也讲过相近的意思:“写游记当然要运用一些材料、文献。但不能多,更不能臃肿。要经过选择,确有感触者,约略用之,并加发挥为好。”要避免庞杂琐碎,那会叫人读不下去的。
每种文体都有相适合的格局,不能想抻长一些就往长了抻,想缩短一些就朝短了缩。汪曾祺先生谈小说写作时,打过一个比方:
“就像一个苹果,既不能把它压小一点,也不能把它泡得更大一点。压小了,泡大了,都不成其为一个苹果。”
作品要修短相宜,这个道理,放在游记散文上,也是合适的。我主张游记一般不必写得太长,太长的篇幅,容易叫人望而生畏。回头看看,中国历代好的游记,篇幅大多不长。应该像写诗那样来写。

游记散文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位置。现状如何呢?说起来未免失望。这一类作品,像是不能登大雅之堂,成了被列在正宗文学之外的一种样式。多年前,汪曾祺先生对我讲,某刊向他约稿,先作声明:不要写景之文。这是很奇怪的,有点文体歧视。
转念,也不好全怨编辑大人门户之见太深,在写的一方,是不是也该问问自己呢?从前我说过,中国山水画的气韵天下无匹。同此山水,入文,应当也是不差的。怎么回事呢?
今人拿笔写游记,像是太过随意,不管有无条件,有没有准备,上来就写,既缺少创作所要求的素养,表达上所应有的文学美又特缺乏,草草下笔,真有些对不起过眼山水了。人家当编辑的退稿不发,你也无话可讲。
模山范水,笔下要有历史背景、哲学背景,还要有情感背景,让文字在心灵氛围中展开。游记是散文,它的表达,必须是文学的,文学的核心是诗意。那种泛泛的堆材料的写法,历史知识再丰富,哲学思辨再深邃,也只是导游词的路数,不能以情动人。

诗,强调感觉。感觉又往往是一瞬间的,忽然就来了,在心里一闪,忽然又没了。这就是灵感。灵感一定是个人化的,它产生诗意。我们有时候读到很绝的文字,常常是作者的灵感。你的灵感来了,马上记住,因为很容易忘掉,靠回忆都回忆不起来。
自然山水是诗,好的游记应当含着诗韵、诗的节奏,也当然可以在心底歌吟。俄罗斯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曾经思考过相似的问题,认为“散文一旦臻于完美,实际上也就成了真正的诗”。
徐志摩的《泰山日出》《印度洋上的秋思》《北戴河海滨的幻想》《我所知道的康桥》等,里面有些段落,都是可以当诗歌来诵读的。抒情是诗的特质,也是浪漫派艺术的主轴和凝聚点。由此发散而成的游记,纸面可以叠印出风景道上的种种奇观。
诗化的游记,可以破一下传统的章法。不一定以游踪为线索贯穿全文。不妨打破时空限定,按照心理时空、情感逻辑行文。景物、情绪可以交叉、跳跃,表达更自由、更舒展。

像写诗那样写游记,文字一定要俭省,尽量使写出的东西篇幅来得短小,少工笔,多写意,没有洋洋洒洒的架势。唐人写绝句就是这么下笔的,决不敢浪费语言。
写诗,开头进入要快,几行就得把读者带进预设的情境。开头不好,整体就垮了。写游记也是同样道理。不能好几个自然段过去了,还没进正题,连景物的模样都没见到呢。
我的经验是,全篇的开头是很难的,就像给文章起标题,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很费斟酌,因为标题流露着文章的情绪——热烈的、冷静的,抒情的、记叙的,不那么容易捉住。想个好开头,哪怕是头一句,全篇的基调就定下了。开头也意味着一个不寻常的视角。找到了这个不寻常的视角,常常是开始一个故事的好起点。
结尾要有回味,不宜直说。理想的文字,固然要写出对于风景的记忆,更要写出对于风景的回味。要让人家眼光离开纸面,心没离开。

诗意的文章不是硬做出来的。写文章要放松一些,自由一些,自然一些。特别是写游记,不能把风景写死了。最感乏味的是把游记做成了流水账、导游词。从文学的角度看,这是无生命的文字。
这样说来,游记的成功,可以归结为三点:
一是诗意情绪的体验,二是艺术感觉的捕捉,三是感应方式的灵透。
形象感也是对于游记的要求。风景的美感是通过形象传达的,文字本身不具备形象性。那么,是不是应该取消游记的资格了?当然不是。
游记绘出的风景不是客观的山水,而是作者用心灵塑造出的山水,是“第二自然”,它会在读者的想象中唤起形象感。这就要看作者写景的手段如何了。这里有高低、深浅之分,一般化的、平淡无奇的大路活,当然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小学生出去春游,比方去颐和园,回到学校,语文课上老师命题作文,写一篇游览记,学生就要调动回忆,脑子里就会浮现颐和园的印象,佛香阁、十七孔桥、昆明湖、西堤的轮廓、方位、造型、色彩等等。起码不要写错,那样会失去最基本的真实。
我在前面说过,古代游记里有地理学的因素,比方南北朝的《水经注》、明朝的《徐霞客游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郁达夫,他的游记里,地理色彩也不淡。
其实,写准山川景物的方位,也不容易,要看你的观察力,而不是虚构的能力。在郁达夫跳荡的目光里,山水的位置感是明确的。运用大尺度的物象结构,营造立体化的视觉感,浮显景物的空间格局,他有这本事。他的《浙东景物纪略·烂柯纪梦》中有这样的句子:
石桥下南洞口,有一块圆形岩石蹲伏在那里,石的右旁的一个八角亭,就是所谓迟日亭。这亭的高度,总也有三五丈的样子,但你若跑上北面离柯山略远的小山顶上去瞭望过来,只觉得是一小小的木堆,塞在洞的旁边。

我多年前去烂柯山,伫立四望,想起郁达夫的话,感到写得准。
从山水世界中激发情绪,再回过头来加以融合,重铸自然,不是简单的事情。这也是汪曾祺先生有感于游记难写的一个原因吧。
想象力能够让游记不限定在小的格局、小的气象里。站在天地之间,精神的翅膀会飞得很高很远,特别是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让你想起遥远的岁月、苍茫的宇宙、过往的人物。
张家界的峰岩怎么会从一片沧海中耸立出来?秦汉的烽火、唐宋的烟云,会让你对历史发出追问。五四作家里,浪漫格调总是和生动的想象结缘的,经典作家就是徐志摩。
他的代表作《泰山日出》,运用的是散文诗的笔法。他用“玫瑰汁,葡萄浆,紫荆液,玛瑙精,霜枫叶”和“光明的神驹”来比喻早霞的光色,而“散发祷祝的巨人,他的身影横亘在无边的云海上,已经渐渐的消翳在普遍的欢欣里;现在他雄浑的颂美的歌声,也已在霞彩变幻中,普彻了四方八隅”这几句,汪洋恣肆,让抒情主人公跃然于画面的前景,带了双翼的灵魂热奋地驰骋,魂魄昂扬,意气风发,表现的是一种解放了的精神。

这种顺从情绪、放纵想象的写法,与其说是自然风姿的再现,不如说是客观景物在作者心目中的幻觉化,或者称为作者心境的艺术化。文字与自然浑融一体,物象升华为意象,这是一种美妙的境界,也是中国浪漫派文学的传统。
文学想象是有根基的,行所当行,止所当止,不是无限度的。根基还是作家的底蕴。
我读今天的游记散文,有感慨。
梁实秋讲过一个意思:中国的读书人访山问水,回到家,都爱写一篇远足记,才算功德圆满,才算没有白出去一趟。
现代人不是活在过去的时光里,可是社会生活的现代性改变——出游已成为常态,并没有促成游记散文高峰的到来,大众化出行也没能拉近人们同大自然的心理距离。这就形成一个悖论:今人同风景离得这样地近,而同自然美离得那样地远。什么原因呢?只从文学角度看吧。

现时,较少有人肯做摹景状物方面的技术训练了,许多人凭了一点旅行经验和习作底子便来写作,较差的语文基础无法满足艺术要求,美的写景篇章就较难出现。语言是和内容粘在一起的。
学校老师讲授文学理论,把二者分家,一个是形式,一个是内容,这是为了讲课的方便,能使原理清楚。
在创作中,是分不开的。你不能说这篇散文真好,就是语言差点,真应了那句话——意图很好,实现得很坏。奇丽的风景遇到粗鄙的文字,实难指望写景的成功。游记散文,语言应该是美的。
文学语言应该是个人化的,而不是公共化的、类型化的。读多了、读熟了经典作品,把作者名字掩上,一看文字,就知道是谁写的。
另外,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语言是有民族性的。

我写国内景观,比较自由,笔下是顺的;写起国外景观,就比较生涩。因为写国内的,常用“写意”之笔,这套笔墨用到国外的景物上,好像写不出那种味道,非得用“工笔”才合适。
什么道理呢?中国文章讲求感性,很多观念来自经验,语言的弹性较强,意会的空间大,造成“艺术的模糊”,但是缺少思想挖掘的深度;西方文章讲求理性的力量,逻辑严密,但是深刻的哲理有流于观念图解的危险。对照着看,一个较虚,一个较实。
这种差异没有高下之分,写好了,都是经典。能够加以融合,更是等而上之。其实,我们不是直接用英语创作,我们对外国文学的感受,都是从翻译作品那儿来的。我在写海外游记时,有时会捉不到语言上的感觉。
写游记,是对大地行走的文学记录。这种行走,是有精神内容的。
借用伊塔洛·卡尔维诺的话,是为了回到你的过去和寻找你的未来而旅行,卸掉行囊,情绪状态好像仍然“在路上”。
读游记,是心灵被文字带到了路上,你好像和作者一同行走。林清玄讲过:“人不是向外奔走才是旅行,静静坐着思维也是旅行。”过去说的卧游、神游,大概接近他的这个意思。其实,如果跨出文学范围往大了看,写游记、读游记的文化意义也是有的。
人活在世上,免不了要处理四种关系:一是人和人的关系;二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三是心与身的关系;四是今天和明天的关系。
这里面,我们走进山水,就反映了人和自然的关系。游记散文里的山山水水、花花草草,就是大自然的文学化表现,山含情,水含笑,融合了作家的主观感受。人类生活依赖自然,文学创作也依赖自然。从这个角度看,说游记散文有生态文学的因素,是有道理的。
文学永远无法完整地再现自然之美,我们也不强求这种“完整”。我们需要的是融合了美好情感的自然、诗意的自然,因为人类的精神在这里栖居。
作者简介:
马力,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旅游报》原副刊部主任,主任编辑。著有散文集《旅游漫笔》,《鸿影雪痕》,小说集《炼狱和天堂》等。
(本文部分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即删)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