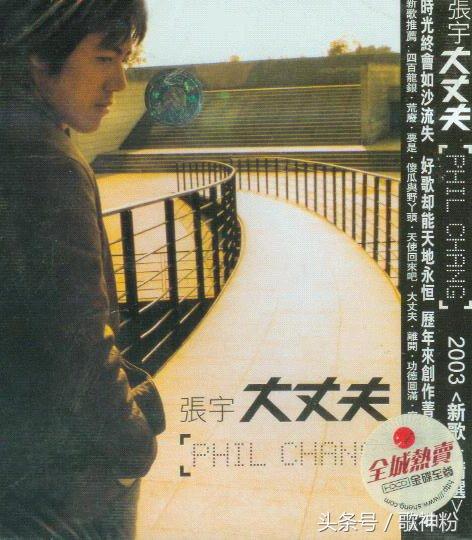丈夫为救受伤女孩被砸伤(故事丈夫被砸伤)

本故事已由作者:王稻壳,授权每天读点故事app独家发布,旗下关联账号“每天读点故事”获得合法转授权发布,侵权必究。
1
七月的湘西闷热潮湿,来了半个月,太阳好像欠我的债,躲得无影无踪。
我本为新小说搜集素材,可除了满身的湿疹一无所获。老田看我每天百无聊赖,有点过意不去,晚上总陪我喝两杯解解闷。
老田顿了顿,似乎在记忆里挑拣了一番,说:“现在信息发达,养蛊的事人人都知道。我小时候还算得上奇闻,那时候不叫养蛊,叫养药。
养药的都是女子,不管老少都称为养药婆。有两种人最容易被当成养药婆,一种是漂亮的姑娘,另一种是外地嫁过来的小媳妇。
我年轻的时候,村里组织我们几个小伙子进山,说是伐树,到了目的地才发现是一座孤零零的竹篱笆院子。
一家六口——两个老人,一对夫妻和两个孩子——全都被狼咬死了。
我们把尸体收到山下,村干部才告诉我们这家里的媳妇被当成养药婆,孩子总受欺负才搬到了山上住。没想到躲得了人却没躲过狼……”
“那这个媳妇到底有没有养蛊?”我忍不住问。
“没人真会放蛊,否则还能受这个气?这么多年来,我只听说养药婆被害,没听过养药婆害人。所谓的蛊,无非是一些常见的疾病,头疼腹痛寄生虫什么的,现在大家都讲卫生,蛊一个个都没了。”
“这么说蛊全是假的了?”
老田点点头,似乎又想到什么,说:“话虽如此,但怪事还是有那么一两件。
大概三十几年前,附近有个村子嫁过来一个外地媳妇,长得相当漂亮。当时我二十郎当岁,我们一帮小伙子特地跑了几里山路去闹洞房。
那媳妇性格很大方,被我们的热情感染,一直满脸笑容,还给我们跳了几段舞。我以前老听人形容姑娘像花一样,一直不理解没有五官的花怎么和人相比。
直到那次闹洞房,才体会到这个比喻的妙处。现在回忆起来,她的相貌已经模糊了,但总觉得她就笑嘻嘻地站在花丛里。”
老田的眼神涣散了一下,马上又聚拢起来,接着说:“但幸福的日子没过多久,不知道从谁那里传出来,说这个外地媳妇是养药婆,此后大家就躲着她了。
我后来到附近找人,又见过她一次。她低头溜着墙根,像个过街老鼠。
她嫁的人是个石匠,父母早亡,人很老实厚道。他们夫妻两个经常一起采石,一起雕刻,非常恩爱。
婚后大概一年,石匠凿山时被石柱拦腰砸在底下。媳妇怎么也搬不动,就去村里叫人;但每个人看到她都把房门一关。她挨家挨户跪着哭,没有哭出来一个人。
据说最后她独自回到丈夫跟前,陪着他直到断气。从那以后,她就一个人搬进山里住了,很少有人见她出来过。
第二年石匠忌日那天,他们村里出现了一场怪病。这病倒也奇怪,专门传ran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死了五六个人。
丈夫被砸伤,妻子求遍全村没人救,他过世后村民开始遭祸。
消息传到了周围的村子,惊动了市里的医疗队。所幸这病不了了之,以后也没再发作。”
“那您说,这病是不是那个外地媳妇下的蛊?”我嗅到了一些故事素材的气息。
“这就不知道了。”老田说,“山里有个瘴气也是常有的事,每年都会因此死人,但一般都是抵抗力差的老人和孩子。那次专门传染年轻人,大家都说是养药婆恼恨这些有力气的小伙子不去救她男人,所以才下了这种蛊。尤其是时间凑巧还是石匠的忌日。”
我来了兴致,问老田:“这个媳妇,呃,这个婆婆现在还住在山里吗?”
老田摇摇头说:“不太清楚。后来听说她生了个女儿,原来进山的时候就已经有孕在身了。她们母女的消息非常少,也没人愿意主动打听,只有这个悲惨的故事流传了下来。她如果还在世,算起来今年应该六十岁上下,她女儿也差不多三十四五岁了。要是现在,石匠多半能救出来,毕竟不是当场砸死,熬了大半天才咽气。”
我想着这位外地媳妇,肚子里怀着孩子,眼睁睁看着老公在石头下面痛苦哀嚎,一点一滴地流逝生命,是何等的绝望和无助。
而这桩惨剧完全可以避免,只是因为一个恶毒的谣言,就轻易毁掉了原本可以很幸福的一家人。
老田看我脸色凝重,有点后悔讲这个故事,就岔开话题,“我还知道一个小小的奇闻,听说附近小学里有个孩子会说鸟语。马上就要暑假离校了,你要有兴趣可以去看看。要是他真会鸟语,我倒想让他问问我的喜鹊,为什么两个月了也不开哨。”
2
我找到于飞的时候,他正收拾行李准备回家过暑假。
于飞十三岁,正在读小学六年级。山里孩子淳朴,对我这样的生面孔也没有戒心,听说我为了鸟语而来,便热情地给我学了几段。
他能学好几种鸟叫,声音尽管足以乱真,但更像一种口技,懂不懂鸟语无从判断;尤其叫声中夹杂着一些奇怪的音符,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我听完感觉没什么奇特之处,电视上的模仿秀似乎还要更逼真宛转。我掩饰失望之情,和于飞闲聊了几句,准备回到住处也收拾行囊,明天一早就离开湘西。
我问于飞离家多远,他说家在山里,要走八九里的路。我又问他为什么没人来接,他说爹妈早去世了,家中只有一个外婆,岁数大了不方便来。
从三年级以后,假期都是他独自往返。
我听到“山里”和“外婆”两个关键词,心念一动,问:“你外婆多大年纪了?”
于飞回答:“六十一了。”
我思忖片刻对于飞说:“我想进山玩玩,能不能在你家借住两天?我会付房钱。”
于飞好像不太清楚房钱的含义,只是点点头说:“你要不嫌累,可以跟我一起走。”
我帮他背着行李,领着他先来到老田家。
我收拾了一些个人用品,跟老田说进山住几天再回来,房间先给我留着。
我的另一个目的是打消于飞的顾虑,让他知道我和本地人有联系,不是随随便便的外来人。但于飞没有意识到我的苦心,兴趣全在老田的鸟笼上。
笼中的喜鹊听到后从恹恹中精神起来,抖擞几下站到了栖杠上,似乎在踮起脚尖向墙外张望。于飞继续学鸟叫,那应声越来越近,越来越急,旋即就来到我们头顶。
我和老田抬头看,一只黑白相间的喜鹊停在院中的樟树上,双翅微微扇动,在稀薄的阳光下闪烁出宝石蓝色。
笼中的鸟上下翻飞,树上的鸟怯怯地不敢靠近,只能一声声地呼喊交谈,如泣如诉。于飞小声求情:“爷爷你把它放了吧。”
老田默不作声。
我看他表情似乎还想把树上的喜鹊一起捉下来,怕于飞难受,就拉着他匆忙出了院子。于飞恋恋不舍,走出老远还在眺望那棵樟树。
离开田河寨,没多久就开始上山。
于飞发出了不同种类的鸟叫,山中也回复了几种声音。然后于飞对我说:“现在还不会下雨。”
“鸟告诉你的?”我问。
于飞点点头,“它们从来没错过,比天气预报还准。”
果不其然,直到我们下山来到村里,还是干打雷不下雨。山里的村子和外面截然不同,由于平整的地块不多,十来户人家星罗棋布,分散在绿意盎然的密林之间。
湿气更加浓重,一度像在水下穿行。残存在树叶上的水滴,在我们的惊扰下纷纷扑簌而落。
我抬头仰望,只见破碎的天空好像波光粼粼的水面,明灭相间,变幻不定。
到了于飞家,刚进院子就看到吊脚楼前有一套古拙的石桌石凳,显然经过了巧匠的雕琢。
我不由得想起了那个惨死的石匠。于飞的外婆见到我有些吃惊。我赶忙自我介绍,说只是想进山游玩。
老人热情地把我让进屋内,给我倒了一杯蜂蜜水。说是山里的野蜂蜜,不免有些腥味。我喝了几口,浓香甘甜,非但不腥,还感觉味道有好几个层次。
老人似是看透了我的心思,没等我问就解释说:“野蜂不挑花,酿出的蜜都是混着的。”
我由衷赞叹,喝完蜂蜜水问道:“婆婆您贵姓?”
老人说:“我姓蔡,不嫌弃的话叫我蔡姨就好了。”
她身着扎染的蓝印花短衫,衣装古朴,但举止谈吐却不像一般的农村婆婆;虽然满头银发,从眉眼之间仍可以看出年轻时也是一个美人。
我暗暗祈祷,这或许是老天对我十几天等候的一点补偿,让我遇到了老田故事里的女主角。
蔡姨带着歉意对我说:“家里倒是还有一间空房,只是很多年没人住了,又霉又潮。你还是和于飞一起住吧,这孩子睡觉很踏实。”
正合我意。我总不好上来就问蔡姨三十多年前的事,先跟孩子多聊聊,说不定能听到更多的故事。
山里天黑得很快,刚吃过晚饭屋里就有些影影绰绰。蔡姨拉着灯泡,说:“家里还没有收费的电视,只有一个卫星锅,收不到几个台。”
我说走了半天山路,又困又乏,现在只想睡觉,就随着于飞进了房间。
房内陈设简朴,好在竹床有一米三四宽,还可容得下我们两个人。
和于飞聊天得知,他出生后不久,父母就相继离世,因此他对两人毫无印象。
他的父亲不是本地人,但具体什么地方他也不知道。问过外婆,只说长大了会告诉他。
于飞的外公死得更早,他从没听外婆讲起过。每次问起来外婆总是岔开话题,一个字都不提。
我知道那是一道永远也揭不开的伤疤。
我问于飞鸟语是怎么学的,他说是山魈教的,让我大为吃惊。
我正要详细追问,于飞已经迷迷糊糊睡着了。
我躺在床上,竹楼外枝叶婆娑,树影摇曳,营造着淡淡的诡异气氛。山里的故事还真是多,光是于飞家就不止一桩。
我打开手机,只有一两格的2G信号,打电话都勉强,上网是不可能了。
3
次日一早,于飞说要去采点岩耳招待我。
在田河寨我听他们提过这东西,只长在悬崖峭壁的石缝里。
采集人把绳子一头固定在山顶,另一头绑在腰上,悬吊在绝壁间,耐心搜寻。
无论如何,我不能让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只身涉险,就主动要求跟于飞一起去。
我俩简单吃了点早饭就出发了,于飞身背竹篓,腰悬布袋,完全褪去了学生的气息。我俩之字形向上攀登,不多时来到一处断崖前。
于飞找了棵树,熟练地绑好绳子,将身一纵就下去了。
我俯身下望,所见茫茫,早没了于飞的身影。只有绳子摆来动去,可以想象他在下面的忙碌。
我原地坐下,心想万一绳子出了故障,还能及时补救。四周没了遮挡,我打开手机居然发现还有飘忽不定的4G信号。
趁着这个机会,我赶紧看了看朋友圈、微博,刷了刷新闻。
大概一小时后,于飞上来了,随身的布袋也略微鼓了起来。“我怕你着急,先采了一点,够中午吃的了。”
归途经过一片池塘。于飞竖起手指对我做了个噤声的手势,然后蹑手蹑脚过去,片刻间就抓了四五只青蛙,扔进了背篓里。
我没敢多问,心想吊脚楼就这么大,真要炼蛊我留点心迟早能发现。
回到家里,蔡姨看到于飞带来的东西,说:“这下一天的菜都有了,中午岩耳腊肉,晚上辣子田鸡。”
岩耳还真对得起这份危险,在蔡姨手艺的加持下,嫩滑鲜美难以言表。我的味蕾也发挥出久违的潜力,绽放出繁复的味道组合。
吃完午饭,我正要找机会和蔡姨聊聊,她却直接睡午觉去了。
于飞打开电视,把音量调得极低,在满屏的雪花噪点中寻觅人影。我无所事事,在躺椅上半睡半醒。
刚要睡着时,我突然灵台清明,意识到一件事情:竹篓里的青蛙在回来的路上一直叫个不停,但到家很快就不叫了,不会是死了吧?
我过去打开竹篓,空空如也,青蛙已经不在里面。难道被蔡姨杀了?
我去厨房一看,那几只青蛙端坐在地上,瞪着眼睛,不叫也不跑,仿佛被下了定身咒。我注意到一个淡淡的白圈围着青蛙,就好像孙悟空用金箍棒给唐三藏画的圈子。
从厨房出来我问于飞:“听说山里有人有会养蛊的,你知道吗?”
于飞摇摇头,反问我:“什么是蛊?”
我看他表情不像装的,只好换一个话题,“上次你说鸟语是山魈教的,我觉得挺有意思,能给我详细讲讲吗?”
这个话题对于飞的胃口,他打开话匣子:“再往山的深处走,有一个箐沟,下面就住着一个山魈。外婆说沟里跌死过人,不让我去那边,但我总是偷着去。沟边的野果子特别多,渣梨、野葡萄,还有鸡脚爪。鸡脚爪可不是鸡爪,又叫拐枣,它的果子不能吃,但果子柄甜得很……”
小孩子说话爱思维发散,我打断他的美食回忆,再次引向主题,“你是采果子时碰到山魈的吗?”
“对。我六岁那年,摘野葡萄时不小心滚下沟去。醒来就看到一张奇怪的脸,一半像人一半像猴子,当时还不知道是山魈。我吓得拔腿就跑,它却没跟上来。
我跑了一阵也没找到出口,好像鬼打墙,兜兜转转又回到山魈这里。它冲我摆摆手,转身捧出一把果子。
我不敢不接,挒着身子张开衣兜由它倒进去。它很开心的样子,张嘴就学起了鸟叫,引得附近的鸟都叫了起来,我在旁边都听呆了。
叫了一阵,它突然抓起我,力气非常大,一下把我扔了上去。我眼看要撞到沟边的树上,却不知怎么一下穿了过去,正好落在了沟沿上。
我回到家没敢告诉外婆,但知道山魈没有坏心眼。从那以后,我就常去箐沟,没几次就和山魈熟络了。
它不会说人话,但鸟语叫得跟真的一样。我觉得有意思就跟着它学。过了一年我到七岁,外婆送我去山外上学,一个月回来一次,就很少去见山魈了。”
“你的鸟语里面总夹着几个奇怪的音节,听起来好像是‘萨尔瓦梅’,也是山魈教的?”
“嗯,有几句我也觉得不像鸟叫,但山魈就是这样一遍遍教的,我就记在脑子里了。”
“假期你还要去箐沟吗?”
“去啊。正好明天还要去采岩耳,你跟我一起,咱们先去箐沟看看。”
“这么危险,我尝尝鲜就可以了,不再吃了。”
“明天再采就不是咱们吃了,要卖了交学费。”
次日一早于飞跟外婆说去采岩耳,老人家没有怀疑。我俩带好绳索等工具,出门后没多久就调转方向,朝箐沟走去。
所谓箐沟,就是树木茂盛的山沟。站在沟边,看下面好像一个狭长的椭圆,长数百米,宽只有几十米。沟壁陡峭,底部大约七八米深。
山魈曾把于飞抛了上来,幸亏他当时六岁,不过三十来斤,要是现在只怕没有可能了。
于飞像采岩耳那样,掏出绳子绑在沟边的一棵树上,麻利地缘绳下去,三两下就来到谷底。
这将近三层楼高,我从没玩过攀岩,臂力也不行,只好咬紧牙关拽着绳子往下出溜,搞得狼狈不堪。
好容易到底,向前走了几步再回头看,只见沟边雾气缭绕,景色与俯视时完全不同。树木瞬间增加了数倍,层层叠叠,将四周围得密不透风。
刚刚用过的绳索也完全不见了踪影。
于飞看我愣在那里,说:“这里古怪得很,每次下来都觉得树变多了,山石像长了脚,偷着挪了位置,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那你以前怎么回去?”我话音未落,忽听草丛呼呼啦啦,一个黑影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急速冲向于飞。
我心里暗叫:坏了。于飞正对着我,我想挡在他前面也来不及了。
于飞听到了动静,转身和那黑影照面。黑影停住脚步,我才看到它头顶毛发蓬乱,面目难辨,不知是人是兽,应该就是于飞所说的山魈了。
它伸手把于飞抓了起来,举过头顶,似乎要往地上摔。我顾不上思索,正要一头撞向山魈。没想到它将于飞抛向空中又接住,俩人抱在一起,欢呼雀跃,就像多年的老友重逢。
山魈注意到我,凑过来和我对视。
多年的食果饮露使他面目肌肉变形,骨架嶙峋,脸色惨白;但那额头下面分明是一双人类的眼睛。这不是猴子,是一个野人。
于飞用鸟语和他交流,一边说一边指向我,看来是在介绍。野人弓着身子紧张的体型逐渐放松。
我试探着问他:“你是人类吗?叫什么名字?”
野人听不懂,但起码知道我在和他说话。
他没有对我讲鸟语,而是一遍遍地说:“因考么豆,萨尔瓦梅……”
我也同样一头雾水,不知道这是不是野人独有的语言。
很可能他从小就被遗弃在山里,由野兽或鸟类抚养长大,耳濡目染;这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只会说鸟语。
4
野人对我失去兴趣,注意力又放在于飞身上。我趁机在沟内走了走,从底部向上看,似乎不止七八米深。
沟沿四周树木森然而立,枝繁叶茂,树冠之间互相搭接,遮天蔽日,只留一个狭窄的缝隙可以看到天空。我感觉置身一个幽深的井中。
我顺着野人的来路走过去,一路杂草过膝。在石壁上发现了个黑黢黢的洞穴,应该是野人的家。我怕洞里还有别的东西,不敢进去,就继续向前探索。
没走几步就看到地面有个微微隆起的鼓包,周围的草被薅得干干净净。
一些造型别致的草叶堆放在土包前,有些青绿,有些已经干枯发黄。我捡起一看,是草编的小鸟,各式各样,惟妙惟肖。这是野人的手艺吗?分明是民间艺术品啊。
土包不远还有个草垛,几米见方,半人多高。
我以为是野人晾晒的干草,走近一看,居然全是草编小鸟,看起来数以万计。估计这些年里,野人就是靠手工来打发时间。
我正看得入迷,只听身后一阵风声,野人转瞬来到我面前,冲我龇牙咧嘴,一脸凶相。我赶忙退后几步。
于飞也跑了过来,挡在我俩中间,对我解释说:“坟地这边的东西谁也不能动。”
我怕附近还有别的禁忌,就来到沟边,研究为什么下来之后景物就变化了。绕了一圈,没有发现出口,难怪于飞说鬼打墙。
刚才从上往下看,沟的长度方向两端还是缓坡;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迹象了。
我把视线转向地面,粗看没什么异常;可拨开乱草,地上有道白印子,巴掌来宽,沿着沟边绵延不绝。
说是石壁上掉下来的渣子倒也能勉强解释,但我马上就联想到了蔡姨家里围住青蛙的那个白圈。
这时候于飞跟了过来,随身的竹篓里装了各种水果,应该是野人给的。
“乱走是出不去的。”于飞说。
他带领着我沿着箐沟的长度方向走,尽头本来是个缓坡,可现在被高耸的岩壁堵上了。
来到跟前,于飞不慌不忙地褪下裤子,冲着前方撒了一泡尿,在石壁上浇出一个口子,仿佛凭空腐蚀出一个山洞。
“快走,干了就不管用了。”于飞推了我一把,我踉跄而出,本以为要进入黑漆漆的洞里,可一眨眼就发现自己站在坡上,周围树木稀疏。回头再看箐沟,也全都正常了。
看来童子尿可以破地上白圈的障眼法。于飞跟在后面跳了出来。野人远远望着这边,大力挥手,显然是万分不舍。
“他怎么不跟着出来?”我问。
“应该是不敢吧……从没见他出来过。”
我也向野人挥手作别。于飞说:“他看不见我们了。”
我俩朝昨天采岩耳的高地进发。一路上我不断回忆野人的举止相貌,慨叹他如何一个人在沟底生活了这么多年。
于飞采岩耳时,我又用手机上了会网。不过没再刷无聊的微博和新闻,而是搜了很多关于野人的报道。
回到吊脚楼,我满腹心事,午饭吃得潦草沉闷。
我想问蔡姨一些话,但只能等机会避开于飞。
我脑子里浮想联翩,一会儿是故事,一会儿是现实。
蔡姨在一旁悠闲地清洗岩耳,耐心地挑出渣子,然后放在竹筐里准备次日的晾晒。
好容易等于飞睡了午觉,我刚要开口,蔡姨却说:“你见到他了?”
我愣了一下,猜测她说的是谁。
蔡姨面色沉静,丝毫没有犹疑。口气虽是询问,但显然已经知道了答案。
我只好点点头。多了个心眼没有说话,想看看蔡姨到底知道多少。
蔡姨没有停下手上的活计,说:“他是飞飞的爸爸。”
基于一个小说作者的职业敏感,这个可能性我已经猜测过了。
“您会下蛊是吧。”我说,“我看到了箐沟周围的白圈,他被困在里面了。”
“是观天蛊,用青蛙炼出来的。我本来不会下蛊,我母亲是养药婆,她想教我,我一直不肯学。因为她,从小村子里就没人跟我玩,我恨死了养药炼蛊。
我想的就是长大后远远嫁出去,再也不回这个家。后面的事你可能在外面听过了,飞飞外公临死的时候,实在是太痛苦。
我不忍心,就想起了母亲总在我耳边念叨的那些个配方。我抓了一条蛇,炼出药,让他平静地走了。
这时候我才知道,我一直拒绝的东西,其实就长在我身上,印在我心里。”
“那第二年的那场病?”我试探着问。
“也是我下的蛊,应该判死刑了吧。不过从那次之后,我就再也没用过,直到……”
“直到于飞的爸爸?”
“于飞的爸爸是个研究鸟类的博士,十四年前来到山里寻找濒临灭绝的鸟,也借住在这个吊脚楼里。
我女儿那时候刚刚二十岁,还没有出过这座山,很快就爱上了他。我也是粗心,直到女儿有了身孕才察觉到。
于飞的爸爸不想要这个孩子,说自己还没有成就事业,没到要孩子的时候。希望我女儿能把孩子打掉,他会带着她一起离开,到城市里生活。
可是我女儿不答应,她不愿意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想把孩子生下来,四个人一起住在山里。
可一个从花花世界来的人,怎么可能长期生活在闭塞的山里。有一天夜里,于飞的爸爸就偷偷跑了。”
说到这里,蔡姨叹了口气。
我也思量了一下,换做是我,不免也要做出同样的选择。
这种与世隔绝的地方,无论多漂亮的姑娘,都没办法留住男人的心,尤其是一个对事业有追求的男人。
蔡姨接着说:“他在山中迷了路,转了一天一夜,又回到了吊脚楼。我女儿也哭了整整一天一夜。我守寡二十年,不能让女儿再走我的路。
我炼出观天蛊,把于飞的爸爸封在了箐沟里,打算困他一阵,磨灭了他出去的念头,再和他商量去留。其实我也想过,如果他死活不留,我也不强求,我已经做好了让他们两个一起离开的准备。
我是不想出去了,飞飞的外公埋在这里,我还能陪他说说话。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我女儿生飞飞时难产。可惜没有治病救人的蛊,我看着她每一口气越来越短,脸上的血色一点点消退,好像又回到了二十年前……
我一直在想,是不是那一年我在村里下蛊,害死了几条人命,现在报应来了。上天从来都知道怎么折磨一个人——最大的惩罚不是让你死,而是让你的亲人死。
我的魂早在那一天就随着飞飞的外公去了,只留下这具身体,为了女儿又多活了二十年;现在为了飞飞,我还得拼了命地活着。我把女儿葬在了箐沟里,让飞飞的爸爸陪着他,这一陪就是十四年……”
“您知道飞飞去过吗?”
“知道,他们是父子,迟早要见面的。我不想让飞飞这么小就知道真相,就给他爸爸下了黑犬蛊,让他忘掉语言,说不出话。
到现在他也不知道飞飞是他儿子,毕竟从出生到六岁他一面都没见过。”
原来野人不会说话的原因是这样。可黑犬蛊只能让他说不出人话,但他是鸟类学家,反倒刺激他开始说鸟语。
仅仅因为不愿留下,飞飞的爸爸就受到这样残酷的对待,我觉得不寒而栗,忍不住说:“把一个从城市来的人,禁锢在一个狭小的山沟里十几年,没吃没喝,了无生趣,比坐牢可要残酷百倍。要是我宁可死了。”
“所以活着比死可难多了。但做过的事必须付出代价,一报总要一报来还。我下蛊害人,到头来生不如死。他害死我女儿,也要付出点什么。
我只是让他陪着我女儿,没想存心折磨他。把他关进箐沟的时候,我就用蛊限制了他的智力,他的思维和猴子差不多,感受不到人的痛苦。
猴子本来就生活在山里,也无所谓了。”
“即便是猴子也是成群结队,有自己的小社会。他孤零零守着一个坟地,你怎么知道他感受不到痛苦?”
“这些年里,我常常去箐沟陪女儿待会。他在一旁蹲着,从来没说过话,也看不出有什么耐受不住的样子。”
“那也许是怕你,不敢表露出来。你知道他会讲鸟语吗?”
蔡姨点点头,“以前飞飞偷着去的时候,我都在后面跟着,怕出什么意外。我在沟边听到过他教飞飞鸟语。他是研究鸟类的,这是他的天赋。我的蛊禁得了他讲人话,禁不了他说鸟语。”
“你知道他鸟语讲的是什么意思吗?”
蔡姨摇摇头,“我不懂鸟语。”
“他的鸟语里面总夹着几句奇怪的话,比如‘因考么豆,萨尔瓦梅’,有没有印象?”
蔡姨不置可否,即便她听过,估计也早就忘了,毕竟没什么意义。
“上午在山顶,我手机上网查了一下,‘因考么豆,萨尔瓦梅’其实是一句西班牙语。”
“西班牙?”蔡姨皱起眉头,“他刚来的时候,好像说起他曾在那边留学。我记得他许诺我女儿要去西班牙办婚礼。”
“那就对了,看起来黑犬蛊不仅没有禁掉鸟语,也没能禁掉外语。”
“刚才那句话什么意思?”
“我很难受,救我出来。”(作品名:《鸟语》,作者:王稻壳。来自:每天读点故事APP,禁止转载)
点击右上角【关注】按钮,第一时间看更多精彩故事。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