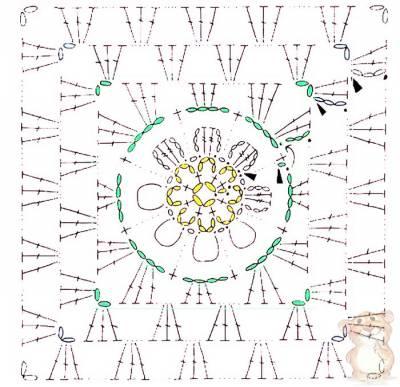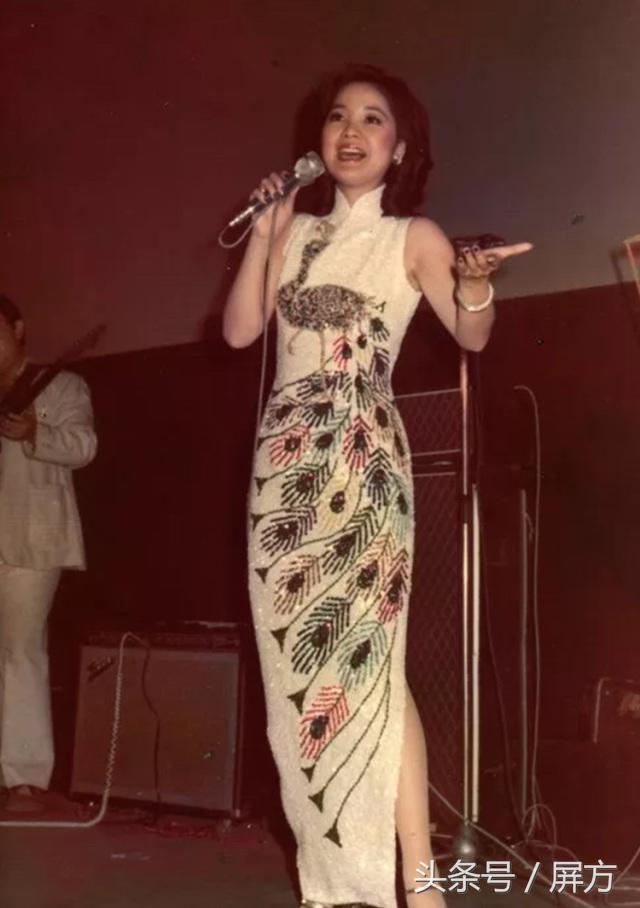春芽你想不到的美味(乌蒙山的春芽)


清明时节,乌蒙山深处,春雷炸响,雨水湿润了山林,桃花打落一地。
早上6点过,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木杆镇细沙村的建档立卡户刘平强叫醒小儿子刘登飞,就着水吃点饼子,准备好背篼。
两人收拾停当,披上雨衣,背上背篼,趟过家门口的细沙河,一头扎进苍茫的大山里。山坡上的竹林里,一棵棵破土而出的嫩芽,饮着露水肆意生长。
这次进山和往年不一样,刘平强心里有两个愿望:大儿子刘登明今年高三了,得多给他一些生活费,小儿子刘登飞想要一辆单车。
“我们两口子都没文化,出门买火车票都麻烦,找路都找不回来,巴不得孩子多读点书。”刘平强说。

3月31日,刘平强和他的小儿子刘登飞准备上山菜笋。新华社记者 胡超 摄
愿望寄托在漫山遍野的筇竹林里。18年前,刘平强在煤矿打工时伤了左脚,干不了重活,春笋和孩子就成了家里的希望。
大关县地处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境内从400多米(最低海拔)到2700多米(最高海拔)都有竹子生长。其中,筇竹是国家三级保护植物,为西南地区特有。
统计显示,大关县现有筇竹资源近21万亩,占全国筇竹总面积的约六成,距离县城70多公里的木杆镇是筇竹分布区的核心地带。
在中国,食用竹笋的历史久远,《诗经》就记载“其蔌维何,维笋及蒲。”但春笋对细沙村村民来说,不仅是一道美味,还是生计。

刘平强父子走在上山采笋的路上,他们从家走到笋地需要花半个小时。新华社记者 胡超 摄
雨下了一晚上,河水涨起来,云雾绕在山腰。山腰上的竹林有一人高,山坡则有三四十度,非常陡峭;刘平强趴在竹林里,猫着腰找合适的竹笋。
笋子有一层硬硬的绒毛,采集方法不对容易被扎伤。捋着笋子根部,斜着往上一折,咔嚓一声,一根笋子就出来了。然后,用小刀划过笋叶,哧溜一声,露出嫩黄肥厚的笋肉。往后一丢,笋子就落到背篼里。
这一套动作,刘平强一天要重复一千来次。自然养育着采笋人,他们也尊重自然。“采小留大,采密留稀”,这个道理,他们五六岁时便知道了。
采笋季从3月底持续到4月底。实际上,笋子能长50天,但村里只让村民采30天,笋子不能全部都采完。
雨雾太大,站在山上听得见隔壁山梁的说话声,但看不见人影,衣服很快湿漉漉贴在身上。中午,父子俩就吃点带的饼子充饥。下午五点过,他们的背篼里已有70多斤笋子。山里天黑得早,采笋人从四面八方的深山里冒出来,三三两两沿着河谷往山外走。

大关县木杆镇细沙村竹山一景。新华社记者 胡超 摄
“竹笋不能隔夜,要不然就老一节,当天采必须当天卖。”刘平强说。
在两条小溪交汇的入山口,专门开辟出一片空地,村民用竹子和防雨布搭了二十多顶简易的帐篷,劳作一天后在帐篷里过夜,次日一早就进山采笋,林业部门也设置了现场办公点。
细沙村村民何勇兵收购了9年的笋子,他用一张大塑料布铺在地上,支一个台秤;采笋人回来了,就自己去称一下,报个数给他。
“79斤,285块。”刘厚彬和郭光春夫妇,早上8点多出门采到这些笋子。卖笋子要付现钱,如果打白条,何勇兵就收不到笋子。
鲜嫩的春笋,大多换成了孩子的单车、衣服、书本和地里用的化肥。苗族群众张明光和张明崇兄弟,从20多公里外的高桥乡车来村赶来;他们家里都是建档立卡户,那里海拔高,庄稼产量低。
“孩子长得太快了,跟春笋一样。(卖竹笋)一季能挣四五千,就是准备给孩子买衣服鞋子,给庄稼上化肥。”张明光说。
天色已晚,乍暖还寒的季节,雾气从山顶流下来,小雨在昏黄的灯光下划一道道细线,炊烟袅袅升起,帐篷里飘出腊肉的香气。

村民在帐篷里准备晚餐。新华社记者 胡超 摄
这些筇竹笋经过商家深加工保鲜后,远销日本、韩国、新加坡及东南亚国家。2017年,大关县筇竹笋产量已达8000多吨,农村劳动力在出笋季节人均采笋收入可达五六千元,筇竹笋销售收入占到大多数农户经济收入的80%以上。
但大自然的馈赠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有绿水青山才有金山银山。大关县先后对2万多亩筇竹进行了中低产林改造,在保持筇竹林种群原生态繁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筇竹的产笋量。
细沙村有2万多亩竹林,今年发了300多张入山证。为了保障竹林资源,村里新种了3000多亩筇竹和1.2万多亩方竹。
筇竹一节一节长,村民生活水平也一节一节高。现在,细沙村的建档立卡户从2014年的178户减少到117户,全村人均年收入从2013年的1300多元,增长到了去年的4800多元。

这是大关县木杆镇细沙村刘厚彬和郭光春夫妇的手。新华社记者 胡超 摄
以前细沙村有很多土坯房、茅草房,现在村民靠着采笋和外出务工,这五年时间新增了260多栋砖房,甚至还有了给外地客商歇脚的旅馆。
长期致力于筇竹研究的西南林业大学亚太林学院院长董文渊说,大关县贫困人口的分布与筇竹生长区域在空间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让筇竹变成“绿色银行”,生态和扶贫形成互补互利。
在中国,贫困人口大多集中在山区、沙区,林业扶贫是实现生态文明和脱贫发展的根本之策。
“此处乃竹乡,春笋满山谷;山夫折盈把,把来早市鬻。”白居易在《食笋诗》如此写道。一千多年过去,这样的山野图景依然充满生机。
在刘平强家的后山上,他和媳妇已栽下了七八千棵竹苗,准备移栽,“今年再种10来亩,给儿子上大学做准备!”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